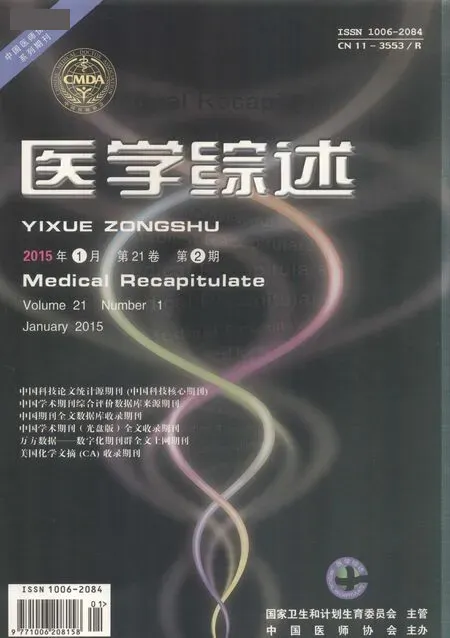呼吸機計劃性脫機的研究進展
王寶華,郭煒妍(綜述),浦踐一(審校)
(河北聯合大學附屬醫院重癥醫學科,河北唐山063000)
隨著重癥醫學科的發展,全世界每年有越來越多的住院患者需要機械通氣[1],并且隨著人口老齡化,機械通氣的使用將逐漸增多[2]。接受機械通氣治療的大多數患者有術后急性呼吸衰竭、肺炎、充血性心力衰竭、膿毒癥、創傷或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等[3]。當導致患者呼吸衰竭的病況開始改善,可能存在的代謝、炎癥和感染病況得到盡可能糾正時,就要開始考慮從完全機械通氣支持向自主呼吸的轉變,也就是所說的呼吸機的脫機過程,但目前該過程仍十分復雜,大約20%的機械通氣患者經歷困難脫機,脫機過程中的諸多環節缺乏循證醫學依據。現對呼吸機計劃性脫機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脫機與脫機的時機
呼吸機的脫機是指逐漸降低機械通氣水平,使患者自主呼吸逐步恢復,最終脫離呼吸機的過程。在大多數患者中,這一過程還包括拔出氣管內插管的過程。目前脫機的時機有很大的隨意性,常以個人的判斷及經驗為依據[4-5]。出版于1965年的第一本機械通氣教科書指出:“臨床醫師要了解撤離呼吸機的合適時機和速度,需要大量的判斷和臨床經驗。通常,應盡快地開始撤離(通氣機)”[6]。及時的脫機可明顯降低重癥醫學科住院病死率,降低機械通氣并發癥發病風險,并且縮短住院時間、減少醫療費用。因此,臨床醫師應積極地使機械通氣持續時間縮至最短。有研究統計[7-8],大約有15%的停止機械通氣患者在48 h內需要再次插管,并且ICU中的拔管失敗率變化較大,在外科ICU中平均拔管失敗率為5%~8%,而在內科或神經科ICU中可高達17%。然而,那些過早意外自我拔管的患者,有40%~60%不需要再次插管,所以尋找脫機的時機顯得尤為重要。目前常用的脫機入選標準包括:導致患者呼吸衰竭的病因得到控制,血流動力學穩定,呼氣末正壓通氣≤5 cmH2O(1 cmH2O=0.098 kPa)的情況下氧合指數>200,未應用鎮靜藥或阿片受體藥物[9]。專家建議,如果機械通氣患者滿足這些規定標準,醫師需要每日評估這些患者自主呼吸的準備狀態,為其提供自主呼吸的機會[10]。鄭大偉等[11]依據急性呼吸衰竭呼吸功能評分系統的各項分值相加的總值,建立了一種呼吸系統的評價體系,動態評估患者呼吸功能狀態,應用該評分體系,計算一般脫機指征≤4分,可明顯縮短機械通氣時間降低呼吸機相關肺炎的發生率。
2 脫機的參數
脫機參數是評價患者自主呼吸的客觀標準,反映患者呼吸肌的機械參數變化。血氧分壓反映患者氧合的變化,二氧化碳分壓水平是撤機的主要參數。無輔助自主呼吸可以更直接評價患者自主呼吸能力。
目前常用的脫機參數可通過神經肌肉功能和呼吸肌負荷來測定。神經肌肉功能的測定:①最大吸氣壓是用力吸氣產生的壓力,常用來測試呼吸肌力,但由于危重患者常不能保證充分合作,其本身不能作為預測脫機后果的可靠指標;②呼吸道閉合壓是測定吸氣后打開關閉呼吸道0.1 s時的壓力,自主呼吸期間,呼吸道閉合壓異常升高可以提示神經肌肉功能不良,呼吸道閉合壓、呼吸道閉合壓與最大吸氣壓比值是預測拔管成功最佳方法,不受氣管導管的阻力影響;③肺活量可評價單次呼吸肌做功,其值<10 mg/kg常預測撤機失敗;④最大隨意通氣是盡力深、快呼吸時,每分鐘所能吸入或呼出的最大氣體量,反映呼吸肌貯備力。呼吸肌負荷的測定:分鐘通氣量、順應性、呼吸道阻力等。除此之外,Yang和 Tobin[12]研究發現,在用T型管的1 min試驗中,呼吸頻率(以每分鐘的呼吸次數表示)與潮氣量(以升表示)的比值≤105次/(min·L)可相當準確地指導自主呼吸試驗(spontaneous breathing trial,SBT)的成功(陽性預測值78%,陰性預測值95%),該比值稱為淺快呼吸指數。王辰和詹慶元[13]也提出,血乳酸水平、氧輸送和氧耗、胃黏膜內pH值等對判斷患者是否具備有效的氣體交換能力和指導預測撤機轉歸有一定價值。
但是這些脫機參數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均為一個靜態標準,是在休息的狀況下評價循環狀態,運用簡單的方法測定通氣貯備,這些脫機參數并不能直接準確預測患者是否能夠成功脫機。能否找到動態連續脫機參數,有待于研究。專家認為確定患者已經準備好自主呼吸的最好方法是,一旦他們滿足準備就緒的標準,醫師就進行一次SBT[10]。
3 脫機的方法
3.1 SBT SBT可評估患者接受最小程度或無呼吸支持時的呼吸能力。目前常用的SBT模式有壓力支持通氣、持續呼吸道正壓通氣和T管通氣。理想的SBT應在患者清醒并且沒有使用鎮靜藥的情況下啟動。患者必須在沒有通氣支持或支持條件小的情況下自主呼吸至少30 min,并沒有以下任何一項情況:呼吸頻率>35次/min持續時間>5 min、氧飽和度<90%、心率>140次/min、心率持續變化(幅度)為20%、收縮壓>180 mmHg(1 mmHg=0.133 kPa)或 <90 mmHg、焦慮(行為)增加或出汗[13]。壓力支持通氣、持續呼吸道正壓通氣和T管通氣模式在拔管失敗率上并無明顯差別。與臨床醫師經驗性脫機方法比較,SBT脫機方法可明顯縮短機械通氣時間與ICU停留時間[14]。但范學朋等[15]將這兩種方法應用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患者撤機過程中,卻得出相反的結論。在SBT持續時間問題上,有研究表明應根據病種不同選擇不同的SBT持續時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宜選擇1~2 h,心力衰竭、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肺炎患者宜選擇30 min,以期提高脫機拔管成功率[16]。Coplin等[17]對腦損傷患者進行前瞻性、觀察性研究,將滿足脫機標準的患者進行分組,分別進行48 h內停止機械通氣與延遲停止機械通氣,結果表明,延遲停止通氣病死率較及時停止通氣更高,發生肺炎風險增加,并且住院時間更長。因此,臨床醫師應積極地使機械通氣持續時間縮至最短。與常規治療相比,用計劃性脫機方案來停止機械通氣有可能縮短機械通氣持續時間[18]。然而計劃性脫機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優于常規經驗性治療[19]。因為臨床上在制訂SBT入選的標準和停止機械通氣的過程上均存在差異,因此很難確切地說明這種方案的哪一方面或哪幾方面可導致機械通氣時間減少。
當SBT成功后,在拔除氣管插管前,還需要評估患者一些其他因素,如呼吸道分泌物的量、咳嗽的強度以及精神狀態等。如果這些因素滿足后,就可以拔除氣管插管。另外,當出現一次失敗的SBT、過多的呼吸道分泌物、咳嗽無力或精神狀況差時,就應該重新機械通氣,每日評估導致患者呼吸衰竭的因素,重新進行SBT。
3.2 無創正壓通氣及其他脫機模式 數項研究表明,在拔管后48 h內發生呼吸窘迫的患者中應用無創正壓通氣序貫治療可增加脫機成功率[20-23]。有兩項研究[22-23]選取停止機械通氣后發生呼吸窘迫的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進行隨機分組,一組接受標準治療(主要是吸氧和支氣管擴張藥),一組接受無創正壓通氣治療。這兩項研究均顯示兩組間需要再次插管的患者數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其中一項研究[22]顯示接受無創通氣組的病死率較標準治療高。然而,另外兩項研究首先前瞻性地辨別出使患者拔管失敗危險增加的因素,然后隨機分配這些患者,一組在拔管后接受標準治療,另一組預先準備接受無創正壓通氣治療。這兩項研究均顯示,與標準治療組相比,接受無創正壓通氣治療組對再次插管的需求減少[24-25]。因此,如果當患者被認為拔管失敗危險高時,那么在停止機械通氣后早期使用無創正壓通氣可以降低再次插管的發生率。然而,在拔管后有呼吸窘迫的患者,如果在呼吸窘迫開始后才開始接受無創正壓通氣治療,有可能不能從中獲益。事實上,這對一些患者還可能有害。應用無創通氣患者應意識清楚、血流動力學穩定,有咳嗽反射及咳痰能力,有很好的依從性;在無創正壓通氣時缺乏合作,過多分泌物,嚴重力量和負荷失衡以及血流動力學不穩定是失敗的常見原因。無創通氣已作為一種撤機過程中過渡的方法。
傳統脫機方法均要求嚴密觀察患者是否出現呼吸困難,監測動脈血氣分析而調整呼吸機機械通氣參數,這樣既增加了醫護人員的工作量[26],又增加了患者的痛苦和經濟負擔。國外專家對智能化脫機模式進行了研究,證實智能化撤機模式安全、舒適,可減少呼吸做功[27-28]。國內研究表明[29],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患者中,智能化脫機與SBT法在脫機成功率、脫機時間、相關并發癥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智能化脫機可減輕醫護人員負擔,改善患者脫機過程的舒適度。朱波等[30]應用Meta分析進行智能化脫機與人工脫機模式的比較,認為智能化脫機模式能夠縮短機械通氣時間和脫機時間,降低不良事件發生率。國內有學者[31]將68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隨機分為電腦智能組24例、SBT組24例、經驗組20例,結果顯示,電腦智能組(使用SmartCare功能)的脫機時間和總機械通氣時間均較經驗組顯著降低,但與SBT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BT組與電腦智能組以及經驗組與電腦智能組比較ICU住院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電腦智能組脫機成功率為88.3%,顯著高于經驗組(50.0%),但電腦智能組與SBT組(66.7%)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ICU住院生存率、總住院生存率、再插管率、自行拔管率和無創呼吸機輔助通氣率3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目前隨著機械通氣模式的增加,新的呼吸機通氣模式是否有利于脫機使用,還有待于更多的研究。
4 結語
目前存在很多脫機參數,更精準地判斷脫機成功與否的參數還待進一步研究。臨床醫師應積極地使機械通氣持續時間縮至最短,計劃性脫機方案提高臨床工作者脫機意識。目前常用的脫機方法為自主呼吸試驗,如果認為患者拔管后發生呼吸窘迫的風險高,可以提前準備無創機械通氣進行過渡。新興的智能化脫機可明顯改善患者舒適度,減少醫務工作者工作量。
[1]Wunsh H,Linde-Zwirble WT,Angus DC,et al.The epidemiology of menchanical ventilation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J].Crit Care Med,2010,38(10):1947-1953.
[2]Carson SS,Cox CE,Holmes GM,et al.The changing epidemiology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a population-based study[J].Intensive Care Med,2006,21(3):173-182.
[3]Esteban A,Anzueto A,Frutos F,et al.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in adult patients receiv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a 28-day international study[J].JAMA,2002,287(3):345-355.
[4]周厚榮,張謙,楊秀林,等.改良呼吸機脫機指數在急診重癥監護病房急性呼吸衰竭中的應用[J].中國危重病急救醫學,2009,21(7):334-335.
[5]鄭大偉,王承志,劉仁水,等.以改良格拉斯哥昏迷評分15分為切換點在有創-無創機械通氣治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所致嚴重呼吸衰竭的應用[J].中國危重病急救醫學,2011,23(4):224-227.
[6]Bendixin HH,Egbert LD,Hedley-Whyte J,et al.Respiratory care[M].St.Louis:Mosby,1965:149-150.
[7]Epstein SK,Ciubotaru RL,Wong JB.Effect of failed extubation on the outcome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J].Chest,1997,112(1):186-192.
[8]Esteban A,Alia I,Tobin MJ,et al.Effect of spontaneous breathing trial duration on outcome of attempts to discontinue mechanical ventilation[J].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1999,159(2):512-518.
[9]Girard TD,Kress JP,Fuchs BD,et al.Efficacy and safety of a paired sedation and ventilator weaning protocol for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Awakening and Breathing Controlled trial):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Lancet,2008,371(9607):126-134.
[10]MacIntyre NR,Cook DJ,Ely EW,et al.Evidence-based guidelines for weaning and discontinuing ventilatory support:a collective task force facilitated by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Respiratory Care,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J].Chest,2001,120(6 Suppl 1):375-395S.
[11]鄭大偉,曾祥彬,高峰,等.呼吸系統功能評分知道機械通氣治療呼吸衰竭撤機的臨床研究[J].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2013,12(2):146-149.
[12]Yang KL,Tobin MJ.A prospective study of indexes predicting the outcome of trials of weaning from mechanical ventilation [J].N Engl J Med,1991,324(21):1445-1450.
[13]王辰,詹慶元.機械通氣撤離的時機與方法[J].中華醫學雜志,2001,81(16):1022-1024.
[14]朱波,席修明,駱辛,等.計劃性脫機與經驗性脫機的臨床比較[J].中華急診醫學雜志,2006,15(5):437-440.
[15]范學朋,鄧巍,冷德文.不同撤機方式在COPD機械通氣患者的臨床觀察[J].內科急危重癥雜志,2013,19(2):88-92.
[16]徐磊,展春,張納新,等.自主呼吸試驗在機械通氣撤機過程中的應用[J].中國危重病急救醫學,2002,14(3):144-146.
[17]Coplin WM,Pierson J,Cooley KD,et al.Implications of extubation delay in brain-injured patients meeting standard weaning criteria[J].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00,161(15):1530-1536.
[18]Blackwood B,Alderdice F,Burns KE,et al.Protocolized versus non-protocolized weaning for reducing the dur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critically ill adult patients[J/CD].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2010(5):CD006904-CD006904.
[19]Rose L,Presneill JJ,Johnston L,et al.A randomised,controlled trial of conventional versus automated weaning from mechanical ventilation using SmartCare/PS[J].Intensive Care Med,2008,34(10):1788-1795.
[20]李潔,詹慶元.無創正壓通氣輔助有創通氣撤離中切換點把握[J].中國實用內科雜志,2009,31(7):678-680.
[21]有創-無創序貫機械通氣多中心協作組.以“肺部感染控制窗”為切換點行有創與無創序貫性通氣治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所致嚴重呼吸衰竭的多中心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J].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2006,29(1):14-18.
[22]Esteban A,Frutos-Vivar F,Ferguson ND,et al.Non invasive positive-pressure ventilation for respiratory failure after extubation[J].N Engl J Med,2004,350(24):2452-2460.
[23]Keenan SP,Powers C,McCormack DG,et al.Noninvasive positivepressure ventilation for postextubation respiratory distres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JAMA,2002,287(24):3238-3244.
[24]Nava S,Gregoretti C,Fanfulla F,et al.Noninvasive ventilation to prevent respiratory failure after extubation in high-risk patients[J].Crit Care Med,2005,33(11):2465-2470.
[25]Ferrer M,Valencia M,Nicolas JM,et al.Early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averts extubation failure in patients at risk:a randomized trial[J].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06,173(2):164-170.
[26]于湘友,鐘琳.危重患者兩種撤機方式的比較[J].臨床麻醉學雜志,2011,27(4):360-361.
[27]Haas CF,Bauser KA.Advanced ventilator modes and techniques[J].Crit Care Nurs,2012,35(1):27-38.
[28]Branson RD.Modes to facilitate ventilator weaning [J].Respir Care,2012,57(10):1635-1648.
[29]桑嶺,劉曉青,何為群,等.智能化撤機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的應用[J].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2013,12(4):356-361.
[30]朱波,李志強,席修明.智能脫機模式對機械通氣時間影響的系統評價[J].首都醫科大學學報,2013,54(2):191-199.
[31]徐曉婷,劉玲,邱海波,等.電腦智能脫機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脫機的影響[J].中華急診醫學雜志,2012,21(6):603-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