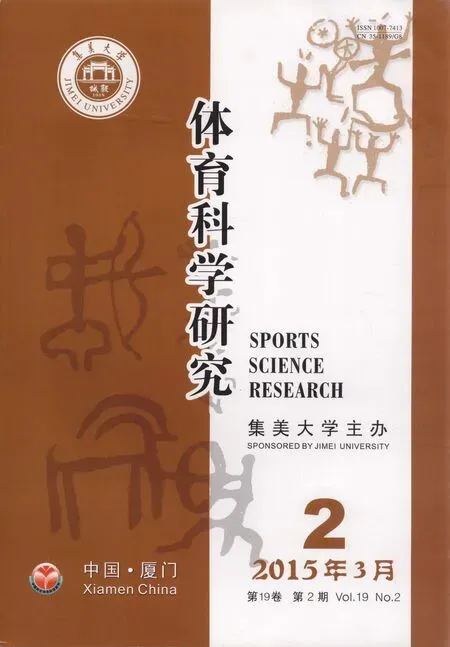“cultural change”視野下的中西方體育研究——闡述中國武術的變容
?
“cultural change”視野下的中西方體育研究——闡述中國武術的變容
燕藝賓
(華南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世界近代史的開端和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存在一個時間差,恰恰是在這個時間差里發生的事情改變了中國隨之以后的命運。大量稱之為西方新事物在中國的出現以及中國自身舊事物的消失,使中國本身進行了一場完全的洗禮。西方體育借此機會通過宗教和軍事等途徑傳播到中國,并借以奧運會和教育的形式使其在中國成為主流體育。在這一過程中,西方文化悄無聲息地傳播到中國,致使依附于本土文化的傳統體育遭到嚴重影響。武術,作為傳統體育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僅是一種身體活動,其原本所蘊含的文化更是豐富多彩。但是,現今武術所表現出來的種種跡象讓人們覺得武術自身獨特的文化被磨滅,加上目前武術進入奧運會的失敗,不禁使人對于武術前景倍感失望。至此,筆者借以文化人類學中“cultural change”為理論基礎,梳理西方體育在中國傳播的來龍去脈,并以此為線索,從文化的角度闡述武術在這一過程中的變容。同時,對于武術自身的本質核心與作為武術載體的身體對于今后武術發展提出見解。
1“cultural change”闡釋
“cultural change”,中國學者大多翻譯為“文化變遷”,日本學者和中國少部分學者翻譯為“文化變容”,“最初明確提出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名文化人類學家Franz Boas”。“cultural change”的含義是指“由于民族社會內部的發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間的接觸,因而引起一個民族文化的改變”。民族自身內部的“cultural change”,其機制是以創造為源動力,例如自身新技術的創造,取代以前傳統的工藝,致使這一部分民族文化得到改變;傳播,是“cultural change”的另一機制,指如果這種發明創造通過不同民族之間的接觸得以傳播,從而致使另一民族發生變化;“cultural change”的第三個機制是文化遺失,新的事物代替舊的事物,就會導致舊事物的消失。但這一機制也不是絕對的,也會存在個例,比如中國在全面西化的過程中,吃飯用筷子的傳統文化還一直被我們所保留;“cultural change”的第四個機制是涵化,涵化是指“由于兩個社會之間發生緊密而直接接觸,人們被迫做出重大文化改變464”。涵化最極端的現象就是文化滅絕,這個機制突出在過程中具有強制性,同時也是區別于文化遺失的一個因素。通過這四個機制,隨之在民族內部對于“cultural change”會做出不同程度的反映,大多屬于復興運動,尤其是本民族在被強迫接受其他文化或者是在侵略時被導入其他文化的情況下,其復興運動就更為強烈,甚至會產生反叛與革命。在進入新世紀之后,“現代化”作為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術語之一伴隨著作為以西方先進工業社會為基礎的西方文化的傳入,被人們所熟知并逐漸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后各個事物改變過程的代名詞。
2西方體育在中國的傳播
2.1 “西方體育”的含義
人們常說的“西方”,其劃分有三個標準: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和政治體制。“地理上的西方指的是本初子午線以西的半個地球,包括南北美洲;政治文化上的西方指的是歐美各國,有時候特指歐洲資本主義各國和美國”;“從文化背景上講,西方文化體系中有一個特有的文化區,那就是基督教文化區”。這三個標準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明確指出以前以及現今“西方”的具體含義。筆者比較認同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威廉·A·哈維蘭的觀點,他認為:“西方是歐洲的和從歐洲派生的37”。這一解釋明確指出了西方一詞的根源所在,從其本質上限定了西方一詞的范圍。
“體育”一詞在對應的英語中,常用的有兩個,其為“physical education”和“sport”。其中“‘physical education’明確是指學校教育系統中所開展的體育活動”,其目的強調的是通過身體教育提高身體運動能力,從而促進身體健康。而英語“sport”一詞,來源于拉丁語“deportare”,后傳到法國變為“desport”,最后傳到英國變為我們現在所熟知的“sport”。“sport”一詞的含義相當豐富,“physical education”也只是它眾多釋義中的一種,它不僅是指身體活動,還包括通過運動使精神得到解放、身心得到愉悅等,但對于是不是促進健康,則視情況而定。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西方體育”是指歐洲的和從歐洲派生的不僅包括學校教育系統中所開展的身體活動,還包括其外的通過運動使精神得到解放、身心得到愉悅等一切身體活動形式。
2.2 以奧運會為代表的西方體育的再創造與在中國的傳播
現今,西方體育中風靡全球的奧運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76年。其創始人為伊菲圖斯,他最初的目的是想通過奧運會使宗教與體育競技合為一體。當時的比賽項目也只有一個,距離為192.27米的競速跑。之后,基督教統治了整個歐洲,它所倡導的禁欲主義,反對體育運動,使整個歐洲體育事業處于一個黑暗時代。奧運會也隨之衰落,加上隨后的一些人為與環境因素,使延續多年的奧運會不復存在。在1891年,顧拜旦向全世界的體育組織發出邀請,參加于1894年在法國召開的第一屆奧林匹克代表大會。1896年,第一屆奧運會在雅典舉行,項目有田徑、游泳、射擊、古典式摔跤等9個大項。相比較于最初的奧運會,比賽中增多的那些項目,是被隨后創造出來并被大眾所接受的,這個過程中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cultural change”。
在首屆奧運會前期,清朝統治者曾接到邀請,但未派人參加。此后,顧拜旦認為中國應是奧運會不可缺少的一份子,“他意識到只有中國參加奧林匹克大家庭,才能使奧運精神發揚光大。于是在1922年6月舉行的第20屆奧委會執行委員會會議上,顧拜旦力薦王正廷為國際奧委會委員”。至此,王正廷成為中國人中的首位國際奧委會委員。1932年中國人劉長春參加了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的第10屆奧運會。隨后,中國的69名選手參加了在德國柏林舉行的第11屆奧運會,其中的國術表演隊隨團首次有組織地在國外表演,也是中國武術首次在奧運會上亮相。“中國臺北選手劉傳廣在十項全能中獲得8 332分,破奧運會記錄,但以58分的微小差距居亞軍,這是中國自1932年參加奧運會以來運動員獲得的第一枚奧運獎牌”。在這之后,許海峰在第23屆洛杉磯奧運會上為中國獲得歷史上第一枚金牌。2008年,在中國的北京首次舉辦了第29屆夏季奧運會,中國以51枚金牌居獎牌榜首名。時至今日,西方體育借助奧運會的形式,成為中國現今的主流體育。中國自上而下在“奧運夢”的意識形態導向下,被西方體育所占據,更深一層次說,中國體育已被西方文化所滲透。
2.3 以“physical education”與軍事體育為代表的西方體育在中國的傳播
中國與西方的第一次接觸,始于“1514年,當葡萄牙人出現在東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時,中國人首次開始同西方的直接交往”。而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始于1840年,西方在獲取資源、特權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各種思想。1861年興起的洋務運動,主要是在軍事上學習西方,套用西方的軍事模式,訓練清兵。洋務運動中聘請英國、德國等軍官教授兵操,清朝末期的教育改革中聘請外國體育教師來華教學。1872年以后,中國多批留學生赴美國、日本等國學習,在國外參與體育實踐或者學習體育專業,回國后推動了西方體育的傳播。“‘為基督征服世界’的口號是19世紀末美國準備向東方擴張所發出的一個強烈信號”[10]。宗教的力量使得當時先進的體育思想傳播到中國,直至影響到今天。“西方體育文化在對諸如中國、印度、日本、朝鮮、越南等古文明國家的傳播初期,均以教育的形式出現,似乎是上帝把‘近代西方體育文化’奉獻給這些近代落后了的文明古國”[11]。體育借助教育的形式傳播到中國,其主要的傳播地點是教會學校,馬禮遜學堂是當時最早的教會學校。之后,教會學校陸續在中國出現。
3以武術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的衍變
3.1 “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的含義
“中華民族”現在指的是中國的56個民族,其中包括55個少數民族與1個漢族,但這不代表在近代中的中國是這個含義。究其指的是什么,要認真分析。在馮天瑜先生的《中國文化史》一書中對“中”與“華”做了如下解釋:“‘中’指居中集眾之旗,引申為中心,中央;‘華’通‘花’,意謂文化燦爛,所謂中國‘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中華’是‘中國’與‘華夏’的復合詞之簡稱,較早出現于華夷混融的魏晉南北朝,《魏書》 、《晉書》多有用例”。以上是對這一詞語的地點做了闡釋,明確指出了“中華”一詞的含義。馮天瑜先生對于民族的定義為:“民族,泛指歷史上形成的,處于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各種人群共同體”。這一定義,指出了“民族”一詞是動態的,卻籠統定義為“各種人群共同體”,所以參考了美國學者威廉·A·哈維蘭給民族下的定義,其為:“民族,指基于共同的祖先、歷史、社會、制度、意識形態、語言、地域,通常還有宗教,視自己為“一個民族”的人們共同體359”。對于“中華民族”,馮天瑜先生的定義為:“在中國這片廣袤,豐腴的大地上生活勞作的各族人民[12]”。在定義中,看到馮先生限定了地點,但對象卻指的是籠統的“各族人民”,同時也沒有指出民族一詞的動態性。費孝通先生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13]”。以上定義都有其專注的方面,但對于“民族”一詞的限定還有所欠缺。根據斯大林的觀點“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所由以產生的基礎是由于人們共同具有四種基本特征,即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民族文化特征上的心理狀態[14]”。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中華民族”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在中國這片廣袤,豐腴的大地上,具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民族文化特征上的心理狀態的穩定的共同體。
人們的意識中,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三個詞語在時間維度上基本可以概括所有發生的事情。同時,未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變成現在與過去,這就可以引申到對于“傳統”一詞的理解。人們普遍認為,傳統的事物就是過去的事物,這僅僅是在時間這個層面的解釋,卻沒有察覺到傳統事物對于現在與未來的影響。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威廉·A·哈維蘭對于傳統的觀點是“在現代化社會里,可以對抗新的分化和整合力量的舊文化習俗”476;我國學者周偉良先生對于“傳統”的解釋為:“傳統不應該是歷史上所有事物的統稱,更不是一切過去的統括,而是對今天依然產生影響的過去的存在,這種存在包括物質形態、制度形態、精神形態的文化[15]”。以上這兩種觀點都突出的表現出過去對于現在的作用,只是在作用層面上的用詞有所不同。可見,一方面,傳統不等同于過去,雖然從字面意義上與近代是相對立的;另一方面,“傳統”是一個始終動態著的事物;最后,“傳統”是被不斷創造出來的,因為會有新元素不斷地被揉合進原有的傳統中。
在對于“中華民族”“傳統”與“體育”的理解上,可以看到這一詞語所包涵的內容如此廣闊,對其作出精確的解釋十分不易,只能接近而達不到完美。所以,筆者采用周偉良先生對于這一詞語的解釋:“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是指在中國近代之前產生發展、由中華民族世代實踐并留傳或影響至今的體育[15]”。
3.2 武術的形成與轉變
在中國的歷史階段中,其體育的形式多種多樣。從項目發展的角度來看,一些項目被淘汰,一些項目被傳承,這之中并沒有優劣之分,要歸于社會選擇的結果。自古以來,中國從來都不缺乏體育運動。例如球類運動中唐朝的擊鞠、宋朝的蹴鞠與元朝的捶丸等,更不用說近代以前的摔跤、田徑運動,其形式多樣、內容豐富,足可以證明中國為世界體育運動的繁榮與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中華民族傳統體育項目中,武術一直延續著它的生命力,并且逐漸成為其主體,承擔著復興中華民族傳統身體技術文化的重任。回過頭來看看真正意義上的武術形成的初始階段,會發現這是一個渾然天成、龐大的系統。在“武術”這一名稱下,我們挖掘整理出眾多的流派、拳種等,足以證明中華民族傳統身體技術文化的多樣性與傳承性。依據這一點,還可以看出武術形成的復雜性,以及富含東方特有的意識形態下的身體技術文化所表現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百家爭鳴。這樣一個龐大的體系,是在自然的狀態下經歷長久的時間積累與文化疊加所形成,并且受到傳統文化與社會因素等各方面的打磨,最終成為一個傳承明確,秩序井然的體系。直到今天,這種傳統文化依然存在,繼續為傳承中華民族傳統身體技術文化而努力。
中國在近代中,受西方的影響和時代等因素的需要,武術也在不斷地轉型。隨著西方體育的大量涌入與作為我國傳統體育項目的武術的不斷成長,使得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產生沖突。隨后眾多的武術文化復興運動接踵而來,“‘土洋體育之爭’是發生于20世紀20至30年代,就西方體育和以武術為代表的本土傳統體育,誰應成為中國體育發展的主流而引發的一場爭論”[16]。伴隨著馬良的“中華新武術”到創于1909年的精武體育會,到后來的中央國術館,直到現在國家大力推行的競技武術,一路走來后發現武術本身的東西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高、難、美、新”等一系列眼花繚亂的動作。不可否認,武術確實是在向前發展,但是它是否失去了絕大多數人對于它的熱愛?
武術是一種以身體為載體的文化,當人們通過從事競技體育去體驗這種文化的時候,卻體驗不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正含義,正如“以身體作為媒介來了解不同文化,不僅僅只是停留在以一個局外者對表象的象征理解,而是通過自身參與民族體育運動用身體作為媒介去體驗外來文化的內涵”[17]。現今,武術在文化層面的改變值得我們去深思與反省,我們對于樹立自身武術文化品牌做出了努力。但是,現今中國武術卻表現出西方體育的樣子。目前來看,本該是保護和發揚隸屬于博大中國文化下的武術文化,使之成為支撐武術本身強有力的基礎,實則對于作為武術文化核心本質的東西丟失的太多,在比賽中套用西方模式,致使現在在中國意識形態導向下的武術變得西洋體育化。
3.3 武術的現代化
“現代化一般是指傳統農業社會或發展中的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乃至發達的現代工業社會發展轉變的歷史過程”[18]。它作為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術語之一隨著作為以西方先進工業社會為基礎的西方文化的傳入,被人們所熟知并逐漸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后各個事物改變過程的代名詞。在這之中,武術也不例外,其一步步轉變的過程也被賦予了“現代化”的含義。現階段,國家大力推行所謂的競技武術,可視為武術現代化過程的定型。競技武術是相對于傳統武術提出來的,解放前人們說的武術是傳統武術,然而,在解放后所提到的武術就單指的是競技武術。競技武術是以傳統武術為母體,并在此基礎上汲取西方競技體育的因素,不斷發展、變化的結果。傳承于傳統武術的競技武術,在中西體育文化碰撞與融合的潮流中,歷經曲折而逐步走向成熟,并成為當代武術運動的主體。
“探究中國現代化轉型中傳統身體意識和身體文化形式的變化,實質上就是從身體的角度對中國現代化路徑進行審視”[19]。武術的現代化轉型可以反映出當代中國人對于武術本身在意識和身體文化層面的改變,同時,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標準的制定,一種符合以西方先進工業社會為基礎的西方文化模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概念會有變化,內容會有改變,但是其本質的東西是不會被取代的。作為武術本質的對抗,塑形與自身文化,都不能脫離身體而談論。武術的現代化轉型也應在這些本質的基礎之上進行轉變,否則反映到文化層面,就會出現文化遺失的現象。繼承本質,結合身體,中國武術才有可能使其自身形成一個自養的循環系統,而不僅僅是一個存在于意識形態下的標本。
4結語
近代以后西方體育在中國的傳播有其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一方面,“落后就要挨打”這句話使中國人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缺陷,所以就主動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和“自強”等口號,這樣西方近代的體育形式就通過洋務學堂對西式兵操的引進而進入中國;另一方面,洋務運動之前,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成為西方文化、教育和體育等最為直接的傳播者;之后,大量的教會學校成為西方體育在中國扎根的主要地點;再一方面,“為基督征服世界”的口號促使了近代教育思想在中國扎根,德智體的全面發展也使體育悄無聲息地在中國大地上傳播開來。在西方文化下的體育,不斷占據著中國整個學校體育系統;最后,作為被挖掘出來并被不斷創造的文化,奧運會以其茂盛的生命力促使著自身傳播到中國,并逐漸占據了主流。
西方體育依附于西方文化模式,文化傳播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在其自身必然產生影響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改變當地的文化。借助于西方強勢文明,致使人們對于本土文化在身體運動過程中產生改變的同時,其意識層面也會產生反差。所以在逐步接受近代西方體育的過程中,中國本土的體育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直至影響到人們對武術本質的理解。本文以文化人類學為理論基礎,借以“cultural change”為探索視角,分析西方體育的傳入、扎根與成為主流體育的一系列過程,并從文化的角度討論了武術在這一過程的轉變。同時,又以武術反饋于身體,使武術回歸于原本屬于它的載體,并從其本質出發,對于武術的現代化轉型提出了筆者的見解。最后,文化只有差異,沒有優劣之分,保持多樣性才有可能使世界多姿多彩,并且文明已經來臨,蠻荒漸漸遠去,所以,重拾“本質”對于保持“自身獨特的文化”已經被人們重視起來。
參考文獻
[1]平野健一郎.國際文化論[M].張啟雄,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48.
[2]黃淑娉,龔佩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M].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09.
[3]威廉·A·哈維蘭.文化人類學:Tenth Edition[M].瞿鐵鵬,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464.
[4]中國體育科學學會,香港體育學會.體育科學詞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39.
[5]李新柳.東西方文化比較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8.
[6]張洪譚.體育的概念、術語、定義之解說立論[J].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06,23(4):1-6.
[7]房淑珍.近代中國奧運記憶[J].體育學刊,2011,18(1):71-74.
[8]崔樂泉.奧林匹克運動簡明百科[M].北京:中華書局,2003:220.
[9]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第七版修訂版)(下冊)[M].吳象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584.
[10]陳晴.清末明初新式體育的傳入與嬗變[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306.
[11]童昭崗,孫麒麟,周寧.人文體育:體育演繹的文化[M].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2:140.
[12]馮天瑜.中國文化史:彩色增訂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9.
[13]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36.
[14]斯大林,曹葆華.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M].毛岸英,譯.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1:1.
[15]周偉良.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概論高級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8-10.
[16]馬廉禎.論現實視角下的“土洋體育之爭”[J].體育科學,2011,31(2):76-84.
[17]馬晟.中國民族體育文化“走出去戰略”的思考——以加拿大中國龍舟運動為例[J].體育科研,2012,33(1):27-31.
[18]陳國強.簡明文化人類學詞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299.
[19]馬廉禎.論中國武術的現代化轉型和競技武術的得失[J].體育學刊,2012,19(3):114-120.
[責任編輯江國平]
摘要:采用文獻資料法與邏輯比較分析法,并借以文化人類學理論中的"cultural change"為視野,探討西方體育對中國武術的影響。研究認為:第一,隨著西方體育的不斷滲入,隸屬于教育系統中的體育系統,被西方體育項目所占據;第二,在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逐漸影響下,西方體育成為我國現今的主流體育;第三,武術隨著西方體育的傳入經歷了數次變革,成為現在國家大力推行的競技武術形式,削弱了武術本身核心的本質與身體文化價值。
關鍵詞:文化;武術;傳統體育;西方體育
The Research of Western and Chinese S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hange”——To Expou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WushuYAN Yi-b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uses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analysis, logic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make a theory of cultural change in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y as a vision to expound the influence of Wushu by Western sports. This paper shows that: first, physical education system that belongs to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dominated by Western sport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ports; Second, Western sport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today’s sports in our countr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Olympic Games; Third, Wushu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change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ports and becoming the country vigorously competitive Wushu in nowadays, which decreases the core essence and body cultural value of Wushu.
Key words:culture;Wushu;traditional sports;western sports
中圖分類號:G8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413(2015)02-0038-05
作者簡介:燕藝賓(1990—),男,河南溫縣人,在讀碩士。研究方向:民族傳統體育、體育人類學。
基金項目:華南師范大學2014—2015年度校學生科研一般課題基金資助(14TKGA03)
收稿日期:2014-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