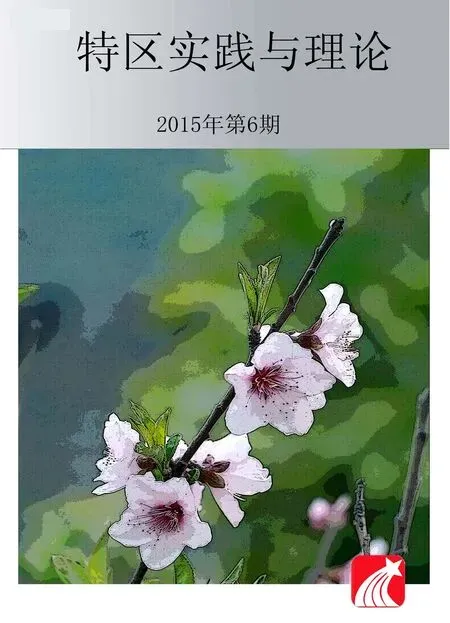論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本質及意義
許先春
論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本質及意義
許先春
創(chuàng)新發(fā)展,表面上看是強調創(chuàng)新的重要性,從本質上看是發(fā)展動力的根本性轉換。在傳統(tǒng)要素驅動弱化、后發(fā)優(yōu)勢逐漸縮小的形勢下,我國發(fā)展到了依靠創(chuàng)新驅動的階段。我國經濟發(fā)展進入新常態(tài),迫切要求將經濟發(fā)展動力從要素驅動切換到創(chuàng)新驅動上來。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體現了我們黨對科技功能的新概括新定位,蘊含著對有限與無限、質變與量變的新思考新理解,從多方面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科技理論、發(fā)展觀、唯物辯證法,拓展了對人類社會發(fā)展資源的認識。
創(chuàng)新發(fā)展;科技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動力;初始質變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五大發(fā)展理念,其中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位列五大發(fā)展理念之首。這一發(fā)展理念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形成的?其本質和意義是什么?本文試圖對此作些簡要分析。
一、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的本質是發(fā)展動力的轉換
發(fā)展動力不同,發(fā)展基點、發(fā)展方式就不同。創(chuàng)新發(fā)展,從表面上看是強調創(chuàng)新的重要性,從本質上看是發(fā)展動力的根本性轉換。
(一)創(chuàng)新驅動是經濟發(fā)展進入新常態(tài)的必然要求
發(fā)展理念是發(fā)展行動的先導。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是在科學把握我國發(fā)展戰(zhàn)略機遇期內涵深刻變化的基礎上提出的。國際金融危機后,黨中央做出了我國經濟發(fā)展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的判斷。在“三期疊加”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我國經濟發(fā)展進入新常態(tài)的重大戰(zhàn)略判斷。所謂新常態(tài),最主要的表征就是速度變化、方式轉變、結構優(yōu)化和動力轉換“四態(tài)”。具體說就是,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fā)展方式從規(guī)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yōu)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發(fā)展動力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chuàng)新驅動。[1]在新常態(tài)的“四態(tài)”中,動力轉換最為關鍵,決定著速度變化、方式轉變、結構優(yōu)化的進程和質量。不轉換發(fā)展動力,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將難以為繼,就會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陷入被動局面。新常態(tài)是我國經濟進入更高層次發(fā)展階段后才出現的狀態(tài),給我國經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習近平指出:“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創(chuàng)新上,就在加快從要素驅動、投資規(guī)模驅動發(fā)展為主向以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為主的轉變上。”[2]他強調,適應和引領我國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關鍵是要依靠科技創(chuàng)新轉換發(fā)展動力。[3]
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是對世界發(fā)展經驗的科學總結。美國學者邁克爾·波特認為,經濟發(fā)展具有階段性,在不同的發(fā)展階段,驅動經濟增長的力量是不一樣的。國家競爭優(yōu)勢的發(fā)展可分為四個階段,即要素驅動階段、投資驅動階段、創(chuàng)新驅動階段和財富驅動階段。當今世界,典型的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發(fā)展都是依靠創(chuàng)新實現經濟跨越式發(fā)展,依靠創(chuàng)新保持長期的經濟增長。進入21世紀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發(fā)生后,主要發(fā)達國家紛紛調整科技部署,把科技創(chuàng)新上升為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以創(chuàng)新為利器推動經濟長期持續(xù)增長。
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是在總結我國發(fā)展實踐、借鑒世界發(fā)展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立足于我國經濟發(fā)展進入新常態(tài)而做出的重大決策,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必然選擇。堅持創(chuàng)新發(fā)展,是對發(fā)展動力的根本性轉換。這才是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的底蘊和實質所在。
(二)實現發(fā)展動力轉換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為什么要實現發(fā)展動力轉換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傳統(tǒng)要素驅動弱化,后發(fā)優(yōu)勢縮小,我國發(fā)展已經到了依靠創(chuàng)新驅動的階段。
首先,從傳統(tǒng)要素驅動方面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資源投入和廉價勞動力,走的是依靠勞動力、土地、能源資源等傳統(tǒng)要素投入和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的路徑。現在,支撐我國經濟快速發(fā)展的勞動力、土地、能源資源等生產要素的供求關系發(fā)生了變化,依靠傳統(tǒng)生產要素驅動經濟發(fā)展的動力逐步減弱。表現之一就是,人口老齡化加劇,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資源豐富而價廉的比較優(yōu)勢不復存在。“而世界上其他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國家利用相對更低的生產要素成本優(yōu)勢,加快發(fā)展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yè),對我國低成本優(yōu)勢形成替代效應。”[4]發(fā)達國家紛紛采取再工業(yè)化戰(zhàn)略,我國傳統(tǒng)的低成本、低價格競爭優(yōu)勢逐漸削弱。表現之二就是,從總量上講我國資源豐富,但在人均上我國重要能源資源的擁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加快發(fā)展的階段,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越來越突出,環(huán)境承載力已經接近或達到上限,能源資源約束日益趨緊。這些情況表明,依靠傳統(tǒng)生產要素高強度、大規(guī)模投入支撐經濟發(fā)展的老路子已經難以為繼。在傳統(tǒng)要素弱化和比較優(yōu)勢喪失的情況下,必須轉變傳統(tǒng)發(fā)展模式的路徑依賴,實現發(fā)展動力的根本性轉換。
其次,從后發(fā)優(yōu)勢方面看。所謂后發(fā)優(yōu)勢,是指后發(fā)展國家在借鑒發(fā)達國家現代化經驗的基礎上,根據各自不同的條件充分發(fā)揮自己的優(yōu)勢實現追趕式發(fā)展甚至后來居上。主要表現是:后發(fā)展國家可以通過學習、引進、消化、吸收,在短時期內掌握先進國家經過長時期探索而獲得的知識和技術;可以從發(fā)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吸取經驗和教訓,減少不必要的代價,少走彎路,在較短時間內走完發(fā)達國家在幾百年間走過的歷史行程。我國作為發(fā)展中大國,過去幾十年中比較好地利用了后發(fā)優(yōu)勢,創(chuàng)造了經濟發(fā)展史上的奇跡。但是,發(fā)展到今天,后發(fā)優(yōu)勢的利用空間逐步縮小,在有的領域已經喪失。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在技術引進上。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只能走“引進——消化吸收——模仿創(chuàng)新”的技術路線。這種跟蹤模仿式的創(chuàng)新屬于低層次創(chuàng)新,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都掌握在外方手里。由于當時我國經濟基礎薄弱、生產力還不夠發(fā)達、科技水平不高,能模仿出來就是進步,低層次創(chuàng)新可以支撐經濟的快速發(fā)展。但發(fā)展到今天,靠低層次創(chuàng)新已經無法帶動和支撐經濟的高速發(fā)展。隨著國際競爭日趨激烈,我國引進先進技術的難度、成本也在加大。創(chuàng)新不足、原始性創(chuàng)新不強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發(fā)展的瓶頸。另外,我國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緊要關頭。在這個緊要關頭,再靠發(fā)揮后發(fā)優(yōu)勢已經無能為力。從國際經驗看,一些國家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資源和引進技術過于依賴,經濟發(fā)展長期建立在低水平規(guī)模擴張上,以自主創(chuàng)新為主的內生動力不強。而那些成功邁過“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經驗:緊緊依靠科技創(chuàng)新打造競爭的新優(yōu)勢。在我國后發(fā)優(yōu)勢逐漸縮小的情況下,能否成功走出傳統(tǒng)的跟蹤模仿低層次創(chuàng)新模式,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是看能否實現發(fā)展動力的根本性轉換。
那么,什么是新的發(fā)展驅動力呢?這就是創(chuàng)新。我國經濟發(fā)展進入新常態(tài),迫切要求將經濟發(fā)展動力從要素驅動切換到創(chuàng)新驅動上來。堅持創(chuàng)新發(fā)展,就是在傳統(tǒng)要素驅動力不斷減弱、后發(fā)優(yōu)勢逐漸縮小的情況下,果斷實現發(fā)展動力的根本性轉換,將發(fā)展動力由傳統(tǒng)要素驅動轉向創(chuàng)新驅動,把創(chuàng)新作為引領發(fā)展的第一動力,把發(fā)展基點放在創(chuàng)新上,塑造更多依靠創(chuàng)新驅動、更多發(fā)揮先發(fā)優(yōu)勢的引領型發(fā)展。最終目的是改變過多依靠傳統(tǒng)要素投入的發(fā)展模式,加快形成新的內生發(fā)展動力,實現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引領發(fā)展。所以說,堅持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實施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科學解答了我國在傳統(tǒng)要素驅動力不斷減弱、后發(fā)優(yōu)勢逐漸縮小的情況下如何進一步發(fā)展的難題。
(三)對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的辯證理解
把創(chuàng)新作為引領發(fā)展的第一動力,絕不是對傳統(tǒng)要素驅動的全盤否定和拋棄。必須認識到,由于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發(fā)達國家相比,我國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不足、產業(yè)結構不合理、發(fā)展方式依然粗放,這就使得傳統(tǒng)發(fā)展動力雖然減弱,但在一定時期和發(fā)展階段仍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依托力量。欲速則不達。由于以全面創(chuàng)新為主要內涵的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模式在現有條件下無法完全、徹底形成,這一客觀實際決定了我們在提出把創(chuàng)新作為引領發(fā)展第一動力的同時,還要挖掘傳統(tǒng)發(fā)展動力的潛力。也就是說,要將科技創(chuàng)新這一新要素滲透、耦合到傳統(tǒng)發(fā)展動力中,通過科技創(chuàng)新來改造傳統(tǒng)發(fā)展動力,激發(fā)和催生傳統(tǒng)要素驅動的新能量。正因如此,十八屆五中全會在提出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時,并不將其絕對化,而是極為審慎、很有分寸地表述為“塑造更多依靠創(chuàng)新驅動、更多發(fā)揮先發(fā)優(yōu)勢的引領型發(fā)展”。這里的“更多”,筆者認為是十分恰當地、辯證地處理了傳統(tǒng)要素和創(chuàng)新要素的關系。既沒有將當下發(fā)展階段的傳統(tǒng)要素驅動一筆抹殺、全盤否定,同時又表明創(chuàng)新的分量和地位在提高、提升。“更多”,并不是說目前條件下已經能夠做到百分之百依靠創(chuàng)新驅動,而是說要著力加大、強化創(chuàng)新驅動的比重。這是立足我國基本國情而做出的實事求是的科學判斷,即不超越發(fā)展階段,又不脫離實際。“在創(chuàng)新驅動的發(fā)展方式中,土地、資本等傳統(tǒng)要素仍然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創(chuàng)新上升到了第一位。”[5]可見,提出創(chuàng)新驅動,并無全然否定傳統(tǒng)要素驅動之意。這是我們要十分注意的。創(chuàng)新驅動,形象地說,就是從跟跑、并跑變?yōu)轭I先和領跑,打造自己的先發(fā)優(yōu)勢。
二、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的理論意義
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體現了我們黨對科技功能的新概括新定位,蘊含著對有限與無限、質變與量變的新思考新理解,從多方面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科技理論、發(fā)展觀、唯物辯證法,拓展了對人類社會發(fā)展資源的認識。
(一)馬克思主義科技理論的深化:由“第一生產力”到“第一動力”
馬克思主義高度重視科學技術,歷來把科學技術活動看成是人類偉大的實踐活動之一,看成是社會進步的動力。馬克思把科學看成是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力量,明確指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6],“勞動生產率是隨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fā)展的”。[7]鄧小平總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特別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和科技發(fā)展的新變化,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8]的論斷。世紀之交,江澤民深刻把握科技發(fā)展突飛猛進、科技在經濟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的趨勢,提出科學技術“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9]的論斷。新世紀新階段,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yè)變革風起云涌、正在醞釀突破的態(tài)勢,習近平在2015年兩會期間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明確提出:創(chuàng)新是引領發(fā)展的第一動力。[10]這一論述抓住了當今世界發(fā)展的重要特征,揭示了創(chuàng)新對當代生產力發(fā)展和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第一位的變革、推動和引領作用,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科技理論。這一論述,在生產力大系統(tǒng)中抓住了科學技術這個關鍵性因素,又在科學技術大系統(tǒng)中抓住了創(chuàng)新這個決定性因素,并且將創(chuàng)新上升到“第一動力”的高度,凸顯了創(chuàng)新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科技功能的新概括:由推動到驅動、由支撐到引領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都是把科學技術作為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推動力量來看待的,反復強調要為經濟社會發(fā)展提供強大的科技支撐。推動和支撐,是科學技術社會功能的主要體現。進入新世紀以來,新科技革命呈現出科技創(chuàng)新出現群體性突破、新的技術群和新的產業(yè)群蓬勃發(fā)展等全新的特點。尤其是科技創(chuàng)新的速度和頻率不斷加快,科技競爭的焦點不斷前移,原始性創(chuàng)新、關鍵技術創(chuàng)新的作用日益突出。有鑒于此,《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06-2020)》明確提出并闡述了新世紀我國科技發(fā)展的“十六字”指導方針:自主創(chuàng)新、重點跨越、支撐發(fā)展、引領未來。引領未來,就是著眼長遠,超前部署前沿技術和基礎研究,創(chuàng)造新的市場需求,培育新興產業(yè),引領未來經濟社會發(fā)展。把科學技術作為引領未來發(fā)展的主導力量來看待,表明黨對科學技術社會功能的認識有了新飛躍。在當今時代,科學技術不僅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推動、支撐力量,更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驅動、引領力量。由推動到驅動,由支撐到引領,表明我們黨對科學技術社會功能的定位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驅動和推動都表明了科技對于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動力作用,但驅動包含了推動的內涵和要求,同時又更加突出“驅”。引領和支撐都是科技動力作用對于經濟社會發(fā)展的表現,引領以支撐為基礎,同時又更加突出“引”。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就是“驅”和“引”這兩種功能相結合而形成的新理念。科技的驅動、引領作用,是通過科技創(chuàng)新這個環(huán)節(jié)來實現的。沒有創(chuàng)新,科學技術的驅動和引領作用則無法實現。科技創(chuàng)新影響、塑造、決定和改變著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未來。
(三)唯物辯證法的新解答:有限與無限
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始終面臨著資源有限性和需求無限性之間的矛盾。早在20世紀70年代,羅馬俱樂部就提出了“增長的極限”問題,指出地球是有限的,空間是有限的,資源是有限的,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掠奪與浪費使經濟增長臨近自然生態(tài)極限,人類社會發(fā)展將會在資源消耗殆盡時停滯。由此引發(fā)了西方社會長達十余年的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有限與無限的大爭論。這場爭論的實質是如何處理資源有限性與需求無限性的矛盾。直到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與發(fā)展委員會提出可持續(xù)發(fā)展理論之后,這場爭論才告一段落。但是,隨著世界工業(yè)化進程的加快,全球資源、環(huán)境約束越來越大,單純地依靠節(jié)約資源、保護環(huán)境、維護生態(tài)平衡已經滿足不了發(fā)達國家尤其是新興工業(yè)體發(fā)展的迫切需要。如何突破有限與無限的矛盾并實現新形勢下的統(tǒng)一?創(chuàng)新發(fā)展、綠色發(fā)展的理念應運而生。在傳統(tǒng)的發(fā)展方式下,土地、水、礦產等資源能源以及資本、管理等要素對經濟社會發(fā)展起主導作用,決定著發(fā)展的規(guī)模和速度。而創(chuàng)新驅動的基本特征是,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勞動力素質提升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第一位要素。人類可以通過科技創(chuàng)新,不斷開發(fā)新的資源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人類創(chuàng)新的潛力是無限的,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潛力可以突破資源的限制,開辟新的發(fā)展空間。通過創(chuàng)新不斷挖掘人類的創(chuàng)造潛能進而創(chuàng)造現實的生產力,彌補資源有限和傳統(tǒng)要素驅動不足的缺失。創(chuàng)新成為解決人類面臨的能源資源、生態(tài)環(huán)境、自然災害、人口健康等全球性問題的重要途徑。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提出了解決資源有限性和需求無限性矛盾的一種方式。
(四)理解質變與量變的新視角:初始質變
質量互變是唯物辯證法的三大規(guī)律之一。過去,我們一般認為,量變引起質變,質變引起新的量變。而現在,新科技革命迅猛發(fā)展,科技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越來越快,科技成果產業(yè)化的周期越來越短。這一方面顯示出,傳統(tǒng)的量變過程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越來越短,質變可能在量變還沒有達到臨界狀態(tài)前就會醞釀甚至內生。另一方面,有些科學發(fā)明、科技創(chuàng)新,一開始就是革命性的,是對傳統(tǒng)的重大顛覆和變革,質變和量變可能是相互內嵌、疊加演變甚至是同時發(fā)生的。而且,突變、驟變、爆發(fā)式飛躍越來越多地出現了。當今世界的許多科技創(chuàng)新成果,一開始、一誕生就顯出了質變的特征,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生存方式。比如,“移大山”(移動互聯(lián)網、大數據、3D打印)、“智云霧”(智慧城市、云計算、物聯(lián)網)給人們的思維、生產生活方式、消費方式帶來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眾籌、P2P網貸等互聯(lián)網金融顛覆了傳統(tǒng)的金融模式,O2O、第三方支付改變了傳統(tǒng)的購物與支付模式,Facebook、微信改變了人類的交往方式。一個創(chuàng)意就能改變整個世界,一個頭腦風暴就掀起一場產業(yè)颶風,一個新點子就可能秒殺一個傳統(tǒng)行業(yè)。新的創(chuàng)意、頭腦風暴、新點子蘊含了與過去全然不同的思路、方法,它一經提出、一經形成,就已經具備了深度改變世界的強大力量。所以,可將其稱為“初始質變”。創(chuàng)新之所以值得重視,之所以成為第一動力,就在于具備了初始質變的特征。這一初始性的質變在隨后的創(chuàng)業(yè)歷程中不斷擴張產能,開始新的量變,又為新的、大規(guī)模的質變開辟了前景。創(chuàng)新的初始質變特征,為我們辯證地、具體而微觀地理解質量互變規(guī)律提供了新的視角。
需要說明的,初始質變并不是對量變的否定。因為當一個創(chuàng)意、頭腦風暴、新點子在形成之前,必然有一個量的先行積累過程。科技創(chuàng)新成果一般都是經歷多次“試錯”和實驗探索之后才得以成功的。
(五)發(fā)展資源的新拓展:從“三大資源”到“四大資源”
物質資源的開發(fā)利用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fā)展的基礎。長期以來,人們認為最重要的物質資源是材料、能源。隨著新科技革命的發(fā)展,信息技術突飛猛進,一馬當先,一躍而成為帶頭的先導技術,人類進入信息化時代,信息資源越來越重要。這樣,信息與材料、能源并稱為現代社會發(fā)展的三大資源。隨著經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人類智慧和能力的發(fā)展越來越決定著對材料、能源、信息資源開發(fā)的廣度和深度。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發(fā)生以來,世界經濟復蘇艱難曲折,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各國紛紛把科技創(chuàng)新作為最重要的戰(zhàn)略資源加以優(yōu)先部署,力圖搶占未來發(fā)展的制高點。創(chuàng)新已經成為資源,并且是戰(zhàn)略資源,其戰(zhàn)略意義愈益凸顯。創(chuàng)新是綜合國力較量的新賽場,誰主導創(chuàng)新,誰就能贏得新一輪的發(fā)展優(yōu)勢。我們黨把創(chuàng)新發(fā)展列為五大發(fā)展理念之首,正是高度重視創(chuàng)新資源的表現。這就大大拓展了傳統(tǒng)的“三大資源”觀的內涵,形成了材料、能源、信息、創(chuàng)新的“四大資源”觀。這就啟示我們:要把創(chuàng)新作為最重要的戰(zhàn)略資源,擺在國家發(fā)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讓創(chuàng)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不斷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制度創(chuàng)新、科技創(chuàng)新、文化創(chuàng)新等各方面創(chuàng)新;要讓創(chuàng)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推動大眾創(chuàng)業(yè)、萬眾創(chuàng)新使創(chuàng)新成為全社會的一種價值追求、生活方式、時代潮流。
實施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是堅持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的內在要求和具體體現。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經濟發(fā)展進入新常態(tài),實施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刻不容緩。必須充分發(fā)揮科技創(chuàng)新的驅動引領作用,深入實施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為經濟社會發(fā)展注入源源不絕的新動力。
[1]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三個五年規(guī)劃的建議》的說明[N].人民日報,2015-11-4.
[2]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4-6-10.
[3][10]習近平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 當好改革開放排頭兵創(chuàng)新發(fā)展先行者 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探索新路[N].人民日報,2015-3-6.
[4]王一鳴.使創(chuàng)新成為發(fā)展驅動力[N].人民日報,2015-4-13.
[5]劉延東.深入實施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N].人民日報,2015-11-11.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1.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664.
[8]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4.
[9]江澤民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5.
責任編輯:鐘曉媚
F061.3
A
1673-5706(2015)06-0030-05
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提高黨的科技治理能力研究”(15ADJ006)階段性成果。
2015-11-26
許先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四編研部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