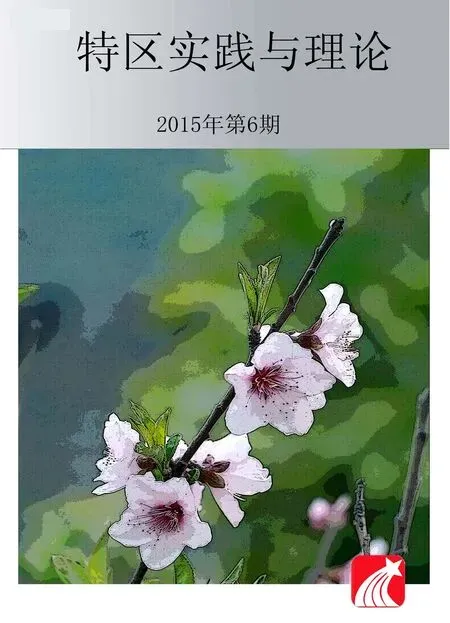論辯證法的本質
趙異
論辯證法的本質
趙異
辯證法的本質是具體的。在革命斗爭環境中,它是批判的、革命的;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條件下,它又是統一的、和諧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踐中,一方面,我們要堅決維持國家統一、社會和諧,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包容社會矛盾在法治范圍內發展、展開、釋放,并促使其得到合法、合理、合情地解決。統籌兼顧這兩個方面,是社會主義條件下辯證法的本質要求。
辯證法;對立;統一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曾科學地揭示了辯證法的本質。即辯證法“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這一論斷為推進國際工人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但是,我們在通常的理解中,往往不自覺地將其理解為可以套用于一切時代、一切環境的萬古不變的公式,把辯證法的本質理解為一切時代都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這種理解既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也不符合馬克思關于辯證法本質的理解。這種理解正是馬克思主義所批判的形而上學的理解、舊哲學的理解。
一、馬克思關于辯證法本質的科學揭示
關于馬克思揭示的辯證法的本質,我們可以用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理論來展開理解。毛澤東指出,任何一個矛盾內部對立雙方在地位上都是不平衡的。在矛盾雙方中必有一方居主導、支配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則居次要、服從地位,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其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著事物的性質,同時,矛盾的次要方面也是必不可少的環節,在一定條件下矛盾的主次方面可以相互轉化。
在馬克思關于辯證法的論述中,也明確肯定了辯證法這一矛盾包含的兩個方面,即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著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2]辯證法是由這兩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共同構成的。并且,辯證法中所包含的矛盾的這兩個方面在地位上是不平衡的。在馬克思生活的資本主義時代,否定的、斗爭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面居于主導地位、支配地位。因此,才有了馬克思關于辯證法的本質是批判的、革命的科學論述。
在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時代,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對立階級,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兩大階級在根本利益上對立,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形象地反映了這一深刻的矛盾。在這個時代,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實踐的、歷史的辯證法在本質上處于批判的和革命的狀態。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大聲疾呼:“實際上和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3]這是資本主義時代的辯證法通過馬克思、恩格斯之口向共產主義者發出的莊嚴號召。
二、辯證法的本質發生歷史性變化
在一戰、二戰的硝煙中,一大批無產階級政黨帶領本國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這些革命黨的政治地位自然地轉變為執政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歷史地位、其所處歷史方位發生了顛覆性逆轉。這些政黨的歷史使命也由打碎舊世界、破壞舊政權,轉變為建設新世界、鞏固新政權。
隨著實踐的深刻發展,實踐的、歷史的辯證法也一同發生了深刻改變。辯證法的本質也由否定的、斗爭的、革命的辯證法轉化為肯定的、合作的、和諧的辯證法。
這種深刻的轉變、轉化、轉折、轉彎很早就已為敏銳的共產黨人所覺察。但是,由于這種轉彎力度大、所處歷史條件復雜等原因而遭遇了許多挫折,走了許多彎路,留下了許多慘痛的教訓。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蘇聯共產黨人首先取得革命政權,成為執政黨。因此,在他們的社會實踐中首先顯現出這種轉折的必要性。因為所謂革命,就是要去破壞兩個對立面所共處的那個統一體即舊社會、舊政權,而革命成功以后,共產黨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新社會,若還要繼續革命,究竟破壞誰的政權、誰的社會?在共產黨建立自己的政權后,黨和人民的主要任務不再是破壞舊社會,而應轉變為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前提下的社會主義建設。
中國共產黨在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后也深刻認識到這一轉折的必然性。這種認識鮮明地體現在黨的八大報告中。在八大報告中,中國共產黨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雖然這一認識在當時還局限于對實踐活動、工作任務的認識、尚未上升到哲學高度。但是,由于當時復雜的國內外環境,加之黨尚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八大報告關于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理論不久便被拋棄了。
三、真理的普遍性與針對性
真理就其從具體經驗中抽象出來、用概念來表達而言,理所當然地具有普遍性。這既是真理、理論的特點也是其優越性。但是,我們對于真理、理論的這一特性切不可作形而上學絕對化的理解。具體說,我們切不可將這種普遍性理解為沒有一定適用范圍的、絕對的、無條件的普遍性。
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明確地指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是社會生活決定意識。也就是說,任何意識、理論、思想、真理都是一定時代、空間的產物,是對這一定時代環境中的社會實踐的反映,都有其針對性。當然,這并不是說,從該時代、空間產生、形成、升華出來的社會意識不再可能對另外的時代、空間的實踐活動具有指導意義。毋庸置疑,這種更大時間、空間的普遍性是完全可能有的。但這又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即另外時代、空間、地域的實踐活動與該理論產生時代和空間中的實踐活動有相似性、甚至相同性。否則,則可以斷定,該理論不具有適用于他時代、他領域的效用、功能。
關于理論適用范圍的有限性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有明確的闡述。如在《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對于他們于1848年提出的這一理論的適用性就曾認真地做了重新審視。“不管最近二十五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共產黨宣言》中發揮的一般基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4]又如,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曾批判了邊沁把英國市儈看成標準的人的觀點。“他幼稚乏味地把現代的市儈,特別是英國的市儈說成是標準的人……他還用這種尺度來評價過去、現在和將來。”[5]
從這一論述中,我們也可以解讀出來這樣一種意義:隨著時代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20多年前得出的某些理論也存在著已不適應實踐活動新的發展的可能性。這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實事求是的態度。
世界上沒有無條件的、適用于一切時空的理論。一切科學理論均有其適用范圍,均是有限的。如西方“三權分立”理論則不適合于中國國情。關于理論的普遍性的有限性問題也是許多哲學家的共識。如康德就曾嚴厲地批判了抽象掉感性經驗的適用于一切內容的空形式即傳統形式邏輯,并稱對這種邏輯的運用為辯證論。康德寫道:“但由于單是知識的形式不論它與邏輯的規律多么一致,也還遠不是以因此就斷定知識的質料上(客觀上)的真理性,所以沒有人敢于單憑邏輯就對于對象作出判斷,或是以任何方式對此有所主張……當我們擁有一種賦予我們一切知識以知性形成的如此表面的技藝時……因而事實上就以這種方式被誤用了。”[6]在此批判的基礎上,康德提出了自己的邏輯學,即先驗邏輯。并根據先驗邏輯,康德推論出了人類只能認識事物的現象而無法認識自在之物本身的著名論斷,即現象與物自體存在原則區別的思想。宣告了人類認識的有限性,也宣告了人類知識只具有有限的普遍性。現代辯證法大師黑格爾也曾痛批過適用于一切對象的傳統形式邏輯。
如何辨別理論的適用范圍或其對某一實踐活動的適用性?根本上是靠實踐活動。如中國共產黨人通過長期的革命實踐、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以及改革開放實踐已充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及其在中國實踐活動中的適用性。
四、列寧、毛澤東關于辯證法本質的論述
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一書中,列寧將辯證法的實質概括為“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7]毛澤東將這一思想概括為辯證法的本質即對立統一法則。列寧又進一步闡述了辯證法的本質:“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對立的斗爭則是絕對的。”[8]毛澤東又將這一思想概括為:“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9]列寧、毛澤東將辯證法的本質概括為對立統一,進而又闡述為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思想,與馬克思關于辯證法本質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這種認識也是由列寧、毛澤東所處的革命斗爭環境所決定的。
如何理解“斗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觀點”,我們認為這里的“無條件”、“絕對”等概念實際意義指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通常意義的無條件性。矛盾雙方的統一必以對立為前提、為條件,而對立也必須以統一為前提、為條件。否則統一不成其為統一,對立不成其為對立,矛盾亦不成其為矛盾,剩下的也只有形而上學的孤立的、靜止的、抽象的、片面的對立、統一了。這顯然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所謂“矛盾的斗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觀點,指的就是,對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統一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的意思。
總之,在革命斗爭的年代,辯證法在其本質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否定的,而在共產黨人已經帶領人民群眾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執掌了國家政權,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時代,應該當說,辯證法在其本質上是肯定的、合作的、和諧的和統一的。
對于辯證法的本質,我們可以描述為:在斗爭實踐中,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它又是合作的、和諧的。這種意義的辯證法本質是具體的本質,這種本質的普遍性是具體的普遍性,而不是形而上學一點論的抽象的普遍性。形而上學的抽象的普遍性主張只有一個永恒不變的本質規定。如孔子的和諧論,它主張無論何種情況,都永遠是統一、和諧居主導、支配地位,只是在此前提下,為適應社會變化了的現實而在細枝末節的策略上做些不傷統一的損益。
五、關于對辯證法的本質全面理解的重要意義
關于辯證的本質的全面理解,不僅要求我們根據社會實踐的實際狀況來決定運用辯證法的哪一方面本質。如在革命斗爭環境中,我們將其主要方面理解為批判的和革命的方面,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條件下,我們又將其主要理解為合作、和諧意義。而更重要的是在當下構建和諧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踐活動中,這一理解還具有更大的現實和理論意義。
首先,鞏固社會主義政權是辯證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本質的必然要求。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和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項基本制度的建立,統一、和諧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旋律。但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又是不斷發展的。因此,它又要求我們必須不斷采取措施、行動來維護、鞏固這一統一、和諧、團結的局面。
其次,認真對待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各種矛盾、斗爭、對立、批判也同樣是辯證法的本質的要求。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階級斗爭、敵我矛盾這樣對抗性質的斗爭、矛盾已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它僅是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當然也需要我們保持警惕。社會中大量存在的是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對于這類矛盾,一方面,我們應充分地肯定、承認它們存在的客觀必然性,另一方面又要十分認真地對待它,科學合理地解決它。當前,我國社會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社會矛盾,諸如勞資矛盾、干群矛盾、生態問題等,是社會發展到該階段必然出現、無法回避的客觀矛盾。它們也是社會主義社會實踐在今天的組成部分。對這類矛盾既不應嫌棄,也不能恐懼,更不能置之不問,而是應當充分肯定、認真對待、科學解決。但是,對待這類矛盾,有些場合我們沒能正確處理。如有些情況下,一些同志害怕矛盾、害怕問題,或者將這些矛盾、斗爭遮掩起來,或者用行政命令強行解決;有的時候,我們無視這些矛盾,視若惘聞,壓制這些矛盾,使這些矛盾長期處于潛伏狀態,這種做法不利于矛盾的解決、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對立、斗爭、否定方面同統一、合作、和諧的方面一道共同構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辯證法,它們都是辯證法不可或缺的環節。并且,在當下社會實踐中,處理好矛盾的次要方面,即對立、斗爭、否定的方面,將會十分有力地促進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統一、合作、和諧方面的發展。當然,維護好社會和諧、國家統一也是解決好各類社會矛盾的根本前提。
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不絕。大一統是中華文明的內在基本價值取向。這一傳統價值觀至今仍深深植根于每一個中國人心靈的深處。這一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正與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要求的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的任務深刻吻合。但是,我國傳統文明又植根于農耕活動,它又有自己的天然不足,即過于強調統一,而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差異、對立、斗爭一面。這一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常常表現為壓制差異、對立、批判、矛盾。這種做法,雖然在一定時期內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但長期來看,則是積蓄了矛盾、積蓄了社會不滿情緒,將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安全隱患。忽視差異、斗爭、對立做法更不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當下社會要求,是我們所應當注意批判的問題。這也應是當前解放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按照辯證法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本質要求,在今天的社會實踐中,一方面強化統一意識,樹立誰破壞統一、和諧,誰就將會被人人得而誅之的意識;在此前提下,允許社會矛盾斗爭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一定程度地展開、發展、釋放,甚至“激化”,并在政府搭建的平臺上科學、合情、合理地解決。害怕、掩蓋矛盾斗爭是沒有出路的,而且在強大鞏固的社會主義政權下,也沒有必要這樣做。只是我們要注意防止這種矛盾斗爭轉化為能從根本上影響社會和諧的方面,即防止矛盾的次要方面轉化為矛盾的主要方面,以致改變現階段辯證法的性質。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22.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7.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5]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69.
[6]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7.
[7]列寧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05.
[8][9]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3;306.
責任編輯:李 彥
B024
A
1673-5706(2015)06-0120-04
2015-10-13
趙異,吉林省延邊州委黨校哲學教研室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