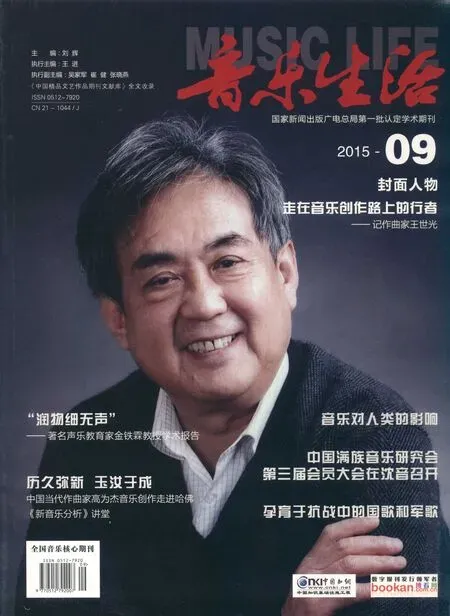宏觀視域下對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狀態的冷思考
文/宋 穎
宏觀視域下對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狀態的冷思考
文/宋 穎
內容提要
在全新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我國對于西方音樂史的研究狀態中所存在的問題,值得我們用一種更加理性和冷靜的態度去思考、對待和處理。民國時期我國學術界對于西方音樂史的研究態度、研究方式、研究理念,也就是對于西方音樂史的整體研究狀態時至今日仍然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對于外來文化的盲目抵制和對于自身文化的盲目自信和熱情也是一種極度不自信的具體體現,而理性地、冷靜地面對外來文化,也是民族文化自信和成熟的一種鮮明體現。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領域所出現的所謂“中國視野”,與曾經偏激、極端的觀點、思維、理念和方式方法確有幾分神似,如不能理性和冷靜地看待學術研究理念和狀態,又何談能夠對我國西方音樂史的研究起到何種益處。冷靜的態度和理念才是真正地從民族的角度出發、以民族利益為根本,才是真正的民族自信,才能真正為我國民族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做出貢獻。
西方音樂史 理性 冷靜 極端 偏激
同我國很多現代西方人文學科一樣,西方音樂史作為一門獨立的藝術類人文學科開始在我國出現和發展也是從上個世紀之初的“新文化運動”開始的。從此以后,西方音樂史在百余年的東西方文化交流與融合的過程中對我國現代音樂學科、音樂藝術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影響和極為重要的作用。當前,在我國的各大高等藝術院校和研究機構中,西方音樂史始終是重要的支柱性專業基礎學科之一,可以說,當前在我國學術界對于西方音樂史對我國音樂發展的重要作用、價值和意義已經形成了一個基本的共識,但同樣,縱觀西方音樂史在我國發展的百年歷程,我國在對于西方音樂史的研究理念、研究態度、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等諸多層面,也就是對于西方音樂史研究的整體狀態上卻始沒有形成一個共識,時至今日,在全新的世界文化潮流中,在全新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我國對于西方音樂史的研究狀態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值得我們用一種更加理性和冷靜的態度去思考、對待和處理。
1.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狀態演變歷程
迄今為止,我國對于西方音樂史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三個主要的階段,而在這三個主要的階段,我國對西方音樂史的研究狀態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和區別。
1.120世紀初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
這一時期是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起源和發展時期。蕭友梅與王光祈堪稱是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兩位開山鼻祖,對我國現代音樂的創立、發展和研究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價值和意義。這兩位我國的現代音樂先驅有著很多的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首先都具有極為深厚的傳統文化基礎與素養,同時又都成長和生活在我國巨大歷史變革時期,有著強烈的愛國之情,同時又都具有歐洲留學的經歷,對于西方音樂都有著極深的造詣,凡此種種都促使著蕭友梅和王光祈,包括當時和此后的所有學貫中西的音樂學者們能夠用一種熱情的、迫切的,但卻以更加理性和冷靜的態度去對待西方音樂史學科、處理西方音樂史學科、研究音樂史學科。這一時期,理性、冷靜的態度也成為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兩個最為鮮明的特征和關鍵詞,這種理性和冷靜在于這一時期以蕭友梅和王光祈為代表的我國民國時期的音樂學者們能夠真正意識到和承認本民族音樂研究體系、理念、理論和方式上的不足和需要提升之處,能夠真正運用歐洲文化中的理性思維、理性研究體系、研究方式、研究視角、研究視域去對待和研究西方音樂史,再加上民國時期音樂學者們深厚的傳統文化基礎與素養,使得這一時期的西方音樂史文獻在翻譯和注述水平和品質上達到了頂峰。時至今日,僅在此一項上就始終沒有超越我們的先驅們。而民國時期我國學術界對于西方音樂史的研究態度、研究方式、研究理念,也就是對于西方音樂史的整體研究狀態時至今日仍然是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的。
1.2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一時期是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第二個階段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由于特殊的歷史因素、政治因素及意識形態因素,我國在此后的幾十年間,不僅僅是在西方音樂史研究領域,在其他的藝術學科及人文學科領域也皆是如此,基本上斷絕了與西方(也就是歐洲及美國)的學術交流與溝通,音樂史領域更是如此。這時我國在西方音樂史領域與外部世界的主要,或者說唯一溝通和交流的對象便是蘇聯,但從客觀事實的角度上來講,就西方音樂史領域來說,蘇聯,或者說俄羅斯音樂和俄羅斯史學界對于西方音樂史的研究都算不上是世界音樂史研究的主流,更談不上先進,因此,僅就研究對象、研究文獻資料的前沿性層面上,當時的我國就已經遠遠落后于世界音樂史研究的主流。而隨著著名的“中蘇交惡”開始,對于當時的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來說,唯一的,僅存的一個對外交流的通道也被堵塞了,我國的西方音樂史研究也很快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完全的“閉門造車”的狀態之中。同時,也像我國其他很多音樂學科一樣,我國音樂學術界對于西方音樂史的研究也出現了一種消極的、偏激的、不理性的、極端的抵制情緒和狀態,就像當時我國聲樂藝術界的那場著名的“土洋之爭”一樣,而從某種角度上來講,這種不良的情緒、理念,或者說狀態在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領域反映得更加強烈,對于學術研究的消極作用和損害也更大。
這一時期,我國對于西方音樂史的研究理念、研究態度、研究方式,也就是整體的研究狀態上都呈現一種極度的不冷靜、不理性的鮮明特征。這種特征,或者說狀態具體體現在,首先是一種極端排斥的態度,認為西方音樂歷史如同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的人文理念一樣,都屬于“腐朽的資本主義”和“腐朽的資產階級”,是有害的,是必須要摒棄和抵制的,這種觀念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體現得尤為明顯。其次是即使當時我國音樂學術界的很多學者雖然并不認為應該完全摒棄和抵制西方音樂史的研究,但在具體的研究理念、研究方式、研究態度上卻對于以往的,也就是“民國時期”的“西方視角”、“理性思維”、“科學態度”、“科學方式”予以全盤否定,認為西方音樂史研究也應該像當時的民族聲樂藝術研究一樣完全回歸民族與傳統,完全運用傳統民族音樂的音樂研究理念、研究方式、審美方式去對待、處理、研究、分析、解構、解釋、解讀西方音樂和西方音樂史料,而此后的無數事實和例證無數次證明,這種研究理念、研究態度和研究的狀態比當時我國聲樂藝術研究界的“土洋之爭”更加荒謬,更加無益于我國西方音樂史的研究工作,同樣對于我國現代音樂的發展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這種態度的錯誤,或者說荒謬之處在于,不冷靜、非理性:沒有意識到西方音樂史研究的研究對象本身并不像聲樂藝術一樣,美聲聲樂藝術和民族聲樂藝術雖然是兩種區別鮮明的聲樂藝術種類,但其二者畢竟本質上都屬于聲樂藝術的范疇,存在著一定的共同性與共榮性,所以我國民族聲樂“土洋之爭”時雖然完全摒棄和抵制歐洲的美聲聲樂藝術肯定是錯誤和不合理的,但其中對于傳統民族民間聲樂藝術的借鑒和吸收也具有一定的正確性和積極性因素,而西方音樂史則指一門完全獨立的史學學科,僅從音樂專業的層面上來講,無論是作曲技術、曲式、和聲、樂理、配器、音樂記譜法等等諸多層面上與我國傳統音樂基本沒有共同性可言,也就更談不上任何可比性,因此,無論是從宏觀的文化視角與領域、審美視角與領域,抑或是音樂專業層面的視角與領域用傳統民族音樂的視角、視域、理念和方式去研究西方音樂史、解讀西方音樂史、解釋西方音樂史都是完全行不通的。這種音樂史研究的態度、理念和整體的狀態也是極為不理性和不冷靜的,而其中更多的是在特殊歷史時期所呈現出的對于民族文化和民族藝術的盲目自信和不健康的熱情,而這種學術研究的狀態對于真正的學術研究和我國現代音樂的發展來講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可言。而從另一個層面上來看,從深層次的文化心理和狀態上來看,對于外來文化的盲目抵制和對于自身文化的盲目自信和熱情也是一種極度不自信的具體體現,而理性地、冷靜地面對外來文化,也是民族文化自信和成熟的一種鮮明體現。
1.3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結束至21世紀初
這一時期是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第三個大的階段。這一時期,隨著“文革”的結束,我國再次開啟了沉重的國門,重新開始與世界先進文化、世界先進科學技術、世界先進社會生活模式、世界先進藝術潮流接觸、溝通和交流。我國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各項事業也都回歸到正確的軌道之上,開始迅速恢復和發展。不僅僅是從西方音樂史研究的角度,也包括整體的文化學術研究,以及社會事業建設的各個層面上也皆為如此,當極度的非理性狀態結束以后,取而代之的必然是理性的回歸。與其他任何一種人文藝術學科一樣,我國的西方音樂史研究也迅速地重新走上正軌,并取得了迅速的復蘇和發展。于潤洋通過自身諸多專著成功地將音樂美學融入了音樂史學研究領域;周凱模則將音樂人類學與音樂史學研究成功融合;楊燕迪在音樂史研究科學方法和方式的確立、豐富和發展上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以蔡良玉、高世杰、孫國忠、姚亞平、王哺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我國現代音樂學者和音樂史學家們對我國當代西方音樂史的研究、發展和進步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使得我國的西方音樂史研究呈現出一種“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和狀態,這對于我國音樂史學和整體的現代音樂發展無疑是正確的,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價值和意義的。而這一時期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復蘇和繁榮從根本上來講同時也正是源于社會開放和變革所帶來的理性的回歸,理性的回歸讓我們在對待學術研究的態度上能夠摒棄以往非理性的、狂熱和不健康的、毫無積極作用、價值和意義的民族觀念,在對待西方音樂史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能夠重新站在西方的理性思維和文化視角之上去對待西方音樂、研究西方音樂、分析西方音樂、解釋西方音樂,從而真正地掌握西方音樂,使西方音樂能夠真正對于我國現代音樂藝術的發展起到真正積極的促進作用、價值和意義。
但在近期,在我國的西方音樂史研究領域和學術界一種觀點甚囂塵上,那就是要用一種所謂的“中國視野”的角度,或者說理念、方式去研究西方音樂史。這不得不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和思考。
2.回顧帶來的思考與反思
正如前文已經有所提及的,縱觀我國西方音樂史的研究歷程,每段歷程都會因為不同的歷史背景、社會背景文化以及社會意識形態類型等諸多的因素而呈現出區別鮮明的狀態,而不同階段我國對于西方音樂史完全不同的研究理念、研究方式、研究狀態也直接導致研究結果的完全不同。在民國時期,我們正確的學術研究狀態使得當時的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民國時期的音樂先驅們用自己理性的、冷靜的、科學的學術研究態度和辛勤的研究工作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西方音樂史料,僅就翻譯和注釋質量而言,我們今人仍舊鮮有能夠超越前人者。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的西方音樂史研究之所以陷入完全停滯的狀態,甚至出現違反最基本學術研究科學理念和規律的盲目民族自信,主張生搬硬套地要用傳統民族音樂理念去對待、研究和解釋西方音樂史,這無疑是荒謬的,同時也是必然不能成功的,對我國現代音樂藝術事業的發展也不可能起到任何積極的作用,反而會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害。凡此種種,都是值得我們銘記的經驗,甚至應該說是一種教訓。歷史告訴我們,無論是對待西方音樂史研究,還是任何一種人文學科研究、現代科學研究,乃至任何一項社會事業,大至國家建設,小至衣食住行,理性的、冷靜的態度都是最基本的前提。而反觀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領域所出現的所謂“中國視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至“文革”結束這一階段的偏激、極端的觀點、思維、理念和方式方法確有幾分神似,如不能理性和冷靜地分析學術研究理念和狀態,又何談能夠對我國西方音樂史的研究具有何種益處。
總而言之,歷史和無數的事例無數次證明,對待任何一種人文學科或者藝術學科,只有采用一種理性和冷靜的態度和理念才能夠真正取得成功,同時冷靜的理性告訴我們,在西方音樂史的研究工作中我們必須要站在西方文化的視角,運用西方的理性思維和科學研究方法才能夠使我們真正理解、掌握運用西方音樂,才能夠真正對我國現代音樂的發展起到真正的促進作用,這才是真正地從民族的角度出發、以民族利益為根本,才是真正的民族自信,才能真正為我國民族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做出貢獻。
[1] 馮長春.黃自音樂美學思想的基本觀點及其本質探微[J].中國音樂學,2000
[2] 劉再生.西方音樂史[M].北京: 人民音樂出版社,1988
[3] 劉國杰.一本謬誤百出放膽抄襲的教材——評《中國民族音樂欣賞》[J].中國音樂,1992
[4] 錢仁康.中國音樂欣賞叢書-總序[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1
[5] 尚家驤.歐洲聲樂發展史[M].上海: 華樂出版社, 2003
(責任編輯 霍閩)
宋穎(1979—)女,沈陽音樂學院藝術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