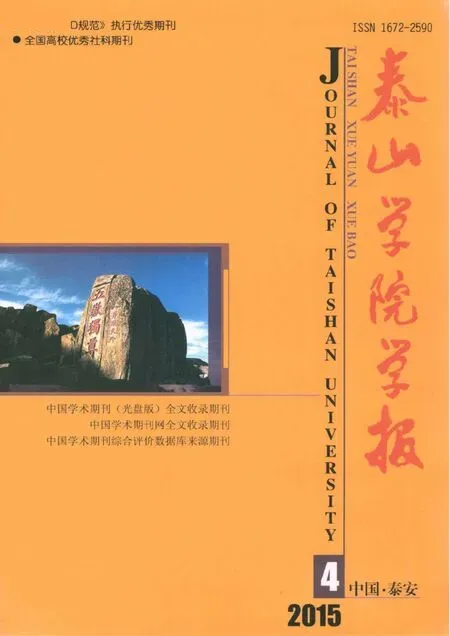2014年魯迅作品研究中的幾個亮點
崔云偉,魏 麗
(1.山東藝術學院藝術管理學院;2.山東藝術學院戲曲學院,山東濟南 250014)
?
2014年魯迅作品研究中的幾個亮點
崔云偉1,魏 麗2
(1.山東藝術學院藝術管理學院;2.山東藝術學院戲曲學院,山東濟南 250014)
2014年魯迅作品研究呈現出異彩紛呈、創意不斷的局面。吳義勤、周南、張克、張全之、楊義等皆對魯迅小說發表了極為精彩的看法。錢理群的《野草》研究,楊義、宋劍華、王國杰的《朝花夕拾》研究,汪衛東的早期文言論文研究,皆可稱得上別具一格。雜文研究中,魏建、劉春勇、宋劍華的闡釋不乏亮點。邵寧寧的魯迅詩歌研究,韓大強的魯迅日記研究,譚桂林、曾鋒的魯迅作品整體研究,皆有其新穎獨到之處。
魯迅作品;研究;述評
在歷年來的魯迅研究中,有關魯迅作品的研究總是異彩紛呈、創意不斷。2014年度的魯迅研究亦不例外。筆者在充分利用網絡資源的基礎上,特意從中概括、梳理出有關魯迅作品研究的幾個亮點。現述評如下,以與學界同仁共同探討。
一、魯迅小說研究
與《吶喊》研究有關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狂人日記》、《阿Q正傳》、《故鄉》。
現代進入中國,意味著“人”的發現,同時也意味著“吃人”的被發現。“吃人”由一個經驗性歷史事實而成為一個文化政治問題,由是成為中國現代性的重要表征。吳義勤、王金勝[1]認為,魯迅在《狂人日記》中首先將“吃人”的觀念化表達熔鑄為一個重要的文學命題和一個經典的文學意象。這個命題和意象同時是對中國歷史與文化之本質認知的隱喻性表達。莫言《酒國》延續并轉換了這一“吃人”敘事傳統。如果說《狂人日記》是一則反抗者的寓言,《酒國》則可視為沉淪者的見證。《狂人日記》呈露出魯迅孤絕的現代性生命體驗,《酒國》卻將諸種狂歡性因素雜糅一處,熔鑄成一個狂歡的世界。《狂人日記》在主旨、意象營構、人物塑造及話語風格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影響了《酒國》。但是,作為傳達某種當代文化隱喻的小說,《酒國》是莫言在特定的現實政治和市場經濟語境中,循著自身創作內在的思想與藝術脈絡,借助頗具民間色彩的先鋒性敘述所完成的個性化美學創制,小說對“吃人”的再敘述也由此成為轉型期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寓言和主體命運的見證。
在《狂人日記》“吃人”意象生成中,有外來文化元素與中國文化元素影響,但學界百年來囿于魯迅周作人的述說,一直忽略了對前者的探究。2012年李冬木提出:《狂人日記》“吃人”意象的生成,“是從日本明治時代‘食人’言說當中獲得的一個母題”,日本學者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將明治時代文明開化背景下的“支那”“食人”言說引進國民性話語,與“吃人”意象生成有著決定性關聯。此說引起研究界強烈反應。李有智、王彬彬、祁曉明皆發表文章,對之提出了強烈質疑。本年度,周南[2]再次發表文章,對于上述文章再次進行了細致辨析。他認為,魯迅獲取吃人信息來源于中國,主要得自古書記載,這根本無需爭論。李冬木將《狂人日記》研究納入日本明治時代的“支那食人”言說,以及由此切入國民性研究話語框架,以后者作為《狂人日記》誕生的外國現代思想文化背景,這是“狂人學史”實質性研究推進。在《狂人日記》所包含的象征性真實的層面上,魯迅對于“吃人”意象的發現,已經超出了進化論人類學,進入了對于中國文化的批判,而這則是日本的人類學和國民性研究都無法提供可資借鑒與模仿的東西的。因而,李冬木的結論:《狂人日記》從主題到形式皆誕生于借鑒與模仿,引起魯研界的爭論,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此次關于“吃人”意象生成的爭鳴探討,推動著《狂人日記》和中國魯迅研究突破一國史觀走向多國史觀,并重視對魯迅創作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思想基礎研究,這對于切當理解《狂人日記》跨文化跨學科視野下的思想藝術獨創是大有益處的。
“游民與越文化”是《阿Q正傳》研究中的一個獨特視角。張克[3]認為,從周氏兄弟對紹興風俗中的“流氓風氣的蔓延”的記憶來看,阿Q的行止做派實則根植于“游民”氣氛濃郁的晚清越地風俗。阿Q作為一個“游手之徒”,其精神世界是一個文化潰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真正起作用的是人的動物本能、是弱肉強食的力量對抗,一切原有的文化符號都在潰敗中走樣變形,失卻其原本的嚴肅性。阿Q生命的“微塵似的迸散”可以說正是越文化本身潰敗的象征。小說最具刻骨銘心之處在于對阿Q這樣一個失去任何文化庇護的卑微的游民難以掙脫“對他的整個存在懷著恐懼”這一根本生存處境的揭示。通觀“游民與越文化”這一命題,已是一個測量當下學院知識分子與底層民眾之間精神距離的現實性命題,其中的幽暗與真相,對諸多學院知識分子來說都會是一個沉重的拷問,但這無疑是真正來自魯迅特有的精神力量的挑戰。
藤井省三《魯迅<故鄉>閱讀史》在中國出版以來,學界對之一直好評如潮。本年度張全之[4]則一反眾議,認為該書有著十分重要的缺憾,概括起來即:局部分析十分精彩,但整體構架存在瑕疵。他認為,為什么是《故鄉》的閱讀史,而不是其他作品?《故鄉》的特殊性表現在哪里?《故鄉》被重構、被改寫,與其他作品有什么不同?這些疑問在該書中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這就暴露出該書在構思和寫作中的巨大漏洞。藤井試圖通過《故鄉》這一個案的考察,尋找現代中國文學空間的演化軌跡及其對讀者閱讀產生的引導或制約作用。但是,相對于“現代中國的文學空間”這一龐大的概念而言,《故鄉》這一文本的支撐力顯然是不夠的。該書借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的理論框架,形成了一個“兩面”支撐“一點”的論述結構。但是這一結構看似嚴謹,實際處于分離狀態。“兩面”無法支撐“一點”,結果就使“國民國家想象”這一核心點處于懸置狀態。
楊義則對《吶喊》、《彷徨》、《故事新編》作了精彩的生命解讀[5]。其《魯迅<彷徨>的生命解讀》認為,《彷徨》一以貫之的精神脈絡是反思,反思乃是在彷徨中的思想深化。《祝福》反思啟蒙運動,已是“后五四”了,但鄉鎮上的士紳罵的還是康有為的新黨,似乎五四的啟蒙尚不及康梁的維新更觸及基層社會。《在酒樓上》反思同代知識者,它們何以陷入“蠅子怪圈”,不能飛得更高更遠?《長明燈》反思“救救孩子”,為何這里的孩子們也和《孤獨者》中犯了同一個“癥候”——赤膊小孩將葦子向瘋子一指,清脆地發出“吧!”的槍聲。《孤獨者》反思進化論和易卜生主義,既然說“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獨的人”,為何這里的孤獨卻連結著人生價值的放棄,連結著送斂和死亡。《傷逝》反思易卜生的“娜拉走后怎樣”,涓生如何走出人生新路支撐新式家庭,子君如何不再重回舊家庭的嚴威和黑暗中,直至走到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這些反思,都推動著紙面上的抗爭和改革,走向實踐的抗爭和改革,在魯迅彷徨的精神世界中,令人隱隱然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
其《<故事新編>的生命解讀》認為,《故事新編》稱得上是現代小說史上的一部奇書。奇就奇在魯迅的書袋雖然是鼓鼓的,卻無意于掉書袋,而是駕輕就熟地出入古今,把現代社會的諸多官場丑態、文界乖謬、民間陋習和摻和著奴性及流氓性的國民心理,糅合在神話、傳說、歷史的著名故事之間。這就有如女媧拔起一株從山上長到天邊的紫藤,攪動地上的泥水,濺出一班能笑能哭的生靈,即魯迅所謂“并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是也。二者的糅合與攪拌,構成了復調敘事,構成了民俗性的狂歡。古人和今人打照面,互相消解對方的神圣的靈光或裝模作樣的擺譜,令人看見他們的不尷不尬而竊竊發笑。小說自身也由此超越純文學傳統而向雜文開放,小說與雜文雜糅,兼具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的功能,開創了一種古今雜糅的“雜小說”新文體。
二、《野草》研究
錢理群在為汪衛東《探尋“詩心”:<野草>整體研究》[6]所作的序[7]中,探討了一個學術研究中的當代性問題,即:當代中國文學距離《野草》已經達到的高度還有多遠?我們能不能借《野草》反思自己,進而尋找擺脫當下中國文學困境的新途徑?錢理群認為,在中國當代文學經歷過“兩次絕望”之后,我們至今仍未走出絕望,更不用說如魯迅那樣走向新的生命與文學的高地。原因全在我們自己。我們很少象魯迅那樣把外在的困境內轉為自我生命的追問:我們既無反省的自覺,更無反思的勇氣與能力。這樣,我們就失去了一次魯迅式的逼近生命本體、逼近文學本體的歷史機遇。我們無法收獲豐富的痛苦,只獲得了廉價的名利、膚淺的自我滿足或怨天尤人。在這樣的生命狀態下的寫作,就根本不會有魯迅那樣的語言突破、試驗的冒險,也只能收獲平庸。于是,當代中國文學就在作家主體的生命深度、高度和力度和語言試驗的自覺這兩個方面和魯迅曾經達到的高地拉開了距離;而“生命”和“語言”正是文學之為文學的根本: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許多當代文學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文學性。這就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困境所在。
2008年,汪衛東撰文《<野草>與佛教》[8],論證了魯迅與佛陀在更深層次上的精神相遇。本年度,崔云偉[9]從此出發進一步論證了魯迅與佛陀的同與不同。他認為,魯迅在《野草》中最終并沒有通達佛陀所說的悟的彼岸,而是仍然站在了堅實的大地上,這是魯迅與佛陀的最大不同。如果說佛陀的超越是對于涅槃寂靜的執意追求,我們可以稱之為“向上超越”,那么,像魯迅這種執意活在人間,在無物之陣中一直戰斗到死的超越,則可以稱之為“向下超越”。雖則魯迅與佛陀在最終追求目標和超越模式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在其他三個圣諦,即“苦諦”、“集諦”與“道諦”上卻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相似乃至相通。從魯迅與佛陀的相同之處,我們看到的是魯迅與佛陀的精神相遇,而從其不同之處,我們看到的則是魯迅與佛陀各自的偉大。
對《野草》作出精彩解讀的還有李培艷和張娟。李培艷[10]認為,魯迅《野草》是清理自身與外部世界關系,尋求自我創生過程的產物。魯迅通過失語與死亡的臨界點打開了“自我”與“世界”的關系,并以象征化的方式,完成了內在世界的客觀化,進而使其自我意識的展開成為可能,死亡的張力隨之亦被化解。張娟[11]則認為,反觀《野草》寫作,和魯迅的北京生活體驗息息相關。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可以看到魯迅作為“都市漫游者”對城市灰暗面的思考,對市民社會世態人情的揭露和城市發展中物質至上的詼諧批判,另一部分偏重靈魂表達的作品則以現代性的思想、西方式的表現方式體現出城市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三、《朝花夕拾》研究
楊義[12]認為,“朝花”是魯迅的童年經驗,童年經驗連結著生命的原始,刺激過天真無邪的好奇心,左右著終生的意象選擇。包括老祖母講的貓是老虎師父的故事,長媽媽渲染的女陰能使敵軍大炮變啞,《山海經》刺激神話興趣,百草園窺探自然生命,無常散播著鬼世界的詼諧,父親的病埋下了中醫現代化的質疑,《天演論》建構了現代思想的新維度,辛亥畸人范愛農引發了對革命變味的反思。這些早年經驗,都提供了魯迅思想母題的最初萌蘗。魯迅在“后五四”,拾起了“前五四”的思想母題之花蕊,把玩思量,與中年時的人事藤蔓糾結翻滾,蹦出了許多“嘎嘎”亂叫的生命。《朝花夕拾》遂成了現代中國最有生命趣味的回憶散文。
宋劍華[13]則認為,《朝花夕拾》中的“舊事重提”隱喻性地表達了魯迅精神還鄉的一種姿態。“百草園”是一個“鄉思”意象的藝術符號,魯迅于此獲得了個人成長的經驗。魯迅從“長媽媽”那里感受到慈祥的母愛,從“藤野先生”那里感受到父愛的溫暖,從“范愛農”那里體悟到做人的道理,這一切都拉近了他與“故鄉”的親密距離。在如何對待民俗文化方面,魯迅也已不再是單一性地給予否定,而是更趨于一種理性思辨的科學態度。這說明魯迅已開始告別文化虛無主義的歷史觀,進而在精神返鄉的過程中呈現出他文化尋根的心靈軌跡。
2013年,張顯鳳撰文[14]從魯迅在《朝花夕拾》中惟獨缺少了對于母親的回憶出發,認為“母親”的缺席直接導致了魯迅將戀母情感不自覺地移向了衍太太,從而使其具備了代理母親與準情人的雙重特征。本年度王國杰[15]認為,綜合《朝花夕拾》中的諸多事例,不難看出魯迅對衍太太并沒有好印象。大概是魯迅回憶中運用的雙重視角:童年視角和成人視角,擾亂了張顯鳳的判斷。魯迅既已熟知衍太太的為人,又怎么可能對她產生情人心理。魯迅外出求學亦并非因為什么“俄狄浦斯式的移情及其幻滅”,確是由于家境困頓至極,加之受到謠言攻擊,傷了自尊。母親形象亦并非如張顯鳳所說是缺席的,而是一直存在,隱藏在細節處或故事背后。她對少年魯迅的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魯迅在小說中也沒有表達怨恨母親的情緒。王國杰繼而對張文所顯示的文風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當前學術界仍然存在著一種對于西方新潮理論的盲目跟從和胡亂套用傾向,張文即是其中的一個典型。這種浮躁的學術風氣,不利于學術研究的健康發展。學術研究理當尊重史料,并以史料為基礎,小心求證,讓史料與文本相互印證學術觀點。
四、早期文言論文研究
2008年,汪衛東、張鑫撰文[16]發現《文化偏至論》中有關施蒂納的材源,是一篇發表于日本明治時期雜志《日本人》上的署名蚊學士的長文《論無政府主義》。本年度,兩位作者繼續撰文[17],在材源考證的基礎上,圍繞無政府主義問題,進一步深入考察魯迅所受材源文章的影響。他們指出,蚊文對魯迅的啟發和影響,有兩個方面值得注意:(一)施蒂納在蚊學士之文中,是作為無政府主義之一脈絡——哲學上的個人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來介紹的,強調的是施蒂納基于個人而反對任何束縛的無政府主義哲學。魯迅對施蒂納的介紹,是把施蒂納放在“重個人”的思想譜系中來加以介紹的,視其為十九世紀末“重個人”思想的首要代表,描述了一個施蒂納—叔本華—克爾凱郭爾—易卜生—尼采的“極端個人主義”譜系。(二)尤可注意者,是魯迅和蚊文對暴力活動的態度。蚊文對實行無政府主義的暴力活動頗不以為然,認為那些主張暗殺、提倡暴力的無政府主義者,堅持以暴亂殺害為義務,令人感到恐懼。這與魯迅對暴力活動的曖昧,與當時的革命語境并不一致,倒有頗多契合。無政府主義和暴力主義言說,都是當時的主流話語,魯迅避而不談,體現了其卓而不群的個性和抱負。蚊文對于魯迅的影響,由此亦可見一斑。
五、雜文研究
《上海文藝之一瞥》是魯迅的一次重要演講。80多年過去了,學界甚至連這次演講的時間、地點、版本等最基本的問題都沒有搞清楚。魏建、周文[18]認為,關于學界所形成的一則共識,即:“二心集版”是魯迅在“文藝新聞版”的基礎上“略加修改”而成的版本的說法,其實是不正確的。這兩個版本的差別在于“作者”的不同。關于學界所形成的另一則共識,即:“二心集版”的演講時間“八月十二日”是魯迅記錯了的說法,其實也是站不腳的。7月20日和8月12日這兩個演講時間的存在,本來就包含著魯迅以同一題目分別做了兩次演講的可能。再從演講的不同地點即“暑期學校”和“社會科學研究會”的相關資料來看,兩次演講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上海文藝之一瞥》除了上述兩個版本之外,還有一個“郭譯日文版”。通過細致比對這三個版本,論者發現,魯迅對《上海文藝之一瞥》的修改距離演講并未相隔很長的時間,因此,斷言魯迅誤記演講日期甚或地點,要冒很大的風險。同時,從“郭譯日文版”與“二心集版”的差別亦可以看出,魯迅修改后的定稿不是對其演講內容的精準再現,從某種程度上說,應是更深一層的再創作。論者繼而對“文藝新聞版”等演講筆錄稿進行了正名,指出從還原演講歷史現場、體驗魯迅演講原味的角度來說,“文藝新聞版”要優于“二心集版”。并認為,對魯迅演講的研究應充分利用那些最初發表的他人之記錄稿,而不能唯魯迅修訂稿是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走近真實而豐富的歷史現場。
在劉春勇看來,魯迅作為世界級文學大師的意義,不在《吶喊》這樣的純文學創作,而在豐富的雜文寫作。那么,魯迅的雜文是怎樣發生的?劉春勇[19]認為,“現代”可以說是一個虛無主義盛行的時代。身處其中的魯迅雖然留日時期懷抱理想主義,但回國后卻認同“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并做絕望的反抗,這都在虛無主義的范疇當中,但通過寫作《野草》魯迅逐漸揚棄了“虛無”而向“虛妄世界像”挺進。對“虛妄世界像”的體認使得魯迅在1925年前后逐漸放棄了“主題性”極強的純文學創作,而選擇了一種文學體制外的、基于“有余裕的”寫作觀念之上的雜文寫作。這就是魯迅的“留白”美學觀。留白的寫作不是剪去枝節,只留與主題的寫作,而是相反,留白是一種散漫性的、將一切“擺脫”、“給自己輕松一下”的寫作。并且,魯迅的這種“留白”美學觀還同時成為其生活的倫理學。
宋劍華、王蘋[20]則通過對于魯迅早期雜文的研究發現了魯迅早期思想的復雜性與矛盾性。他們認為,“聽將令”使魯迅早期雜文呈現出一種激情主義的戰斗姿態,同時也構筑起魯迅積極參與中國現代思想啟蒙的正面形象。透過魯迅與“正人君子”的罵戰,可以發現東、西洋留學生,在對待中國社會變革的認識方面,產生了自五四結盟以來,最為嚴重的思想分歧。但毫無疑問,他們都是中國現代社會當之無愧的知識精英。魯迅早期雜文的創作,還展現出一個神情黯然的背影形象。魯迅對于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原本就不抱有什么信心。他認為“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這說明重功用而講實效的儒家思想,恰恰正是魯迅思想中“毒氣”與“鬼氣”的精神資源。
1993年,李歐梵在其《“批評空間”的開創》[1]中,認為魯迅雜文妨礙了人們的“言論自由”。對此,袁良駿[21]著意指出,在20世紀30年代黑暗中國的“白色恐怖”下,談何“自由”,又談何拓展“公共空間”。即使象魯迅這樣的著名作家,也根本沒有什么言論自由。李歐梵不向蔣介石要“公共空間”“自由天地”,卻向魯迅大要特要,似乎中國當時沒有“自由天地”“公共空間”,都是魯迅之罪。這樣的邏輯不能成立。即使就事論事,李歐梵的言論也根本無法成立。沒有“自由、平等、博愛”,奢談什么“公共空間”?廣大中國勞苦大眾呻吟在死亡線上,有什么“公共空間”?至于責怪魯迅有什么“兩極分化的心態”,也根本不能成立。莫非蔣介石們的亂殺亂捕不是“兩極分化的心態”,倒是反對他們亂捕亂殺的魯迅卻成了什么“兩極分化的心態”嗎?
對魯迅雜文作出精彩解讀的還有李怡、張鐵榮[21]等。
六、詩歌研究
《無題·洞庭木落楚天高》是魯迅舊詩名篇,數十年來有關該詩詩意的解說,堪稱層出不窮。邵寧寧[22]認為,究其根由,則多因闡釋者誤將詩中“眉黛”一詞硬解為“女性”而起。實際上,“眉黛”一詞在該詩中喻指“遠山”,更進一步說,是指古詩文中常用來與洞庭對舉的“九嶷”。關于該詞種種捕風捉影式的解說,不但使該詩原有的屈騷情致變得晦蔽,而且使其深刻的現實憂憤變得淺薄、庸俗。類似的錯誤,同時也存在于對包括《無題·一枝清采妥湘靈》《贈畫師》《湘靈歌》等在內的其他一些魯迅詩作的解說中。如何在本屬史學的方法的考據與文學作品的審美詮釋之間找到恰當的結合點,以保證這種實證的努力不致因捕風捉影式的“索隱”誤入迷途、淪為笑談,這是當前現代文學研究(包括魯迅研究)必須警惕的問題。
七、日記研究
魯迅日記是魯迅一生經歷的生動寫照,其中有文化、有民俗,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公務活動以及人事往來、書賬記錄等。近年來,魯迅日記,包括其他一些名人的日記(如吳宓日記、胡適日記、顧頡剛日記)都受到重視,研究者開始利用魯迅日記從中挖掘文化信息、民俗信息,以更好地推進文化研究和民俗研究。
20世紀初葉政府以融入世界現代化的名義,對傳統民間節日尤其舊歷年進行改造,出現了中國各階層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的碰撞與分化。韓大強[23]認為,作為時代思想先鋒的知識分子們既響應政府的號召,力行新歷法,又在行動上、心理上與傳統節日習俗保持著某種程度的藕斷絲連;而普通民眾尤其下層百姓,則依然以舊歷節慶為生活實踐,顯示出難以割舍的精神情懷。通過檢閱魯迅日記中關于“陽歷新年”與“陰歷新年”的記錄,可以窺視出20世紀初期中國傳統節日觀念的變遷,以及精英知識分子們對傳統節日習俗疏離與妥協的心路歷程。傳統文化尤其是民間重要節日內容與儀式是民眾的現實與精神的生活世界,而且代代相傳,與他們的人生、家庭融為一體。簡單、粗暴地否定與改造是難以奏效的。經過近百年的碰撞與交鋒,各種力量更加理性地認識到:一種健康的多元節日文化格局應是互相尊重、相互融合、互相改造、和合而成。
八、魯迅作品整體研究
以上文章著眼于魯迅作品各分集及文類研究,本年度還有一批論文是從各種視角和層面對于魯迅作品的整體透視研究。較具代表性的視角和文章主要有:
1.鬼文化視角。譚桂林《鬼而人、理而情的生命狂歡》[24]認為,魯迅文學世界中的“鬼魂”敘事,充分體現了“鬼”文化在語義上的豐富性與形態上的多樣性。魯迅對鄉間賽神、社戲這些民間節日中的鬼魂扮演中所顯示的“狂歡化”特征的贊美,是因為他深切而獨到地看到了底層民眾在這些狂歡活動中所獲得的心靈感覺的復蘇與精神力的張揚。從魯迅的“鬼魂”意象的描寫,可以看到但丁《神曲》等西方文化的影響痕跡,而更多的則是對中國古代文學中豐富深厚的鬼魂敘事傳統的繼承,并在這種繼承中體現出五四新文化的時代精神。
2.母題學視角。譚桂林《現代中國文學母題的發展與魯迅創作的經典意義》[25]認為,在現代中國文學中,魯迅是最早開辟童年母題文學園地的作家,他對上海生活與文化的直接介入不僅對現代文學、對現代上海都市文化的發展直接產生了影響,而且切實地促進了中國現代都市母題文學的應運而生與積極發展。魯迅的文學創作不僅提供了許多人物形象給新文學作家們以啟示,而且提供了許多精致、雋永的原型意象給新文學家們作為模仿的范本。從母題角度切入到魯迅研究,不僅讓我們深入地認識到魯迅文學世界的創造性的資源由來,更可以讓我們看到在20世紀中國新文學的發生與發展中,魯迅的文學創作是如何成為經典的。
3.音樂學視角。曾鋒《魯迅的文學創作和音樂》[26]指出,對國外藝術學、音樂化文學的譯介和研究,使魯迅接觸到了豐富的音樂知識和文學音樂化技巧。在魯迅的文學創作中,滲透著豐富多樣的音樂化成分和手法,如化用動機的重復與變奏、復調音樂、主導動機手法等,其創作也完滿地印證了T.S.艾略特關于語義的音樂的理論。該文把對魯迅與音樂的分析最終落實到了一個具體的可以進行實際操作、分析論證的層面,不但進一步展示了魯迅語言藝術的獨特魅力和成就,而且使人進一步確信,魯迅作品確實是一個由聲音、語義、意象、思想等諸多層次、因素組合而成的相互生發、相互呼應的整體藝術結構。
[1]吳義勤,王金勝.“吃人”敘事的歷史變形記——從《狂人日記》到《酒國》[J].文藝研究,2014,(4).
[2]周南.狂人日記.“吃人”意象生成及相關問題[J].東岳論叢,2014,(8).
[3]張克.游民與越文化:《阿Q正傳》的啟示[J].江蘇社會科學,2014,(4).
[4]張全之.對《魯迅<故鄉>閱讀史》的閱讀與思考[J].粵海風,2014,(4).
[5]楊義.《吶喊》的生命解讀[J].廣州大學學報,2014,(3).魯迅《彷徨》的生命解讀[J].江蘇師范大學學報,2014,(1).《故事新編》的生命解讀[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2014,(2).
[6]汪衛東.探尋“詩心”:《野草》整體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7]錢理群.《野草》的文學啟示——汪衛東《探尋“詩心”:<野草>整體研究》序[J].書城,2014,(1).
[8]汪衛東.《野草》與佛教[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1).
[9]崔云偉.魯迅與佛陀的同與不同——由汪衛東《<野草>與佛教》所想到的[J].中國海洋大學學報,2014,(6).
[10]李培艷.“自我”與“世界”的雙重“他者化”——關于魯迅散文詩集《野草》的思考[J].現代中文學刊,2014,(5).
[11]張娟.都市視角下的魯迅《野草》重釋[J].南京師大學報,2014,(4).
[12]楊義.《朝花夕拾》的生命解讀[J].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14,(1).
[13]宋劍華.無地彷徨與精神還鄉:《朝花夕拾》的重新解讀[J].魯迅研究月刊,2014,(2).
[14]張顯鳳.母親的缺席與隱秘的傷痛——再讀《朝花夕拾》[J].魯迅研究月刊,2013,(3).
[15]王國杰.衍太太是少年魯迅的夢中“情人”嗎?——與張顯鳳商榷[J].社會科學論壇,2014,(3).
[16]張鑫,汪衛東.新發現魯迅《文化偏至論》中施蒂納的材源[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5).
[17]汪衛東,張鑫.由《文化偏至論》中施蒂納的材源看魯迅對無政府主義的接受[J].魯迅研究月刊,2014,(1).
[18]魏建,周文.《上海文藝之一瞥》的謎團及其國外版本[J].魯迅研究月刊,2014,(7).
[19]劉春勇.留白與虛妄:魯迅雜文的發生[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1).
[20]宋劍華,王蘋.“熱風”與“寒氣”——從雜文看魯迅早期思想的復雜性與矛盾性[J].魯迅研究月刊,2014,(4).
[21]李怡.大文學視野下的魯迅雜文[J].魯迅研究月刊,2014,(9).張鐵榮.探究詞語里面的深意——魯迅雜文中的兩個關鍵詞芻議[J].河北工業大學學報,2014,(6).
[22]邵寧寧.魯迅詩作的屈騷情致與現實寄寓——兼論現代文學研究的索隱、考據及審美詮釋問題[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11).
[23]韓大強.疏離與妥協——魯迅日記中關于年的意識[J].魯迅研究月刊,2014,(3).
[24]譚桂林.鬼而人、理而情的生命狂歡——論魯迅文學創作中的“鬼魂”敘事[J].揚州大學學報,2014,(2).
[25]譚桂林.現代中國文學母題的發展與魯迅創作的經典意義[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4,(2).
[26]曾鋒.魯迅的文學創作和音樂[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1).
(責任編輯 閔 軍)
Several highlights of the Research of Lu Xun's works in 2014
Cui Yun-wei1,Wei Li2
(1.School of Arts Management, Shandong College of Arts, Jinan, Shandong, 250014;2.School of Traditional Opera, Shandong College of Arts, Jinan, Shandong, 250014)
In 2014, the study on Lu Xun's works took on a splendid and innovative situation. The following scholars gave their wonderful opinions about Lu Xun's novels such as Wu Yiqin, Zhou Nan, Zhang Ke, Zhang Quanzhi and Yang Yi. Qian Liqun's study of Wild Grass, Yang Yi, Song Jianhua and Wang Guojie's research on Life is A Moment and Wang Weidong's study of classic thesis at early time have a unique style. In the study of Lu Xun's essays, Wei Jian, Liu Chunyong and Song Jianhua's interpretation is fantastic. Shao Ningning's study of Lu Xun's poems, Han Daqiang's study of Lu Xun's diaries, Tan Guilin and Zeng Feng's holistic study of Lu Xun's works all have their novelties.
Lu Xun;review
2015-05-10
崔云偉(1974-),男,山東鄒平人,山東藝術學院藝術管理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
I210
A
1672-2590(2015)04-009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