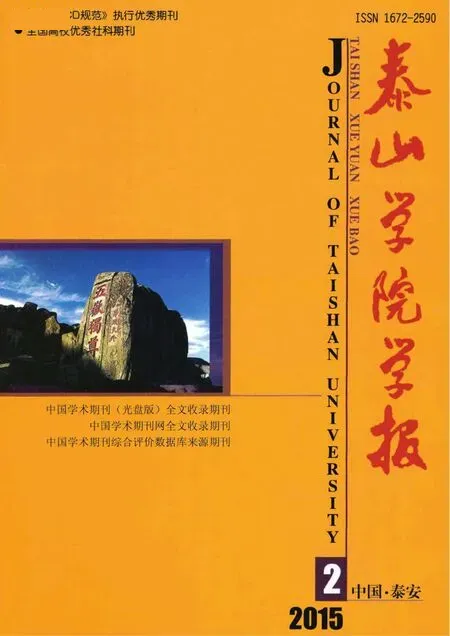荀子人性論:從“性樸”到“性惡”的內在邏輯
孫旭鵬
(東南大學 人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1189)
荀子人性論:從“性樸”到“性惡”的內在邏輯
孫旭鵬
(東南大學 人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1189)
荀子一方面認為人性“本始材樸”,另一方面力主“性惡”。“性樸”與“性惡”非但不存在任何矛盾,而且從“性樸”到“性惡”存在著思維發展的內在邏輯。“性惡”是以“性樸”作為前提,“性偽合”將荀子的“性樸”與“性惡”聯系起來,共同構成了荀子的人性論,從“性樸”到“性惡”是荀子人性論發展的必然邏輯,“性樸”是“偽”的基礎,“性惡”是“偽”的對象。
荀子;人性論;性樸;性惡;性偽合;內在邏輯
荀子究竟持有怎樣的人性論,在學界歷來就有較大的爭議。表面上來看,荀子是“性惡”論者,因為他專門做了《性惡》一篇,來對孟子的性善說加以批判。然而很多學者又反對將荀子盲目地斷定為“性惡”論者,因為荀子的確也有“性樸”的思想,他講過人性“本始材樸”。由此,荀子的人性論問題就變得復雜起來,一部分學者持荀子是“性惡”論者的觀點,主要依據就是荀子《性惡》篇的闡釋,然而這部分學者卻無法解釋荀子為什么又講“性樸”;一部分學者思想于是更進一步,試圖推翻以往認為荀子是“性惡”論者的思維定式,力主荀子是“性樸”論者,甚至懷疑《性惡》篇為荀子后學所作;而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荀子的“性樸”論與“性惡”論并不矛盾,荀子的“性樸”與“性惡”只是在不同的維度上對人性的一種考量。其實,荀子的“性樸”與“性惡”不僅是在不同維度上對人性的考量,并且“性樸”與“性惡”之間存在著思維上的內在邏輯,質言之,荀子有“性樸”的思想就必然會有“性惡”的思想,“性樸”是“性惡”思想的前提,“性惡”是“性樸”思想的必然發展,由此,荀子的人性論便不是一種“性樸”與“性惡”的二元對立,恰恰是“性樸”與“性惡”緊密聯系在一起,共同構成了荀子的人性論。
一、性樸:“情”未發動的本初之“性”
荀子認為人性是“本始材樸”的,是無所謂“善”或者“惡”的。荀子的“性樸”是指在未進入社會關系之前天然的人性狀態,可以這樣認為,荀子講的“性樸”就是指“情”未發動時的狀態,這樣的人性是“天”賦予的。
荀子講:“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荀子·正名》)在這里,荀子明確地講“性”是“天之就”,也就是先天的,并且這種先天的人性是無善無惡的,因為荀子認為君子與小人的先天之性是沒有任何差別的,他講:“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荀子·榮辱》)也就是指人性并不天然包含著“善”或者“惡”的因子,君子和小人的區別是后天形成的。從荀子“性者,天之就也”的思想來看,荀子是將人性歸之于“天”的,荀子講:“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荀子·天論》)很顯然,這里的“天情”也就是荀子所講的“情者,性之質也”,這種“情”就是指好惡、喜怒和哀樂,不過在“天之就”的“性”中,這種“情”是“臧”的,所以荀子講“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由于在“天之就”的人性中,“情”是藏著的未發的,所以人性是“樸”的,所以荀子又進一步講“性者,本始材樸也”(《荀子·禮論》)這樣的話。由此可見,在荀子的“性樸”論思想中,人性是“天”給予的,是一種天然的“樸”的狀態,是無善無惡的,然而這種“本始材樸”的人性中,又隱藏著“好惡、喜怒、哀樂”的“情”,只不過這種“情”是藏著的未發動的。因此,荀子的“性樸”其實包含著“性者,天之就也”與“情者,性之質也”兩部分的內容。
那么是否就可以用荀子的“性樸”思想來否認荀子的“性惡”思想呢?顯然是不能的。“性樸”與“性惡”只是荀子思考維度不同而造成的,“性樸”是在進入社會關系之前,“情”未發動的本初狀態。如果沒有將荀子的“性樸”思想放在荀子特定的思考維度,而籠統地認為荀子在任何情況下都主張“性樸”,就很容易產生理解上的偏差。比如周熾成先生就認為荀子的“性樸”思想與荀子《性惡》中提出“化性起偽”的主張相矛盾,是一個極大悖論,周先生是這樣說的:“顯然,化性就是改變人性,變化人性。既然人性是‘不可學,不可事’的,為什么它是可以‘化’呢?既然人性是固定不變的,為什么它可以‘化’呢?今語有云:先天不足,后天補。但這僅僅是補而已,并不是說改變先天的東西。前面對人性所說的‘不可學,不可事’與現在對它所說的‘矯飾’、‘擾化’當然是不相容的。”[1]在這里,荀子講的“不可學,不可事”的人性是在“性樸”這一維度上來思考的,也就是沒有進入社會關系之前的“天之就”的人性,而《性惡》中可以改變的人性顯然不是“性樸”維度上的人性,而是“性惡”維度上的人性,“性惡”維度上的人性就是“情”已經發動時的狀態,我們后面再談。周熾成先生在這里理解上之所以會出現偏差,就是因為將荀子“性樸”維度的人性與“性惡”維度下的人性相混淆,認為荀子指的是一個意思,其實不然,“天之就”的人性不是荀子要改變的對象,荀子要改變是進入社會關系之后“情”發動之后的人性,荀子認為“情”發動之后的人性為“惡”,而“情”未發動的人性為“樸”。路德斌先生認為:“荀子言‘性’有兩個維度:在‘人生而靜’層面,‘性’乃‘樸’也;在‘感于物而動’層面,‘性’趨‘惡’也。”[2]確實是這樣,“人生而靜”的層面其實也就是“情”未發動的狀態,而“感于物而動”的層面其實也就是“情”發動后的狀態,這確實是荀子言“性”的兩個不同維度。荀子的“性樸”就是著眼于“情”未發動時人性的本初狀態而言的,“性樸”不是荀子要改變的對象,荀子要改變的是“性惡”。
二、性惡:“情”發動之后的過度之“欲”
荀子的“性樸”思想是就“情”未發動時人性的本初狀態而講的,而其“性惡”思想則是就“情”發動之后的欲求狀態而講的,在進入社會關系之后,原本“天之就”的人性就趨向于“惡”。
荀子講:“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后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荀子·性惡》)荀子認為原本“本始材樸”的人性在進入社會關系之后,如果單純地順從自己的情欲,就會產生爭奪,勢必造成社會的混亂,必然造成“惡”的后果。因此,荀子講“性惡”是從社會關系的維度來考量的,其強調的不是人性本“惡”,而是在社會關系中順從人性而造成的社會之“惡”。荀子講的“善”和“惡”完全是從社會關系的維度來加以考量的:“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荀子·性惡》)之所以會產生社會之“惡”,究其原因不在于“情”未發動時人性的“本始材樸”,而在于“情”發動之后的欲求狀態。荀子講:“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惡》)這與前面荀子講的“欲者,情之應也”都是指“情”已然發動后的狀態,荀子認為“情”一旦發動就產生“欲”,如果對這種“欲”不加以節制的話,就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爭奪,勢必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因此就必須對“情”發動之后產生的“欲”進行一定的節制:“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荀子·正名》)荀子雖然認為需要對“欲”進行節制以免產生“惡”,然而他同時也認識到“欲”是不可能完全去除掉的,因為“欲”是“情”的自然發動,只能使“欲”處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以達到社會之“善”,荀子講:“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所以,荀子在這里講是“養人之欲”,而不是要對“欲”徹底去除的態度。
進一步講,荀子并非認定“情”發動之后的“欲”就必然是“惡”的,而是只有“欲”超過了一定限度,破壞了社會的正常秩序之后,才是“惡”的。荀子認為“欲”的多寡并不是社會治亂的根本原因,而關鍵在于“心”的作用,如果“心”能節制過多的“欲”,那么“欲”即使再多,也是無害于社會的,荀子講:“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于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于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于亂!故治亂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荀子·正名》)荀子認為要防止社會之“惡”關鍵在于“心”的作用,只要“心”能夠對欲望進行必要的節制,那么欲望的多寡并不會妨礙正常的社會秩序。所以“欲”本身并不會必然地產生“惡”,“惡”產生的原因就在于“心”沒有節制“欲”,只有過度的“欲”才導致了社會之“惡”,荀子講“性惡”就是在這個維度上加以考量的,許建良先生也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情欲的多少,因為這本身是人性的因子之一,關鍵在于‘心之所可’。譬如,情欲雖多,但由于心能對此有效地制約,因此,由情欲而來的沖動就失去外在作為的連接點,即‘動不及’,這種狀態本身對真性的維持以及本性的良性運行,也根本夠不成什么傷害。即使欲望不多,但情欲向外施行作為的連接點卻暢通無阻,這是心容忍的結果,即‘心使之’,這自然就破壞了本性的健康運行,并能引發混亂。”[3]總之,荀子的“性惡”是指“情”發動之后,“欲”沒有經過節制而造成的社會之“惡”,荀子的“性惡”并不是指“欲”是惡的,而是始終從社會的實際效果來講“惡”。
三、性偽合:“性樸”與“性惡”的內在邏輯
前面我們分別分析了荀子的“性樸”以及“性惡”思想,那么是否就意味著“性樸”與“性惡”之間是截然分離的呢?顯然不是的。在荀子那里,雖然“性樸”與“性惡”是從兩個不同的維度來進行考量的,然而“性樸”與“性惡”思想卻緊密聯系在一起,“性樸”是“性惡”的基礎,“性惡”是“性樸”的必然結果。荀子的人性論可以用“性偽合”來概括,“性”是指“本始材樸”的天然之性,也就是“性樸”的部分,而“偽”則是對待“性惡”應該采取的措施,也就是“性惡”的部分。
荀子講:“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圣人然后分也。”(《荀子·禮論》)正因為人性是“本始材樸”的,所以一旦進入社會關系之后,就會產生欲望,欲望過度了就會產生“惡”的效果,而“偽”正是對治“惡”的,所以荀子講“無性則偽之無所加”,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性樸”,那也就不會有“性惡”因此也就不需要“偽”了。為什么講如果沒有“性樸”,也就不會有“性惡”呢?正因為“性樸”,所以會產生好利之心,于是才會出現爭奪的情形,如果像孟子認為的那樣,人性本身就具有善端的話,那么就不會產生爭奪,也就不需要“偽”了,荀子正是從這個角度批評孟子的性善論的:“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圣王,惡用禮義哉!雖有圣王禮義,將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惡》)可以這樣認為,正是因為人的本性無善無惡,順應這種本性才有可能產生社會之“惡”,如果人的本性天然是善的,那么自然就不會產生社會之“惡”,也就不需要什么“偽”了,孟子與荀子人性論的立足點是不一樣的,孟子立足“性善”,荀子立足“性樸”,路德斌先生分析了孟子與荀子“性”的差異:“在孟子,‘性’是一個具有形上學意義的概念,其基本內涵是‘人之所以為人者’,這也是唐、宋以后儒家學者思維中的‘當然’的‘性’概念。但荀學中的‘性’完全不具有形上學的意義,因而也完全不具有‘人之所以為人’的內涵。”[4]總之,荀子的“性樸”思想恰恰成了其“性惡”思想的基石,“性惡”是以“性樸”為基礎的,而從另一方面來講,“性樸”由必然地導向“性惡”,因此,荀子的“性樸”與“性惡”思想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恰恰是緊密聯系在一起,從“性樸”到“性惡”具有十分嚴密的思維邏輯。
上面我們講了“性樸”與“性惡”的關系及其內在邏輯,我們很容易發現,在荀子的人性論中,“性樸”與“性惡”都是不可或缺的,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然而“性樸”是荀子人性論的基礎,也是“偽”進行的基礎,是靜態不變的人性存在,而“性惡”則是荀子人性論的發展,是“偽”的對象,是一種動態變化的存在。因為“性樸”是“天之就”的,是人性的本然狀態,當然也就不可能改變什么,所以“性樸”處于一種固定不變的狀態,是一種屬“天”的狀態:“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愿其所參,則惑矣。”(《荀子·天論》)可以這樣認為,荀子的“性樸”就是一種“天職”,是不可改變的存在,所以后天之“偽”所能改變根本就不是“性樸”,而只能在“性樸”的基礎上來進行。而另一方面,“性惡”則是“偽”施加的對象,荀子講:“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后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后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后正,得禮義然后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通過“化性起偽”的方式,“性惡”就不斷地得到改變而趨向于“善”,因此,在荀子那里“性惡”是一個動態發展的存在,而不是固定不變的,“惡”是一種完全可以憑借后天的“偽”加以去除的,因此荀子很自信地認為“涂之人可以為禹”。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因為“性惡”的產生本身就是后天的,而不是先天的,當然是可以改變的,不能改變的恰恰是先天的“性樸”。總之,在荀子的人性論中,“性樸”是先天的靜態的不可改變的,而“性惡”是后天的動態的可以改變的。
四、結語
荀子的人性論包含著“性樸”與“性惡”兩個維度。“性樸”是“天之就”的,是“情”未發動時的狀態,而“性惡”是后天的,是“情”發動后過度之“欲”造成的。同時,“性樸”與“性惡”又不是截然分開的,“性樸”與“性惡”共同構成了荀子的人性論,“性樸”是“性惡”的基礎,“性惡”是“性樸”的發展,“性樸”是“偽”的基礎,“性惡”是“偽”的對象,“性樸”是先天的靜態的不可改變的,而“性惡”是后天的動態的可以改變的。總之,荀子的“性樸”與“性惡”之間存在著思維上的內在邏輯。
[1]周熾成.荀韓人性論與社會歷史哲學[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
[2]路德斌.性樸與性惡:荀子言“性”之維度與理路——由“性樸”與“性惡”爭論的反思說起[J].孔子研究,2014,(1).
[3]許建良.荀子性論的二維世界[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2).
[4]路德斌.荀子與儒家哲學[M].濟南:齊魯書社,2010.
(責任編輯 梅煥鈞)
Theory of Human Nature by Xunzi:Logic from Austerity to W ickedness
SUN Xu-peng
(School of Humaniti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1189)
Xunzi thought that on the one hand,human nature was austere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wicked.Not only did austerity and wickedness have no contradictions,but logically they were inter-related.Wicked nature was based on austere nature,and they developed into the human nature theory which combined them together called"pseudo alloy of nature".And it was the inevitable logic from austere nature to wicked nature with austerity the basis of being pseudo and wickedness being the object of being pseudo.
Xunzi;Human Nature Theory;Austere Nature;Wicked Nature;Pseudo Alloy of Nature;Inner-logic
B21
A
1672-2590(2015)02-0054-04
2015-01-0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supported by“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和江蘇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資助項目(KYLX_0070)的階段性成果。
孫旭鵬(1981-),男,山東海陽人,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哲科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