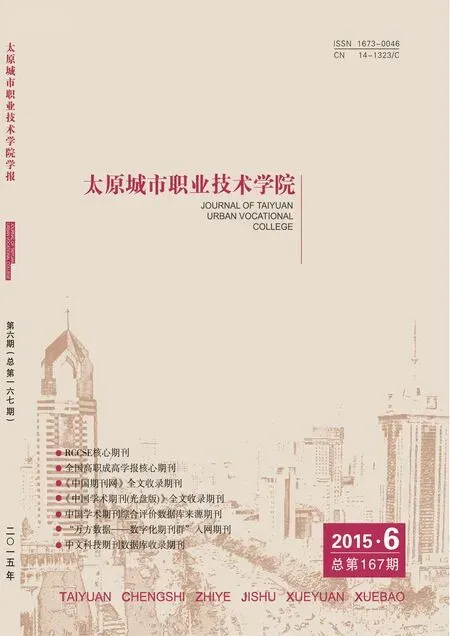論《德伯家的苔絲》中道德標準的雙重性對敘述的影響
章書瑜
(福建師范大學,福建 福州 350001)
1928年,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她的文章《論托馬斯·哈代的小說》里說:“如果我們打算把哈代置身于他的同輩伙伴之中,我們應該稱他為英國小說家中最偉大的悲劇作家。”《德伯家的苔絲》是哈代被世人津津樂道的代表作,也是最能體現他創作精神的重要作品之一。正當維多利亞時期的資本家們為資本主義制度沾沾自喜的時候,哈代通過“一個純潔的女人”的悲劇命運向世人揭露出維多利亞時期的道德觀念的虛偽和腐朽。
一、維多利亞時期道德標準的雙重性對敘述的影響
哈代在1890年發表的文章《英國小說中的坦率》中,呼吁人們應該公平對待男性與女性。因為從本質上說,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那么世俗觀念里的男女地位,也應該平等。他譴責關于社會的幸福取決于人們生活的純潔度這樣違背人性的觀念,并責備宣傳此觀點的小說。維多利亞時期將女性貞操神圣化,并且將貞操視為女性的評判標準。該時期的道德觀對男女實行雙重標準,一方面,無條件地要求婦女保持絕對純潔;另一方面,對男性的行為不作任何限定。
在《德伯家的苔絲》中,尤其從苔絲的母親昭安·德北和安璣的母親克萊爾夫人的言語中我們可以看出,女性的貞操在當時變成了交易的談判條件。克萊爾先生和克萊爾夫人將女性的純潔度放置第一位,認為安璣要娶一個“純正、貞潔的女人”,安璣也認同,并將苔絲形容成像“祀神的貞女一樣純潔”;對苔絲的母親而言,出發去亞雷·德伯家之前的苔絲盡管外表成熟得“像個婦人”,但“其實她比一個小孩子大不了多少”,苔絲無辜美是她的“王牌”,“她只要把王牌抓住了,她就一定降得住他。”我們可以看出,盡管昭安也高度重視苔絲的貞操,但她更關注苔絲的交換價值。
亞雷是造成苔絲悲劇命運的“撒旦”。他是個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極端地厚顏無恥,認為自己有錢,可以為所欲為,可以隨便地踐踏別人的尊嚴,可以蹂躪純潔的少女。雖然亞雷家有錢,但他的生活并不幸福,與母親的關系長期不好,父親又去世了,缺乏親情的溫暖,沒有生活目標,精神上極度空虛。在這樣的生活狀態下,亞雷不可能理解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意義。他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漂亮女人的強烈吸引力。在苔絲被亞雷侮辱之后,人們對品德敗壞的亞雷任意玩弄拋棄女性的行為不但視若無睹,而且把一切譴責與非議都指向苔絲。亞雷逍遙法外,而苔絲卻永遠地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再也無法解脫。
二、苔絲對道德標準的認識過程對敘述的影響
苔絲失身后,那條“深不可測的社會鴻溝”把她與外界隔開。在她回家的路上,她遇到一個男人刷的那些張著血盆大口的字“不,要,犯(奸淫)”,苔絲鄙夷地說:“呸,我不信上帝說過這種話!”她時常自問:“女人的貞節,真是一次失去了,就永遠失去了嗎?”這表明苔絲對世俗的道德價值觀開始產生了懷疑。此刻她認為自己沒罪,但也感覺到了她有可能面臨異樣的世俗眼光。
第一個當面向苔絲指出孩子是“觸犯社會的罪惡”的是教會牧師,在苔絲的孩子生病后他不僅未對苔絲報以同情和幫助,還在苔絲請求牧師“按著教會的儀式,把他埋葬了”時,牧師蒼白地回答:“因為還有別的原因,所以我就不能那么辦了。”至此,敘述者利用基督教會的成員和牧師對苔絲的態度,讓苔絲意識到了基督教義下的世俗道德立場是女性不能有婚前性行為;敘述者也讓苔絲發現亞雷的婚前性行為并未給他帶來任何困擾。然而,這能說明苔絲已經認識到世俗道德標準具有雙重性嗎?顯然不能。
苔絲和安璣結婚前,苔絲想要誠實把過往的痛苦告訴安璣。昭安對她的猶豫“保持沉默”:“受過苦惱的女人,世界上可就多著啦,有些還是頂高貴的女人呢;人家有了都不聲不響,你有了為什么就該大吹大擂呢?沒有那么傻的人。”
從昭安的言語中我們看得出,昭安明白世俗道德標準的雙重性。如果一個女性有婚前性行為并告之自己的丈夫,很可能會傷害丈夫的自尊心;而如果一個男性有婚前性行為并告之自己的妻子,對他們家的名譽不會起根本性的影響。苔絲或許從昭安的勸告和教會中的人看出了世俗道德標準的偏見,但她認為安璣是一個“頂好的男人”,她堅信安璣不會和世俗人一樣。至此,敘述者已經讓讀者看到了即將發生不幸的苗頭。
三、安璣與苔絲道德立場的對立對敘述的影響
安璣向苔絲表白其曾經的放蕩史,使用的方式并非人物自身的直接闡述,而是敘述者的敘述。“48小時”這段敘述既呼應了敘述者前期所做的暗示,并且給讀者制造了另一個難題。讀者既聽不到安璣在“招供”時自身的語言表述,更看不到他在“招供”時的表情動作。哈代的目的在于通過敘述的存在與消失,將讀者的注意力引向安璣與苔絲對各自性歷史的不同態度。
驅使安璣說出性歷史的動機有兩個:第一,他認為苔絲太純潔了,他必須把自己骯臟的部分說出來,只有苔絲能接受,他才能在純潔的苔絲面前抬起頭;第二,他相信如此美好的苔絲一定會原諒他。而驅使苔絲說出被亞雷誘奸的經歷的動機也有兩個:第一,她單純地想對安璣誠實,這樣才能守護基督教“夫妻雙方必須誠實”的教義;第二,她相信如此愛她的安璣一定會原諒她。安璣猜對了,可是苔絲猜錯了。因此,我們可以將敘述者的敘述分成兩部分:第一,言語表達的內動力;第二,對對方反應的預期。苔絲原諒安璣而安璣無法原諒苔絲,正是因為他們各自所站的道德立場不同。苔絲認為他們的婚前性行為的經歷從道德而言是平等的,“我的罪惡也許和你的一樣嚴重”,可安璣不這么認為。
同樣是婚前性行為,同樣是“罪惡”,安璣得到了苔絲的原諒,卻不能原諒肉體和精神都被損害的苔絲。他未意識到他堅守的道德標準不僅會讓他失去愛他的人,還會破壞他的婚姻生活,甚至要了一個心靈純潔的女子的命。安璣一直將苔絲視為“自然的女兒”,既然是“自然的女兒”,那么她必定是純潔無瑕的,然而原來這個女子早已失去貞操,還曾經生過一子,他的第一反應與維多利亞時期的人們一樣,都認為她是“淫蕩的女人”。安璣沒有看到苔絲才是整個事件的受害者,他沒有看到亞雷奪走的只是苔絲的身體,而不是她的靈魂,而這正是哈代堅持在副標題加上“一個純潔的女人”的真正理由。
四、哈代的道德立場的轉變將敘述指向何方
19世紀的進化論思想和宇宙論思想對哈代影響很大,正如哈代自己所說,從青年時期起,他就受到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影響,是《物種起源》最早的擁護者之一,進化論思想促使他對人類的自主權意識產生懷疑。哈代接受了進化論在道德倫理方面的學說,建立起進化論倫理觀。
哈代小說中體現的人物與環境的矛盾性一直貫穿于小說的多樣性中,哪怕評論家不愿接受這樣不符合現實主義的敘述藝術,也不得不承認在道德標準的雙重性影響下的敘述必然驅使苔絲走向異化。如:
她從這一片繁茂叢雜的幽花野草中間,像一只貓似的,輕輕悄悄地走了過去,裙子上沾上了杜鵑涎,腳底下踩碎了蝸牛殼,兩只手染上了蘚乳和蛞蝓的黏液,露著的兩只胳膊也抹上了黏如膠液的樹莓,這種東西,在蘋果樹干上是雪白的,但是到了皮膚了,就變得像茜草染料的顏色了。
哈代用大量諸如此類的敘述謹防這部作品變為倫理道德的直接控訴,卻在無形當中產生了極大的張力。在這段文字中,張力的產生不是由于個人經驗的表達,而是由于文本模糊了人物、敘述者和隱含讀者之間的界限。因此,它揭示了人類、自然與超自然之間的明顯界限;也揭示了人性與超自然性的不確定性。這種敘述自然而然地將讀者的視角放置于超自然力量上,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命運”。
哈代正是采用看似殘忍無情的敘述方式控訴道德的殘酷、人類的脆弱,比起激烈的批判,這種方式讓作品更具個性化、人性化,更能打動人心。因此,使得《德伯家的苔絲》經過歷史的沉淀依舊能夠打動人心的根源,并不是一波三折的情節,而是哈代的敘述和語言。
[1]弗吉尼亞·伍爾夫.論小說與小說家[M].瞿世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202.
[2]Hardy.“Candour in English Fiction,”in Thomas Hardy's Personal Writings[J].London:Macmillan,1967.133.
[3]Cox Don Richard,ed.Sexuality in Victorian Literature[M].Knoxville:U of Tennessee P,1984:94-103.
[4](英)托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絲[M].張谷若,譯.北京:人們文學出版社,1984:198,199,60,64,113,123,151,141,147,268.
[5]Florence Emily Hard.The life of Thomas hardy[M].Macmillan,London,1993:198.
[6]聶珍釗.哈代的小說創作與達爾文主義[J].外國文學評論,2002(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