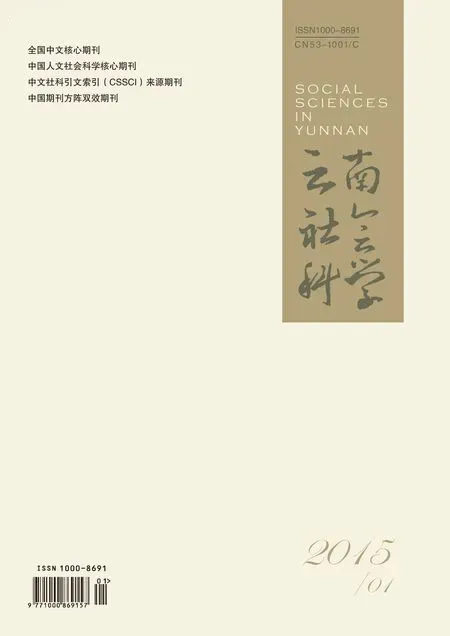先秦“文”“質”之爭與禮學的演進
左康華
一、“禮義”的發(fā)現(xiàn)與禮學的開端
從《三禮》(即《儀禮》《禮記》《周禮》)的部分篇章所反映的宗周的典章制度來看,周代的禮樂文明,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令人贊嘆的程度。周禮的系統(tǒng),以《儀禮》所言,有冠、婚、喪、祭、朝、聘、鄉(xiāng)、射等禮;以《周禮·春官·大宗伯》所言,禮有吉、兇、賓、軍、嘉,五禮名下又細分為三十六目,內容繁復、巨細無遺,形成了一整套按著一定社會秩序和規(guī)范來進行生產和生活、維系整個社會的生存和活動的具有極大強制性和約束力的典章、制度、儀節(jié)。
如果說典籍的記載尚有后人美化、造偽的可能,那么出土的文物無疑是宗周禮樂文明的忠實見證者。從西周禮制建筑遺跡,到貴族墓葬中出土的成批禮器,再到各類金文、甲骨文的記載*參見楊向奎著,《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無不反映著周禮的普遍性、實踐性與強制性。
考察禮的起源,自古至今影響最大的假說是祭祀說*這一觀點認為禮起源于祭祀活動,最初是指將祭品(玉石或酒)裝在禮器中獻給所祭神祇,隨后推衍出人所需要尊奉的舉止規(guī)范的含義。最早出自《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徐灝箋:“禮之言履,謂履而行之也。”近代學者王國維認為“禮”字最早指以器皿盛兩串玉獻祭神靈,后來也兼指以酒獻祭神靈,又推而廣之為奉神人之事。這一說法應當是有關禮的起源諸說中影響最為深遠、為多數(shù)學者所認可的一種。;此外,古人尚有人情說*該說認為禮起源于對人的情欲的順應與節(jié)制。郭店楚簡《語叢一》:“禮因人情而為之”,《性自命出》篇則載“禮作于情”。《禮記·喪服四則》:“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史記·禮書》:“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風俗說*該說認為禮起源于風俗習慣。《慎子·軼文》:“禮從俗。”《禮記·坊記》:“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jié)文,以為民坊也。”近人劉師培、呂思勉也持此說。參見劉師培著,《劉師培全集》(第2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頁;呂思勉著,《經(jīng)子解題》,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乃至天道說、圣王說*該說認為,禮起源于原始社會的種種禮儀。最早由楊寬提出,李澤厚也持此說。參見楊寬著,《古史新探》,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34頁;李澤厚著,《中國古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頁。,近代學者則有禮儀說*這種說法認為禮起源于天道秩序,而為圣人所制。《禮記·禮運》:“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夫禮必本于太一”。、交換說*此說認為禮起源于人類原始的交往活動,遵循“禮尚往來”的原則;后來逐漸演變?yōu)閹в袕娖刃缘亩Y品交換。參見楊堃著,《西周命冊制度研究·序》,上海:學林出版社,1986。。古人論禮,多臨事取義,各根據(jù)禮的某一方面立說,今人論禮,雖不乏創(chuàng)見,但更是各據(jù)一端,難發(fā)全面之論。然而,無論哪種假說,都承認禮起源于實踐,形成的是一套行為規(guī)范與共尊儀式,且具有一定程度的強制性。曾有學者概括周禮的各項功能,認為其具有政治功能、道德功能、節(jié)制情感功能、社會功能,并且是貫穿一切道德觀念的核心范疇[1](P264~270)。我們并不否認周禮或許在事實上起著這樣那樣的作用,但歸根結底,這些功能的發(fā)揮都還處于自然自在狀態(tài),并沒有上升到理論的思考層面。而禮的實踐層面的豐富,并不能代替哲學的思考。因此,這一時期有“禮”而無“學”;禮學尚處于孕育期。
發(fā)生于春秋末期的“禮崩樂壞”的現(xiàn)實危機說明,“日用而不知”的單純實踐,已經(jīng)不能適應變動的社會現(xiàn)實。面對周禮的價值危機,思想家們必須從理論上對禮的本質及功能進行思考與探索,以圖從日益崩潰的禮儀典制中拯救出禮的價值內核。用理性的目光審視禮本身,審視禮的本質、功能及意義。
這種思考首先表現(xiàn)為“儀”與“禮”的區(qū)分。春秋時期,開始有人意識到禮的形式與內容的不同。學者們普遍注意到了《左傳》的如下記載:“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左傳·昭公五年》)[1](P667~668)關于“儀”與“禮”的另一次討論則出現(xiàn)在《左傳·昭公二十五年》[2](P765)。可以看出,此時“儀”不但被區(qū)別于“禮”,甚至隱隱與“禮”對立;對“揖讓、周旋”的細枝末節(jié)的追求、行禮如儀已經(jīng)不會被贊為“善于禮”,反而可能因為某種價值原則的缺失而被嘲笑為“焉知禮”。
需要注意的是,《左傳》的其他記載則說明“儀”在當時依然具有不可動搖的權威性*《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載:“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可見對于禮儀的強調依然存在。參見(清)洪亮吉撰、李解民點校,《春秋左傳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630頁。。在“揖讓、周旋之禮”的強約束力并未消散的同時,對于“禮”的格外強調就顯得引人注目。究其內涵,人們已經(jīng)開始注意禮的形式與內容的區(qū)分,并做出了禮義高于禮儀、內容高于形式的價值判斷:“揖讓、周旋之禮”是為禮儀,是禮之末;“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是為禮義,是禮之本。若不知禮以其義為本,而“屑屑焉習儀以亟”,不過是徒有其表而無其實,或者雖有禮儀而失其大用,舍本逐末,不可贊為知禮。
如果將禮義與禮儀的分離視為內在精神與外在形式的區(qū)分,那么在禮儀之外,禮義也從同屬于形式的禮器乃至禮數(shù)上剝離,禮的精神徹底擺脫了形式的束縛而得以彰顯。
禮器或稱禮具,是禮典中所使用的、體現(xiàn)差別的器物;禮數(shù)則是禮器、禮儀的具體的數(shù)量,“名位不同,禮亦異數(shù)”(《左傳·莊公十八年》)[2](P248),是等級地位之差的最直觀的表現(xiàn)。就前者而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3](P1216)的追問;就后者而言,“失其義,陳其數(shù),祝、史之事也”(《禮記·郊特牲》)[4](P706)的輕視:二者所反映的,都是禮的內在精神——禮義,對于禮的外在形式——禮儀、禮器、禮數(shù)的全面超越,最終確立了“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禮記·郊特牲》)[4](P706)的最高原則。
禮義的產生,是對儀式活動的本質與規(guī)律的總結,又使禮擺脫了禮儀的軀殼的束縛而獲得了長久的生命力。首先,禮義的存在使禮制的構建更具靈活性。“禮者在于所處”,禮義可以用于指導禮制的建設,禮制可以在禮義的指導下因時而變、有所損益,不致再次面對先秦時的危機;其次,禮義的抽離促使人們從思想學術層面而不再是制度典章層面研究禮、認識禮,換言之,從形而下的器物、行為層提煉出形而上的意義,是“禮”向禮學進化的起點;對于禮的現(xiàn)實層面的反思,促使人們意識到禮的真正價值之所在。
二、以禮文為價值追求的儒家禮論
如果將禮儀與禮義近似等同于禮的外在表現(xiàn)與內在精神的話,禮文與禮質之別則更為復雜。孔子及其弟子有關“文質彬彬”以及“繪事后素”的有關討論,將“文”“質”這一對概念范疇引入了禮學研究的視野。
從字源學角度看,“文”與“禮”似乎天然地聯(lián)系在一起。《說文》釋“文”:“錯畫也。象交文。”段玉裁注:“錯畫者,交錯之畫也。《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錯畫之一耑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5](P425)《易·系辭下》云:“物相雜,故曰文。”[6](P319)可見“文”的原始意義當是指條紋、紋彩交錯的具有美感的樣態(tài)。這種有規(guī)律的具有美感的樣態(tài),在天表現(xiàn)為“剛柔交錯”,在人則表現(xiàn)為“文明以止”*《易經(jīng)·賁卦·彖辭》:“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參見李學勤主編,《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頁。。《禮記·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guī),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4](P820)其所描述的行禮的程式、復雜的裝飾,乃至配合著樂曲的節(jié)拍,無不與“文”所代表的豐富的紋理和合理的秩序相合。這使得“文”與“禮”在內涵上有了相通之處,繼而能夠互用。《論語》中,無論是夫子“郁郁乎文哉”的贊嘆,還是“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的自我期許,其中對于“文”的定義,無不與“禮”的概念盡相吻合。
“質”是作為與“文”相對的概念進入研究視野的。《說文》訓“質”為“以物相贅”,又訓“贅”為“以物質錢”;段玉裁注“質贅雙聲。以物相贅,如春秋交質子是也。引申其義為樸也、地也,如有質有文是。”[5](P281)可見“質”的本義是以物交易,引申開來,“質”首先具有實體性:相較于“文”的工巧形式,“質”更側重內容,因而引申出“實質”“本質”之義。其次,“質”作為未經(jīng)加工的素材、質地,又往往與樸實、自然等特征相關聯(lián)。無論是本質義,還是質樸義,“質”都與“文”的文采、文飾緊密聯(lián)系而又構成矛盾;因此,“質”作為與“文”相對的概念范疇被引入禮學的研究,就顯得順理成章。
從《論語》的記載來看,孔子及其弟子堅持“文質彬彬”,也即是人的行為舉止與自然本性協(xié)調共濟的原則:“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3](P400)在棘子成與子貢的討論中,子貢反駁了棘子成“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的觀點,認為文、質就猶如動物與其皮革的關系,“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文、質相輔相成,去彼無此、去此無彼[3](P840~842)。以孔子為首的儒家認為“文”表現(xiàn)于外,構筑起了進退揖讓的禮儀形式系統(tǒng),“質”隱含于內,內化成為人心的道德規(guī)范;二者之間的關系以“文質彬彬”為原則,即外在的禮儀必須與仁義的內在品德協(xié)調相配、不偏不倚,才能共同構成禮的理想狀態(tài);奢、易則文飾有余而其質不足,失于虛華,儉、戚則其誠有余而文飾不足,失于粗鄙,任何一方的偏勝都會導致禮的缺陷。
多有學者用內容與形式這對范疇來概括“質”與“文”之間的關系,認為“禮的文質關系反映的是禮的形式與內容、意蘊,或禮呈現(xiàn)的式樣與其本質、精神、功能的關系。”[7](P1)然而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文/質”說是對“儀/義”說的繼承與發(fā)展:在內容與形式之外,“質”與“文”更是指先天的生理素質與后天的禮樂教化;儒者所追求的“質”,更多地存在于道德范疇,是一種天性追求仁義的、樂于接受禮樂教化的本性,正如《禮記·禮器》所言,“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4](P333)。這里,“質”與“文”超越了單純的內容與形式,而是構成一種正向關聯(lián),共同指向更為完善的道德境界。《國語·晉語》中,胥臣答晉文公:“胡為文,益其質”[8](P387),以及前引“文猶質也,質猶文也”,無不是這一觀點的反映。
從儒家追求的另一項“質在文先”的原則中,可以更明顯地看出這種繼承關系。在“文質彬彬”的合乎中庸的理想境界難以達到時,孔子認為應當堅持“質在文先”“仁在禮先”。《論語·八佾》載:“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3](P157~159)就像禮儀的外殼不能束縛禮義的價值,與文采煥然的禮樂制度相比,質樸的本性更為可貴,因為“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9](P71)。
然而,當禮學的研究從“儀/義”論進入“文/質”論,儒家所無法割舍的對于“文”的價值追求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儒者的立場。以完整的“文”“質”內涵來審視儒家的文質論,可以看出儒家有意回避了“質”的全部內涵,而更多地停留在道德范疇,認為只有易于接受禮樂教化的本性才可稱之為“質”;其所追求的是文化了的“質”,而與“質”的本義有所偏離。無論孔子怎樣表示出對于“巧言令色”“便辟”“善柔”的深惡痛絕,都不可能真正反對英華發(fā)外、煥然成章的文象;無論怎樣強調“質”的先在性,都不可能真正以質之樸代替文之華*儒家所追求的“質之樸”,也往往是符合“文”的審美的“大圭不琢”的美玉,而并非真正的質樸甚至簡陋的質料。。換句話說,對于華麗之形式的追求、對于價值生命的向往,是深刻在每個儒者靈魂中的本能。這種對于核心概念的含混與避重就輕無疑使儒家“文質彬彬”的原則最終屈服于“禮文”的價值追求。
三、諸子的攻訐與禮意的復歸
從禮義到禮文,儒家文質之說超越了此前禮學研究中形式/內容的簡單劃分,使禮學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極大地豐富了先秦禮學的研究成果。但與此同時,儒家重禮文而輕禮質的實際立場也招致了諸子的批判。
批判的焦點之一是儒家質論的偏頗。老子并不認同儒家對于“質”的定義,而是以純乎天然的、未經(jīng)雕琢的本性為“質”,認為任何外在文飾的贅附都是對“質”的戕害:“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10](P151~152)在老子看來,既然宇宙萬物皆歸本于自然,這未經(jīng)雕琢的自然便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一切人為的加工與文飾都只會損害其本來面目。所以他要發(fā)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老子·第十二章》)[10](P45)這樣的警告,并提倡“見素抱樸”和“復歸于樸”。
韓非持相近的立場,并進而認為文盛即是質衰:“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11](P133)韓非子認為,“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11](P133),如果事物的本質足夠美好,那么沒有任何禮文能夠修飾;反過來,需要禮文來裝飾的事物,正說明了本質的枯萎。
對此,莊子更為尖銳地提出了“文滅質”的主張:“文滅質,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莊子·繕性》)[12](P136)在道、法諸家的思想家們看來,文、質無法共存,對一方的強調必然會損及另一方,因此權衡之下取“質”而輕“文”乃至棄“文”。
批判的焦點之二則是儒家的文繁之弊。《墨子·非儒下》中批判的“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13](P291),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時人(特別是社會中下階層的民眾)心目中儒者的形象。墨子認為耗心力于文采修飾無益于國計民生,故而反對禮的繁文縟節(jié)。《墨子·非樂》篇中對于樂的批評是這一觀念的集中反映:“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13](P251)即便在后世,學者對于儒家雖然持基本肯定的態(tài)度,然而對于其流弊之所在,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司馬談“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論六家要旨》)[14](P3290),劉子“流廣文繁,難可窮究”(《劉子·九流》)[15](P520)的批判,皆可為證。
就諸子對儒家文質論的攻訐而言,前者補充完善了禮質的內涵,指出了禮文所具有的掩飾功能對自然本性的戕害;后者更是鮮明地指出了儒家堅持的禮文的價值立場所可能帶來的奢靡之弊。然而,諸子尚文輕質的立場不可避免地割裂了禮的文質,其對禮文的激烈否定則更不可取。禮的發(fā)展程度,可以作為文化是否發(fā)達的一個標準,甚至可以作為文明成熟程度的標志。禮萌生于先殷,至夏、殷而稍具規(guī)模*陳戍國通過對先秦史料的研究,參考現(xiàn)代考古成果,認為多種禮萌生于有虞時期,到夏代,禮的門類多已具備而初具規(guī)模;殷禮已代表了相當高度的文明,五禮齊備而儀節(jié)漸趨繁縟。參見陳戍國,《中國禮制史》(先秦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69-176頁。。周代繼承前代文明積累,又經(jīng)周公制禮作樂*有關周公“制禮作樂”的傳說,最早見于《左傳·文公十八年》所載季文子之言,更廣為人知的出處則是《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在經(jīng)古文學者口中,《周禮》更是周公所建官政之法。近代以來,疑古之風盛行,周公制禮作樂的傳說乃至三禮的可靠性受到極大質疑,甚至被認為全部出自漢儒的偽造,影響甚大。建國來,陸續(xù)有學者對這一觀點做出修正,認為三禮中某些篇章可以與先秦古籍互證,若以三禮為全偽,則中國將無信史可言。有持中之論認為,今存三禮,雖然羼雜了不少戰(zhàn)國時代的禮制,又經(jīng)過漢朝人的篡改,但大體為先秦禮書;周公不一定是三禮的作者,但禮的設計及實施肯定是周初統(tǒng)治者所為,而主要是周公。,文物制度已燦然可觀。我們可以批評文明的發(fā)展對于人的自然本性的抑制乃至戕害,卻絕無可能拋棄歷代的積累而真的重返自然。
對此,莊子重提禮意*本文之所以先用“禮義”而后用“禮意”,是出自對《莊子》原文的尊重,對二者可能有的差異不多分析。,試圖以此消解文質之爭議。與老子反禮的主張不同,莊子從根本上是認同禮文所代表的尊卑秩序的,認為其代表了天地之間固有的規(guī)律。《莊子·人間世》認為命與義是“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的根本原則,《天道》篇則載“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莊子·天道》)[12](P116),其中透露出的無可辯駁的尊卑之意與道家另一支派的楊朱學說一味“貴生”“全生”的主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段文字而常被人們懷疑并非莊子學說。現(xiàn)代學者李鏡池、陳鼓應等先生從《易傳》與道家之間的關系闡明了《系辭》在自然觀方面所受到道家的影響。在這里,它從天道有尊卑先后之序而推及人道的秩序,正體現(xiàn)了道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維方式,與內篇《人間世》中,對“子之愛親”與“臣之事君”這兩大宿命的認同,具有一脈相承的關系。。因此,莊子所激烈反對的,就是痛恨俗世之人“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莊子·大宗師》)[12](P65),認為這反而是對真正的禮意的遮掩。《莊子·大宗師》所載“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一段,子貢認為臨尸而歌不合禮,反被孟子反、子琴張二人嘲笑為“惡知禮意”,這里的情景與對話正透露了莊子與儒者對待禮儀的不同態(tài)度。儒者認為臨尸而歌是對喪禮的漠視、對友人的漠視,是一種非禮的行為;莊子則認為人有生有死,這是天道秩序之所在,因此人應當順從天道的安排,就像幼子順從父母的安排那樣*《莊子·大宗師》載:“父母于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參見(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64頁。,這才符合與大化同流的更高層次的禮意。
四、“文質相救”的動態(tài)平衡
面對“文質彬彬”的理論設計與“文多質少”*這句話是喜好黃老的竇太后給予儒者的評價。《漢書·萬石衛(wèi)直周張傳》載:“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參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第七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195頁。的現(xiàn)實評價的南轅北轍,以董仲舒為代表的西漢儒者選擇將“文”“質”發(fā)展成為兩套禮樂制度,試圖以“文質相救”的動態(tài)平衡取代“文質彬彬”的靜態(tài)平衡,并與“三統(tǒng)說”相關聯(lián),形成一套“文質再而復”的社會歷史觀,用于指導漢代禮制的實踐。有學者認為,“文質說是一種東方獨特的文化思想,它經(jīng)歷了一個由倫理哲學、歷史哲學到文化哲學的歷史發(fā)展,最后才進入文學領域。”[16](P9~13)而在禮學的視域下,文質論從倫理哲學向歷史哲學的發(fā)展,正是文質論從禮論向禮制論的發(fā)展。
漢代儒家認為,夏、商、周三代禮之大體相因而不能變,但在具體的實踐中各有所側重,表現(xiàn)出不同的特質。董仲舒提出的三代改制質文說,通過對上古禮樂制度細節(jié)的構建,主張一種文勝則救以質、質勝則救以文、文質更迭循環(huán)的“文質互救”說。《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載:“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17](P204)“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侈員,惟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首服嚴員。鑾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鼓,用錫舞,舞溢員。先毛血而后用聲。正刑多隱,親戚多諱。封禪于尚位。”[17](P205~208)在后文中,董仲舒不厭其煩地描述了夏禮、質禮和文禮,并將一質一文、一商一夏的禮樂系統(tǒng)與有虞、夏、商、周四代的禮樂實踐相聯(lián)系,這種禮樂系統(tǒng)的追述與《禮記·表記》的記載相比,其中不乏沖突之處*《禮記·表記》以為夏屬質,親而不尊,《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則認為夏屬文,尊尊而多義節(jié);《禮記·表記》以為商屬文,尊而不親,《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則認為商屬質,親親而多質愛。,聯(lián)系董仲舒所描述的四代禮樂制度如此豐富的細節(jié),大致可以斷定,孔子時文獻就已“不足征”的有虞、夏、商禮,基本不可能在董仲舒時全盤重現(xiàn),那么很難將其所描述的上古禮樂制度視為歷史的真實。
因此,這里對于禮樂制度的“描述”(或者說是“構建”),最大的亮點在于“文”“質”不再被簡單地視為“外在文飾”與“內在品德”,而是被當作了上古禮制所表現(xiàn)的風貌的代稱:“文”是因尊尊的特質而表現(xiàn)出的文勝于質的禮樂系統(tǒng),“質”是因親親的特質而表現(xiàn)出的質勝于文的禮樂系統(tǒng);兩套系統(tǒng)文質同存,并因文質各有側重而得以命名。禮在歷史的發(fā)展中,往往會出現(xiàn)偏文或者偏質的弊端,這時就需要以質救文或者以文救質,從而加以補救損益。
這種以文、質為兩種禮制、往復互救的主張,在兩漢學者那里,成為一種共識。司馬遷在《史記·高祖本紀》中贊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huán),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tǒng)矣。”[14](P393~394)《鹽鐵論·救匱》載:“橈枉者以直,救文者以質。”[18](P400)《漢書·杜周傳》載杜欽給成帝的上書:“殷因于夏尚質,周因于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19](P2674)甚至直到東漢時期也無出其右,何休在《春秋公羊傳注》中認為:“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皆所以防愛爭。”[20](P13)乃至《春秋緯》《白虎通》等概莫能外,使得兩漢文質論在整體上表現(xiàn)為“文質相救”、往復循環(huán)。
以董仲舒為首的西漢儒者繼承了先秦儒家所使用的文質論的概念范疇,將“文”“質”發(fā)展成為兩套禮樂制度,試圖以“文質相救”的動態(tài)平衡取代“文質彬彬”的靜態(tài)平衡,是理論上的創(chuàng)見,也從另一個角度彌補了先秦儒家禮論的不足。然而,前面提到,“文家”與“質家”的區(qū)別,多是體現(xiàn)于對坐而食與同坐而食、制爵三等與制爵五等、封壇上位與下位等具體而微的細節(jié),從董仲舒對“質家”的描述中,很難看出有虞禮、商禮之質樸,反而對其繁復的禮制印象深刻。漢代學者多埋首于文質禮制論的構建,使禮學研究從禮論轉入禮制論,促進了禮在制度上的落實,卻在客觀上加重了儒家禮學的“文繁”之弊,有待后來者的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