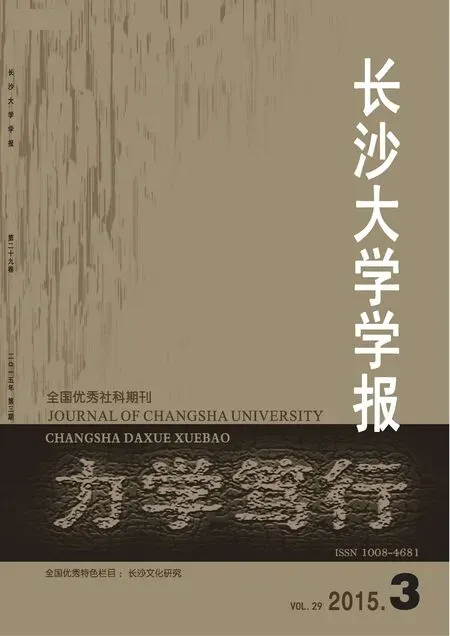近代以來自然科學發展視域下的上帝觀變遷——從終極因到終極關懷
韓先虎
(山西機電職業技術學院思政部,山西長治046011)
一
近代科學史并不與世界近代史同步,而是以1543年日心說的出現為劃界。在日心說之前,科學和宗教可以說還談不上沖突,因為科學本身都沒有獨立性,哲學、科學、宗教在世界的終極原因方面甚至擁有相同的權利和資格,如古希臘的自然科學對世界起源問題的回答本身就是以自然哲學的形式出現的。發展到近代,科學開始脫離宗教和自然哲學的母體,表現為注重觀察實驗的作用,提倡數學方法、邏輯推導和實驗方法的結合,自然科學所得出的結論與宗教中許多原有的結論相矛盾,而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出版,成為劃時代的一件大事,作為結果,近代自然科學對宗教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上帝被賦予新的理性化和自然化的內涵,這當中有兩種值得注意的方向。
其一是唯理論的上帝觀。唯理論依賴的是理性自身的演繹,甚至都不需要借助經驗材料,它只需要在純粹理性自身的推演中就可以抵達“理性的普遍”。如笛卡爾以“我思故我在”這個內在自明的觀念為基礎,開始演繹上帝的概念:自我的完滿是有限的,從自我這個有限的完滿中不可能產生出“上帝”無限的完滿性,所以自我只能是來源于上帝。笛卡爾的上帝是理性化推演和改造的產物,以追求明證確定的必然性的最高保證。斯賓諾莎反對笛卡爾的二元論傾向,認為實體只能是一,而不能是多,只有自因的、無限的、唯一的東西才能被稱為實體,那么這種實體只能是作為整體的宇宙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說上帝和自然就是一回事。這樣,上帝成為無矛盾的宇宙的內在因,上帝與自然并不表現為分離關系,我們探尋自然就是探尋上帝,神學與科學都可以視作追尋同一實體的兩種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可以看成是基督教與科學之間進一步作用影響和達成調解的產物。斯賓諾莎描述的上帝,實在性己經被消解,完全是非人格化的,他似乎并不關心人類的命運,只是以自身的規律形式而運行,上帝的創造被解釋為自然的自我生成與自我繁衍,它純粹只是與自然一致的客體而己。
第二種是自然神論的上帝。一個在創造中不講求規律的上帝似乎和荒謬、不可思議沒什么兩樣,而一個創造中必然依照某種規律的上帝才是讓人信服的,上帝應該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等非人格的存在。這種討論客觀上和自然科學的發展成果相一致,自然神學充當了科學和宗教的折衷者:傳統神學認為上帝創造了自然,而且創世后,上帝繼續在自然中行動。牛頓力學則表明世界一經創造,在上帝的原初動力的推動下就開始了有秩序的運行,其運動方式表現為力學規律式的運動,上帝此后再也不必接手,而可以采取一種放任的態度,宇宙自身可以按照牛頓所揭示的力學的規律永恒運轉。神性等同于理性秩序和理性和諧,在自然神論中正統神學與牛頓力學微妙地融合了。
這一時期的上帝觀向理性過渡,排斥人格神的特征,在一些情況下也為科學理論充當了理論預設和解決難題的救急神,指向宇宙、世界乃至人生的終極原因。正如黑格爾所指出的,“上帝在近代哲學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古代哲學中大得多。”[1]
二
十八世紀,自然科學有了更為全面深遠的發展,在物理學的帶動下,化學、天文學、生理地理學等學科迅速跟進,這些科學不僅帶來知識的激增,技術文明也開始體現出了強大的實際功用,最富代表性的事件是1776年蒸汽機的改進,拉開了工業革命的大幕,人們更傾向于接受客觀的、經驗的事實,人們更樂于用新的直截了當的科學理論來做出自然的解釋。甚至連自然神論中的上帝似乎也變為一種可有可無的假設,如拉普拉斯明白確定的表述“我不需要上帝這種假說”,這也意味著以拉普拉斯為代表的唯物主義者開始批判自然神論者。人類還需要這種認識論假設意義的上帝嗎?如果不需要,那么上帝還承擔何種功用?在這一論題的討論中,康德的宗教思想進路是另辟蹊徑的。
康德的認識論可以看成是對休謨懷疑論的理論回應,正是休謨的冷峻啟發了康德。休謨將經驗論的原則貫徹到底,他認為知識只能來源于人的知覺,而人對上帝、物質實體、精神實體全都不可能有知覺,也不可能形成關于它們的任何知識。康德一定程度上贊同休謨的觀點。不過,康德并不打算完全驅逐上帝,上帝還是有其存在的合法性的。首先,上帝是一種理念性的構想,是人們從外部事物和人的思維中概括和提升出來的,是人性自我完善的產物,起著引導人的價值和目的論的作用;從實踐理性即道德角度而言,為了實現道德與幸福的結合達到至善,必須假設上帝的存在作為保證,上帝是在實踐理性的推論中得出來的。“我現在主張,理性在神學上的單純思辨運用的一切嘗試都是完全無結果的,并且按其內部性來說毫無意義的,但理性的自然運用的原則是根本不可能引向任何神學的,因而如果我們如果不以道德律為基礎或用道德律作引線的話,就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什么理性的神學了。”[2]上帝存在是實現人類至善、人們自覺向善的邏輯假定:上帝存在只是實踐理性的一個必要的“懸設”[3]。在康德這里真正實現了宗教與科學的分離,從此,科學的發展無需在宗教中尋找終極因支持,因為在康德看來,這根本就是一種先驗的幻相,知識不能去觸碰超經驗領域。從結果上看,康德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批判也起到了解構傳統基督教的作用:上帝像物自體一樣不可能被理論理性所認識,而只能在實踐理性的領域中被相信。康德實現了一種轉變,為宗教開辟了一個完全屬于理性和內心世界的領域,實現了“神學的人學化”,為真正的信仰開辟了道路。從反面上看,康德的上帝已經沒有了實體和自然方面存在的理由,只是理性演繹的結果。這必定會一定程度上會導致價值的無所依托,如雅可比在致費希特的信中就指責康德哲學必然會導致虛無主義[4]。
的確,康德的上帝觀也有其較為單調的一面,由于強調理性的運用和作為實踐理性的預設的作用,總體上偏于知識論,而基本不涉及存在論維度,這也為包括批評者在內的后繼者留下了廣闊的空間。施萊爾馬赫算是最早成功地從理論上回應康德哲學的神學家。“康德對于現代宗教思想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沒有一個人比康德的影響更大,但施萊爾馬赫可能是個例外。”[5]施萊爾馬赫受康德哲學的影響,但又不滿意康德對理性的過度強調,他認為康德的上帝觀說到底缺乏宗教性,缺乏體驗感性,表面上對上帝敬重,而實質上卻是最瀆神的思想。施萊爾馬赫認為,宗教不是宇宙論,上帝不是人類所畏懼的創造者、主宰者;宗教也不是形而上學,不是為了某種倫理體系之不得已做出的預設,不應該表現為刻板的道德要求,宗教的本質既不是思維也不是行動,而是人在“絕對依賴感”中呈現出來并能被體驗到的無限者,這是每一個具有宗教體驗的人都會產生的切身經驗與感受。同康德強調理性、貶低情感相區別的是,施萊爾馬赫注重對直觀和情感的強調,直觀負責把握對象的內容,情感始終伴隨直觀。“宗教的情感基本是對人的行動力量的麻痹,它邀請人享受寧靜,沉醉于寧靜。”[6]宗教最高貴的部分是虔敬性的情感,在這種虔敬的感受之中,上帝與人在心靈中會聚,這是一種無限與有限、暫時與永恒的交融方式,這才是宗教之為宗教的根本。
三
施萊爾馬赫的論著在當時并沒有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沒有能產生出應有的社會影響,在隨后的歷史發展中,科學一路高歌猛進,如同尼采所言:“上帝死了”。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系統地論證了生物進化及乃至被視為萬物靈長的人的進化理論,對于宗教神學的上帝創世說真正構成了致命打擊。二十世紀,科學給出的理論圖景又有新的突破,從宏觀至微觀,從宇宙至人體,人類迎來了科學技術一體化的空前發展時代,宗教不斷地退卻,不過在宗教的退卻中,人們發現科學似乎并不勝任無限的價值觀這一任務,人們能使用科學原理來規劃戰爭,人們也能用科學原理發明致命武器,使戰爭的殺傷效率變得更高,但是人們唯獨不能從科學中獲得人類為何會發動慘無人道的戰爭的答案——科學只能告訴人們“實然”的原理,卻并不能提供“應然”的道理。科學就這樣以不可思議的方式和虛無主義、商品化拜物教微妙地結合于一起,西方社會在“上帝之死”后又面臨“人之死”的問題,人難以找到價值根據和意義的依托,心靈的不安依舊伴隨著時代中每一個存在的個體。
現代人不再需要傳統意義上的宗教,但是一方面,現代人又仍然無法擺脫宗教,從生命的本能沖動層面來看,現代人仍然需要宗教,這是西美爾的基本結論。西美爾區分了“宗教”與“宗教性”,“宗教”是作為宗教活動的物化或者說是外化形式,“宗教性”則是指人的宗教虔誠、情懷等內在性的東西,是人生命的本能沖動。西美爾認為,上帝概念的存在和科學并不沖突,上帝是社會整合性的代名詞,在現代社會高度分化的生活中,“個體只有通過與自己的上帝的關系才能找到自己確定的身份(認同)。”[7]宗教的本質不在于外在的方面,而在于宗教性這樣內在的形式,宗教是人之生命的“內在本質的先驗性基本形式”[8]。沒有這種形式,生命就沒有演進,生命就無法表達自身。
宗教神學家保羅·蒂里希則試圖超越哲學和宗教的界限,在堅持神學的立場的同時,也借鑒了存在主義的思想理路,蒂里希認為,人始終可能面對空虛、無意義的威脅,只有深入到人的存在問題這樣的本體結構中才是唯一途徑,在此當中,蒂里希發現了人處于非存在性(即有限性)焦慮這種深層困境,提出要戰勝這種困境,唯有通過“存在的勇氣”,因為,人意識到、籌劃自己“存在”是以意識到了“非存在”的懸臨為前提的,存在的對面就是非存在,“非存在”的威脅時時都需要人去面對,存在的勇氣就是信仰的體現。信仰的指向就是終極關懷的指向,蒂里希由此引出他的終級關懷的思想,“人無條件地關懷著那么一種東西,它超越了人的一切內外條件,限定著人的存在條件。人終極地關懷著那么一種東西,它超越了一切初級的必然和偶然,決定著人終極的命運。”[9]]終極關懷概念的提出者是蒂里希,但并不應視為全新的概念和蒂里希的專利,其精神一直存在于既往所有哲學和思想所追求的人的超越性問題里,不過這恰恰表明在蒂里希這里,宗教完成了一種在面向人的現實生活中尋求超越性的轉向,宗教將是這種完成超越性的最高表達。在蒂里希這里,宗教終于落實到了人的終極關懷。蒂里希試圖表明,只有人的存在和存在的意義才是宗教所關注的內容,人可以通過宗教的路徑最大限度地實現自身的超越本性。人唯一值得信仰的就是這種“存在的勇氣”,“在對命運和死亡的焦慮中我們體驗到這種力量;在對空虛和無意義的焦慮中我們看到這種力量;在對罪過和譴責的焦慮中我們感覺到它的作用。把這三重焦慮承擔起來的勇氣一定植根于這樣一種存在的力量之中:它比自我的力量強大,也比人處于其中的世界的力量強大。”[10]在蒂里希看來,這種存在的勇氣只能來自超越的上帝,使得人能夠不受非存在威脅、能夠直面虛無,只有“存在—本身”的自證才能克服“非存在”的威脅,有限性是宗教存在的理由,“上帝”在這里承擔了人類超越追求的至上目標,是對人的存在隱含問題的全部回應,也承擔了人類越出生存困境的終極力量的功用。蒂里希使用了海德格爾對“存在”和“存在者”之間的區分方法,認為“存在—本身”既不指某一特定的事物,也不指稱全體事物的集合,所以不能用日常的語言來描述,但卻是使一切事物得以存在的基礎和力量源泉。在蒂里希看來,“上帝”就是這種“存在—本身”,就是超越一切名言領域的有神論的上帝,就是“超越上帝的上帝”。因為,肯定上帝存在同否定上帝存在一樣,都不是適合描述上帝的語言,都是把上帝看成具體的存在者了。
無論現代人怎樣殺死上帝,無論人們如何混跡委身于科學技術的庇護、逃避本真的存在和自由,都無法從根本上回避人之如何去存在問題的終極嚴肅性,生命本能地又需要宗教,人從根本上就存在著對終極關懷的宗教屬性。也許從某種意義上說,宗教是人類存在和命運之本質的代名詞。在科學強盛的同時,上帝觀自身也在發展,并在科學的挑戰中得到了自身的洗禮,它不再承擔解釋世界方面的終極因,卻負擔起人的心靈完善和終級關懷的功用。如果我們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進行解讀,這種上帝觀的轉變實際上表明在當代西方社會人對人的作為實踐活動之組成部分的精神活動的日益重視,并且有把這種精神活動本體化的傾向,實際上,精神生活并不能完全取代社會實踐,也并不存在人類可以達到完滿、完善與永恒的信念,人的本質在于人的實踐性而不在于精神性,真正的途徑在于在社會實踐中實現人的境域改善和人的類本質的不斷生成。
[1]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卷4)[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2]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康德.實踐理性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劉森林.物與意義:虛無主義意蘊中隱含著的兩個世界[J].中山大學學報,2012,(4).
[5]利文斯頓.現代基督教思想(上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6]施萊爾馬赫.論宗教[M].鄧安慶,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8]西美爾.現代人與宗教[M].曹衛東,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9]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0]蒂利希.蒂利希選集(上)[M].上海:三聯書店,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