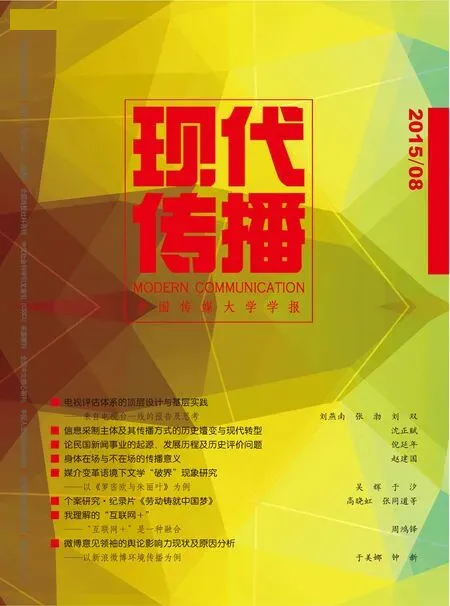論藝術傳播的節日特質
■ 廖維
論藝術傳播的節日特質
■ 廖維
本文立足藝術,通過分析節日的特質來探究藝術與節日之間的本質關系。節日作為藝術的生發與傳播的重要媒介環境,促進藝術的發展和傳承。受到伽達默爾從時間本體研究藝術的節日特征啟發,本文更進一步對節日時間、節日空間以及節日精神進行深度剖析和挖掘,多方面闡述藝術傳播的節日特質。
藝術傳播;節日時間;節日空間;節日精神
古圣先賢關于藝術與節日之間的關系大多立足于節日而對藝術進行分析、判斷,較少立足于藝術來談論節日。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Plato)在《對話錄》法律篇中,曾判斷過藝術與節日的關系——藝術是節日的伴侶。“神靈憐憫人們的苦難,因此用有規律的節日規劃人們的生活;并且,以繆斯、阿波羅和狄奧尼索斯等神靈作為節日的陪伴,通過這樣的神圣陪伴,社會就會恢復它應有的秩序。”①繆斯、阿波羅和狄奧斯尼索斯都代表著藝術,柏拉圖認為藝術是助力節日,幫助人們度過困難和規劃生活的手段。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說,節慶只有通過藝術才會出現。②德國哲學家尤瑟夫·皮柏(Josef Pieper)在談論節慶與藝術的關系時,提出藝術是節日的媒介,他認為:節慶只有透過藝術媒介,才能反映其最深刻核心——對世界之禮贊;“一個沒有歌唱、音樂和舞蹈的節慶,一個沒有有形可見慶祝形式的節日,一個沒有任何藝術氣氛點綴的節慶,都是無法想象的。”③
從藝術本體來談論節日的,以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為代表。他在《美的現實性——作為游戲、象征與節日的藝術》一文中,詳盡地論述了藝術所具有的游戲、象征及節日的特征。在藝術的節日特性中,他主要從時間本體上指出了藝術的時間與節日時間的相似性④,形成了人們進行藝術欣賞和參加節日儀式時類似的心靈感受。他還指出“過去時代的藝術只有通過時代的過濾器和那種保持著生命力,激發出生命力的傳達,才能傳遞給我們。”⑤而節日便是這種保持生命力,激發生命力信息的載體。同時,他還說,“節日,它是要重新建立所有的人相互交往的契機。”⑥也就是說,節日時進行的藝術交流,是一種“大眾”傳播,它的受眾面是“所有人”。
受到伽達默爾的啟發,本文立足于藝術,通過分析節日的時間特性、空間特性和節日儀式的精神特性等特質,探討節日是否創造了藝術得以生發和傳播的條件。
一、藝術傳播的節日時間特性
節日時間具備以下特性,故更容易滿足藝術傳播的時間條件。
第一,閑暇前提。節日里不必工作,是一種對現實的超越,脫離出為生計奔波的生活常態,能夠去認識世界,感受生命,思考人存在的理想以及價值所在。這就是節日帶給人的時間權力,體現了節日的時間本質——閑暇(leisure)。閑暇是人在節日時的一種基本狀態。只有處于閑暇的狀態,人才能真正享受節日。藝術創作和欣賞都是在閑暇時產生的,節日也給所有人提供了這樣一種休閑機會,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參加節日活動,有欣賞藝術的可能。節日時間不工作,必然會使實際利益受損,享受節日,放棄了一天勞動的收獲,也意味著奉獻出工作的成果。“奉獻在本質上就是一種犧牲,因此它跟功利正好相反。”⑦所以,節日所具有的非功利性與藝術的非功利性正好切合。閑暇的節日時間相當于藝術審美中的虛靜,必須有這樣一種基本狀態,才會達到凝神觀照,方利于創作和感受藝術作品。
第二,審美頓悟。伽達默爾認為,節日時間是一種充實而不空洞的體驗。對于一段日常時間而言,不同的人可以將它用作不同的事情。節日時間則不同,人們不再“為了某物”疲于奔波,而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中,感受自己生命的“此在”,成為一種實現了的屬己時間。節日關注人內心情感的表達與交流,因此具有“屬己”的特性,是生活中“充滿”“神圣”的人生“專屬”時間,所以觸碰生命情感的機緣多,容易觸發創作靈感,實現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體驗的溝通與交流。而且,節日時間源自于歷史和信仰的神圣性,以及節日時間突破了當下無意義的未來性,亦強化了審美頓悟。節日將人們聚集在一起,彼時彼刻成為所有人的屬己時間,人不僅面對自己的內心,還實現了與他人情感的共鳴與交流,形成情緒的放大,感受的強化,更容易實現審美的共鳴與頓悟。
第三,傳承創新。節日時間的重復性為藝術傳播創造了展示平臺,實現了藝術的多次傳播。對于藝術而言,多次傳播實現了人們對藝術作品的多次解讀。對一部藝術作品而言,人們關注度的積累形成了它流傳的基礎。而一部藝術作品之所以得以流傳,其條件便是它的信息能盡可能多地到達受眾。當節日時間中反復出現一個藝術主題時,它必然會受到人們更多的關注。多次傳播意味著傳承,為了保證藝術傳播的效果,必然要求進行藝術創新。其中包括同一藝術主題可以進行不同藝術門類,甚至不同藝術表現手法的多次創作。每一節期,節日儀式總是被期望和往年有所不同,對往年的形式有所突破。藝術在這種創新的內在動力作用下,在內容和技巧形式上不斷挑戰過去突破自身,實現發展。
二、藝術傳播的節日空間特性
節日作為“日子的節點”,其時間的重要性不容置疑,節日空間對藝術傳播的作用亦不可小覷。
第一,空間聚合藝術受眾。節日是所有人都參與的活動,所以節日中的藝術傳播獲得了天然的受眾,形成藝術的群體傳播。那么,群體傳播便會對空間有相應的要求。首先,需要有一個寬闊的公共場合,可以容納很多人;其次,空間有地域限制,一般只作用于該文化或社會構成中的個體,而對于偶然路過,偶爾停留的人不具備控制力。節日中藝術傳播的受眾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節日的主辦者,他們要想盡一切辦法凸顯節日的主題和精神。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以藝術的手法去裝飾空間,以此將節日空間與平日空間區別開來。第二類受眾是普通的參與者,他們是節日活動的主體。由于沒有參與前期的策劃,對于節日空間一無所知,直到節日當天,才第一次感受和體驗節日空間的氛圍。這樣的體驗是新鮮的,豐富的,具有觸發性,并且容易受到周圍人群情緒的影響而增大。第三類是嘉賓。嘉賓人數少卻有著相對高的社會地位,他們的社會影響力大小決定了節日的重要性強弱。節日空間的布置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為了滿足嘉賓的觀點和品味,他們的感受與評價影響著節日活動的內容設置以及節日中藝術的發展方向。
第二,藝術裝飾節日氛圍。裝飾使節日空間變得突出,與生活空間區分開來。節日空間的裝飾因其含有人類的專注力與情感,而獲得其獨立的存在價值。節日裝飾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往往隨著節日、空間以及社會的需求和人們審美觀念的變化而變化。一個無序的時空通過裝飾的輕重、多少的布局,顯示出了空間的主次功能,從而也在人們的行動過程中,彰顯了時間的秩序。有些節日裝飾事物本身已成為一種藝術,比如,中國節日中的窗花、剪紙、年畫以及對聯(春聯)等等。由此,藝術便與裝飾一起,成為塑造和劃定節日空間,營造節日氛圍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第三,節日專有藝術空間。在物質生活匱乏的時代,藝術對于先民是可貴而珍稀的,往往只有在豐衣足食的時節才能實現。這種前提的實現對于先民來說是神圣和不易的,因而慶祝活動的舉行也會選擇具有神圣地域特征的空間。正如節日的主要儀式活動往往會在教堂、廟宇、宗祠等地方舉行,人們也往往在這些地點的部分區域見到藝術的表現形式,比如,教堂里的雕塑、壁畫、管風琴和唱詩班,廟宇里的塑像,以及宗祠建筑的樣式等等。隨著節日的發展,那些專門為節日中藝術的展示功能而建造的建筑也獲得了發展,比如中國村落中的古戲臺,西方戲劇演出的劇院等等,在人類歷史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它們都是藝術展示、發展的專屬地。
三、藝術傳播的節日精神特性
如果說節日包括節日時間、節日空間和節日行為(儀式)三部分的話,統合這各部分的,是節日精神。這種精神,通常被叫做“節日氛圍”,用巴赫金(Бахтинг,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的話叫做“無處不在的世界感受(gala spirit)”。節日精神主要是通過節日儀式的人類行為體現。節日精神的存在增強了藝術信息的節日特質,影響了藝術傳播的效果。
德國社會學家涂爾干(émile Durkheim)指出(節日)儀式的本質在于它有種激發人們生活繼續下去的精神動力。⑧這也正是節日精神的內核所在,為了保證一代又一代的人們能克服困難生存下去,保證精神力源源不斷地生成,所以節日必須反復舉行。藝術之所以能與節日緊密相連,本質即在于它同節日一樣,有追求自由的理想,它能夠塑造人心目中理想的美,通過呈現人世的美好,幫助人們渡過和緩解現世的苦難,感受和肯定生命的價值。需要指出的是,藝術側重個體的精神感受,而節日強調群體的共同感受。在節日中進行藝術傳播,就是要將這種個體的精神感受通過藝術傳達給每一個人,形成群體的共同感受。藝術的節日精神主要體現為復活節和狂歡節精神。
第一,藝術的復活節精神。復活節精神⑨是人們針對死亡的現象,保持的對于生命所秉承的一種態度,它象征著“重生與希望”。從遠古時代起,死亡現象就較之其他現象更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為了理解這種死亡現象,寄托對于逝去的人的情感,人們發現了生命的輪回。比如,每一天太陽的東升西落,每個月月亮的盈虧圓缺,每一年,四季的交替變換,這些變化因為同生活生產息息相關而引起了人們強烈的情感,這種情感喚起他們的行動。比如,“埃及人就有促使旭日東升的咒語,每天都要誦念。”⑩
人們不知道人死以后會怎么樣,但活著的人推測人死后也會像天象與植物一樣,有自己的輪回。這種觀念被表現在節日行動中,在特蘭西瓦尼亞地方的基督升天節上,就有象征死而復活的巡游儀式。11世界各地普遍常見的春天慶典也是在這一層意義上被確立的。“對于農民們而言,……種子下地,就等于死亡,播種就等于下葬,‘播下的種子,惟有死去,方能復蘇。’死亡和葬禮過后,人們就會對復活和新生翹首以盼。”12死、生被人們高度關注,并在每一次節日儀式的不斷舉行中反復思考,它成為藝術表現的永恒不衰的主題。在尼采的“悲劇起源——酒神祭祀節”中,酒神狄奧尼索斯的名字也表達了這一重生的概念。“希臘人望文生義地把酒神(Dithyrambos)曲解為‘雙重門之王’,因為在他們的語言中,thyra就是‘門’的意思。這種解釋可謂大錯特錯。現代語源學的研究表明,Dithyrambos的意思是神圣的跳躍者、舞者、生命的賜予者。但是這種曲解卻也確實耐人尋味,因為它表明希臘人相信酒神就是再度誕生。”13關于狄奧尼索斯誕生的傳說也告知人們狄奧尼索斯經歷了死亡,并且重生不死。也許這也正是人們欣賞悲劇以后能得到“凈化”(katharsis)的感覺的本質所在吧,悲劇給人的,其實不是死亡,而是重生的希望。
第二,藝術的狂歡節精神。前蘇聯著名文藝理論家巴赫金有專著論述“狂歡化詩學”理論。巴赫金說,“狂歡節的世界感受,具有強大的蓬勃的改造力量,具有無法摧毀的生命力。”14這也正是節日精神的強有力體現。
節日,總是歡樂的,這種歡樂是一種對生命力量的釋放,是個體對長期服從于社會倫理道德的禁忌行為的一種調節,所以,它帶有突破、反抗和否定的“狂”的特色。對于個體的人來講,“在狂歡中所有的人都是積極的參加者,所有的人都參與狂歡戲的演出。……人們過著狂歡式的生活。而狂歡式的生活,是脫離了常軌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是“翻了個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15事實上,“每一節慶本身都隱藏著‘至少一點點的過度’。”16狂歡不僅僅是狂歡節特有的產物。任何一個節日對于個人的行為來講,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狂歡的特征,就算是喪葬儀式也是如此,比如中國鄉土的葬儀,在人逝世以后都會大放鞭炮,敲鑼打鼓宣告天下,更有甚者會邀請樂隊、歌隊和舞蹈隊來娛樂親人朋友,乃至素不相識賓客。17
藝術主要追求這樣幾種具有典型狂歡化特質的節日精神。(1)平等。每個人都能過節,節日時間和活動內容對于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值得一提的是,在狂歡節中,平等在社會關系中得到了“一反常規”地突出。“在狂歡節上大家一律平等。……支配一切的是人們之間不拘形跡地自由接觸的特殊形式。在封建中世紀的嚴格等級制度背景上,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等級和行會隔閡背景上,這些人被不可逾越的等級、財產、職位、家庭和年齡的壁壘所分割。人們之間這種不分彼此、不拘形跡的自由接觸,……成為整個狂歡節的世界感受的本質部分。”18平等,是人們一直關注和追求的社會理想,是藝術理想生活化的鮮活形象,以及孜孜以求的永恒主題。(2)自由。自由以非官方的民間化呈現,它是狂歡行為的另一特征,它主要體現為顛覆和否定。“這種世界感受,同一切現成的東西、完成性的東西相敵對,同一切妄想具有不可動搖性和永恒性的東西相敵對,為了表現自己,它所要求的是各種動態的‘普羅透斯式’的閃爍模糊的形式。狂歡節語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征都充溢著更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著對占統治地位的真理和權力的可笑相對性的意識。……必須強調指出,狂歡節式的諷擬遠非近代那種純否定性的形式上的諷擬,狂歡節式的諷擬在否定的同時又有再生和更新。一般說來,民間文化完全沒有單純的否定。”19在狂歡節的民間特性中,有很多典型的元素,包括物質(肉體)因素,諷擬,降格,游戲等等,巴赫金歸納出4個最具代表性的特殊范疇分別是親昵的接觸、插科打諢、俯就和粗鄙。這些狂歡式的范疇,本質上都是存在于人們生活中民間化的鮮活特征,都是“不能上臺面”的非官方的行為,它們是普羅大眾為了爭取與權力階層相對等的權力而做出行為表達,是一種關于“自由”的表達。(3)更生。更生(rebirth)的意思是重新得到生命,比喻復興,再生。與更新(update)不同,更生更強調生命的死亡與新生,它意味著事物的交替與變更。它以狂歡節中主要的加冕脫冕儀式為代表。“國王加冕和脫冕儀式的基礎,是狂歡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這個核心便是交替與變更的精神、死亡與新生的精神。”20“加冕本身便蘊含著后來脫冕的意思,加冕從一開始就有兩重性。……狂歡式里所有的象征物無不如此,它們總是在自身中包孕著否定的(死亡的)前景,或者相反。誕生孕育著死亡,死亡孕育著新的誕生。”21
狂歡節精神對于藝術來說,其實質是人類對現實的反抗,對于平等、自由、更生的追求,對于生命的把握,對于自我價值實現的追尋。
綜合上述,正因為節日所具有以上各種特質,和藝術有著共同的人本聯系,才連接了藝術與節日,這也正是藝術傳播具有節日特性的根源。節日與藝術在本質上都是人類精神的力量源泉。人類通過舉行節日和藝術的活動,獲得心靈休憩和情感交流的條件,從而取得克服困難、持續發展的精神動力。
注釋:
① Plato,(Laws 653 d 1).原文如下:The gods,therefore,had compassion for their hardships of men and punctuated their lives with the rhythm of festivals;and as companies in their festivals they gave them the Muses,Apollo,and Dionysus,so that through the divine companions in the community the order of things might be restored(653c-d).中文為本文作者自譯。
② 《實踐神學》Praktische Theologie,p.73.《每一節慶都在藝術范圍內》同前,P.839。轉引自[德]皮柏:《節慶、休閑與文化》,北京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57頁。
③⑦16 [德]皮柏:《節慶、休閑與文化》,黃藿譯,北京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57、18、19頁。
④⑤⑥ [德]伽達默爾:《美的現實性:作為游戲、象征、節日的藝術》,張志揚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83、88、16頁。
⑧ [法]愛彌爾·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東、汲喆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三卷第四章積極膜拜。
⑨ 這里的復活節并不僅指西方復活節的主復活日(在每年春分月圓之后第一個星期日),而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具有“重生與希望”精神的同類節日的統稱。
⑩(11)(12)(13) [英]簡·艾倫·哈里森:《古代的藝術與儀式》,劉宗迪譯,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8-39、42、51、66頁。
(14)(20)(21) [前蘇聯]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白春仁、顧亞鈴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178、179頁。
(15) Chrysostom:《論圣神降臨節》De sancta Pentecoste,hom.I.Migne,PL 50,455.轉引自[德]皮柏:《節慶、休閑與文化》,黃藿譯,北京三聯書店1991年版。
(17) 筆者于2014年夏,有幸親自在河北省樂亭縣看到了這種儀式。
(18)(19) [前蘇聯]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李兆林、夏忠憲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頁。
(作者系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北京市藝術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責任編輯:張國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