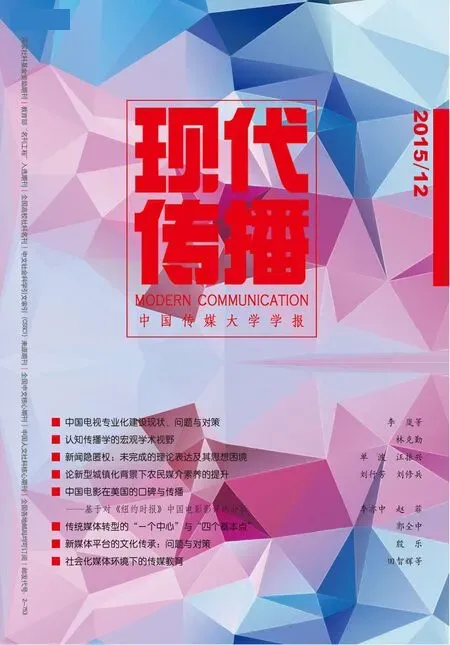新媒體語境下電視紀錄片話語方式衍變探析*
■ 武新宏
新媒體語境下電視紀錄片話語方式衍變探析*
■ 武新宏
本文從敘事學、傳播學角度,分析新媒體環境對電視紀錄片敘事的影響,從敘述內容、敘述角度、敘述方式等方面,闡述新媒體環境下電視紀錄片話語方式的衍變,以期為進一步提升電視紀錄片創作藝術感染力及影響力,做些有益探索與思考。
新媒體語境;電視紀錄片;話語方式
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在《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中指出,任何材料都適宜于敘事。敘事存在于一切時代、一切地方、一切社會。①作為非虛構藝術形態的紀錄片也存在敘事。從誕生之初盧米埃爾的《水澆園丁》《火車進站》到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納努克》,以至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國》《與全世界做生意》等中國電視紀錄片作品,一直在用真實素材講故事。只是在不同時代,由于話語環境不同,敘事的話語方式有所改變。
新媒體(New Media)作為概念最早于1967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網(CBS)技術研究所所長戈爾德馬克(P.Goldmark)提出。但在中國被廣泛認知與運用則是在2005年以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新媒體”定義為,“以數字技術為基礎,以網絡為載體進行信息傳播的媒介。”由此,新媒體可以理解為是繼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之后出現的新形媒體,是利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通過互聯網、無線通信網、有線網絡等渠道,以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服務的傳播形態和媒體形態。新媒體以信息交流的互動及時、信息內容的海量共享、信息呈現的多媒體與超文本,以及信息傳受的私密化與個人化,影響著媒介話語環境及媒介生存環境。
最明顯的改變是傳受方式的移動化、傳播內容的微型化與碎片化。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6月24日發布的《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5)》顯示,中國網民利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到85.8%,新媒體應用正在向“微傳播”轉型,媒介融合提速。在此媒介環境下,包括電視在內的傳統媒體,在運營策略、傳播理念、制作方式及傳播渠道等方面,都需作出相應調試與改變。紀錄片一直在探索提高關注度與影響力的方式與方法,從2011年1月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開播至今播出的中國電視紀錄片作品來看,從文本分析角度而言,主要的改變表現在三個方面:話語內容的非虛構堅守與宏大主題回歸、敘述角度的多重凝視與復合敘述、敘述方式的多樣化與行動性呈現等。
一、話語內容:非虛構堅守與宏大主題回歸
從傳播學角度講,媒介有引導輿論、監測環境、傳承文明的價值與功能。新媒體環境下,傳播渠道與傳受方式發生諸多變化,但內容的價值性與可信度依然是高質量傳播的核心競爭力。新媒體固然有信息海量、互動及時等優勢,但其傳播內容存在虛假信息、垃圾信息甚至有害信息的可能性比較大。網絡視頻、網絡自制劇等視頻內容也不同程度存在內容良莠不齊、邊緣化、低俗化等現象。紀錄片在內容方面則具有真實、客觀等天然優勢。
1.非虛構堅守
紀錄片(Documentary)從本源上講,是指形象化的文獻,是歷史敘述的影像參與。1932年英國紀錄片大師約翰·格里爾遜發表論文《紀錄片的第一原則》指出,紀錄片是“對事實新聞素材進行創造性處理”的影片,而“對自然素材的使用,是至關重要的標準。”②一般認為這是對紀錄片最早的定義。1979年美國教授編寫的《電影術語詞典》認為,“紀錄片,一種排除虛構的影片,具有一種吸引人的、有說服力的主題或觀點,但它是從現實中汲取素材,并用剪輯和音響來增進作品的感染力。”由此奠定了紀錄片“非虛構”的本質屬性。紀錄片取材于真實生活或曾經發生的歷史事件,有權威的信息來源,注重內容的教育功能、社會意義及審美價值。
進入新世紀后的中國電視紀錄片,紀錄理念多元,增加人物扮演以及數字再現等表現手法,無論取材歷史還是現實,內容的“非虛構”屬性與“真實”底線一直堅守。出現《活力中國》《歸途列車》《舌尖上的中國》《絲路,重新開始的旅程》等一系列優秀作品。2015年5月播出的《與全世界做生意》取材于現實生活,展現中國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拼搏與奮斗,每一個人物、每一個故事都來自現實生活,作品用真實的故事展示中國人融入世界的艱辛與勇氣。6月播出的《貝家花園往事》取材于歷史,通過“現實中人”對歷史資料的尋找與還原,展現曾經發生在中法之間的重大歷史事件,以個體目光透視時代風云,以真實史料呈現人物的家國情懷與精神追求。
2.宏大主題回歸
新媒體環境下,紀錄片題材內容也體現出對國家話語、宏大主題的回歸。這是國家處于復興與崛起時代的必然。由于非虛構的本質屬性,任何時期,紀錄片都發揮著意識形態宣傳與引領的作用。中國紀錄片題材內容的變化,隨時代演進而改變。1950至1980年代整整30年時間,中國紀錄片側重國家話語、宏大主題,對領袖、英雄及國家大事等內容多有關注。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慶典紀實》《毛澤東出訪蘇聯》《紀念萬隆會議》,等等。19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帶來平民意識的覺醒,紀錄片把鏡頭對準普通大眾,“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如《沙與海》《藏北人家》《德興坊》等。新世紀以來,特別是2011年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開播以來,紀錄片有意識地進入主流視野,重新回歸國家話語,體現出對國家復興、民族崛起重大主題的關注與呼應。從《旗幟》《辛亥》《豐碑》《我的抗戰》,到《舌尖上的中國》《超級工程》《大國重器》,再到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系列作品《東方主戰場》《讓歷史告訴未來》等,題材內容涉及歷史政治重大事件、科技文化國家重點工程、經濟建設國家策略等,具有突出的主流價值性與國家話語特征,體現出鮮明的時代色彩與社會責任意識。這是作為傳統媒體的電視紀錄片在數字化時代生存及擴大影響力的內容優勢所在。
二、敘述視角:多重凝視與復合敘述
敘事者需要選取一個特定的視角進行言說,敘事才能鋪展衍生。敘述視角是敘述者對所敘人物、事件進行觀察與講述的方位與角度。它不是附屬物,相反,“在絕大多數現代敘事作品中,正是敘事視角創造了興趣、沖突、懸念乃至情節本身。”③每一視角的選擇都寄寓著敘事者的價值判斷、情感取向和審美追求。法國電影理論家克里斯蒂安·麥茲(Christian Metz)認為,“一個影像的存在本身表明它是經過某些敘述人理性的選擇與安排的,無論那是導演的、作為語言客體的電影本身的,還是一種處于影片背后某處的‘潛在語言焦點’的理性。觀者在翻閱一本事先安排好的畫冊,可是翻轉每一頁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某些‘司儀’,一些‘偉大的影像制作者’。”④由此而言,一個吸引人的敘事,可以隱含多個觀察角度,可以有多重凝視,其吸引人的程度與影像制作者所呈現敘述角度的豐富程度緊密相關。
中國電視紀錄片從1958年誕生之初到1980年代,在“形象化政論”審美理念指導下,敘事角度多采用制作者無限制的零聚焦視角進行全知全能的講述,解說詞貫穿全片,敘述視點相對單一。1990年代開始,隨著弗拉哈迪、直接電影等紀錄理念的浸入,中國電視紀錄片敘事視角開始發生改變,在全知全能敘述的同時,加上片中人物自己的講述,出現人物現場同期聲,如《沙與海》《望長城》等,片中人的“現場”講述賦予普通大眾話語表達權。進入新世紀以后,紀錄片創作注重可視性、戲劇性等藝術審美效果,制作者駕馭敘事技巧的能力進一步增強,敘述角度的選擇與設置更加豐富。比如《對照記·猶在鏡中》《我的詩篇》《貝家花園往事》等,以第一人稱“我”為敘述視角,增加歷史與現實的融匯感、觀看者與講述者的交流感。尤其《貝家花園往事》,以制作者“全知”視角引領、操控諸如歷史事件當事者、相關知情者、尋訪者、研究者等眾多敘述者,從不同角度對同一歷史事件與人物進行觀察與講述,形成多重凝視、復合敘述。使影片興奮點間距縮短,滿足新媒體環境下受眾對動態化、微小敘事的欣賞需求。第一集《鄉關何處》通篇由“制作者”講述一個關于中法友誼的歷史故事,這是第一重凝視,也是統領全篇的全知全能的敘述。在此引領下觀者可以了解故事的來龍去脈。由此引出歷史事件當事者的后人“尋訪者”出現,以“我”的角度來尋訪父親的花園,尋找父親在中國的足跡,此為第二重凝視,來自現實尋訪者“我”的凝視起到引出疑問、設置懸念、與歷史相勾連、拉近與觀者距離等作用。而在尋找過程中發現父親的書信、日記等歷史資料時,又讓“父親”親自出現“讀”自己的信,此歷史人物“我”屬于歷史事件“當事者”的敘述。透過此第三重凝視,觀眾可以看到歷史瞬間的真實狀態,看到人物當時的內心矛盾與情感糾結,起到還原歷史真相、塑造人物性格、推進情節發展等作用。其間穿插父親的朋友、母親的妹妹、弟弟等相關“知情者”的講述,此為第四重凝視,從不同側面進一步印證、說明歷史事實。第五重凝視來自研究者、專家學者的評價與評說,幫助觀者對歷史事件及人物的歷史地位及影響作出較為全面的了解與判斷。一部作品多重凝視,復合敘述,各司其職,在不同層面使敘事層層推進、環環相扣,增加時間的穿越感和空間貫通感,從而增加作品的戲劇性與藝術張力。2015年6月15日至18日每晚20:00,《貝家花園往事》在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面向全球播放,騰訊視頻、鳳凰網、愛奇藝、優酷土豆同步上線,首播以來贏得專家一致好評,也引來網友廣泛熱議。此種強化敘事層次及戲劇化呈現的探索,不失為新媒體語境下紀錄片提高關注度與影響力的一個努力方向。
三、敘述方式:強化“節奏”與“動態性”呈現
新媒體的傳播速度以“秒”為計量單位,秒殺、快速瀏覽帶來的是在最小時間成本內對最精彩、最刺激、最大量信息獲取的渴求。這一收視習慣和行為,對于包括紀錄片在內的影視藝術作品而言,意味著故事內容精彩的同時,講述故事的方式也要新穎與精彩。近年來紀錄片較為明顯的改變表現為“節奏”的強化與事件的“行動性”呈現。
美國符號論美學家蘇珊·朗格(Susanne K.Langer)在《情感與形式》中指出,節奏是在舊緊張解除之際新緊張的建立。⑤它們不需要均勻的時間。對于影視作品而言,節奏顯在的表現是對時間及事件進程速度有意識的掌控。長鏡頭營造的緩慢,短鏡頭營造的急促,都是節奏的體現,也體現著一定的話語內涵和審美取向。美學家朱光潛認為,節奏是一切藝術的靈魂。⑥節奏決定作品的輕松與沉重,決定人物的情緒與張力的大小,也決定情節的發展與推進方向。紀錄片是對生活的真實記錄,是生活場景、人物言行、事件演進一系列素材的堆積,如何調控,節奏把握很重要。中國紀錄片誕生之初,由于以“解說加畫面”為敘事模式,對生活場景及人物事件的呈現,節奏相對比較緩慢且缺少變化。1990年代在不干擾、不介入、做“墻上蒼蠅”理念指導下,有的紀錄片作品流于對生活流水賬式的跟拍紀錄,節奏拖沓,缺少對時間的有效分割與調控。新世紀以來,紀錄片強調觀賞性與戲劇張力,注重敘事節奏的輕重緩急、行止交替。出現《舌尖上的中國》《絲路,重新開始的旅程》《歸途列車》《與全世界做生意》等一大批節奏感強,具有鮮明時代氣息的作品。
紀錄片《與全世界做生意》,透過普通個體往返于世界貿易中的艱難足跡,呈現當代中國人的生活狀態與精神追求。作品敘事張弛有度,節奏在“舊緊張”解除與“新緊張”出現之間建立。第一集《與世界的距離》,片子開始“先聲奪人”,在畫面出現之前先出聲音,現場同期聲“原地踏步走”,這是第一個“緊張”,不知道“誰”在喊口號。接下來是踏步的腳的特寫,這是第二個“緊張”,因為不知道“誰”在踏步。鏡頭搖到臉部,顯示外國工人在踏步喊口號,這是第三個“緊張”,因為不知道他們來自哪里,為什么要踏步。接下來是中國工人的踏步,是兩國不同膚色工人在一起唱歌,“我們華堅人,領跑產業革命。我們華堅人,肩負時代使命。”至此畫面呈現的內容都是動態的,也解釋了這些人是華堅企業的工人。但為什么踏步喊口號,仍然是個謎。觀眾期待下一個新的“緊張”出現。所謂“緊張”實際是懸念,是行為累積的情感期待。一系列動態的視聽語言,營造出“張”的節奏,此后則是舒緩的“馳”的節奏。用一組外國工人在車間工作的特寫靜止畫面,配以解說詞介紹,揭示謎底,消除緊張。他們從埃塞俄比亞,來到廣東東莞接受中國企業的文化培訓。380天之后回到自己的國家,繼續在那里的中國企業工作。作品在動靜之間、張弛之間,體現出敘述者對節奏的把握與掌控,也呈現出生動鮮活的故事。這種富有節奏的動態性呈現較之靜態的講述,對喜歡移動化、快速瀏覽的受眾而言,更具吸引力。對紀錄片創作提升可視性與關注度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新媒體語境下紀錄片話語方式的改變悄然而無所不在。面對新的媒介環境,電視紀錄片依然有自己的生存空間。可以借助新媒體平臺籌集選題、發布信息、播出作品,也可以聯合新媒體共同創作,共謀發展。但做好自己,練就自身過硬本領,提高敘事能力和話語水平,仍然是增強紀錄片生命活力的根本所在。
注釋:
① [法]羅蘭·巴爾特:《敘事學作品分析導論》,張寅德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
② 李恒基、楊遠嬰:《外國電影理論文選》,三聯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頁。
③ [美]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頁。
④ [法]克里斯蒂安·麥茨:《電影語言:電影符號學導論》,劉森堯譯,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4頁。
⑤ [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劉大基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頁。
⑥ 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頁。
(作者系揚州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張國濤】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電視紀錄片與中國國家形象塑造研究”(項目編號:13BXW02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