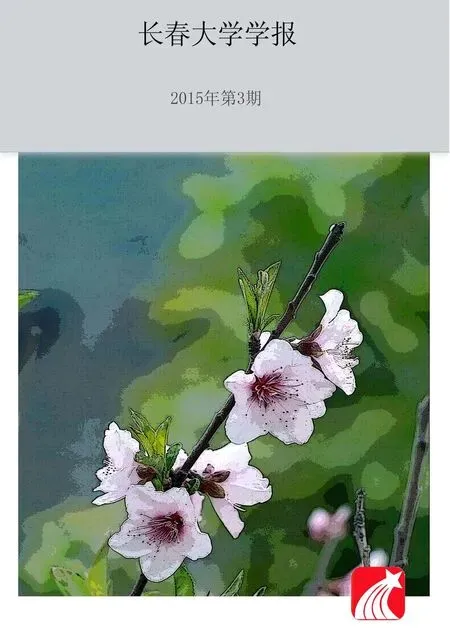《勒阿弗爾》的美學與政治
——兼論考里斯馬基的電影藝術
譚笑晗
(東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長春 130024)
《勒阿弗爾》的美學與政治
——兼論考里斯馬基的電影藝術
譚笑晗
(東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長春 130024)
阿基·考里斯馬基,享譽世界的芬蘭導演,他的作品《勒阿弗爾》不但在形式上注重色彩、光線和剪輯,而且在內容上呈現出巴迪歐所謂愛與政治的結合,是一部佳作。從這部影片中,也能透視出考里斯馬基的電影美學。
阿基·考里斯馬基;《勒阿弗爾》;美學;政治
阿基·考里斯馬基(Aki Kaurismaki,1957-)是芬蘭首屈一指的電影導演,同時也代表了歐洲電影的前進方向,加之他本人倔強孤傲的人格魅力,使其成為歐洲影壇的重要角色之一。考里斯馬基生于芬蘭奧利馬提拉(Orimattila),坦佩雷大學新聞學出身,畢業于赫爾辛基大學,之后在慕尼黑電影博物館自學電影,當時已經是小有名氣的電影評論家,后來跟隨哥哥米卡·考里斯馬基(Mika Kaurisma¨ki)走上了電影之路。二十幾年來拍攝了很多可以載入世界電影史的影片,成為歐洲影壇不可多得的“怪才”。
《勒阿弗爾》(Le Havre,2011)是考里斯馬基“海港城市三部曲”的第一部,拍攝于法國上諾曼底省港口城市勒阿弗爾,勒阿弗爾擁有僅次于馬賽港的法國第二大港,因此治安堪憂,是法國內政部所謂重點治安區,甚至存在“市區暴力”。然而,考里斯馬基這部電影卻告訴我們,勒阿弗爾沒有壞人。影片主要講述了擦鞋匠馬塞爾沖破重重險阻幫助一個非洲黑人男孩偷渡到英國尋找母親的故事,其中夾雜著他需要面對妻子阿菜緹的不治之癥,無形中給影片憑添了戲劇性。從馬塞爾和阿菜緹兩個人物的設置上也可見考里斯馬基在這部影片中有對馬塞爾·卡爾內及其《天堂的孩子》(Les enfants du paradis,1945)致敬之意。《勒阿弗爾》顯然集中了考里斯馬基諸多巧思,是他從藝術形式的各個方面對從影經歷的總結,因此具有較高的美學意義。本文嘗試從這部電影出發,進而梳理出考里斯馬基的電影藝術及其美學。
1 光影與鏡頭:《勒阿弗爾》的電影語言
一個導演的風格往往成為他的標簽,如小津安二郎的仰拍、阿巴斯的全景鏡頭和貝拉·塔爾的長鏡頭等。從風格上說,考里斯馬基的電影也如很多歐洲導演一樣追求視覺上的極簡主義,而這種極簡主義背后蘊含著導演對于電影主題、人物、背景和色彩等諸多方面的深入思考,《勒阿弗爾》同樣延續了考里斯馬基的一貫風格,從不同的角度呈現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對于色彩、光線和鏡頭的處理。
考里斯馬基非常重視光在電影中的運用,《勒阿弗爾》中幾乎每一個鏡頭都存在光線對場景的烘托,一般是光線從側面進入畫面,強調人或者事物的特質,也有從鏡頭背后產生的高光,凸顯畫面中的重要部分,這兩種光線的使用在電影中往往交叉運用,但都恰到好處,如港口集裝箱被打開后,考里斯馬基用多個鏡頭介紹生活在集裝箱里的非洲黑人偷渡者,這些特寫鏡頭定格在偷渡者的面部,幾乎都給了高光,這就把他們那種漂泊的恐懼和流離的茫然刻畫得細致入微;而集裝箱外面的法國警察等人身上的光線則做了側面光源處理,通過光區別了室內和室外兩群人,同時也集中交代了影片的主要人物,可謂一舉兩得。光線在《勒阿弗爾》中并不僅僅是渲染環境的工具,它也起到心理象征的作用,當馬塞爾請小鮑勃舉行演唱會時,小鮑勃以一個剪影的形式呈現,因為和妻子發生口角并分居使他苦惱,所以用剪影表現愁云籠罩,當妻子出現在他面前時,則給了他面部一個高光,其喜悅之情溢于言表,其間觀眾竟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光線的轉換變化,從這種舞臺劇式的風格也可以看出考里斯馬基將電影中光線和色彩的運用推向了極致。
此外,《勒阿弗爾》的畫面顏色也非常考究。整個影片的畫面呈現出淡淡的藍灰色,明顯借鑒了梅爾維爾的風格,門窗的顏色、人們的衣著和廣闊的大海都呈現出藍色,既是因為故事發生地的港口背景,又重復著考里斯馬基電影一貫的“做舊”風,而影片中的幾抹紅色據他自己說是來自小津電影中紅色茶壺的美感,[1]這種藍灰色寫意加紅色點染的手法使影片從始至終給人一種不急不躁的平和之感而又不乏瞬間的驚喜,紅色是考里斯馬基在《勒阿弗爾》中比較鐘愛的顏色之一,雖然出現的次數不多,但是也賦予了紅色非常深的意義,比如妻子生病住院后,馬塞爾送給妻子一束紅色康乃馨,后來在病床頭又出現一支紅色玫瑰,都是對阿勒提病情向好的暗示;小鮑勃演唱會上的紅夾克非常惹眼,一方面是妻子重回身邊的激情所致,一方面也象征幫助馬塞爾戰勝困難的決心;而影片最后黑人男孩行前的紅色外套無疑是順利逃離勒阿弗爾的寓意。由此可見,《勒阿弗爾》的畫面顏色設定并不是毫無來由,而是根據故事情節發展的需要用顏色配合敘事和人物的心境,雖然表現出來的都是小細節但是卻可以看出考里斯馬基的功夫遠在電影之外。
在鏡頭上,考里斯馬基的場面調度非常明晰,剪輯也很直接,但運動鏡頭很少,他多用固定鏡頭渲染氣氛或表現人物,而這種固定機位的選擇并不是記錄的而是藝術的,都是經過精心安排而看上去恰到好處,使畫面呈現出一種規規矩矩的穩定性,每一組鏡頭所呈現出的畫面比例、色彩和結構都非常協調,處處可見小津安二郎對考里斯馬基的影響,而影片最后那個粉色桃花在風中輕搖的空鏡頭儼然和小津如出一轍,頗有向其致敬之意。《勒阿弗爾》中的固定鏡頭不但數量多,而且質量也很高,每一個鏡頭都經過精心處理,很多鏡頭借鑒了西方繪畫作品,如警長和小酒館老板娘交談的那個場景就有意無意間借鑒了塞尚《玩紙牌的人》的構圖。值得說明的是,《勒阿弗爾》的布景和表演都具有很強的戲劇性,前文所述以小鮑勃為中心的光線轉換本身帶有很強的舞臺性,只有在現代戲劇舞臺上才會有這樣的燈光出現,考里斯馬基將之用于電影中無疑是一次電影實驗。馬塞爾家里的布景也頗具戲劇效應,給人的感覺是用家具建構出了一個舞臺,無論是馬塞爾和妻子還是和黑人男孩都在這個舞臺中進行表演,因為家具排列組合的張力指向就是鏡頭的中心舞臺。就表演而言,演員的很多表演都刻意放慢了速度,以造成一種舞臺效果,警察發現港口集裝箱中偷渡者那場戲本來應該是非常緊張的,但是卻被考里斯馬基做了“慢處理”,以至于給了黑人男孩逃走的時間,這種場景設置和獨幕劇非常類似。
2 雙重主題:愛與政治的雙重變奏
法國思想家巴迪歐認為,哲學既是一種斷裂,又是在斷裂處制造出一種新的綜合,電影作為一種哲學實驗反映出了這種斷裂與綜合,繼而成為形而上學意義上的綜合藝術。巴迪歐同時指出愛與電影存在著親密的關系,他以道格拉斯·瑟克(Douglas Sirk)的《無情戰地有情天》(A Time to Love and a Time to Die,1958)和阿蘭·雷乃(Alain Resnais)與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1959)為例,說明電影的運動來自于愛,向政治而去。[2]從這個意義上說,《勒阿弗爾》也是一部愛與政治相互交織的電影。一方面給觀眾制造出了善與愛的多種可能性;一方面呈現出了鮮明的種族和移民政治。
《勒阿弗爾》從愛開始。馬塞爾年輕時是個作家,向往自由,人到中年選擇生活在勒阿弗爾當一名擦鞋匠,一天的收入雖然不多,但是悉數補貼家用;他和鄰居之間相處和睦,大家知道他家里生活拮據,因此總是予之一些吃食作為資助;妻子勤儉持家,對馬塞爾的照顧無微不至,可見以馬塞爾為中心的人物和環境設置充滿著濃濃的愛意,無論是夫妻之間還是鄰里之間都呈現出愛和善的關系。同樣是因為愛,黑人男孩隨爺爺轉道勒阿弗爾是為了和遠在英國的母親相聚,為了這次相聚,他們可謂歷經劫難。就這樣,導演讓這有愛的一老一小在勒阿弗爾相遇,他們的愛是推動《勒阿弗爾》故事情節發展的行動元之一。對于馬塞爾來說,第一次看見黑人男孩是在碼頭,逃出集裝箱的小男孩已經長時間未進食,海水齊腰,可以說又冷又餓,馬塞爾看到孩子的眼神即刻心生憐憫,是內心本能的善讓他無論克服任何困難都要幫助男孩擺脫困境。對于男孩來說,他深深地感激馬塞爾,所以處處為馬塞爾考慮,特別害怕因為自己影響了馬塞爾的生活和聲譽。另外,馬爾塞的鄰居出于愛心和同情心都給與馬塞爾以極大支持,無論是雜貨鋪老板還是越南人,無論是小酒館老板娘還是小鮑勃聽說此事后都伸出援手,使得《勒阿弗爾》整部影片愛意融融。
《勒阿弗爾》也呈現出了某種種族和移民政治。種族和移民問題一直以來都是歐洲電影導演所關心的問題,很多電影以此為中心建構敘事,如2013年金棕櫚影片《阿黛爾的生活》的導演柯西胥就是一例,無論是《谷子和鯔魚》(La graine et le mulet, 2007)還是《伏爾泰的錯誤》(La Fauteà Voltaire, 2000)都和移民有關,歐洲導演對移民和種族問題的思考由此可見一斑。由于歷史的原因,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歐洲其他國家,種族問題和移民問題都是政治問題,在勒阿弗爾這樣的港口城市,問題則更具普遍性和嚴肅性。黑人男孩隨著爺爺偷渡到勒阿弗爾,目的是去和同樣偷渡到英國的母親匯合,之后被更夫發現以致警察全城搜捕逃走的小男孩,情節雖然簡單,但是考里斯馬基呈現出的卻是一個非常嚴肅的社會問題和問題背后的矛盾性。一方面,偷渡在法國屬于犯罪行為,但是馬塞爾和小男孩的行為卻能夠換來觀眾的同情以至于道德感戰勝了法律;另一方面,就世界范圍而言,種族、移民和偷渡等問題確實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沒有人會懷疑其中的合法性,這兩方面雜糅在一起使得平淡的敘事背后存在深刻的矛盾性,加之考里斯馬基在《勒阿弗爾》中特意加入了一個新聞片段,內容是警察和偷渡者的對峙和偷渡者的凄涼處境,旨在反問政府對偷渡者的態度是否合法,更深化了這種矛盾性。需要說明的是,《勒阿弗爾》中的愛與政治并不是兩條線索,而是交織在一起的共同體,在愛中反思政治,在政治中表現愛。最能體現這種愛與政治雙重變奏的人物是警察,警察是一個有愛之人,他阻止槍手開槍放走了男孩,但是卻一次又一次出于警察的天職給馬塞爾施壓,而影片結尾處警察的愛戰勝了政治,幫助馬塞爾和孩子度過難關,也是考里斯馬基的神來之筆。
《勒阿弗爾》的結局設計與考里斯馬基之前的影片都存在與眾不同之處,影片的兩條線索都以“大團圓”的喜劇模式收場,黑人孩子在馬塞爾的幫助下順利離開法國,馬塞爾的妻子也大病痊愈,這種結局與其說是故事性的不如說是寓言性的,同時也建構了一個愛與政治同生共存的烏托邦世界。但無論如何,這都使考里斯馬基的電影完成了一次轉型,也使余下“港口城市三部曲”更值得期待。
3 考里斯馬基的電影美學
《勒阿弗爾》是考里斯馬基繼《薄暮之光》(Laitakaupunginvalot,2006)后的又一部作品,雖然拍攝前后只用了50余天,但卻積蓄了導演本人五六年的能量,每一個細節的設置都傾注著導演的心血,因之雖然不能稱其為考里斯馬基的代表作,但是無論在電影敘事、主題還是語言上都堪稱考里斯馬基的集大成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勒阿弗爾》也能透視出考里斯馬基的電影美學。
考里斯馬基的電影主要關注小人物和邊緣人,就電影主題而言,他思考的是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苦難和命運,無論是表現芬蘭還是芬蘭以外,平凡人都是考里斯馬基表現的重點。早期的“無產階級三部曲”可以說是這種邊緣人生活的代表作,《天堂孤影》(Varjojaparatiisissa,1986)講述的是一個垃圾工人和一個售貨員的曲折愛情;《升空號》(Ariel, 1988)則是女工幫助礦工重獲自由的故事;《火柴廠女工》(Tulitikkutehtaantytto¨,1990)更為決絕地呈現了對生活失去信心的火柴廠女工抱負社會的人性狀態。可見三部影片都是以小人物為中心進行主題敘事的,后來的《波西米亞生活》(La vie de bohème, 1992)和“芬蘭三部曲”同樣延續了這種主題之思,從各個方面將邊緣人生活的辛酸與無常呈現出來。如《勒阿弗爾》一樣,在生活背后,考里斯馬基思考的是社會、政治、制度和人的關系,即使如芬蘭那樣高度發達的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也會遇到各種問題,所以“無產階級三部曲”和“芬蘭三部曲”呈現出的不是一個芬蘭問題而是世界問題,即人在社會壓力和命運遭際面前向何處去。考里斯馬基想辦法給出問題的答案,所以在“無產階級三部曲”和《勒阿弗爾》的結尾處都設計了一個“遠離”的模式,“乘船去他鄉”仿佛成為一種政治烏托邦,也似乎是考里斯馬基的理想國。
考里斯馬基非常重視光線和音樂在影片中的作用。首先,考里斯馬基對光線的關注就像是印象派畫家對色彩的關注,嚴肅而認真。特殊光線在電影中的作用無非兩種:渲染氣氛和強調形象,這兩種手法考里斯馬基都運用得淋漓盡致。在中近景鏡頭中,考里斯馬基強調人物光影同周圍環境的對比度,以此暗示人物內心世界的情緒和人物之間的張力,在特寫鏡頭中,則用強光呈現出面部表情的細微變化以深入到人物情感深處,這種處理既將電影場景還原為類似舞臺劇的布景程式,給觀眾以身臨其境的空間感,又在純電影語言上加以創新,不脫離電影又超越于電影,是一種比較有新意的嘗試。如《天堂孤影》中尼卡德吃晚飯的那個鏡頭,人物靠著百葉窗吃飯,夜光從百葉窗外傾瀉下來,橫條型光影映在尼卡德的身上,和他穿的格子T恤相呼應,而百葉窗的影子同時也映在他的臉上,造成一種畫面的錯亂感,這樣一來就把他當時那種不安的心緒刻劃出來。類似這種光線的運用在考里斯馬基的電影中可謂比比皆是,不難看出這是其志趣所在。其次,考里斯馬基電影中的音樂與眾不同,幾乎每一部電影都存在小型樂隊演出的場景,《列寧格勒征美記》(Leningrad Cowboys Go America,1989)更是以樂隊的出路和遠征為話題進行構思。其電影中的音樂節奏清亮明快、歌詞樸素真摯,基本上都是搖滾樂,無論在哪種題材的電影中出現都給人以積極和向上的感覺,這種對電影音樂的鐘情完全來自于考里斯馬基的個人感受,他從小就對搖滾樂和流行樂興趣頗濃,所以在電影中多設置這種場景。
考里斯馬基的電影中都存在一種“懷舊風”。所謂“懷舊風”并不是指影片主題和事件的懷舊,而是在形式上的“做舊”,是在刻意地還原20世紀的某個時代,正因如此在他很多電影中看不到時間,如《勒阿弗爾》這部電影若不是出現歐元紙幣,觀眾甚至可以將故事發生的時間想象成是在半個世紀之前,《列寧格勒征美記》和《波西米亞生活》等影片概莫如是。此外,無論是電影道具的設置還是人物的衣著都有“做舊”的痕跡,仿佛考里斯馬基的電影里就只有那么幾件家具和幾套衣服,《勒阿弗爾》畫面顏色并不是純藍色,而是藍中帶灰的藍灰色,這也是一種“舊”的表現。考里斯馬基的這種“懷舊風”和他的早年經歷有關,他成長于1960年代,他自己說那是一個盛產搖滾、黑夾克和嬉笑流行音樂的時代,這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3]所以在他的影片中不乏這諸多因素,既可以看作是電影的美學風格,同時也是考里斯馬基的個人印記。
歐洲影壇一度盛傳考里斯馬基行將息影,但是《勒阿弗爾》的出現不但打破了這種傳言,而且開啟了“海港城市三部曲”之旅,同時也開啟了考里斯馬基電影藝術的新航向,雖然在題材上繼續延續前兩個三部曲的底層人敘事模式,但是卻一改之前帶有悲劇性的結局以“大團圓”的結局收場;雖然在電影語言上因循了之前的考里斯馬基一貫風格,但是《勒阿弗爾》更加重視音樂、色彩、光線和畫面之間的組合作用;雖然在人物角色選擇上還是考里斯馬基的原班人馬,但是無論是安德烈維爾姆斯還是卡蒂奧廷寧隨著年齡的增長在表演上都更加成熟,這諸多方面構成了《勒阿弗爾》的動人之處。更重要的是,《勒阿弗爾》代表了考里斯馬基的藝術成就,無論是對純粹電影內部的思考還是對電影外部問題的理解都上升到了新的高度,這對于一位高產導演來說實屬不易。《勒阿弗爾》只是“海港城市三部曲”的第一部,憑借此片,考里斯馬基留給人們對之后兩部影片諸多期待,也給人們創造了充分的想象空間。
[1] Peter von Bagh.AkiKaurisma¨ki:The Uncut Interview[J].Film Co-mment,2011(5):39.
[2] Alain Badiou.Cinéma[M].Paris:Nova edition,2010:344.
[3] Peter von Bagh.AkiKaurisma¨ki[M].Paris:Cahiers du Cinéma et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 de Locarno,2006:11.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of Le Havre -On the Film Aesthetics of Aki Kaurismaki
TAN Xiaoh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ki Kaurismaki,a world-renowned Finnish director,whose works Le Havre emphasizes on color,light and editing in the form and shows Badiou's combination of love and politics in the content,being a masterpiece.The film aesthetics of Aki Kaurismaki can be recognized from the film.
Aki Kaurismaki;Le Havre;aesthetics;politics
J911
A
1009-3907(2015)03-0130-04
2014-12-06
譚笑晗(1987-),女,吉林通化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電影美學研究。
李鳳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