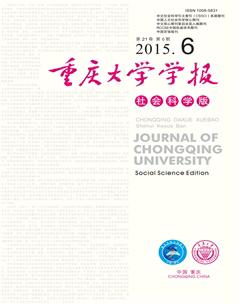“環境正義”視域下的環境法基本原則解讀
摘要:
2015年正式施行的新《環境保護法》作為環境保護領域的基本法首次明確了環境法基本原則,體現了形式法治的要求,釋放出環境法要以基本原則規范為中心來構建和發展基本原則解釋體系的信號。環境正義理論體現實質法治的要求,雖源起美國,但中國也面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交織的環境正義問題。新法確立的“保護優先”、“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公眾參與”、“損害擔責”四項原則的內涵與環境正義理論存在著深度契合。以“環境正義”為視域思考環境法基本原則,在豐富、深化環境法基本原則解釋的同時,也為環境正義法律化提供路徑思考,促成環境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統一。
關鍵詞:環境法基本原則;環境正義;環境法治
中圖分類號:D91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
10085831(2015)06015908
中國《環境保護法》自1979年制定實施以來已30年有余,期間的國家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條件,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近年來,接連發生的城市霧霾、水污染以及生態破壞等公共環境事件,往往交織著經濟發展、地區差異等社會性問題;環境問題的日益復雜與環境治理的難度,亟需尋求現代化的環境治理方法與體系。為有效應對中國環保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在歷時3年的精心醞釀后,新《環境保護法》終于通過審核,并于2015年正式施行。修訂后的《環境保護法》直面環境立法的基礎性問題,所彰顯與傳遞的理念對環境法治體系構建具有重要意義,包括首次明文宣誓環境法的基本原則,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加強政府責任與懲處力度,明確公眾參與權等一系列重大立法創舉,充分體現了中國在環境治理問題上推行“環境法治”的明確態度與堅決立場。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環境法治”是“法治中國”內涵的具體化,也是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環境法治”是一個綜合性、統領性的概念,涉及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多個環節的銜接、互動,是建設法治中國背景下中國環境保護的新概念、新思維、新綱領。本文結合近期《環境保護法》的修改,試圖以全新的視角,以環境法基本原則為切入點,探討“環境法治”的思想性、基礎性問題。采用部分法教義學觀點,引入“環境正義”理論,為接下來將要展開的環境法基本原則和環境法治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鋪墊。
一、環境法基本原則的研究價值
自環境法學科誕生以來,學者們就在不斷地從價值論證、比較法借鑒等多個角度研究環境法基本原則,但這些討論多停留于學理探討。直到新《環境保護法》出臺,基本原則被明確規定在法律條文中,才實現了環境法學者們多年的夙愿。環境法原則之所以受到關注,在于從規范體系構建的角度上,環境法基本原則將作為統領性規范影響環境法體系完善、政策制定以及司法適用。正如“私法自治”之于民法體系、“罪刑法定”之于刑法體系,基本原則作為部門法研究和適用不可或缺的要素,將成為環境法體系獨立的標志。
法律原則多是法律價值的體現,每一項具體法條、制度出臺都是價值博弈的結果。中國環境法學在過去30年的發展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重視環保價值理念的宣傳,研究多具有學科交叉性,包括環境科學、環境倫理學和環境社會學方面的知識介紹;或是將道德和價值論證作為依據反思現行制度;許多研究還未曾“援法而言”卻在規范之外旁征博引[1]。這就導致了環境法領域價值泛濫,凌駕于規范之上而忽視了形式法治的要求,從而失去了法學學科特色,故有學者詰問環境法“緣何不像法學” [1]。就價值問題爭論不休,卻忽略了法律體系的有序構建。體系的混亂必然導致各種規范沖突失衡,有些規定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要求,導致政府的環境行政行為“無法可依”,司法機構則“有法不依”,環境法被指為“沒有牙齒的法律”。不斷修改舊法,不斷出臺新法,如果沒有基本原則的指引,很難構建統一有序的環境法體系,很難保證環境法的權威性和穩定性。如果環境法研究罔顧立法基本原則,還停留在倫理價值的論證、稗酤外國理論以及脫離法律規則的宏大論證層面上,那么這樣的研究也很難對實踐有所貢獻。一個包含過多實質價值負擔的環境法治概念,很容易使價值判斷凌駕于實證法之上,而導致環境法秩序與權威的建立變得更加困難,更無法解決復雜性與迫切性兼具的環境法治實踐問題。近年來法學各學科出現的法教義學主張,就是試圖通過技術方法在實質價值要求和形式規范構建之間達致平衡。教義學方法是區分法學和其他以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的重要方法,服務于法律適用和判斷過程,基本方法是法律解釋和法律體系化[2]。在環境法研究中提倡基本原則的解釋和研究,就是要用教義學的技術方法,辯證地處理環境法治中形式層面與實質層面的關系。環境法治實現的前提是規范完備與體系化。此次新《環境保護法》作為環境保護的基本法明確了環境法基本原則,以規范方式體現了中國環境法的價值取向,是法教義學技術方法對環境保護形式法治的最新促成。環境法基本原則的功能是“確保法律規則在法律的制定、解釋、執行和司法各環節始終保持其統一性,并能有助于解決上述各法治運行環節可能出現的沖突”[3]。無論是崇尚理性構建主義的德國、法國以及歐盟環境法,還是奉行經驗主義的英美環境法,環境法基本原則都以不同形式出現并發揮化解沖突、指導立法與規范司法的作用教義學傳統深厚的德國吸取其民法典體例,在環境法總則部分對基本原則作出規定;《歐洲共同體條約》中的第130R、130S和130T是關于歐盟環境法原則的規定。參見夏凌《法國環境法典化對我國的啟示》(《江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柯堅《環境法原則之思考——比較法視角下共通性、差異性及其規范性構建》(《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1969)、加拿大《環境保護法》(1988)等重要環境立法,盡管包含著預防、公眾參與等環境法原則的思想,但在立法中并沒有直接以環境法原則的形式予以確認。因此,英美法系的環境法原則主要是指法官在司法活動中通過判例形成的一些適用于環境司法的普通法原則,如行使所有權不得損害他人的原則。參見柯堅《環境法原則之思考——比較法視角下共通性、差異性及其規范性構建》(《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基本原則將使環境法研究徹底擺脫價值和倫理的綁架,任何新興價值和倫理作為法律問題進入環境法領域都要通過基本原則的檢驗,不能夠隨意將價值和理念稗酤,而要恪守基本原則劃定的界限。因此,構建環境法原則和規則的法教義學體系,是發展獨立的環境法學研究的重要環節。
二、環境法基本原則的闡釋:“環境正義”法律化途徑
新《環境保護法》第5條規定:“環境保護堅持保護優先、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公眾參與、損害擔責的原則。”具體規定了4個基本原則,即“保護優先”原則、“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原則、“公眾參與”原則以及“損害擔責”原則。下文解讀環境保護法基本原則和“環境正義”之間的關系,以期通過辯證分析,促進環境法基本原則的闡釋與發展。
(一)“環境正義”緣何重要
“正義”是法治追求的終極價值,“環境正義”在環境法體系中具有特殊的含義,其本質是社會正義,即環境利益與環境負擔的公平分配問題,所以它是連接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重要機制。如何平衡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如何實現分配正義是新環境法體系需要協調解決的重要問題。
如上述,“環境正義”的實質在于環境利益和環境負擔公平分配的問題,目的在于平等地實現生存和護衛生活的權利,在“自然資源”受到商品化、政府占用以及私有產權安排等多方面的威脅時,以更有活力、更加公平的制度安排對環境問題作出回應。當然,不能夠將“環境正義”概念生搬硬套,要提煉中國的環境正義概念。目前中國有關“環境正義”的研究多集中在國外理論介紹與論證上,而忽視了中國本土的“環境正義”問題。“環境正義”概念緣起于美國20世紀80年代初的環境保護運動
1982,美國北卡羅來納州Warren Country的居民舉行示威活動,抗議在阿夫頓社區附近建造多氯聯苯廢物填埋廠。這次抗議在當地產生強烈反響,引起了美國國內的一系列窮人和有色人種的抗議。抗議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目的在抵制將有毒工業設立在貧窮和有色人種的社區。這是美國人首次聚焦有色人種和貧困人口的環境不公正問題。1983年美國審計局和基督教會公布的研究結果都表明,有色人種和貧困者聚居區成為有毒廢物處理的首選點。越來越多類似的抗議活動引發了對環境正義的普遍關注。1991年,第一次有色人種環境峰會在華盛頓召開,確立了17條“環境正義”原則作為行動宗旨。參見侯文蕙《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環境保護運動和環境保護主義》(《世界歷史》2000年第6期第16頁);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耿建新、宋興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頁)。,盡管環境正義運動濫觴美國
美國環境保護局(EPA)在20世紀90年代末提出了環境正義的完整定義:“環境正義是所有人,無論種族、膚色、國籍,或收入的差異,都能被公平對待;有意義地參與開發、實施和執行環境法律、法規、政策中去。這將實現人人都能夠獲得免于遭受環境污染損害健康的相同程度的保護,實現人人都平等地參與到環境決策過程中并因此在良好的環境中健康地生活、工作、學習。”參見《什么是環境正義》(美國國家環保署環境正義辦公室網http://www.epa.gov/environmentaljustice/, 2015年1月7日訪問)。,但環境非正義的問題在全世界普遍存在
自然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分配被發達國家主導,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資源和財富流失的局面,污染物跨境轉移、跨國企業掠奪當地資源等現象更加劇了這種狀況。參見王韜洋《從分配到承認:環境正義研究》(《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10頁)。。對于中國的環境正義問題學界已有一定的研究
環境正義一進入中國,就受到了法學界的關注。蔡守秋教授較早地介紹了環境正義的概念并提出正義應該是環境法的基本價值理念。中國較早關注環境正義問題的還有臺灣學者紀駿杰和清華大學的王韜洋博士,兩人雖然不是法學學者,但是他們關于環境正義的介紹使很多法學學者受到啟發。此外,一些學者將環境正義本土化之后,力主研究中國特有的環境正義問題。如武漢大學晉海博士的《城鄉環境正義的追求與實現》一書就提出了中國特有的環境正義問題: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城鄉差異形成的環境非正義狀態。還有學者研究城市廢棄物處置、污染項目選址的環境正義問題。在法理學界,第一個研究環境正義問題的是吉林大學的馬晶博士,她的博士論文《環境正義的法哲學》從法理學的角度解析了環境正義的基本問題。:收入差距、階層差距、地區發展不均以及城鄉二元結構與環境問題交織,形成了中國特有的環境正義問題。在中國城市環境質量改善的同時,農村則出現了地力衰竭、生態退化、水源污染等嚴重問題。農村成了許多污染企業首選地,整個村莊的環境和村民的健康受到威脅,許多學者都注意到了中國的生態環境存在城鄉二元化的趨勢[4],這個結論也得到政府的官方確認。中國環境立法目前也存在著“城市中心主義”的傾向:環境法律法規都側重滿足城市環境保護的需要[5],從主體、原則到適用對象都很少考慮到農村環境保護的需求
從研究環境爭議案件的不同主體所占比例看,無論是在環境民事案件還是在刑事案件中,農民群體作為原告或者是被告的比率要遠大于其他社會群體。“在環境民事案件中,涉農比例相對最高,為41.53%;在環境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是自然人的比重為97.9%,單位的為2.1%,其中,被告人為自然人的案件中,被告人身份為農民的占74.4%,個體戶占8.9%,其他身份為16.7%。可以發現,在環境刑事案件中,涉農比例高達72.84%”。參見熊曉青、張忠民《影響環境正義實現之因素研究——以環境司法裁判文書為視角》(《中國地質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第43頁)。。環境污染導致農村的生態環境遭受損害,而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破壞制約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并形成惡性循環。
除了研究缺乏對中國本土問題的深度解析之外,“環境正義”研究總是在法學外圍尋找論據,從環境倫理學、環境經濟學和環境哲學中汲取理論,卻沒有能從基本原則與環境正義關系角度完成規范解析。新《環境保護法》追求環保高標準,對污染者加大處罰力度的同時,更要考慮這些經濟成本最終會由誰來買單。如何將“環境正義”這樣的價值納入法律體系從而實現其法律化應該是目前環境正義研究的重點。“環境正義”這一抽象價值需要從要素分析的角度,對比它與現行環境法基本原則的關系,將正義的理念注入環境法規范體系。本文以環境正義為視角解讀環境法基本原則,以期為環境正義法律化的實現提供路徑思考。
(二)“保護優先”原則
“保護優先”從字面意思理解,是指在社會管理活動中,將環境保護放在優先位置,在環境利益與經濟利益沖突的情況下,將環境利益放在首位。根據可持續發展的立法目的,經濟和環境發展相協調的立法宗旨,不能絕對地認為,在一切情況下,環境利益都處于優先地位。學者竺效經過對國外立法、國內相關論著和已有立法政策文件的分析得出,“保護原則”在新法中承擔了風險防范原則在學理上的功能:遇到環境(生態)風險科學性不確定的情形,應以保護環境(生態)為優先原則[6]。由于缺乏官方的釋義,并不能將“保護原則”與風險防范原則劃等號。但根據新法立法目的以及該法第39條
第39條原文為:國家建立、健全環境與健康監測、調查和風險評估制度;鼓勵和組織開展環境質量對公眾健康影響的研究,采取措施預防和控制與環境污染有關的疾病。,并結合中國簽署的國際環境條約,風險預防原則只能是在一定的特殊領域“有限適用”[7],而不宜將其草率地推廣。環境保護依賴科學的證據,對于那些科學研究尚存極大不確定性且對于民眾健康、安全等具有重大影響的領域可以適用風險預防原則,風險預防原則是“保護原則”在特定領域變通適用的原則。
風險防范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最早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的西德有關控制酸雨和霧霾的清潔空氣法中。在國際法層面,風險防范原則最早出現在保護海洋的區域性公約中,逐漸發展成為歐盟環境法中的核心原則[8];《聯合國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第15條也明確宣示了該原則,其核心是判斷環境侵害的風險。風險的分析由“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兩部分組成[9]。“風險評估”是對特定環境決策行為的后果進行科學調查和數據測量[10]; “風險管理”是政府對風險評估的結果進行調整和平衡;風險的評估與管理和環境正義的實現關系密切[10]。無論是保護原則還是在特殊情況下適用的風險預防原則,都需要平衡社會差異群體的要求。
從“風險評估”的過程看,以科學統計為主的評估方法,會涉及到環境正義的問題。傳統風險分析法忽視了受風險人群在性別、種族、貧富等方面的個體差異[11],同樣的風險在不同地域和人群中造成的影響不同,如果風險評估過程缺乏民主參與,就會導致立法與政策缺乏公信力而無法順利執行。環境正義理論提供的借鑒是:現代人生活在一個風險社會中,風險事件是 “文明社會的火山”,隨時可能爆發。社會中弱勢人群、少數群體的權利更應該予以重視和保障。“風險評估”依賴的數據定量統計分析也有其局限性,很難做到客觀全面,缺乏深入少數群體的實證調查研究,缺乏“商談民主”形式。此外,對于特殊地區而言,“風險評估”總是就個別事件“就事論事”,而沒有長期跟蹤計算發生在此地的全部環境事件的“積累的風險”,可能造成環境非正義問題。而在相關實踐中,“風險評估”往往被當成是環境決策的結果而非幫助環境決策的有效工具,后續“風險管理”的缺失也會導致環境非正義現象出現。
以上問題提示立法決策在實施“保護原則”的過程中,要按照環境正義理念來重新思考環境“風險評估”的過程與方法。忽視個體差異和民主參與的問題可以通過“風險管理”來糾正,在風險管理過程中,一定要保障相關利益群體的知情權與參與權,這也是實現環境政治民主的良好契機[12]。環境正義要求保護弱勢群體的環境利益,風險防范原則與保護原則的宗旨在于保護環境和人類健康免于環境威脅。所以風險證明責任應該由實施危險責任的一方承擔。這一點應該體現在有關證明責任的環境立法與司法實踐中。
(三)“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原則
“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原則”實際上就是學界所稱的“污染綜合防治原則”。蔡守秋教授認為其定義應為:“對污染的整體、系統、全過程、多種環境介質的防治。”[13]由此看來,其意義相當于“預防原則”,即對開發和利用環境行為所產生的環境質量下降后果采取預測、分析和防范。預防原則(Prevention Principal)被稱為是“環境法的燈塔”,甚至被稱為是“黃金原則”。在國際環境法中,預防原則產生于處理跨界污染的“特雷爾冶煉廠案”,與“一國不得損害外國環境的國家責任”有著密切聯系,要求各國在環境立法、政策制定、污染管控等方面具有避免跨境損害的勤勉義務[14]。
有學者認為區別“預防原則”與其他原則的關鍵在于預防措施的采取不以充分因果關系的存在或者充分證據為前提[15-16]。這就導致在環境行政管制的過程中預防原則可以充分地適用;而在以證據與事實為導向的司法裁判過程中,預防原則的適用受到阻礙,司法環境正義也就無法實現。環境問題的舉證需要專業知識,普通人對環境領域的專業不甚了解,無法有力舉證;環境污染的潛伏時間較長,受害者可能在很長時間內遭受健康損害卻不知具體的原因,或者因為時間較長面臨證據滅失的危險,也就無法及時在環境損害司法裁判中獲得環境正義救濟。預防原則使用的前提是“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對預防成本與所獲得的經濟環境效益進行比較才能決定是否采取預防措施,作為環境影響評價(EIS)制度的一部分,“成本—效益分析”被廣泛應用
1930年代美國一些州法令中,規定控制洪水的項目審批和決策必須運用成本效益分析。1969年美國的《國家環境政策法》要求一項環境影響評價應當在美國環境保護署(EPA)備案。1974年的《太陽能研究、開發與示范法》規定太陽能項目的合理性必須有成本效益分析加以論證。美國總統里根在1981發布12291號行政命令,規定一項條例是否通過和執行,是否具有重要性等問題都要通過成本效益分析加以證明。中國也借鑒國際經驗,在1979年頒布的《環境保護法》中規定了環境影響評價制度。2002年頒布的《環境影響評價法》較為系統全面地規定了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其中第17條關于“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報告書”內容中,明確規定了“建設項目對環境影響的經濟損益分析”。參見42 U.S.C 4332(2)(B)(1976),42 U.S.C. 5877(C)(1976),46 Federal Register 13,193(1981)。。成本效益分析之所以在實踐中獲得人們的信賴在于強調貨幣價值同時量化利益和收益,這無疑為選擇提供了現實的依據。但“成本—效益分析”經常得出一些糟糕的結論
一個例子是Philip Morris煙草公司對捷克增加煙草消費稅做了一個成本效益分析,竟然得出了如果政府鼓勵吸煙,將會增加財政收入的結論。原因是因為吸煙導致煙民早死將為政府節省一筆數額龐大的醫療費用和養老保險費用,它將有效地抵消煙草發展對公共財政形成的負擔。參見Philip Morris Funded Study of Smoking in the Czech Republic stating that the Czech government had a net gain of $147.1 million from smoking 28nov00,http://www.mindfully.org/Industry/Philip-Morris-Czech-Study.htm,2015-01-07;另外一個例子是世界銀行(Word Bank)首席經濟學家Lawrence Summers的成本效益分析研究報告則論證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污染轉移的合理性。參見約翰·貝米拉·福斯特《生態危機和資本主義》(耿建新、宋興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4頁)。,原因在于將成本量化,就是在決策過程中推行財富至上或是貨幣至上方法。市場經濟的投票不可能完成社會的公平分配,它犧牲了社會分配的公平去追求財富和利益的最大化[17];公共決策會影響到社會成員的利益,故社會成員都對公共決策享有發言權,“成本—效益分析”顯然忽視了這一點[18]。這也是被環境正義論者極力反對的方法。
要修正“預防原則”可能導致的環境非正義后果,就應將“環境正義” 理論注入預防原則之中從而對實踐中出現的偏離進行糾正,即在“成本—效益分析”的計算中考慮社會公平分配的方法。有學者認為通過在具體分析中區別不同社會群體的負擔與收益的方法,經過精細地計算,“成本—效益分析”也可以為環境正義服務,改造版的“成本—效益分析”完全可以用來解決分配正義問題[19]。
“預防原則”中的“源頭原則”就體現了“環境正義”精神。在歐盟法中,“源頭原則”(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 At Source)是預防原則在處理廢物污染領域中的具體體現。處理廢物污染的“源頭原則”要求具有危害性的廢物處理要在源頭進行,廢物生產地要設置專門的設備處理廢物,避免廢物的運輸和傳播。無論是環境正義誕生的美國“沃倫抗議”,還是英國蘇格蘭納拉克郡村民反對PCB事件,其起因都是因為違反了“源頭原則”[20]。可見,預防原則、源頭原則與環境正義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三者的有機統一可避免預防原則可能導致的環境非正義后果。
(四)“公眾參與”原則
“公眾參與”原則是指公眾有權通過一定的程序或途徑,參與一切與公眾環境權益相關的環境開發、決策等活動,并有權得到相應的法律保護和救濟,以防止決策的盲目性,最終使該項決策符合廣大公眾的切身利益和需要[21]。公眾參與原則是中國環境法多年實踐的經驗總結,也是環境正義的必然要求。這一項原則在各類環境法律法規中也多有規定:在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環境聽證制度中公眾參與原則都發揮了重大作用。如何真正地貫徹該原則,讓公眾實質性地參與環境立法決策的方式是個重要的問題。美國早在1969年的《國家環境政策法》(NEPA)中就確立了公眾參與原則,但1980年代之后爆發的環境正義運動恰恰說明了公眾參與環境決策的機制并沒有得到保障,美國國家環保局專門設立環境正義辦公室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保證環境信息公開、決策過程的透明。如何實現重要環境信息的披露,尤其是保證利益相關群體的知情權非常重要。政府應當將公民參與環境決策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制化,政府與公民的互動應該是“雙向互動”。一方面,政府能夠及時全面真實地了解公眾的意見;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及時向社會公布有關環境群體事件的動態和處理結果,重大環境污染事件的責任、原因和處理結果,并且有義務向公眾展示與環境正義有關的科學研究成果。
環境正義的概念與要求,特別強調不論具有何種差異的利益相關者,都能夠實質性地參與環境立法與政策制定過程。搭建環境正義所提倡的“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作為西方人文社科領域的經典概念至今仍不斷地被提及和討論。“公共領域”是公權力和私人形成有效對話的領域,是市民社會和國家權力中間的調節閥。公眾可以在公共領域中對社會問題自由地、非強制性地發表意見看法,形成不受公權力支配的評論。參見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版第116頁)。在環境正義語境下的公共領域問題,無疑是想切中環境正義概念中一個關鍵點:“公民都可以實質性地參與到有關環境利益和負擔分配的環境立法和決策中。”就是形成一個公意平臺,使意見自由地交流以促進環境正義目的的實現。環境正義往往需要政治力量即公權力的支持,而環境正義運動的主導者多是社會中的代表貧弱者利益的公民和私人組織,其實現需要公權力和社會力量的對話協商,“公共領域”就為這種溝通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平臺。新環保法對環境公益訴訟的支持所彰顯的精神理念,與“公眾參與”原則一致,同時也是“環境正義”理論在中國環保法中的體現。
(五)“損害擔責”原則
“損害擔責”原則是“污染者付費”(Polluter Pays Principle)的立法表述,作為一項調整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市場秩序的原則,最早出現在24國組成的經濟與合作組織(OECD)簽發的一系列指導性文件中[22]。損害擔責原則通過分配環境預防和控制措施的成本,達到“稀缺資源合理有效利用”、“避免投資市場失靈”的效果。隨后,該原則出現在歐洲議會《第一環境法令》中,并逐漸在《里約宣言》、《保護東北大西洋環境公約》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of the North East Atlantic (1993) 32 ILM 1069, Art.2. 、《波羅的海公約》
Baltic Sea Convention, Art. 3(4) 發展出了環境損害規則的含義,并被當作侵權原則來適用。在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它逐漸發展成為了環境法基本原則。此原則要求污染者對其污染行為買單,這符合社會正義的要求,也是實現環境正義的途徑。雖然“損害擔責”與“污染者付費”原則其含義基本一致,但立法最終并未直接采用“污染者付費”這一說法的重要原因是,法律上“污染者”的范圍實難確定,“污染者”并不僅指產生污染行為的生產者,還應該包括污染產品的使用者和消費者;加之環境污染的整體性和復雜性,污染是多方累積造成,很難確定污染者。學者柯堅考察國外立法,發現許多國家并未采用“污染者付費”的術語。
“損害擔責”(污染者付費)原則是通過提高污染生產者的成本從而提高污染產品的價格而使其失去市場競爭優勢,或者通過稅收手段來達到目的。由于其起初是一項經濟原則,基于自由市場原理而設計,現實中市場調節失靈使經濟手段很難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反而會產生污染者轉嫁污染成本而產生環境非正義的問題。故損害原則不宜拘泥于經濟調節手段,要擴大污染者承擔的責任范圍。傳統觀點認為污染者只需要按照行政法規對污染行為后果進行賠償;而在環境正義的思路下,污染者的賠償還應包括其污染行為造成的社會損害,強調對受到環境污染侵害的弱勢群體的賠償責任,從而在損害擔責的同時實現環境正義的追求。
“損害擔責” 原則是環境正義的直接體現,強調分配公正。而國際環境法中“差別待遇原則”(Differential Treatment)也強調一種分配公正,它不僅要求各國根據實際行為擔負責任,還進一步強調要考慮不同國家具體情況從而予以設定不同的義務和責任,尤其是對處于不利地位的國家予以特殊優待,最終實現國家環境保護的平等合作。差別對待范圍涉及正義的諸多領域,如程序、實體和結果分配等方面[23]。 “損害擔責”原則與“差別待遇”原則的核心精神都是實現環境正義主張,而“差別待遇”原則可以理解為是一種矯正正義。中國環境正義研究者提出了中國環境狀況的地區差異、城鄉差異,因此在損害擔責原則適用的過程中也需要考慮到這種地區差異,因地制宜才能夠真正實現公正。
三、環境法基本原則之于環境法治的重要性
在當今法治中國的話語倡導之下,如何實現環境法領域的良好秩序以實現 “環境法治”值得反思。
根據法的一般原理,法治分為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形式法治注重規則構建與程序完備以追求法的普遍性、穩定性和可預期性,以規范為中心的形式法治最能體現法學特色;實質法治通過法的價值判斷來論證法的正當性,反對把法視為封閉系統,認為法律與道德、倫理、社會與政治緊密關聯[24]。 “環境法治”不僅在形式方面要求環境法律體系結構完備,邏輯嚴密,相互協調,更在實質層面要求環境法律體系體現正義、平等、公平等“良法”之不可或缺的價值要素。
從環境法治的形式層面看,環境法基本原則將起到完善環境法體系結構、統一協調環境立法、促進環境法規則的解釋和適用以及解決疑難案件的作用。法律原則、法律規則和法律概念是法的三要素[25],很難想象一個法治國家的環境法體系中沒有基本原則的規定。只有法的要素齊備且邏輯嚴謹、各項環境法制度和單行法協調統一才能滿足環境法治的形式要求。不同于微觀的、確定的并且以“全有或全無”的方式適用的法律規則,基本原則具有宏觀性、開放性和根本性,發揮著指導規則制定和規則解釋的作用。環境法基本原則的根本性體現在它反映了社會關系的本質和規律,是長期以來中國和域外先進國家環境法律實踐的理性提煉;而基本原則不僅是環境保護法的基本原則,也是整個環境法體系的指導原則,將對目前正在修訂的大氣污染防治法和后續將要修訂的各個環境單行法律法規發揮指導作用;環境治理的社會形勢不斷發生變化,開放性則體現了環境法基本原則的現實張力,通過基本原則的解釋和發展使靜態環境法體系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環境法基本原則還可以通過發展其解釋體系而適用在司法審判中,尤其是適用在解決疑難案件中。“窮盡規則方可適用原則”原理和原則的抽象性使基本原則是否可以直接司法適用引起爭論,集中體現在“瀘州遺贈案”[26]的后續爭論中。但筆者認為,環境法基本原則并不是簡單的道德宣誓性原則抑或是在立法技術薄弱的情況下的權宜規定,而是經過多年實踐積累的提煉,每個單項原則都已經有十分充分的學術研究和梳理,且每項原則的具體內容學界也大體達成共識。在這種情況下,基本原則司法適用并不是放縱法官的自由裁量,而恰恰相反,在規則體系的大前提無法涵蓋生活事實的情況下,基本原則可以劃定法律的界限,限制法官自由裁量,從而保證形式法治的實現。
實質法治體現了法的倫理價值。如果法治意味著“良法至上之治”,那么什么是“良法”的追問就顯得尤為重要。自然法學派最大的貢獻就在于提醒世人體現正義和公平的法律才是“良法”
蘇格拉底把正義視為法律的最高標準, 認為正義是立法的本質。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的好壞在于是否符合正義, 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促進正義的實現。斯多葛學派以“自然法”與“人類法”(實在法)的二元區分作為理論基礎, 認為“人類法”只有在符合“自然法”時才是正義的。參見李步云、趙迅《什么是良法》(《法學研究》2005年第6期)。。正如羅爾斯所指出:“法律和制度,不論其如何有效率和條理,只要不正義,則必須改造和廢除。”[27]環境立法的背后存在諸多互相矛盾的價值取向,比如安全、公平、效率等,環境正義就是從分配正義的角度向基本原則提出挑戰。環境法基本原則,不僅在形式法治的層面具有工具意義,還在實質法治的層面具有倫理意義。要想在環境領域實現良法之治,就務必使基本原則符合正義的要求。正義要求在環境法領域不僅要重視“代際正義”,更要重視如何實現社會正義。中國人口、地區發展差異性較大,環境保護的問題必然會與中國經濟發展需求產生緊張關系,對中國環境立法和執法提出巨大挑戰。從環境正義角度發展環境法基本原則,在后續立法和個案中處理價值、平衡利益,是環境法學需要解決的問題,用環境正義的理論闡釋和發展環境法基本原則的意義就在于實現良法之治。過去環境法研究注重實質價值的探討,充斥著倫理情懷卻有失規范價值,充斥著各環境學科的理論卻有失法學特色,其中也存在著將西方理論“稗販”來診斷中國問題的現象,造成了對中國現實的遺忘和誤讀。環境法基本原則確立了環境法體系的價值導向,是從規范的角度對過去環境法倫理研究的總結和升華,也是環境法體系建構和環境法發展的一個新方向:讓環境法價值倫理的探討從其他學科的綁架中解脫出來,回到法學研究的規范軌道上來;讓公平、正義等良法之價值在環境法基本原則中體現,從而在環境法體系中貫徹;讓環境法基本原則的解釋和闡發成為環境法學研究的一個新的增長點。
過去環境法研究注重實質法治的方面,忽視了形式法治的重要價值。一定程度上,法律體系的無序、行政法規泛濫、環境標準混亂極大地削弱了環境法實施的效果。環境法基本原則在形式和實質兩個層面助益于環境法治,是連接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的紐帶;基本原則的確立和發展也將實現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的有效結合。基本原則的闡發也要充分關注基層呼聲,貫徹社會正義的要求。環境正義運動自產生發展至今已有30余年,在中國近年來的環境公共事件中,已出現了環境正義的訴求。環境法基本原則和環境立法作為環境法治“頂層設計”的一部分要充分關注這種來自基層的需求才能夠獲得內生力量,實現制度設計與基層實踐的對接,促進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互動,才能形成科學、現代、合理、有效的中國環境法治的治理模式與框架。參考文獻:
[1]鞏固.環境法律觀檢討[J].法學研究,2011(6):66-70.
[2]張翔.憲法教義學初階[J].中外法學,2013(5):916-919.
[3]竺效.論公眾參與基本原則入環境基本法[J].法學,2012(12):127-133.
[4]晉海.城鄉環境正義的追求與實現[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8:86.
[5]中國社會科學院環境與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環境與發展評論(第1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312.
[6]竺效.論中國環境法原則的立法發展和再發展[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4(3):4-16.
[7]李艷芳,金銘.風險預防原則在我國環境法領域的有限適用[J].河北法學,2015(1):43-49.
[8]FISHER E. Is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justiciable [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2001,13(3):315.
[9]HORNSTEIN D T.Reclaiming environmental law: A normative critique of comparative risk analysis [J].Columbia Law Review,1992,92:562-570.
[10]KANNAN P M.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More than a cameo appearance in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law[J].William Mary Environmental Law Policy Review,2007,31:410-411.
[11]KUEHN R R.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implications of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J].UIll L Rev 1996,103:121.
[12]HUANG L A.The dialogue between precaution and risk[J].Nature Biotechnology,2002,20:1076 -1078.
[13]Sadeleer N d.Environmental principles: From political slogans to legal rules [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89.
[14]BIRNIE P,BOYLE A,REDGEWELL C.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nvironment[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47-149.
[15]Bullard R D.Confronting environmental racism,voices from the grassroots[M].South End Press,1993:203-206.
[16]Bullard R D.Unequ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communities of color[M].Sierra Club Books,1994:7-12.
[17]HSU S.On the role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environmental law: A book review of frank ackerman[J].Envtl L,2005,35:171.
[18]彼得.S.溫茨.環境正義論[M].朱丹瓊,宋玉波,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27.
[19]Sunstein C. Lives, Life-years, and willingness to pay[J].Columbia Law Review,2004,104:213.
[20]BULLARD R D.Race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J].Yale J Int’l L,1993,18:319- 328 .
[21]汪勁.環境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06-107.
[22]OECD.Environment and economics guiding principles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Recommendation of May 1972)[EB/OL].[2015-05-16]. http:// ww w.ciesin.org/ docs/008-574/008-574.html.
[23]李春林.國際環境法中差別待遇研究[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150.
[24]張翔.形式法治與法教義學[J].法學研究,2012(6):7-9.
[25]張文顯.法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12-114.
[26]葛洪義.法律原則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和作用[J].法學研究,2002(6):3-14.
[27]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