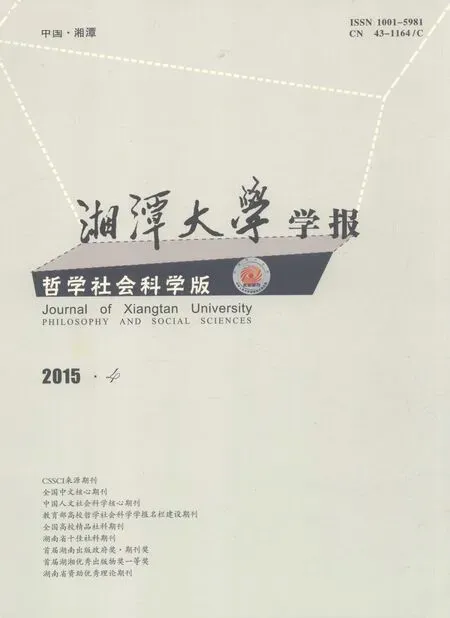解殖民與返殖民:1980年代中國文學思潮再解讀*
劉永春,張莉
(魯東大學文學院,山東煙臺264025)
解殖民與返殖民:1980年代中國文學思潮再解讀*
劉永春,張莉
(魯東大學文學院,山東煙臺264025)
摘要:解殖民與返殖民兩種話語是1980年代中國文學思潮的一個重要主題,兩者的對抗貫穿了整個歷史時期,并為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1980年代的大多數文學現象、思潮、流派都是在兩種話語互相競爭的文化框架中產生、發展和消失的。深入分析兩者的互動機制是重新進行“八十年代言說”的重要途徑。同時,這種互動機制也是半殖民視野中現代中國文學發展的組成部分。
關鍵詞:文學思潮;解殖民;返殖民;話語機制
1980年代初,在經歷了十年“文革”之后,中國文學再次走到了與新文化運動時期相似的十字路口。對歷史的總結和對方向的焦慮是同類歷史時期共同的文化特征,而兩者扭結的地方恰恰在于如何看待半殖民性與解殖民性參差互現的現代性傳統。通過這個入口,1980年代的中國文學思潮呈現出鮮明的兩極分化特征:一方借助強烈的民族主義話語,試圖回到解殖民性話語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本土性軌道上來,在新的歷史關口、新的時代環境中實現文化意識上全新形態的“解殖民”;另一方則借助現代啟蒙話語,試圖重尋西方文化觀念、文學思潮、寫作技法在中國的在地化,并進而達成文化意義上的“返殖民”,建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解殖民與返殖民兩種話語,相互競爭、相互補充,共同形成的雙螺旋話語結構,時時隱現在各個文學思潮之中,成為1980年代中國文學思潮的鮮明特征。
從話語競爭的激烈程度來看,1980年代無疑是20世紀歷史上最為風云激蕩的時期之一,本土的、西方的、混生的各種話語互相激發,歷史與未來被放置在同一個場域中進行討論。其結果是整個時期的文化都具有某種失范的歷史面貌,具有強烈的不穩定性和過渡性。在解殖民和返殖民兩極之間反復游移的80年代文化使得這段歷史時空充滿了復雜的話語動機,在錯綜復雜的內部機制下,各種形式的本土話語和外來觀念形成激烈的對話關系。這樣的文化結構填充了由“文革”到1990年代市場經濟改革之間的巨大歷史裂縫,消弭了巨大的歷史悲劇帶來的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使得返殖民與解殖民尖銳的對立催生出的破壞力大體抵消,反而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時代風貌。究其根本,解殖民與返殖民兩種話語方向互相依存、互相抵消,一起構成了1980年代中國文學發展的主要動力。在兩者的競爭互生中,1980年代文學具有了20世紀其他年代難以企及的話語活力和活潑氛圍,使其成為理想主義的黃金年代。對1980年代文學思潮在解殖民和返殖民兩極之間的游移進行分析,可以進一步呈現其復雜的動力機制和詩學特征,并進而厘清與之相關的諸多文學史現象。
“晚清至今的現代中國文學,與其說是現代性的文學,不如說是半殖民與解殖民的文學。殖民性的嵌入、抹除、遺留問題,干預并決定了現代中國文學的主體走向和風貌格調。”[1]這樣的狀態在1980年代初依然存在。只是這里所謂的“嵌入、抹除、遺留問題”在1980年代語境中更加具化成為文學思潮中的極性運動方式。于是,中國本土現代性的內涵與外延問題在1980年代時空中變成了解殖民與返殖民爭奪的核心領地,對現代性的重寫與置換貫穿了整個19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1980年代文學所面對的文化資源選取、創作方法更新、敘事形式變革等棘手問題,在實際的創作和批評中都同時分化出解殖民和返殖民兩種方向,兩者呈現為緊張的對抗關系。對整個1980年代中國文學思潮進行認識,甚至對當下的各種1980年代言說進行梳理,也必須還原到這個無法繞開的結點。
一、主體重建:現實主義的一元慣性與現代主義的多元訴求
新時期之初,中國文學的最重要任務是合法性的重建,“重新確立了歷史的主體和主體的歷史”。[2]242在這個過程中,傷痕、反思、改革等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相繼構成了“歷史的主體”的主要話語形象,沿著解殖民的方向漸行漸遠;而意識流小說、朦朧詩、人性論與人道主義、探索戲劇等則構成另一種力量,將西方現代主義觀念作為返殖民的途徑激烈推進。兩種截然相反的方向共同形成新的“主體的歷史”,共同以啟蒙的面目出現在中國文學的舞臺上。與新文化運動時期相同,思想啟蒙的共名再次遮蔽了兩種路徑天然具有的巨大分野,而不同的路徑訴求之間的相互拮抗則被簡單視為中西之爭。造成這種誤讀的原因,既包括彼時反思文革、回歸“解殖民”革命傳統的意識形態需要,也包括現代主義觀念本身的駁雜性及其與中國本土文化語境的不兼容性。緊迫的時代車輪并沒有為現代主義的輸入準備充足的耐心和辨別力。
“解殖民”與“歷史總體性的修復”同質異構。所謂“解殖民”,通常認為“就是拆解、消解、消融、抹去殖民化的不良影響,解構殖民宰制話語和西方中心主義,重建民族國家的主體性”,與“反殖民”不同,其重點是“多層面地、結構性地、系統地去除殖民性質,更側重文化、心理層面,而且隱含了重組去殖后的現代文化與本土文化的關系問題”[1]。1980年代初的“解殖民”話語主要表現為對現實主義傳統的置換,將“文革”時期“極左”的政治形態置換為十七年文學的革命形態,并賦予其全新的時代意義,即將文革中的“極左”觀念視為置換對象,以控訴與反思為形式、以人性為工具、以回歸現實主義傳統為目標。因此,對文革的反思修復了具有“歷史總體性”的“主體的歷史”,保證了“歷史的主體”的合法性,并導致了對十七年現實主義傳統在一定程度上的回歸,這種解殖民話語“在反思‘文革’時,帶有多么強烈的政治認同感,那種下意識的表達,也表明了它與五六十年代文學的一脈相承,而這正是這個時期文學最本質的特征”。[2]241這個同時兼具“重建民族國家的主體性”和“重組去殖后的現代文化與本土文化的關系”雙重作用的過程,起源于傷痕文學、深化于反思文學、完成于改革文學。現實主義一元化的歷史慣性和“歷史總體性的修復”構成“能動的相互投射、生成和置換的關系結構”[2]243,以傷痕、反思、改革等主導的現實主義形式抵制著新生的、異質的、非本土的、由更年輕一代知識分子推動的“返殖民”話語。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這里我們使用的“返殖民”不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而是文化上的,指稱的是文革后出現的以西方價值觀念為準繩、力求將中國現實代入到西方語境中的種種努力。有意弱化甚至全盤遮蔽中西文化語境的差異,認同于西方殖民話語刻意制造出的“塑像”,主動陷入受殖者的“迷思”,是返殖民話語的主要特征。在1980年代,這種話語的最大外部特征是以“現代化”作為想象終點,并將其作為區別于解殖民話語的主要界線。敏米(Albert Memmi)在《殖民者與受殖者》一文中詳盡分析了殖民者制造受殖者“塑像”并進而陷后者于“迷思”之中的話語過程,在此基礎上,他指出:“由仰慕而至仿效,等于就是贊同殖民化,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受殖者一旦順應了自己的命運,也就堅決否定了自己,換言之,他是另一種方式否定了殖民者的現實。否定自我和愛慕他人,是一切欲求同化者的共性。以此尋求解放的人,這兩方面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在對殖民者的愛慕中,潛藏著以己為恥、自我怨恨等等復雜的心態。”[3]41返殖民話語出現在1980年代初,同樣源于對中國文化未來走向的理論焦慮,為了對抗解殖民話語所導致的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價值觀念的回歸和對現實主義主流地位的再次確認,返殖民話語不惜以激烈的批判話語和極端的西化訴求來塑造自己的文化圖景。“1982年-1984年的現代派論爭,就是在政治、時代、民族三種巨型話語的交鋒和聯絡中展開,評論界由此對西方現代派、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以及現代化與現代派的關系等基本問題做出各自的解說。由于這次現代派的討論還多少受到建國以來,尤其是“文革”時期左傾政治話語余風的制約,故對文學現代性的訴求還沒有完全擺脫褊狹的階級立場、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觀念、以及政黨意識的干擾。”[4]31解殖民與返殖民兩種話語的分野不在于是否要脫離文革思維、重建社會文化的合理結構,而是在于將中國文學引向何方,是由傳統現實主義暗示的一體化、返回歷史,還是引入西方現代化意識、重建多元化的文化結構。換言之,啟蒙的動因、對象和目標相同,采用的資源、途徑和方法則判然霄壤,恰成針鋒相對之勢。兩者的張力愈強,文化啟蒙的“繁榮”愈烈。
返殖民話語在1980年代文學思潮中主要以“現代化”訴求,借助西方的現代主義來對抗歷史的重新總體化。“‘現代化’只是掩飾‘殖民化’的一種美詞。”[5]194現代主義則是返殖民化話語的基本內容。1980年代關于現代主義的理論論爭肇始于陳焜發表于1981年的《漫評西方現代派文學》一文。該文詳盡討論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概念、內涵、手法、源起、特征等,廓清了將現代主義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的解殖民話語方式,指出不能以現實主義為唯一準繩去衡量現代主義文學觀念。“西方現代派可以說基本上不是現實主義的。如果一定要拿現實主義做是非標準,那現代派就無法談了,它就是一無可取之處了。實際上,我們這些年是把反現實主義當作一個可怕的罪名提出來的,不論什么作品,只要說它是反現實主義的,這個作品就完了。所以,在談現代派文學時,這樣一個問題也是不能回避的——非現實主義的東西有沒有一點生存的權利?”[6]56從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對立出發,在新的時代背景中,為現代主義爭取存活空間和話語權利,這在當時是非同凡響的,可以視為1980年代返殖民話語的開端。尤其是在該文結尾,作者雖對現代主義的局限有所保留,但暢倡之意卻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示。
現在有些同志對民族化的問題很強調,似乎談談西方的東西就是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我覺得,民族化是應該提倡的,因為我們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和豐富的文化遺產,我們的民族文化有許多長處;但是,光強調民族化還不夠,還要學習和借鑒國外的優秀文化。應該承認,我們的文化史是有缺陷的。為了發展我們民族的文化,需要不斷地接受一些新的東西。比如,“四人幫”這類問題的出現,在某些國家是不可想象的。這不能單單歸結為某幾個人的責任,也說明我們的文化有缺陷。再比如,從文藝的角度來講,那種公式化、概念化的東西,現在在許多國家,不要說存在幾十年,就是幾年也不大好想象。這也說明我們的文化有缺陷。[6]58
在這里,以民族化為核心的解殖民話語與以現代派為核心的返殖民話語直接對立起來,雖然兩者共同指向“文革”這一反思對象,但分析理路和最終結論卻大相徑庭。該文將“文革”期間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歸結為中國文化的本體性的缺陷,并認為只有通過“學習和借鑒國外的優秀文化”才能從根本上加以解決,而最重要的途徑則是現代主義的引進。更為學界所熟知、更直接將現代化與現代派連接起來的則是徐遲發表于1982年的《現代化與現代派》一文。這篇論文以現代派作為現代化的必然結果:“我們將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并且到時候將出現我們現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學藝術。”[7]117此后,對現代主義的性質、觀念及其在中國的適應性問題的爭論構成了返殖民話語與解殖民話語的主要對抗形式。這種對抗隨即表現為朦朧詩論爭、對探索戲劇的論爭、對意識流小說的論爭、對高行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的論爭等文學思潮的劇烈碰撞。兩種話語此消彼長,幾經交鋒,到1980年代中期,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進入中國的障礙已經幾乎消失,于是大量引進現代主義的“方法年”(1985 年)和“觀念年”(1986年)成為那時的歷史坐標。
到1980年代中期,雖然解殖民與返殖民兩種話語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文學觀念層面的對抗暫時沉寂下來,對塑造“主體的歷史”和“歷史的主體”的爭議被懸置,但是關于中國文化未來走向的爭論并沒有停止,反而以更為深潛的方式轉換為對改變當下中國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邊緣位置、尋求合理的身份認同方式的不同思路。各自分別提出的文化尋根與走向世界兩種不同的未來設想正面交鋒,解殖民與返殖民的競爭也更為激烈和直接。
二、身份焦慮:文化尋根的本土主義與走向世界的秩序認同
“所有后殖民國家都曾經有過或者依然擁有某種類型的‘本土’文化。……后殖民社會的創新發展常常取決于這種前殖民本土文化及其活躍程度的影響。”[8]1111980年代中期,一方面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觀念的引入已經是大勢所趨;另一方面,向比現代中國更為久遠的古代文化傳統回歸、挖掘其中的優秀質素作為當今社會的文化資源或者反面教材,逐漸成為熱潮。可以說,文化尋根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源于西方現代主義大規模引進所帶來的文化緊迫感,新中國成立后甚至近現代革命中國的文化傳統作為1980年代初解殖民話語的主要內容已經失去了其整合作用,因而對傳統文化精髓的深入挖掘成為最為急迫的任務。這種情形與1920年代中期的“整理國故”思潮有著某種理論方向上的契合度。同時,在返殖民話語盛行的語境中,民族文化主體的話語建構和未來走向成為進一步解殖民化的核心議題。
文化尋根、回歸傳統,是為了對抗日益流行的西化風潮。針對返殖民話語中將人性封閉化、孤立化和心理化的趨勢,文化尋根理論反其道而行之,將古典時代的中國文化傳統視為現代意識的核心,將重新認識傳統看做重新認識現代(人)的前提條件。例如,1984年12月的杭州會議被看做尋根思潮誕生的標志,就在這次會議上,季紅真認為“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實際上也是對人自身的重新認識”,阿城則認為“中國人的‘現代意識’應當從民族的總體文化背景中孕育出來”。[9]15這里突出強調“民族的總體文化背景”當然是為了與返殖民話語進行區隔,以堅持民族文化本位為原則,通過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復興來推進解殖民歷史進程。從更大的范圍看,文化尋根思潮是民族文化現代性進程在1980年代中期的發展形態,也是其必經之路和必然選擇。這種“民族的總體文化背景”更容易在返殖民話語面前形成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力,構建起嶄新的民族文化主體。尋根文學沿著這樣的思路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書寫,選擇那些能夠形成民族認同的文化因素進行肯定,對那些負面的文化因素則進行尖銳的批判。這種策略符合解殖民的需要,也可以對抗返殖民帶來的方向偏差。
西方學者早就指出,在現代民族發展過程中,本民族的話語形象需要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進行建構:“共享的黃金時代記憶、共同的祖先和男女英雄、他們所代表的共同的價值觀、族群起源的神話、移民和神的選擇、群體的象征、領土、令他們與眾不同的歷史和命運以及他們的各種血族關系和祭祀的傳統和習俗等,為理解族群的過去與民族的現在及未來之間的相互聯系,尤其是為理解族群和民族、前現代與現代之間的連接和斷裂提供了解惑的鑰匙。任何忽視這些族群象征因素的解釋都無法使我們領會民族現在的自我理解,或無法使我們理解民族對它們自己的歷史和命運的特殊信仰。并且,沒有對民族內在歷史的足夠理解,我們就會發現我們自己無法估量和判斷在全球時代民族的未來發展。”[10]129這里所列舉的各種“族群象征因素”恰恰是尋根小說最主要的表現對象,也是其反抗返殖民話語的主要途徑。尋根思潮將這些因素放置在民族文化傳統從“前現代到現代之間的連接和斷裂”背景中,從而在“族群的過去與民族的現在及未來”的歷時性層面上進行總體反思,構建出“民族的總體文化背景”及其當代命運。在歷時性層面上展開文化分析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不同的參照物,從而產生對民族文化中許多質素的駁雜判斷和復雜情狀。“文化尋根,實際上也是一種反文化的回歸。”[9]16這種特點決定了1980年代尋根文學中大量出現了所謂“最后一個”的文學主題。“最后一個”所包含的復雜立場來源于尋根思潮作為解殖民話語所采用的總體性視角和歷時性方法。
毫無疑問,尋根思潮的假想敵就是引入中國的西方現代主義。有學者在梳理兩者的關系時認為,兩者的扭結點在于“尋找”,即對人的現代意識的發掘與深化,而返殖民話語的重心在于以個體為本位,尋根思潮對其進行的糾正當然也就要從民族本位的角度出發。
喧囂一時的“現代派熱”,在新時期文學發展中盡管是一個短暫的插曲,但畢竟完成了自我覺醒的第一步。由此發生的“尋找”意識可以看作是“尋根”思潮的先聲。從新時期文壇的“現代派熱”到“尋根熱”,是一部分中國作家自我意識逐漸深化的過程。[9]15
這里的“喧囂一時”、“短暫的插曲”等語匯明白無誤地表達著對現代派的貶抑,而“自我意識逐漸深化”則試圖強調尋根思潮對現代派的優越感和超越性。簡言之,現代派只是尋找自我,而尋根思潮尋找的則是民族文化精神及其前現代、現代和未來命運,似乎兩者高下立判。在比較兩者的藝術能力時,同一位作者更是直言:“如果說,在卡夫卡或博爾赫斯的作品中,呈現的是某種需要費力辨識的世界圖像,那么,在這些‘尋根派’作家筆下你可以直接感悟到人格的意味。”[9]16這些人格類型孕育于中國傳統文化最深、最久、最本質的那些斷面之中,隔著悠久的時空仍然在尋根文學中散發出濃烈的藝術魅力和強大的現實干預能力。只是,這種“歷史人格”的重生能夠多大程度上改造日益物質化的社會現實,那時的理論家們并未深入思考。從今天看來,文化尋根作為文化話語所具有的姿態意義和作為文學思潮所具有的敘事創新似乎要遠遠超過其對社會現實的批判能力和為文化發展方向的指示能力。如同20世紀歷史上的其他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一樣,簡單的回歸傳統并不能直接帶來徹底的解殖民,相反,很多時候,卻更能凸顯某些位于中國文化傳統深層結構中的本質性缺陷。
尋根思潮竭力倡導的“根”的概念最初來自西方文學,本質上是世界范圍內解殖民話語的組成部分和表現形式,體現了受殖者改變世界文學秩序的渴望,本身充滿革命性的先鋒意識和重構各自民族文化傳統的自覺意識。當時的世界語境中,尋根意識更多地包含著受殖者反抗西方殖民者的政治努力和重構民族歷史的話語反抗,以反抗西方中心主義、尋求受殖者平等的現實地位為旨歸;中國語境中,尋根思潮更具文化保守主義色彩,并非重寫而是持守某些既有的文化邏輯,尤其是道德主義,因而更具結構性,而有意遮蔽了世界語境中的解構沖動。與此同時,其解殖民色彩被中國的尋根思潮充分利用。尋根文學的主將韓少功將尋根思潮的解殖民性做了充分說明:“幾年前,不少作者眼盯著海外,如饑似渴,勇破禁區,大量引進。介紹一個薩特,介紹一個海明威,介紹一個艾特瑪托夫,都引起轟動。連品位不怎么高的《教父》和《克萊默夫婦》,都會成為熱烈的話題。作為一個過程,是正常而重要的。近來,一個值得欣喜的現象是:作者們開始投出眼光,重新審視腳下的國土,回顧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學覺悟。他們都在尋‘根’,都開始找到了‘根’。這大概不是出于一種廉價的戀舊情緒和地方觀念,不是對方言歇后語之類淺薄地愛好;而是一種對民族的重新認識、一種審美意識中潛在歷史因素的蘇醒,一種追求和把握人世無限感和永恒感的對象化表現。”[11]27阿城更是認為:“中西文化的發生發展,極不相同,某種意義上是不能互相指導的”,并進而將尋根文學的作品視作“顯示出中國文學將建立在對中國文化批判繼承與發展之中的端倪”的明證。[12]鄭義則認為中國文化要走向世界,必須首先向古老的傳統回歸,即“跨越文化斷裂帶”,建構起完整的民族文化主體。[13]總體上,尋根思潮的支持者們保留文化尋根的解殖民外殼、棄除其解構主義策略、忽略其作為(后)現代主義組成部分的屬性,而從民族主體建構及其與返殖民話語的對抗性出發,將現代派文學觀念視為假想敵,主張以中國傳統文化結構中的優質成分重塑民族性與現代性,從而達到與返殖民傾向相拮抗的目標,完成中國民族文化的現代轉化。這種“買櫝還珠”式的借鑒方式決定了文化尋根熱潮不能持久,不能根本解決1980年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的走向問題,不具備足夠充分的文化創新意義。
與此同時,“走向世界”在此時也已經成為探尋中國文化與文學未來出路的重要思路。1986年,曾小逸主編的《走向世界文學:中國現代作家與外國文學》的出版掀起了尋找中國文學接軌世界文學的可能性與有效途徑的熱潮。一時之間,“走向世界”成為聚訟紛紜的熱點議題,如何融入世界文學格局,甚至如何成為文學強國,成為關乎中國文化歷史命運的焦點問題。在此背景下,三聯書店的“文化生活譯叢”和以“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名義編輯出版的“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商務印書館“漢譯名著”系列、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藝理論叢書”、山東文藝出版社“文化哲學叢書”、遼寧人民出版社“美學譯文叢書”、文化藝術出版社“思想者書系”、貴州人民出版社“《現代社會與人》名著譯叢”、中國工人出版社“世界著名文學獎獲得者文庫”等數量眾多、規模龐大的翻譯成果紛至沓來,迅速形成了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態勢。對西方文學作品的移譯更是多到不可計數。這種局面與1980年代前期現代派傳入中國的情景相比,已經有了很大變化。此時的“走向世界”包含著更多的文化自信及改變世界文學秩序的決心。“西方文學對東方文學的影響與東方文學對西方文學的影響之間的不平衡,是世界歷史發展不平衡的產物。然而,不平衡的被打破終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甚至不妨斷言,一體化世界文學實現的必由之路,正寓于這種不平衡的不斷被打破之中。”[14]16從現有的不平衡狀態到新的“一體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在尋找著自己的機會,那就是融入業已形成的“總體文學時代”。“總體文學時代的任何一種成功的、繁榮的、發達的民族文學,無不以某種方式得益于外來的、他民族的文學;他民族文學,已經構成了任何民族文學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任何民族文學與他民族文學的交流已絕不是——至少絕不僅僅是——一種解決本民族文學內部發展危機的權宜之計,也絕不是一種自我封閉和自我完成的過程,而毋寧說已經成為任何民族文學的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14]24-25基于此,作者強烈反對“文學上的狹隘民族主義”,反對“對本民族文學的‘民族性’的近乎拜物教式的崇拜”,反對將中國文學變成“文學木乃伊”。[14]34-36作者提出的“愈是世界的,愈是民族的;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這樣一個循環邏輯流行一時,影響至今。
然而,問題難點在于“如何將以往以西學為摹本的外源型文學研究、文學史編撰的學術模式,轉化為以后的真正以中國文學現象為中心的內生型的學術創造機制?”[15]在當下的世界格局中,尤其是在西方文學觀念和文化理念仍然居于主導地位的背景中,中國文學的主動融入也意味著對既有秩序的認同和歸依。其中自然包含著返殖民的風險,尤其是導致中國文化產生主體性彌散甚至內部“迷思”的可能。西方的價值觀念很容易伴隨著返殖民話語再次進入到總體性的中國文化,為了尋找中國文學的當下身份,文化尋根和走向世界兩種努力并未給出全面而準確的解答,解殖民與返殖民兩種傾向的對抗仍然存在,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依然晦暗不明。“正因為殖民主義并非被殖民統治者外在地強加上殖民地上一套全新全異事物,把認為是外來的東西盡數扔掉并不能達至解殖民。殖民主義在新與舊的微妙混合中衍生出一種新的自覺意識,解殖民必須走相同的路。解殖民所需要做的,絕不是回歸殖民年代以前被標榜為源遠流長、連綿不絕的純正傳統,而是要富于想象力地去創造新的自覺意識和生活方式。”[16]76因其自身難以避免的局限和時代背景的轉換,尋根文學思潮很快衰微了,代之而起的是先鋒文學——又一次返殖民話語的高潮。解殖民與返殖民的對抗由對民族文化身份的總體性思考轉向了更為具體、分歧更深的敘事策略層面。
三、敘事策略:先鋒文學的強力拆解與新寫實主義的溫情重構
1982年,加西亞·馬爾克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一消息刺激了中國文學界,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進入世界文學主流舞臺的渴望被迅速釋放。拉丁美洲文學大爆炸被中國文學界視作可復制的成功模式,成為中國進軍世界文學舞臺的捷徑。同時,我們在關注拉美文學大爆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時,不僅僅要看到文學技法層面的啟示作用,其對先鋒文學的立場與姿態所具有的文化啟示同樣值得關注,那就是對社會現實的尖銳批評和對主流價值觀念的拒斥,特別是對新時期以來現實主義主導地位的直接對抗。“它意味著對在俄蘇文學影響下建立起來的中國文學傳統模式的消解。”[17]403這種消解本身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先鋒小說家也被稱作“晚生代作家”。雖然文學史上每一代作家都是晚生于前代作家的,但是陳曉明將先鋒小說家的“晚生”性質進行了詳細界定:面對知青作家,他們具有“歷史的晚生感”,因為無法進入宏大的、無所不在的文革敘事;面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和文學大師,他們具有藝術上的“遲到感”,只能“用現代漢語模仿、改裝、重述、拼合、拆解‘大師’們的話語而已”;面對現實主義傳統,他們具有文化上的“頹敗感”。于是,先鋒派的處境變得極其微妙和尷尬。面對當時的主流文化,先鋒小說始終自覺處于邊緣位置。“作為自我表白的話語,先鋒文學始終講述自己的歷史,它玩弄著自己的游戲,它不想顛覆,也不想填補和替代那個中心。……盡管說,先鋒派的行為說到底都是一種對個人表白權利的永久更新,而一切權利最終都是政治性的;但是,在意識形態充分活躍的時代,這種遠離權力中樞的游戲精神,這種否定、拒絕、非承諾的姿態,則是在開辟一條通往不可歸約的現實的精神歧途,在那里,藝術行為僅僅是釋放、書寫著和理解著自我的生命銘文而已。”[18]41借鑒西方的精神資源,抱持著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雄心,先鋒小說卻只能采取自我放逐的書寫方式和形式至上的敘事策略。這種選擇中包含著的對主流文化的無聲反抗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陳曉明將先鋒小說稱作“無邊的挑戰”和“無望的救贖”,說明了其作為西方文化與價值觀在中國進行在地化過程的艱難。
同時,陳曉明從后現代主義角度對先鋒小說進行分析,指出了其在1980年代中國文學思潮中的反叛姿態和文化意義。必須注意的是,這種所謂的后現代性其實與其西方源頭有本質的不同,它仍然是中國本土作家反抗以尋根文學作為最新形式的民族主義話語的基本手段。陳曉明概括出了先鋒文學所具有的8個后現代主義特征,而這些特征無一例外地與先鋒小說作為青年精英文化的表象和作為非主流文化采取的激進策略的歷史地位相關。如,“對中心或本源的拆除”、“對宏大歷史敘事完整性的解構”、“自我與人物的祛魅或符號化”等,都是返殖民話語進入某種受殖文化時最常采用的藝術手段,因為其根本目的正是“把現代批判與分析精神帶給非西方世界”。[19]60也就是說,西方晚期資本主義土壤中產生出來的后現代話語被引進中國,變成了對抗現實中的宏大敘事傳統的利器。中國的先鋒文學將其主要作為文化姿態而非敘事手法進行使用,徹底掘斷了自己的后路,只能越來越決絕,越來越極端,最后被大眾拋棄的命運也就不可避免。同時,對文化傳統和現代歷史進行總體性的深刻批判,暗合了馬爾克斯等作家對拉美歷史的文化審視和詩學批判,暗合了西方對東方文學反面性的期待視野和“塑像”企圖。從馬爾克斯等拉美作家(也包括法國新小說、美國“垮掉的一代”等)到中國先鋒派文學的話語流動過程構成了當時世界范圍內后殖民主義來臨之前返殖民話語的活力與影響。
面對中國文學傳統和強勢的西方文化兩個對象,先鋒文學通過激烈的形式革命來反抗前者,卻又迎合后者。1980年代的先鋒文學“不僅示喻了對傳統文學制度的解構,同時也從另一個方面表達了對強勢文化的屈從。貌似自尊自強的文化要求,無意間又恰恰成為弱勢文化自卑心理的佐證。”[20]305在這種情勢下,一方面先鋒文學不為主流文化所容納,自我放逐于邊緣位置,另一方面不為大眾所接受,被驅逐至邊緣位置,先鋒文學的生存日益艱難。更重要的是,它已經變成了西方話語向中國流動的最好管道,成了“西方霸權統識”的代言人。“西方霸權統識的各種面貌都有雙重特征:一方面,即是對全人類文化的貢獻(同時,西方霸權統識的淵源也絕稱不上是純粹承傳于歐洲或西方本身,在顯示出全人類文化在其中的作用) ;另一方面,又是帝國主義宰制其他文明的表現,權力的影響和效應無所不在。這些影響和效應,滲透于‘種族’、‘進步’、‘進化’、‘現代性’和‘發展’等觀念里,形成的時空領域中伸延的等級體系。于此,我們可見西方沖擊是極為復雜,所衍生的效應亦異常繁多:它既包含著對文明和人類福祉不容忽視的貢獻,亟待汲取,但權力的影響和效應又彌漫一切,和貢獻交織混雜,不即不離。”[16]72-73于是,在多重壓力下,先鋒小說退出歷史舞臺的進程也就開始了。
取而代之的新寫實小說從誕生之時就具有對先鋒小說明顯的反撥意識。在先鋒小說本身的敘事能力走到窮途的同時,1980年代末的社會環境產生了巨大變化。“就客觀或外部原因來說,先鋒文學在20世紀90年代遭遇了全球化和中國大眾化浪潮的沖擊。這兩股潮流所帶來的,就是消費主義、通俗化的興起。”[21]219-220新寫實小說從詩學姿態到敘事技法、文本結構、主題建構、情感蘊涵都呈現出強烈的反精英、反西化、反虛無的解殖民特征。新寫實小說試圖在消費主義和大眾化的時代中建構起屬于中國本土的當下敘事,通過“擬客觀”的現實呈現方式達到向庸常現實回歸的詩學愿景,也即將中國文學敘事從反中心的形而上云端重新拉回雖然無意義卻清晰真實的地面上來。它努力建構的不再是某種宏大的中心敘事,而恰恰就是那個業已被先鋒文學拋棄的生活廢墟。
新寫實小說甫一產生,理論界就迫不及待地將其界定為“后現實主義”,認為其“超越了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既有范疇,開拓了新的文學空間,代表了一種新的價值取向”。[22]56但是,單純將新寫實小說界定為“后現實主義”從而肯定其對傳統現實主義的反叛,這種命名角度遮蔽了新寫實小說對先鋒文學及現代主義文學觀念更大程度上的反叛,忽視了新寫實小說理念在對抗返殖民話語、回歸本土敘事方面的強烈訴求。新寫實小說所采取的寫作策略與敘事技巧等都應該放置在當時消費化和大眾化的時代背景中、放置在解殖民與返殖民兩種話語的對抗中來進行理解。雖然它包含了對社會現實的重新解讀、對人文價值的重新建構,但“更應該是一種對文化現代性的懷疑乃至于拒絕的態度,是社會現代化遭遇挫折之時文學的本能的應激反應,并在不知不覺中構成了對于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反思。”[23]493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對新生代小說的理解應該以解殖民與返殖民兩種話語的劇烈激蕩為背景,不能忽略當時社會環境與文化轉型所帶來的巨大影響,不能單純從內部結構的角度對新寫實小說進行定義與分析。所謂的“零度介入”、“生活流”等藝術特點服從于新寫實小說對現代性焦慮的宏觀表達,表現出“對現代化目標的焦慮,對達成這一目標的手段的懷疑,對民族-國家意識形態體系的潛在抵觸等”。[23]504新寫實小說產生于大眾化和消費化的時代背景中,并以日常化的真實自居,但其詩學結構背后依然隱藏著巨大的意識形態訴求和解殖民沖動。伴隨著全球化而產生的新的返殖民力量和更加充分市場化的本土文化環境并沒有給缺少形式創新、缺乏深度模式、拒絕精神超越的新寫實小說留下多少發展空間。進入1990年代后,新寫實小說被迅速淹沒于多元、失范、無序的文化空間中,那是一個更加“白云蒼狗”、更加“一地雞毛”的話語場域,新寫實小說的文學觀念無力跟進對社會的寫實性展示,從而被迫迅速退潮。
結語
在歷時性的角度,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論爭、文化尋根與走向世界的分野以及從先鋒文學思潮到新寫實主義觀念的嬗替構成1980年代解殖民與返殖民兩種話語相互競爭的三個主要階段,也是兩者對抗的重要場域。在共時性的角度,這種對抗沿著從主體建構、身份焦慮到敘事策略的下延軌跡不斷深化,看似逐漸拋棄形而上的理論思辨而進入具體的書寫方式選擇,但是兩種話語的糾纏卻越來越激烈。尖銳對立的競爭雙方一起被納入了思想啟蒙的共名,紛紜復雜的文化局面下暗流洶涌。1990年代之后,社會文化背景的迅速轉換導致1980年代的文化、文學思潮被過于迅速地歷史化,仿佛“理想主義”等文化標簽成了其全部特征,而這種符碼化、虛擬化、消費化的文化懷舊所具有的當下性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從解殖民與返殖民的拮抗進行對1980年代文學思潮的總體回顧,可以拓展“八十年代言說”的新的途徑。事實上,兩種反向的話語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上文的分析難免缺漏或謬誤,但無疑,解殖民與返殖民兩種話語之間的競爭互生是1980年代文學思潮的核心主題之一。在這個框架下,1980年代文學呈現出立體、有機、繁復的話語結構和動力模式,是重新認識1980年代中國文學思潮的有效途徑。
如同文學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1980年代同樣是豐富復雜的,有著多面的、立體的、自反的內部結構,也有著不同話語傾向的激烈碰撞,絕不是單一的、本質化的。任何以單面的文化語匯、單向的精神維度、單調的價值判斷進入1980年代文化空間的嘗試都將無功而返,不管是以理想主義作為其唯一精神特征還是以“歷史化”的方式化約其復雜性從而進行文學史的機械定位,都是究其一點、不及其余的做法。同樣,任何“重返”都要以承認目標空間的復雜性為前提,而非將其本質化并將其“包含在當下意識之中”,作為進行當下現實批判的手段。[24]199真正的歷史化必須建立在對過往文化空間的客觀解析基礎上,而非以現實的意識形態需要為旨歸。
總體來看,迄今為止的“八十年代言說”還存在諸多問題,不盡人意,更遠未達到客觀化、學術化、復雜化的程度。本文對1980年代解殖民與返殖民兩種話語取向的分析也遠不夠全面。同時,僅僅從解殖民與返殖民出發,自然也不能涵蓋歷史空間的全部復雜性。實際上,殖民、半殖民、后殖民、反殖民、返殖民、解殖民等紛紜復雜的話語體系共同形成貫穿于整個世紀的龐大文化系統,其內部不斷相互競爭、沖撞、分裂,衍生出多元、多向、多態的社會文化形態,在歷時性和共時性維度上都呈現出極其復雜的面貌。從根本上講,正是如此復雜的話語形態推動也豐富著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并深刻影響著現代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互動關系。
參考文獻:
[1]李永東.半殖民與解殖民的現代中國文學[J].天津社會科學,2015(3).
[2]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思潮[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3][法]敏米.殖民者與受殖者[M]//許寶強,羅永生.解殖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4]李永東.“現代派”還是“偽現代派”——關于80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的論爭[J].柳州師專學報,2008(8).
[5]葉維廉.殖民主義:文化工業與消費欲望[M]//葉維廉文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6]陳焜.漫評西方現代派文學[J].春風譯叢.1981(4).
[7]徐遲.現代化與現代派[J].外國文學研究,1982(1).
[8][澳]比爾·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倫·蒂芬.逆寫帝國:后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M].任一鳴,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9]李慶西.尋根:回到事物本身[J].文學評論,1988(4).
[10][英]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M].葉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1]韓少功.文學的根[J].作家,1985(4).
[12]阿城.文化制約著人類[N].文藝報,1985-07-06.
[13]鄭義.跨越文化斷裂帶[N].文藝報,1985-07-13.
[14]曾小逸.論世界文學時代[M]//曾小逸.走向世界文學:中國現代作家與外國文學,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5.
[15]賈振勇.文學史的限度、挑戰與理想——兼論作為學術增長點的“民國文學史”[J].文史哲,2015(1).
[16][法]皮特埃斯,巴克雷.意象的轉移——“解殖”、“自內解殖”和“后殖民情狀”[M]//許寶強,羅永生.解殖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17]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18]陳曉明.無邊的挑戰[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19][法]南迪.親內的敵人(導論)——殖民主義下自我的迷失與重拾[M]//許寶強,羅永生.解殖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20]孟繁華.中國當代文學通論[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
[21]陶東風,和磊.中國新時期文學30年(1978-2008)[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22]王干.近期小說的后現實主義傾向[J].北京文學,1989(6).
[23]許志英,丁帆.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24][日]加藤三由紀.重讀八十年代文學——以“重返八十年代文學現場”為根據[J].孫放遠,譯.當代作家評論.2010(1).
責任編輯:萬蓮姣
Rethinking of 1980s Literary Thoughts in China with the View of Decolonization and Recolonization
LIU Yong-chun,ZHANG Li*(College of Chinese,Ludong University,Yantai,Shandong 264025,China)
Abstract:Disputing between Decolonization and Recolonization is one of most important literary themes in 1980s China which lasted all through the decade and provided huge power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Most literary phenomena,thoughts,and schools developed under the competition of these two literary discourses.To revaluate the 1980s literature,it is supposed to research the interactive pattern of the two discourses.Also,this interactive pattern is a part of 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20c China literature with a view to semi-colonization.
Keywords:literary thoughts; decolonization; recolonization; discourse pattern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981(2015) 04-0079-07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當今中國文化現狀與發展的符號學研究”(項目編號: 13&ZD123) ;重慶市教委課題“傳播符號學視域下的渝東北生態涵養發展區綠色公共領域建構研究”(項目編號: 14SKL06)。
作者簡介:劉永春(1976-),男,文學博士,魯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張莉(1990-),女,魯東大學文學院2013級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