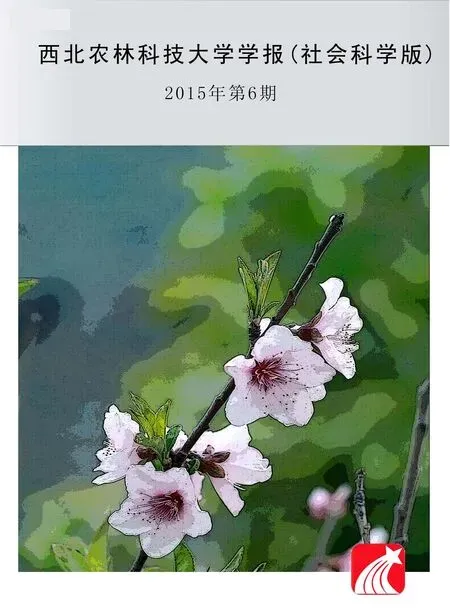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企業式家庭農場
高萬芹,蔡山彤
(1.武漢大學 社會學系,武漢 430074;2.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武漢 430074;
3.西南財經大學 天府學院老年服務與管理研究所,成都 610000)
?
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企業式家庭農場
高萬芹1,2,蔡山彤3
(1.武漢大學 社會學系,武漢430074;2.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武漢430074;
3.西南財經大學 天府學院老年服務與管理研究所,成都610000)
摘要:在政策與市場的推動下,以改造傳統農業為目標的企業式家庭農場應運而生。企業型家庭農場的生產經營方式具有如下特征:高資本技術要素、大規模專業化經營、集約化生產管理及企業化的市場銷售和風險規避方式,這完全符合政府對現代農業的期許,因而常常被樹為典型。但是,因為在發展中要求較高的環境、面臨較大的風險,企業式家庭農場只能是少數精英農戶的選擇,大多數小農無法走通此路。因此政府不應將農業現代化的目標完全寄托于企業式家庭農場身上,大量存在的小農、中農等多元經營方式作為現代農業基礎,仍將發揮重要作用。
關鍵詞:企業式家庭農場;高值農作物;資本勞動密集;規模經營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的引出
自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建立新型家庭農場開始,各地方政府都在不斷加大對家庭農場的扶持力度,把家庭農場視為新型農業主體的重要實踐方式之一[1]。所謂家庭農場,是指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從事農業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生產經營,并以農業收入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其實質是采用先進的技術和現代農業生產要素改造傳統農業中落后的經營方式。之所以提倡家庭農場,一是對大規模企業經營實踐效率效益的反思[2,3],另一方面是因為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符合中國人多地少、農村剩余勞動力眾多的國情,土地的社會保障仍是重要的戰略問題[4];加之家庭經營的方式十分適合農業生產的特點而具有效率效益[5],因此,家庭農場被視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主要發展方向。然而,學界對家庭農場的具體經營形式及其規模并沒有達成統一的認識,這種分歧主要體現在對現代化大家庭農場和小規模家庭農場兩種模式的爭論上。
主流觀點認為現代化的家庭農場不同于傳統小農的經營方式和邏輯,家庭農場應該走資本密集型的大農場之路,以收益最大化為目標,以市場為導向,融合科技、信息、農機、金融等現代生產因素和現代經營理念;以規模化經營、企業化管理為組織特征[6-9]。這種家庭農場類似于企業,其本質是農業資本經濟[10]。企業式家庭農場能夠面向市場需求,以現代生物工程技術改造傳統農業,發展生態高效農業,解決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問題,并實現農民增收[11]。作為高資本、高技術投入的現代農業經營形式,弱質的小農是難以發展成現代化的家庭農場的,因此,政府應該積極培育家庭農場主成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并規范土地流轉市場,加大金融、技術等政策扶持,為家庭農場的成長打造好外部環境[12-14]。
另一種觀點認為家庭農場應立足于小農經濟,以農戶家庭內部勞動力投入為主,發展“勞動和資本雙密集”的小而精的家庭農場[15]或者是“小農+中農”的小規模家庭經營,而非依賴機械和雇傭勞動的資本密集型的大家庭農場[16],政府應該加強生產環節的配套服務,解決小農戶與大生產、大市場之間的困境[17]。
兩種觀點的分歧在于農業現代化走一條資本密集型的規模經營之路,收益讓資本或者少部分農民占有,還是農業收益保留在農業領域并由大部分農民占有?也就是說家庭農場的規模和經營方式要不要立足“小農經濟”。在改造傳統農業的過程中,現代農業技術要素和資本要素比例的加大,很可能會造成農業被資本異化,但是,落后的小農生產方式確實存在難以可持續發展的問題[18]。面對這種兩難困境,黃宗智認為發展資本和勞動雙密型的小規模園藝業是一種有效的路徑,中國高附加值農作物的發展空間(主要是蔬菜、瓜果、木本堅果、花卉等園藝業),給以家庭勞動力為主的“小而精”家庭農場帶來了機遇[15]。蔬菜等非谷物類農作物,需要密集的勞動力投入(栽種、收割、采摘、澆水、除草、施肥、施藥等),很多環節無法采用機械,同時這些作物的產值又比較高,農戶可以憑借小規模土地收入所得滿足家庭消費需求。與谷物類家庭農場可以高度依賴機械不同,非谷物類家庭農場需要高度依賴勞動力,這對以家庭勞動力投入為主的“小而精”家庭農場具有重要意義,符合人多地少的國情,也比雇工經營的方式便宜和高效。
黃宗智看到了高值農作物的發展空間帶給小而精“非谷物類家庭農場”的重要契機。然而,高值農作物的發展空間也引來了資本,特別是政府對規模經營和現代農業的鼓勵,資本密集型的雇工式家庭農場大量產生,因其較高的現代技術要素和企業化的運營管理,而容易被政府塑造為典型,其經營規模也超出以自身勞動力投入為主的家庭農場。這種雇工式家庭農場已經超出黃宗智意義上的“小而精”家庭農場,因其在農業生產中無法用機械來替代勞動力,其雇工成本占據生產投入的很大一部分,現代農業技術的資金投入也占據了較大的比例,生產要素配置已經不同于資本節約型的小農經濟,走上了依賴雇傭勞動和技術的資本密集型的農業現代化之路,類似于企業經營。
原本小農是無資本優勢、保守型的,但在市場經濟興起下,經濟效益較高的經濟作物以及一些畜牧水產養殖的發展空間讓農民自我積累有了質的突破,再加上政府的推動和扶持,一些家庭農場已經出現了資本和雇工投入雙密集的現象,農業經營的企業化邏輯不斷凸顯。本文著重探討非谷物類的家庭農場生產方式及其經營的特殊性對家庭農場發展的影響。
二、企業式家庭農場的生成及其特征
2009年起全國開始試點家庭農場,各地依據自身條件的不同,形成不同的規模和經營模式,城鎮化進程中村莊內部的資本積累、留守勞動力和土地流轉市場的發展,以及國家政策的持續推動成為家庭農場產生的重要力量[19]。然而,在鼓勵發展規模經營的同時,一些家庭農場的發展已經超出了家庭經營的范疇,走向了資本技術密集型的企業式家庭農場,陳義媛更是把這種農業轉型過程中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比重的上升,看做是資本主義式家庭農場在中國的產生[20]。在建設現代農業的過程中,必然會帶來資本技術要素投入比重的上升,這不僅從生產力上,也從生產關系上改造著農業經營的方式和形態[21]。在這場現代化的改造中,家庭農場的形態和類型也出現了多樣化,由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變為家庭成員為主要的經營管理者,然而又不完全類似于農業企業式的大規模經營,因此很值得我們研究。筆者以中部地區H市郊區家庭農場的發展經營狀況為例,探討在資本、技術和現代經營管理知識相對匱乏的小農是如何走向現代化的雇工式家庭農場,并進一步反思其生成條件、經濟屬性及其典型性。本文經驗材料來自于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在 2014年12月到2015年1月展開的為期15天的課題調研。
H市從2009年起,開始試點發展家庭農場,并逐步形成了一批現代都市郊區型家庭農場,這些家庭農場一般直接面向市場。H市農業主要在新城區,本文以其中N區家庭農場的發展狀況為例來進行說明。N區是一個人少地多的地區,農戶大都在種地,當地政府比較支持家庭農場的發展。截止到2013年底,N區有家庭農場百余家,已在工商部門登記注冊20多家,帶動土地流轉達1萬余畝。家庭農場共有勞動力200余人,雇傭人數近1 000人,土地承包面積從20~300畝不等,土地流轉根據土地所處位置的好壞,每畝按600~1 000元/年租給農場主,家庭農場農業收入平均達20萬元以上,其中較為成功的是土生土長的“菜樂家庭農場”。
(一)企業式家庭農場——菜樂家庭農場的發展
G村現有村民小組6個,農戶315戶1 139人,全村勞動力889個,其中常年外出務工189人。全村農用地總面積4 847畝,其中耕地3 308畝、林地70畝、養殖水面100畝,其他1 369畝(村莊外垸由河流沖積形成的灘涂)。因為較多的土地面積,很多農戶留在村莊中務農,村里30畝以上的家庭農場有14戶。
李某,今年50歲,村里規模最大的家庭農場主,他原本是一個菜販子,90年代末因生病加上生意失敗背負債務,被迫回家種地還債。剛開始種了近10畝的常規蔬菜作物,夫妻倆自產自賣,但總體效益不高,很有生意頭腦的李某發現反季節蔬菜的收益更高,便在2001年搭起竹架大棚,改種反季節蔬菜。李某為了獲得更好的產量和效益,還主動學習和接受一些農技培訓,以改進品種和種植技術。2004年,在市里的農業技術培訓過程中,受到啟發,開始引進“豬—沼—菜”生態農業模式,當年搭建了15畝的竹架大棚,建起了養豬場,養了3頭母豬、出欄了54頭小豬。收益見效后,李某逐漸擴大種植規模和養殖規模。截止到2013年底,一共擁有148畝的鋼架大棚,創利潤80萬元左右;養殖場母豬數57頭,出欄數超過1 000頭,純利潤10萬元左右。2014年種植規模擴大到186畝(租金也由原來的600元上漲到900元,租期延長至16年)。現在他的“菜樂家庭農場”已經是市級示范家庭農場和科技示范基地,成為集生產和銷售一體,種養結合,外加餐飲休閑的綜合型家庭農場,并擁有了自己的商標和品牌。
(二)企業式家庭農場的主要特征
1.生產面向市場。李某并非單純的商品化小農,而是具有較高市場分析與定位能力,用現代技術和經營理念改進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管理者。李某長期堅持自銷,每天都會到菜市場擺攤,除了銷售,還能時刻了解市場行情,根據市場行情及時掉頭轉向,爭取在價高時賣出,在行情不好時更換品種。李某的蔬菜基地里面種植的都是有特色、產量大、賣價高的品種,這些品種都是他在詳細觀察了市場之后引進的。此外,李某也非常注重農產品的市場信譽和品牌效應,經過幾年的積累,他的農產品已經在當地農貿市場中有較高的口碑。
2.高技術投入。李某十分重視引進新技術來抵御風險,增加市場收益。從剛開始種植蔬菜,他就積極學習一些高收益品種的種植技術,定期參加市里、區里的技術培訓,與政府的農技服務人員長期保持聯系,并在專家的指導下把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模式用于實踐。“豬—沼—菜”循環生態模式就是他在接受技術培訓時受到啟發而采用。一是種養結合,循環使用,降低了成本;二是提升了錯季銷售能力,降低了市場風險;三是形成了高附加值的品牌效應。這種循環農業中,一些質量較差及其銷路不好的蔬菜等可以用來養豬,豬糞、蔬菜廢渣等用來生產沼氣,沼氣用來做溫室育苗養殖,沼渣作為有機肥料通過管道輸送到田間,沼氣沼渣還有防蟲效果,降低了對農藥化肥的需求,提升了農產品的品質,因而具有了較高的附加值。每年他節省肥、水、電支出2萬多元,節省農藥支出0.5萬元,而且蔬菜上市期提前,產量和質量提高了15%左右。循環農業的模式,連年為他節支10萬元以上。一般來說,他的菜一到批發市場就會被商家一搶而空,價格還比別人貴。即使遇到行情不好的時候,李某也有較強的抵御能力,蔬菜可以不用出售,直接作為豬飼料;豬肉價格較低時,用無法銷售的蔬菜作為飼料,可以推遲銷售時間,等到價格較好時再出售,增強了產品的錯峰能力,高價售、低價藏。有些農產品上市供不應求,他就請教專家,提高產品的復種能力,以增加產量,延長產品的銷售時間。
3.高資本投入。面向市場的定位和高技術投入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李某僅搭建148畝的設施大棚,總投入就超過300萬元,其中政府補貼60萬元。到現在,蔬菜基地和養殖場投入已有420萬元。實際上,李某從2002年采用設施農業開始,就踏上了民間借貸之路,為了搭建竹架大棚從民間借款3 000元,利息5分,付利息2 200元。2004年建設豬場和沼氣池時,民間貸款10萬元,利息3分,付利息7萬元。2006年擴大養豬規模時,還從民間貸款20萬元,利息是3分。2010年李某將貸款還清,有了60萬元的剩余資金,他又進一步的擴大種植規模,將種植面積擴大到123畝(每畝租金600元)。當年為了搭建33畝的鋼架大棚又貸款18萬元(總共花費45萬元),民間借貸僅利息累積達到50萬元。
除了民間借貸,還有大量的銀行貸款,特別是從政府鼓勵發展科技示范戶和家庭農場以來,從2006年開始,通過政府工作人員的關系,陸續貸到一點銀行貸款。2011、2012、2013、2014分別通過承包經營權向銀行貸款30萬、40萬、35萬、35萬元,獲得全部貼息。截止目前,他從銀行貸款160多萬元,到2014年底為止,李某還有100萬元左右的貸款尚未償還。
4.大量雇工。伴隨著經營規模的不斷擴大,再加上蔬菜等高附加值農作物需要密集的勞動力投入,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勞動量遠遠超出家庭投入能力的范圍,兩夫妻只能雇工進行生產,夫妻兩人主要負責生產安排、監督管理、市場銷售和技術指導等,很少直接參與生產過程。
雇傭的農業工人基本都是本村人,2014年,在總成本投入中,長工20人,每年每人工資是2.4萬元;短工最多時有40多人,雇工工資每天60元。每年的雇工成本不斷上升,占據了很大一塊份額。再以2010年為例,李某用去年盈利的60萬全部進行擴大生產,流轉土地123畝(每畝租金600元),租金再加上種子、農藥、化肥等其他流動成本57萬元;長工18個,投入近42萬元,短工投入21萬元左右,當年投入雇工成本63萬元;不計夫妻倆人的勞動收入及其固定資本的折舊費,雇工成本占據流動資本投入比重的52%左右;當年純收入蔬菜33萬元,豬15萬元,流動資本利潤率為41%。
李某的家庭農場已經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小農經濟,在利潤的驅使下,其流轉的土地傾向于突破人情邊界,以支付流轉費的方式擴大經營規模。他們并不擔心擴大規模后勞動力不足所造成的生產不便,而是采取雇工的方式[20]。且雇工主要是為了滿足生產需要,這就具備了農業資本主義的經營性質[21]。此外,從生產要素的投入看,李某在生產經營的過程中,并不是處于節約資本或是降低風險的保守態度去經營農業,而是不斷通過對農業技術的學習和市場機會的敏銳把握,不斷地加大對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投入比重,借貸在資本周轉中也占據了很大一部分,是有著較高現代生產要素投入、資金循環和雇工體系的微型企業式家庭農場。
三、企業式家庭農場發展的制約因素
從總量上計算,李某的家庭收入是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而增加的,但實際上其邊際效益是不穩定的、經營風險是成倍增加的。大部分企業式家庭農場由于在市場風險控制能力、經營管理能力、資金環境等方面的差異,很難像李某一樣成功。高投入、高收益、高風險的經營模式,讓不少農民在盲目投資擴大以后,出現虧損。企業式家庭農場的運轉面臨一系列制約條件,只有少部分農場能夠成功突圍。
(一)企業式家庭農場發展的人力資本困境
小農一般傾向于保守,其經營規模和經營方式大都以維持家計和保持家庭內部的生產、消費平衡為準[22],很少有農戶會有企業家般的擴張精神,純粹為了生產和利潤,而非消費目的,把全部收益,甚至是依賴借貸來不斷地擴大再生產。一般小農缺乏這種類似于企業家的擴張精神,因此,村莊中能成為企業式家庭農場主的人比較少,一般都是由經濟能人和村莊精英轉化而來,他們不斷地擴大規模,甚至是采取雇傭勞動,直到超出家庭勞動力直接管理的范圍和資本投入的承受限度。
此外,企業式家庭農場在面向市場、集約化的經營管理能力等方面比一般農戶要高。不僅要求農場主要有企業家般的精神和魄力,更需要經營能力,而不是盲目地擴大規模。其集約化的經營管理方式要求農場主能夠根據市場來進行決策和轉型,更集中合理地運用現代農業生產技術和經營策略,提高效率效益。李某在經營家庭農場的過程中,不管是“豬—沼—菜”模式還是鋼架大棚的改進、新品種的引進,都是在探索市場和學習現代農業技術的基礎上,不斷改進生產模式的結果。其直接的經營管理和直銷式的營銷策略,也控制了層級管理的風險并降低了中間環節的成本。此外,做品牌農業、注冊產品商標、提升產品附加值的營銷策略,都讓他保持了較高的收益狀態,但這種經營能力和魄力是普通農民所不具備的。即使是村莊精英或經濟能人,像李某這樣成功的也很少,很多人在走向規模經營的道路上,以背負債務告終。例如同是省科技示范戶的夏某(村主任),就在盲目擴大經營規模后,背負債務,走向破產。20畝左右的規模,他可以控制和盈利,但達到一百多畝以后,采取雇工的企業式管理,就難以獲利。像夏某這樣的村莊能人盲目擴大規模后,走向失敗的很多。
(二)企業式家庭農場的市場困境
受市場供需結構及其市場飽和的限制,決定了家庭農場盈利空間有限,只有少部分農場主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勝。不像大宗糧食作物,經濟作物的收益受市場供需結構影響顯著。我國經濟作物的市場結構總體上供大于求。以蔬菜市場為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菜籃子工程”的推動下,我國蔬菜的總產量迅速提高。2002-2011年,蔬菜種植面積基本穩定在19 000千公頃左右,而蔬菜總產量在60 000萬噸上下浮動。目前,我國的蔬菜市場基本上處于飽和狀態[23]。隨著資本規模經營和現代農業的大力推行,局部農產品呈現過剩狀態。現在,人口只占世界19%的中國,集中了世界上80%的大棚,生產出了全球67%的蔬菜,而中國生產出的蔬菜有一半以上被浪費了。除了蔬菜,50%以上的生豬,50%的蘋果、40%的柑橘,都是中國生產的[24]。很多地方出現了菜賤果賤傷農的情況。與市場供過于求相對應的是市場供給信息的不對稱,這導致市場波動性很強。不少地方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推行一村一品,農民一哄而上更是加大了種植經濟作物的風險。此外,農業產業所創造的增加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低,鼓勵資本下鄉大規模經營,讓農業收益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農民能夠分得的利益越來越少。
正因為市場結構性供給過剩,而依賴市場稀缺和高經濟附加值的企業式家庭農場的生長空間才更加有限,在市場利潤空間的壓縮下,只有少部分生產管理、營銷能力強的農場主才能在市場的淘汰賽中存活,大部分企業式家庭農場像夏某一樣處于賠損狀態。
(三)企業式家庭農場的制度困境
企業式家庭農場的發育需要土地流轉市場、勞動力市場、農機市場和農技市場等要素市場的不斷成熟。從土地流轉市場來看,因為企業式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一般超出了自己熟人社會的范圍,有的甚至是流動性的家庭農場[25],這就需要地方政府和村級組織出面解決土地流轉的問題,租金高、租期不穩定是家庭農場面臨的問題,此外還有一些額外的交易成本,都增加了家庭農場的負擔。從勞動力市場上說,農業較低的平均利潤使家庭農場難以承擔較高的雇工成本,農場主只愿意付較低的工資價格,而較低的工資價格無法解決農場優質勞動力稀缺的問題。從農技的供給狀況上看,大部分家庭農場都無力解決現代生產要素和先進技術引進過程中的技術難題,創新型的家庭農場比較少,大都是跟風式學習他人較為成熟的技術和模式,這也將其帶入市場慢慢飽和的困境。再就是政府政策的影響,政府在治理農業的過程中,更多地出于對政績的考慮,而非單純的市場績效[26];那些符合政策要求的、代表政府發展現代農業理念的家庭農場更容易獲得扶持。國家及省市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資政策規定在“千畝”以上,還有一些財政貼息貸款和農業政策保險都必須是省市示范型家庭農場才能獲得,只有家庭農場中的佼佼者才有資格申請。許多家庭農場為了獲得一些設施農業的項目補貼,可能會超出自己的能力流轉土地,從而最終導致經營失敗。政策扶持環境的不利,難以真正有效地給予家庭農場正確的支持。
(四)企業式家庭農場的資金困境
對于企業式的家庭農場來說,資本投入在家庭農場的運轉中已經占據十分重要的位置,資本投入和周轉資金跟不上是很致命的。因此,良好的金融借貸環境對家庭農場的發展來說十分必要。家庭農場面臨的金融環境的制約主要是指金融借貸能力的限制。一方面普通的農戶不具備成長為企業式家庭農場的資金,缺乏預付資本和初始基金。農村的金融體系并不發達,農民獲得信貸資金特別困難, 中國2.4 億個農民家庭中,大約只有15%左右從正規的金融機構獲得過貸款,85% 左右的農民要獲得貸款基本上都是通過民間信貸來解決;另一方面,正規的金融機構不愿意進入農村,農業是弱質產業,農民是弱質群體,貸款回收的風險較高,成本也比較高,只種幾畝地的2.4 億個農戶,要進入金融系統,確實讓很多大銀行感到成本很高[27]。
家庭農場是有門檻的,需要一定的資本量(預付資本包括租金、農資、機械投入和部分雇工工資)和良好的“人力資本”(面向市場、經營能力,風險抵抗力等)[18]。此外,還需要一定的制度和政策支持環境。正是因為上述結構困境和外在條件的限制,在當下的環境中,家庭農場只能是作為個體突圍性的存在。家庭農場的成功意味著農業的收益由少部分農戶來獲得,國家出錢出力來幫助這少部分農村精英成為現代化的農業主體。為此政府要提供技術培訓和技術服務,創造好制度環境,包括融資環境、稅收優惠、土地流轉市場、農業公共品供給的傾斜以及大量政策補貼。幫助精英成為更強的精英,讓其成為現代農業和新型農民的示范。
四、企業式家庭農場發展的誤區
企業式家庭農場的成功運營似乎化解了“三農”問題的困境,滿足了當下政府和學界對家庭農場的全部想象。職業化的農民、專業化的生產和規模化的經營,既解決了誰來種地的問題,又提高了農民的收入。但是,這種家庭農場的運營模式不易普及。家庭農場的繁榮具有虛假性,留守在農村的2.4億農民,只有少數能夠像李某這樣在稀缺性和競爭性的市場經濟中獲得成功和較高的經營收益。
家庭農場是現代農業的一種探索,在一些發達地區和大都市的郊區,外在環境和條件成熟的地方可以適當提倡,少部分個體農民可以通過努力發展為效益較好的家庭農場。但政府不能因此就過度提倡。一方面,家庭農場存在結構性問題,發展空間有限,大量補貼可能導致資源浪費和效率損失[28];另一方面“三農”問題并非單純的現代化問題,從政治、社會影響上看,在大部分農民無法離開農業、轉移為市民的條件下,農業作為保障而非發展用途的客觀要求仍然存在。大力扶持家庭農場實際上是擠壓小農戶的生存空間,幫助大戶打敗小農[29]。扶持“精英農戶”,邊緣化小農;同時也擠壓了那些以自身勞動力投入為主的“中農”的生存空間和非雇傭勞動的“小而精”的家庭農場的發展。而不管是作為農村社會穩定器的留守老人農業[30],還是作為農村中堅力量的中農[31],還是具有發展意義的小規模家庭農場[9],依然具有經濟學意義上的效率效益和政治社會意義的保障功能。
因此,政府在提倡發展家庭農場時,也要把規模控制在家庭勞動力投入為主的范圍內,防止雇工式的家庭農場,盡量實現農業產值的平均化,尤其是高值農作物的家庭農場,其資本和雇工式的經營方式,已經超出普通農戶的經營能力和風險控制范圍,過度鼓勵其發展,只會讓農民去冒險創業,導致農業經營失敗的幾率更大。
五、結語
中國現代農業的局面不應是家庭農場一支獨秀,而應是小農、中農和企業式家庭農場多元共存,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人多地少的背景下,農業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不會是一蹴而就的,企業式家庭農場作為現代農業實現方式的一種嘗試可以獲得適當扶持,但不能因少數典型個案的成功而忽略了廣大小農的利益。通過技能培訓和社會化服務推進小農經濟的改造,保持農村社會的穩定,也許更加符合國家和農業的長遠發展。
致謝:本文寫作的問題意識來源于與魏程琳、王海娟、杜鵬、杜嬌的集體調查,張建雷、韓慶齡博士對本文提出了修改建議,特此一并致謝。
參考文獻:
[1] 新華網.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的若干意見[EB/OL].[2013-01-31].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1/31/c_124307774.htm.
[2]于洋.中國農業規模經營的理論反思[J].農業經濟,2003(12):15-17.
[3]羅伊·普羅斯特曼,李平,蒂姆·漢斯達德.中國農業的規模經營:政策適當嗎?[J].中國農村觀察,1996(6):17-29.
[4]張曉山.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對策[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8(8):28-33.
[5]許經勇.論農業企業規模經營[J].農業技術經濟,1986(10):13-16.
[6]高強,劉同山,孔祥智.家庭農場的制度解析:特征、發生機制與效應[J].經濟學家,2013(6):48-56.
[7]蔣輝.蘇南地區進一步發展家庭農場的探討[D].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7.
[8]關付新.我國現代農業組織創新的制度含義與組織形式[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5(3):47-51.
[9]張敬瑞.家庭農場是我國農業現代化最適合的組織形式[J].鄉鎮經濟,2003(9):18-19.
[10]曾福生.中國現代農業經營模式及其創新的探討[J].農業經濟問題,2011(10):4-10.
[11]劉啟明.家庭農場內涵的演變與政策思考[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87-94.
[12]胡筱亭.家庭農場發展與金融支持策略研究——以上海松江家庭農場為例[J].農村金融研究,2013(12):22-29.
[13]任亞軍,施勇.家庭農場發展與金融支持——以江蘇省淮安市為例[J].金融縱橫,2013(6):75-79.
[14]施國慶,伊慶山.現代家庭農場的準確認識、實施困境及對策[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5(2):135-139.
[15]黃宗智.“家庭農場”是中國農業的發展出路嗎?[J].開放時代, 2014(2)::176-194.
[16]賀雪峰.重新認識小農經濟[EB/OL].[2014-07-17].http://www.guancha.cn/he-xue-feng/2014_07_17_242295.shtml?XGYD.
[17]黃宗智.中國新時代的小農場及其縱向一體化——龍頭企業還是合作組織?[J].中國鄉村研究,2010(8):11-30.
[18]桂華.中國農業生產現狀及其發展選擇[J].中國市場,2011(8):18-22.
[19]張建雷.社會生成與國家介入:家庭農場產生機制研究[J].地方財政研究,2014(10):16-27.
[20]陳義媛.資本主義式家庭農場的興起與農業經營主體分化的再思考[J].開放時代,2013(4):137-156.
[21]王立新.農業資本主義的理論與現實:綠色革命期間印度旁遮普邦的農業發展[J].中國社會科學,2009(5):189-208.
[22]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組織[M].蕭正洪.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12.
[23]我國蔬菜供給數量趨于飽和,產品質量有待提高[EB/OL].[2013-09-05].http://market.chinabaogao.com/nonglinmuyu/0951642962013.html.
[24]溫鐵軍.資本過剩與農業污染[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3(6):64-67.
[25]余練,劉洋.流動性家庭農場:中國小農經濟的另一種表達[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6):9-13.
[26]龔為綱.農業治理轉型——基于一個全國產糧大縣財政獎補政策實踐的分析[D].華中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29-30.
[27]陳錫文.資源配置與中國農村發展[J].中國農村經濟,2004(1):4-9.
[28]孫新華.農業經營主體:類型比較與路徑選擇——以全員生產效率為中心[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3(12):59-66.
[29]賀雪峰.政府不應支持大戶去打敗小戶[EB/OL].[2013-05-17].http://news.wugu.com.cn/article/20130517/52525.html.
[30]賀雪峰.土地問題的事實與認識[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5-19.
[31]楊華.“中農”階層:當前農村社會的中間階層——“中國隱性農業革命”的社會學命題[J].開放時代,2012(3):71-87.
[32]黃宗智.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中國的農業發展[J].開放時代,2012(3):10-30.
The Entrepreneurial Family Farms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GAO Wan-qin1 ,2CAI Shan-tong3
(1.DepartmentofSociology,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4;
2.ResearchCenterofChinaRuralGovernance,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430074;
3.InstituteofElderlyServicesandManagement,TianfuCollegeofSouthwestern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Chengdu610000,China)
Abstract:With the transforming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s the goal, entrepreneurial family farms have emerged under the policy and market driven. It was held up as a typical model, because the mode of operating family farms contains high technical elements of capital, professional scale, intensive production management as well as marketing and entrepreneurial risk-averse way. It almost satisfies the government’s expectations for modern agriculture. However, because of higher risk and require greate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is can only be a select of few elite farmers, while most small farmers can not go this road. Therefore, 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an not merely relies on enterpreneurial family farms, it needs to achieve optimal combination of multi-mode of operation, and small and middle farmers are still important.
Key words:entrepreneurial family farm; high value crops; capital and labor-intensive; scale operation
文章編號:1009-9107(2015)06-0074-07
中圖分類號:F306.1
文獻標識碼:A
作者簡介:高萬芹(1987-),女,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社會學。
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 (2014T70706)
收稿日期:(20)2015-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