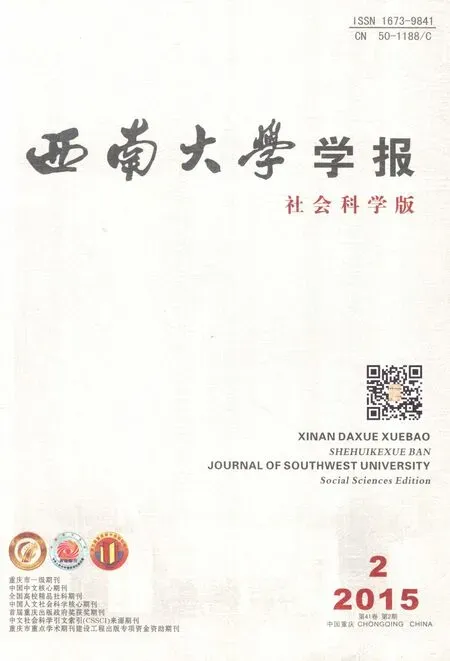從混沌中蘇醒:清末民初身體的重新發現與再認識?
楊 程,許祖華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430079)
從混沌中蘇醒:清末民初身體的重新發現與再認識?
楊 程,許祖華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430079)
清末民初,隨著社會的轉型和西方自然科學理論的涌入,中國傳統的身心觀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思想界逐步形成了以身為本位的身心一元論思想,讓身體由“虛”入“實”,成為有血有肉的物質實體。而尚武、人種改良、新民運動等思潮,一方面希望通過改造個人身體來改造國家,另一方面也強調通過完善國家制度來解放身體,以此形成個人與國家的雙向互動。但是,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前,身體剛從封建禮教的控制中解脫出來,旋即又陷入了被工具化的境地。
身體;清末民初;身心一元論;國家;個人;尚武
身體是“一個人身份認同的本源”[1],然而,身體本身卻又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作為物質的身體是相對穩定的:這一點正好與身體轉向要求身體本身凝固下來以便身體話語能夠依附在一個較為堅實的基礎上相吻合;另一方面,對客體世界的認識則是歷史的、意識形態的、流動的。身體話語如何在這種穩定與流動之間尋求到合理的平衡點以便發起真正有效的反擊?”[2]這是身體史與文化史上一個長期糾結的問題。在中國古代特定的社會環境中,“身”一直作為“心”的附屬,牢牢地被“心”所貶抑和控制著。鴉片戰爭之后,在亡國滅種的壓力下,有識之士開始向西方尋求強國保種之道,大量自然科學書籍進入中國,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走出國門,對西方國家有了更直觀的了解。在此基礎上,受啟蒙主義、進化論等思想的影響,許多思想家對身體有了全新的認識。他們主張身體平等和身體解放,希望通過提高個人身體素質來改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在他們的努力下,中國傳統的身心觀逐步完成了現代化轉型,“身”從“心”的壓制下解放出來。
一、身心一元論與身體實體化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身”與“心”、“形”與“神”的關系一直是重要的命題。且不論楊朱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3]的極端貴身思想,其他先秦哲學家也大多主張身心一元論,對身體較為重視,《道德經》中有“故貴身于天下,若可托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4]之語,莊子提出了“無情”[5]的觀點,試圖擺脫思想對身體的束縛。老、莊都希望身體回到“赤子”的原始狀態,唯此才是最合于“道”的,才能“逍遙游”,這也就是身體的本體論。不過,老莊思想中已經存在著將身體虛化的苗頭,他們所談的身體并不是以骨骼、血管、肌肉、皮膚組成的物質實體,而更像是與山川、草木乃至宇宙本體在本質上相通的概念化的身體。孔子也是主張身心合一的,《論語》中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6]之語。到了孟子,身、心二者有了顯著分野,身成了阻礙心的發展所需要克服的東西:“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7]就是將身擺在了心的對立面,在身體的痛苦中才能“益”其心。后世思想家既接受了孟子以“心”為本位的身心二元論思想,同時又發展了老莊將“身”虛化的理論,使實體的“身”虛化成了“心”的附庸,修身只是克服欲望、保持健康的一種途徑,其真正目的是通過不斷自覺地對身體進行規訓來“修心”,由此便導致了身體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的缺席。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隨著西方現代哲學與自然科學的引入,傳統的身心觀逐步向一元論與實體化的方向轉型。但是,這種轉型并不是徹底的、一蹴而就的,許多思想家還在身心之辨中猶疑與掙扎,這正是晚清五四時期的特點所在。
(一)以身為本位的身心一元論的形成
以身為本位就是要尚獨、尚私,重情、重欲,重視人的個體性和獨特性,這也正是中國古代傳統身心觀中最薄弱的一環。以身為本位的觀念覺醒于戊戌維新時期,當時受西方影響更大的改良派思想家們開始關注并肯定身體的欲望,以康有為《大同書》最具代表性。它雖然成書較晚,但其基本思想形成于戊戌維新時期乃至更早,其核心觀點是“去苦求樂”,主張重視并滿足身體的快樂:“為人謀者,去苦以求樂而已,無他道矣。”[8]7人生在世全為快樂,“居處”“飲食”“舟車”“衣服”“器用”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去苦界至極樂”,男女之間快樂即合,不快樂則分。康有為這種以身體為本位、以快樂為目標的“大同”理想在當時可謂絕無僅有,驚世駭俗。然而,康有為的思想畢竟帶有個案性,當時許多思想家還秉承以“心”為主導或者身心兼顧的理念,嚴復就認為:“蓋一人之身,其形神相資以為用;故一國之立,亦力德相備而后存。”[9]10
以身體為本位的思想到辛亥革命時期漸成規模。在這一時期,身體的欲望與意志力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尚獨尚私的思想蔚然成風。“以知識為全體,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也。人之嗜欲,著于聲、色、香、味、觸、法,而仁義即由嗜欲而起。”[10]“有英人洛克者,謂健全之心意,宿于健全之身體,以此為教育之大眼目。”[11]這也就是“心”宿于“身”、“身”決定“心”的“身本位”思想的雛形。王國維“而意志與身體,吾人實視為一物,故身體者,可謂之意志之客觀化,即意志之入于知力之形式中者也”[12]的身心一體思想,進一步瓦解了中國以“心”為本位的身心二元論傳統。身本位的思想還衍生出了對“獨”和“私”的尊重,楊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之一毛”的極端貴身思想也不再是受到批判的對象:“今夫楊子為我之旨,不過曰個人獨立,不求當世之名位貨利,于不侵人自由之范圍內,縱一己之欲。此不可斥之為無君明矣。”[13]“且夫無國與無家孰急,則必曰家急;無家與無身孰急,則必曰身急。誠以國與家較,家其親切焉者也;家與身較,身其尤親切焉者也。”[14]269這種將一身之利置于國家之利之上的理念在之前是難以想象的。但在這一時期,許多革命家從現實需要的角度仍然堅守著“心”為本位的理念,孫中山就曾說:“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15]
到五四運動前后,以身為本位的思想得到了新的發展,集中表現為尊勞主義和推崇物質文明。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重視腦力勞動而輕視體力勞動的傳統,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這與重“心”輕“身”的身體觀一脈相承。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工人階級地位提升,純粹的體力勞動得到了更多的重視:“新文化運動影響到產業上,應該令勞動者覺悟他們自己的地位,令資本家要把勞動者當做同類的‘人’看待,不要當做機器、牛馬、奴隸看待。”[16]141不僅如此,勞動還成了人生的樂趣,成了痛苦時的消遣:“譬如身子疲乏,若去勞動一時半刻,頓得非常的爽快。隆冬的時候,若是坐著洋車出門,把渾身凍得戰栗,若是步行走個十里五里,頓覺周身溫暖。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勞動。這叫做尊勞主義。”[17]187勞動是創造社會一切物質財富的源泉,由尊勞主義生發出對物質文明的重視:“我們不是否認有精神生活這回事,我們是說精神生活不能離開物質生活而存在,我們是說精神生活不能代替物質生活。”[16]246胡適也認為“人們享不著物質上的快樂,只好說物質上的享受是不足羨慕的”,所以才去“戕賊身體,斷臂,絕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18]5,然而“明心見性,何補于人道的苦痛困窮!坐禪主敬,不過造成許多‘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廢物!”[18]9鑒于此,胡適對西方工業文明、機器文明是極為推崇的,他認為機器不僅可以將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而且還能訓練人的感官:過馬路倘不耳聰目明,就會有危險,“這便是摩托車文明的訓練”[19]。然而,工業文明既是對人類身體的解放又是對人類身體的壓制,陳獨秀、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者對此認識得非常深刻:“因為機器工業底生產品成本輕貨色又好,他所到的地方,手工業之破壞好像秋風掃落葉一般;這時候的勞動者所得工資只能糊口,哪里還有錢買機器,無機器不能做工,不做工不能生活,所以世世子孫只有賣力給資本家做勞動者。”[16]177這種不是人統治物而是物統治人的異化現象,是“爛熟”的資本主義文明難以避免的,不過,五四運動前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還很不成熟,當時的思想家對異化現象的認識僅停留在表層上,深入的認識還要等到1930年代以上海為代表的都市文明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以后。
五四時期的思想家們認識到了經濟獨立對身體獨立的決定性作用。從洋務運動時期開始,諸多思想家提出了禁止婦女纏足、沖破家庭限制等身體解放的理想,然而怎樣將這種理想變為現實,他們大多語焉不詳。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人都意識到了真正的個人解放需要以一定的經濟基礎為依托,身體獨立要從經濟獨立開始。陳獨秀《婦女問題與社會主義》說:“女子喪失人格,完全是經濟的問題。如果女子能夠經濟獨立,那么,必不至受父、夫的壓迫。”[16]190魯迅說:“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20]人最要緊的事無疑是生存,如果沒有養活自己的能力,那么一切身體解放、個性解放便都是空談,涓生和子君的悲劇正是如此。而一旦有了經濟基礎作為保障,個人特別是女性才能不依賴于父兄,不依賴于家庭,久而久之,才能形成“超于良妻賢母的人生觀”的“自立”的人生觀[21]。
(二)身體由“虛”入“實”的過程
如前所述,中國傳統身體觀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將“身”虛化,否定身體的實體價值。而在清末民初,“傳統的‘修、齊、治、平’之道和‘窮獨’、‘達濟’之論已經失去實效”,當時的知識分子“似乎只能找到‘身體’這一最切近、最方便,當然也很模糊的話語體系來表達各自對民族國家危亡的焦慮”[22]。在這種情況下,一度被忽視的作為物質實體的身體也重新進入了思想家們的視野,而身體的實體化過程也就成了“身體覺醒”的重要組成部分。
早在洋務運動時期,薛福成、鄭觀應等人就開始從醫學、生物學、解剖學的角度審視身體,“心”被他們拉下了神壇,由與“道”相通的主宰還原為具體的身體器官:“至心之為用,不過能由大小血管送血以通于腦,以充于周身,而身之百骸活焉,而腦之精氣足焉。”[23]115鄭觀應在比較之后提出了中醫不如西醫的五個方面,對重解剖、科學、實證,“明臟腑、血脈之奧”而“無虛設、無假借”[24]166的西醫極為贊賞。這可視為清末民初之際身體實體化之濫觴。不過,對中醫的信服和對西醫的懷疑難以在短時期內驟然改變,薛福成認為:“余謂西醫之精者,其治外癥固十得七八,但于治內癥之法,則得于實處者多,得于虛處者少。”[23]98
在其后的戊戌維新時期,西方理論的大量譯介特別是《天演論》的出版,使中國知識分子更自覺地運用自然科學原理來審視身體。較有代表性的是“有機體”“質點”及“以太說”。唐才常認為身體是由“質點”構成的,組成人體的各類元素也組成了自然界的其他物質,故而人能與天地萬物相通:“是為地天、人天、天天,故格致家言,可通佛家諸天之蘊;而佛家之積微質微點之心力,而救苦海世界,其諸仁者所有事與。”[25]52這是將西方原子學說與佛教“宇宙全息”的思想融合了起來。譚嗣同的觀點與唐才常頗為相似,提出了“以太說”。“以太”本是西方科學家假想出的光傳播介質,譚嗣同借用來闡明自己的哲學理念,將“以太”視為一切物質組成的本源,是不生不滅、永恒存在的,類似于中國傳統的“道”,人體死亡后,以太又將重新“粘合”成新人。不過,以太說只是譚嗣同為中國傳統身心觀披上的一件洋外衣,骨子里仍舊秉承重“心”輕“身”的觀點,不生不滅的以太只是將佛家輪回與性空理論換了種說法而已。在《仁學》中,譚嗣同一再表示:“以為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26]5“乃中國之談因果,亦輒推本前人,皆泥于體魄,轉使靈魂之義晦昧而不彰,過矣!失蓋與西人同耳。”[26]34“夫心力最大者,無不可為。”[26]96不得不說,譚嗣同將個人身體視為毫不足惜之物的身心觀和他慷慨赴死、英勇就義的行為有著必然關聯。總體說來,唐才常和譚嗣同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學的觀念,但中國傳統文化對他們的影響依舊強大,試圖在西方理論與傳統文化之間尋找對接點,用自然科學理論對佛教和儒家的某些理念進行全新闡釋。比唐、譚二人走得更遠的是嚴復,他率先用“有機”二字翻譯了英文的“organism”,將人體視為一個完整統一的各部分協調運作的“有機體”:“有機體云者,猶云有機關之物體也。”[9]197這就不僅將身體視為互相聯系的統一整體,并特別強調了身體“物”之本性,也就是將身體看作是由各種元素組成的物質實體,直到今天我們仍常常將“有機體”作為身體的代名詞。對達爾文進化論的推崇以及將進化論應用于社會、歷史而不單單局限于生物學的風氣,一直持續到民國建立之后。
到辛亥革命時期,很多思想家已經接受了西方關于物質組成的“原子說”并將其本土化。在進化論的影響下,人們進一步重視遺傳學說,對細胞內的染色體在遺傳中的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主張優生優育以改良人種,并已意識到中國只重父系血緣而忽視母系血緣所導致的姑表親、兩姨親等近親結婚之弊端。章太炎說:“核絲之遠近,蕃萎系焉。(傳稱男女同姓,其生不善。)故父黨母黨七世以內,皆當禁其相婚,以血緣太近故也。”[27]人們已不再滿足于宏觀上的泛泛而論,而是深入至細胞、染色體等微觀層面,這無疑是一個重大進步。在這個時期,身體的實體化進程已經基本完成,中國人的身體早已不再是那個虛無縹緲的依附于“心”的存在。
二、個人的身體與國家的身體
清末民初之際,隨著人們對身體的再發現、再認識,種種身體解放、身體平等的理論不絕于耳。然而,追求身體解放和身體平等的動機是什么?是為了解放自己還是為了拯救國家?大多數思想家給出的答案都是后者。在那個危機深重的年代里,改造個人身體是與強國保種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幾乎是一項政治任務,其中又包含著自下而上試圖通過改造個人身體來拯救國家和自上而下依靠改變國家制度來解放個人身體這兩個部分。這種個人的身體與國家的身體的糾纏,幾乎貫穿了整個中國近現代史:“具體到20世紀中國現代性進程,身體更是每每成為社會的焦點,并多被放大成為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對推動社會變革發揮了應有作用。”[28]
(一)從個人到國家——尚武、練兵與人種改良
長期以來,中國美男子的標準是“白面有須”,中國人欣賞的是謙謙君子的瀟灑飄逸,而非赳赳武夫的雄壯威武,長此以往便導致了中國人身體的文弱。中國第一位公使郭嵩燾在出使西洋時看到洋人體格強健,能用額頭和手掌擊碎核桃,同時又“白皙文雅,終日讀書不輟”,不禁感嘆:“彼土人才,可畏哉!可畏哉!”[29]
在洋務運動時期,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們意識到中國士兵缺乏訓練,很多人甚至有吸食鴉片的惡習,以至于身體羸弱。鑒于此,他們開始呼吁“習武”“練兵”,試圖扭轉中國傳統的重文輕武思想,打造文武兼備的理想人才。薛福成認為:“宋明以來,右文輕武,自是文人不屑習武,而習武者皆系粗材。積弱不振,外侮迭侵,職此之由。”[23]96鄭觀應說:“中國亟宜參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24]90這說明當時的思想家意識到,提高國民的身體素質,已經成為避免亡國滅種厄運的必要途徑之一。
如果說洋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們還是從提升軍力的角度來倡導身體訓練的話,那么戊戌維新時期的思想家們就是從優勝劣汰的角度來提倡整個民族的尚武精神,改變“中國者,固病夫也”[9]18的現狀。同時,這一時期的思想家也意識到家國天下并不是屬于君主一人的,而是由無數人的身體乃至無數身體上的器官組成的:“世界一耳目心腹之所積也。積耳目心腹而成人,積人而成家,積家而成鄰,積鄰而成里,積里而成鄉,積鄉而成黨,積黨而成都邑,積都邑而成國,積國而成天下。”[25]79梁啟超認為:“民弱者國弱,民強者國強。”[30]10如此一來,個人的身體素質就直接關系到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鑒于此,嚴復主張“開民力”,并將“民力”與“民智”“民德”一起視為“生民之大要”。可以說,對中國人體質病弱的憂慮和對尚武、尚動、開民力的提倡,成了戊戌維新時期及后世思想家改造國民性的基點,對身體的改造升華為對整個民族、國家的改造。“倡言‘新民’、‘公民’,都是意欲使‘國’與‘民’的結合更加緊密,使個人由家族依附轉向為國奉獻。”[31]
同樣是受進化論的影響,戊戌時期的思想家們逐步明確了人種的概念,認識到各個人種都處在進化之中,要想不被其他人種所淘汰,中國人就必須通種、保種、進種。唐才常著有《通種說》,嚴復提出了“保種、保國、保教”的主張。由于當時歐美國家居于世界領先地位,所以唐才常、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皆認為白種人優于其他人種,體現出了白種崇拜的傾向。梁啟超說:“白人之優于他種人者,何也?他種人好靜,白種人好動;他種人狃于和平,白種人不辭競爭;他種人保守,白種人進取;以故他種人只能發生文明,白種人則能傳播文明。”[30]13當時的思想家均認為保種是要務,要讓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立足就要通種、進種,讓中國人向白種人靠攏。由此觀之,中國長期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落后,漸漸演變成了對中華民族乃至黃種人本身的不自信,文化、制度上的劣勢導致了中國人在身體上的自卑。此外,在個人與種族關系方面,許多思想家主張,當個人利益與種族利益發生矛盾時,個人利益要絕對服從于整個人種的利益,甚至要為種族利益犧牲自己的生存權,這就是嚴復所說的:“而至生與種較,則又當舍生以存種,踐是道者,謂之義士,謂之大人。”[9]25
自此之后,通過尚武、練兵、提升國民身體素質來強國保種的理念就蔚然成風。“20世紀初葉的中國確實對身體有著一份高度的著迷與堅持。從康、梁一輩開始,知識分子就以一種舍我其誰的態度,努力于推動各種的身體改造運動,營造一個有關身體‘應然’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32]191902年由沈心工作詞的一首學堂樂歌就頗能體現這種風尚:“男兒第一志氣高,年紀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來做兵隊操。兵官拿著指揮刀,小兵放槍炮。龍旗一面飄飄,銅鼓冬冬冬冬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得身體好,將來打仗立功勞,男兒志氣高。”不僅尚武練兵、強國保種的身體改造工程直接與國家利益相連,即便是身體解放運動,也割不斷與國家利益的聯系。比如,康有為《大同書》一方面推崇男女身體平等:“同為人之形體,同為人之聰明”[8]147,“女子未有異于男子也,男子未有異于女子也”[8]148,“原女子被屈之由,本于繁衍人類之不得已”[8]178;另一方面,他又反對墮胎:“為全地人種之故而思保全之,則禁墮胎乃第一要義矣”[8]241,“夫大同之道,雖以樂生為義,然人為天生,為公養,婦女代天生之,為公孕之,必當盡心以事天,盡力以報公,乃其責任,婦女有胎,則其身已屬于公,故公養之,不可再縱私樂以負公任也;若縱私樂以負公任,與奉官而曠職受贓同科矣”[8]233,這又分明是打著公家的幌子將婦女的身體視為生育之工具,讓婦女的身體剛從男性和家庭的壓制下解放出來,旋即又落入了“公”的魔爪。辛亥革命時期,許多知識分子主張婦女解放、禁止早婚,試圖讓婦女從家庭中走出來參加工作、參與社會活動,其思想的本質與目的和康有為相通:“那就是將身體的‘殖民’權利由家庭和禮教體系轉移到國家的手上。”[32]23“‘國’在清末正逐漸取代‘家’的地位成為身體的新統治者。”[32]113婦女的解放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解放了婦女就可以提高國家的生產力,禁止早婚又可以改良人種,這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是一脈相承的。
將個人身體與國家直接掛鉤的思想,到辛亥革命時期更是與中國傳統觀念合流,發展出了新型的“舍生取義”思想,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孫中山、陳天華、鄒容等革命家。他們無不主張犧牲個人、共赴國難:“要學先烈的行為,像他們一樣舍身成仁,犧牲一切權利,專心去救國。”[33]“故我勸列位撞著可死的機會,這死一定不要怕。……泰西的大儒有兩句格言:‘犧牲個人(指把一個人的利益不要)以為社會(指為公眾謀利益);犧牲現在(指把現在的眷戀丟了)以為將來(指替后人造福)。’這兩句話,我愿大家常常諷誦。”[34]“‘身’和政治緊密地結合著,它是政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的目標,同時也是政治的結果”,“‘革命’作為非常態的政治手段,它既以身體(改造、消滅、新生)為目標,也以身體為工具”[35]。孫中山、陳天華和鄒容舍生取義的理想,就帶有鮮明的將身體工具化的傾向。而嚴復所翻譯的“有機體”一詞正來自希臘表示工具的詞匯[36]。其他重視個人身體的思想家,也無不同時強調個人與國家的聯系,個人對民族應盡的義務,重視楊朱利身思想的同時不忘墨子的博愛。“自我身、我家、我國以至于我民族,皆與我有絕大之關系,皆我私也。自我身、我家、我國以至于我民族,若有迫不得已之事,皆我私事也。”[14]270“墨子兼愛之旨,不過曰欲人之愛利吾親,必先愛利乎人之親,然后人報我以愛利吾親。”[13]這種將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自私與博愛完全對等同一化的說法難免牽強,但卻鮮明地體現出當時的知識分子在個人至上與民族至上之間的搖擺、猶疑。一方面是沖破封建束縛的啟蒙主義,另一方面是救亡圖存的國家主義,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壓力下,當時知識分子的這種折中、調和的態度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過,到了高揚啟蒙思想與人道主義的五四時期,不為國家犧牲個人的思想得到了蓬勃的發展。“茍倡絕對的國家主義,而置人道主義于不顧,則雖以德意志之強而終不免于失敗,況其他乎?”[37]“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16]104特別是針對自殺行為,許多思想家都有委婉的批評:“故我之愛國主義,不在為國捐軀,而在篤行自好之士,為國家惜名譽,為國家弭亂源,為國家增實力。我愛國諸青年乎!為國捐軀之烈士,固吾人所服膺,所崇拜,會當其時,愿諸君決然為之,無所審顧;然此種愛國行為,乃一時的而非持續的,乃治標的而非治本的。”[16]40魯迅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單照常識判斷,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緊的自然是生命。因為生物之所以為生物,全在有這生命,否則失了生物的意義。”[38]然而,中國自古便把身體當作是家庭、社會、民族、國家的附屬物,“舍生取義”的行為總是被當作美德傳誦千古,以對身體的拋棄來達到所謂的名垂青史,這實際上是對生命和身體的漠視,是死后的名分對活著的身體的壓制:“在歷史上,只有孝女,賢女,烈女,貞女,節婦,慈母,卻沒有一個‘女人’!”[39]五四時期這種對個人的解放、對虛偽的民族大義的反抗、對個體權益的提倡,恰恰是對身體的重新認識與發現,正如李大釗在《“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中所強調的:“我們應該承認愛人的運動比愛國的運動更重。”[17]205
(二)從國家到個人——破除禮教鉗制,維護身體權利
清末民初之際的思想家們一方面極為重視自下而上由個人到國家的身體改造運動,另一方面也希望通過自上而下調整國家的法律、制度,破壞鉗制身體的封建禮教來達到身體的平等與解放。
在古代中國,受儒家傳統倫理觀念影響,中國血緣宗法制社會的基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倫秩序。“倫是有差等的次序。”“其實在我們傳統的社會結構里最基本的概念,這個人和人往來所構成的網絡中的綱紀,就是一個差序,也就是倫。”[40]在傳統社會中,一個人的身體權利往往由身份決定,甚至犯罪量刑也是如此。比如子殺父與父殺子,同是對他人生命權的剝奪,但由于父與子在封建身份等級上的不同,子殺父即為十惡不赦之罪,定當處死,而父殺子卻可酌情減免量刑。“男子殺妻,罪不至死。女子殺夫,則有凌遲之刑。男子停妻再娶,不過笞杖,女子背夫改嫁,罪至繯首。(曰停曰背,輕重可見。)”[41]259所以,要打破身份對身體的鉗制,就要在國家法律和制度層面維護身體平等,使中國社會“由倫理法走向權利法,或者說,由家族本位走向個人本位的身體權利演變”[32]92。
早在太平天國時期,洪仁玕《資政新篇》就提出了一些維護人的基本身體權利的舉措,如:開設醫院;興辦跛盲聾啞院、鰥寡孤獨院和育嬰堂;廢除酷刑、禁止溺嬰、纏足、買賣人口與使用奴婢等。到洋務運動時期,先進的思想家們對西方法治社會人人平等、賞罰不以身份差別而異的現象已有了初步認識,薛福成就注意到:“子毆父者,坐獄三月;父毆子者,亦坐獄三月。”[23]99特別是他們發現西方人對婦女較為尊重,有女士優先的傳統,與中國壓抑、束縛婦女的做法有很大不同。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下,許多思想家提出了君民平等、男女平等的觀念。王韜提出一夫一妻制思想:“一男而有二女,其不至于離心離德者幾希矣!故欲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先自一夫一婦始。”[42]11鄭觀應《女教》極力反對纏足這種殘害女性身體的行為:“至婦女裹足,合地球五大洲,萬國九萬余里,僅有中國而已。”“茍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學,罄十年之力率以讀書,則天下女子之才力聰明,豈果出男子下哉?”[24]121激憤之情溢于言表,女子才力不輸男子的言論在當時也是極有震撼力的。何啟、胡禮垣認為:“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43]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對自己的身體有完全的自主力,不受控于君、父、夫。另外,身體的平等不僅體現在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也體現在華洋之間。當時隨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外國人在華享有治外法權,犯罪亦不由中國審理,由此就導致了洋人犯罪每每量刑過輕,洋人與華人在身體權益上極不平等。對此,鄭觀應主張:“俾外國人亦歸我管轄,一視同仁,無分畛域。”[24]215
在刑罰方面,中國古代歷來重“刑”(主要是肉刑)輕“罰”,審訊當中經常嚴刑拷打,乃至屈打成招。鄭觀應、王韜等人認為殘忍的肉刑絕不能起到懷柔懲戒、改過自新之功效,不如外國刑罰那樣“寬嚴有制”,故而必須予以革除。如王韜認為西洋犯法者“從無敲撲笞杖,血肉狼藉之慘。其在獄也,供以衣食,無使饑寒,教以工作”,“獄制之善,三代以來所未有也”,而“國中所定死罪,歲不過二三人,刑止于絞而從無梟示”[42]157。鄭觀應認為:“夫天地生人,原無厚薄也。何以案情訊鞫而酷打成招,獨見之于中國?”[24]214與反對婦女纏足類似,鄭觀應也反對閹割這種殘酷的肉刑,在《閹宦》一文中,他認為閹割乃是“極弊之政,為合地球所共無者”[24]200,“是故古今異勢,治亂異法,古雖有之,今亦宜絕”[24]201。這些取消肉刑的呼吁,使刑罰從對身體的迫害轉移到對身體的拘禁上來;從對肉體的粗暴懲罰以及對這種懲罰過程的丑陋展示轉移到限制肉體自由的規訓上來,這無疑是更合于人道,是更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
除了刑罰之外,中國古代的禮儀規范也是建立在身體權利不平等的基礎上,“而舉所謂叩頭、請安、長跪、匍匐、唱諾、懇恩之各種金科玉律,以為之倡,無怪乎相習而成風也”[44]。因為不平等,所以身份地位較低微的臣、子、婦就要在擁有更高地位的君、父、夫面前表現出身體姿態上的馴服——叩頭、請安、長跪、匍匐、唱諾、懇恩等等。這種等級差異不僅體現在身體姿態上,也體現在服制上:“男子喪妻,持服僅及期年,等于父母之喪子女。女子喪夫,乃有三年之服,等于子女之喪父母,且有終身不釋者。”[41]258-259“人們可以從儒家的經典著作《禮記》之中發現,儒家學說對于人體的規范訓練幾乎面面俱到;這種訓練顯然從屬于‘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的封建意識形態。對于統治機構說來,人體不是某種單純的物理存在,人體必須充當意識形態的物質基礎。”[45]要達到身體的平等與解放,讓身體獲得獨立性,不再充當“意識形態的物質基礎”,就必然要破除以“三綱五常”為代表的封建意識。當時很多學者更是認為要破除封建的“三綱五常”就必須破家、毀家,打破父母、兄弟、翁姑、丈夫對婦女身體的暴政:“蓋家也者,為萬惡之首。”“則欲開社會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矣。”[46]正所謂不破不立,如果不能自上而下從國家的法律、制度、政策以及社會的禮儀、規范、習俗等方面加以改革,那么身體的平等與解放永遠都只能是一紙空談。
從晚清到五四是中國社會的轉型期,也是身體意識的轉型期,在這一歷史時期中,身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身體平等與身體解放的理念也日漸深入人心。但是,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前,身體剛從封建禮教的控制中解脫出來,旋即又陷入了被工具化的境地。如果說傳統中國人的身體是隸屬于家庭的,那么清末民初大多數思想家們理想中的身體就應該是隸屬于國家的。換句話說,他們試圖讓身體完成從倫理化的到政治經濟化的轉型,讓身體成為改造國家和社會的基點,用規訓的方式,針對“肉體及其力量、它們的可利用性和可馴服性”進行“安排和征服”,因為“只有在肉體既具有生產能力又被馴服時,它才能變成一種有用的力量”[47]。但我們也應看到,這種個人與國家的互動并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國家不單是代替家庭控制身體、制約身體的壓迫性力量,很多時候它還在制度和政策層面推動著身體平等、身體解放。而身體到底應該屬于個人,還是應該屬于國家,這個命題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們深思。
參考文獻:
[1]大衛·勒布雷東.人類身體史和現代性[M].王圓圓,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3.
[2]趙淳.身體話語:訴求、突破、抵抗[J].外國語文,2013(3):1-4.
[3]王先慎.諸子集成·韓非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78:353.
[4]朱謙之.老子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4:50.
[5]陳鼓應.莊子今注全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193.
[6]楊樹達.論語疏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76.
[7]焦循.孟子正義[M].長沙:岳麓書社,1996:576.
[8]康有為.大同書[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9]胡偉希,編.論世變之亟——嚴復集[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10]章太炎.菌說[M]//章太炎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134.
[11]劉顯志.論中國教育之主義[G]//胡偉希,編選.民聲:辛亥時論選.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132.
[12]王國維.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M]//王國維文集:下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191.
[13]吳虞.辯孟子辟楊、墨之非[G]//胡偉希,編選.民聲:辛亥時論選.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236.
[14]劍男.私心說[G]//胡偉希,編選.民聲:辛亥時論選.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15]孫中山.孫文學說——行易知難(心理建設)·自序[M]//建國方略.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3.
[16]吳曉明,編選.德賽二先生與社會主義——陳獨秀文選[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
[17]高瑞泉,編選.向著新的思想社會——李大釗文選[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
[18]胡適.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M]//胡適文集:第4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19]胡適.漫游的感想[M]//胡適文集:第4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30.
[20]魯迅.娜拉走后怎樣[M]//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67.
[21]胡適.美國的婦人[M]//胡適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444.
[22]程亞麗.新身體·新民·新國家——論晚清民族危機中現代身體話語的生成[J].社會科學輯刊,2010(6):226-230.
[23]薛福成.籌洋芻議[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24]鄭觀應.盛世危言[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25]鄭大華,任菁,選注.砭舊危言——唐才常、宋恕集[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26]加潤國,編.仁學——譚嗣同集[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27]章太炎.族制第二十[M]//訄書.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101.
[28]程亞麗.“腳”上的政治:晚清“廢纏足”小說研究[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5):174-178.
[29]陸玉林,編.使西紀程——郭嵩燾集[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41.
[30]梁啟超.新民說[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31]郭繼寧,鄭麗麗.“疾病”與“治療”——對清末新小說中一對隱喻的考察[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4):149-151.
[32]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33]孫中山.在陸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的演說[M]//朱正,編.革命尚未成功——孫中山自述.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171.
[34]郅志,編.猛回頭——陳天華鄒容集[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63-64.
[35]葛紅兵,宋耕.身體政治[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50.
[36]理查德·舒斯特曼.身體意識與身體美學[M].程相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15.
[37]蔡元培.《國民雜志》序[M]//高叔平,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255.
[38]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M]//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35.
[39]胡適.女子問題[M]//胡適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520.
[40]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38.
[41]憤民.論道德[G]//胡偉希,編選.民聲:辛亥時論選.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42]王韜.弢園文錄外編[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43]鄭大華,編.新政真詮——何啟胡禮垣集[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353.
[44]佚名.箴奴隸[G]//胡偉希,編選.民聲:辛亥時論選.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80.
[45]南帆.文學、革命與性[J].文藝爭鳴,2000(5):22-32.
[46]漢一.毀家論[G]//胡偉希,編選.民聲:辛亥時論選.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139-140.
[47]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27-28.
責任編輯 韓云波
[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 陳寶良
主持人語:揆諸明代史的演進歷程,正統“己巳之變”而導致的一時政治危機,卻因名臣于謙的挺身而出,從而使危機化為烏有,且歷經成化、弘治兩朝的善治,更使社會暫趨穩定,甚或享有盛世之譽。武宗繼位,沉溺游逸而無心治國,因絕嗣而國無儲君,又一次使明代陷于危機之中。正德末年,看似簡單的皇位傳承,背后所蘊涵的豐富的政治史信息,卻頗值得后來的研究者加以重新審視。如何解讀正德、嘉靖之際的政治乃至社會危機?本期所收兩篇論文,顯然已經作了較有建設性的解讀。田澍所撰之文,通過廣征博引的史實考辨,證明內閣首輔楊廷和在處理絕嗣危機時的種種失策之舉,不失為一種讓人耳目一新之論;陳旭所撰之文,雖僅以論證林俊與“大禮議”的關系為主旨,然“大禮議”實為正德、嘉靖之際政治危機的主要表征。就此而論,兩文實則互相呼應,對于解讀正德、嘉靖之際的這段歷史頗有裨益。當然,正德、嘉靖之際是明代社會、文化發生重大轉變的時代,諸如因《嘉靖事例》與《嘉靖新例》的出現而導致制度性的變革,或因“大禮議”而導致的士風變化,無不是研究者需要加以深入探討的課題。
I206.5
A
1673-9841(2015)02-0131-08
10.13718/j.cnki.xdsk.2015.02.017
2014-05-01
楊程,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