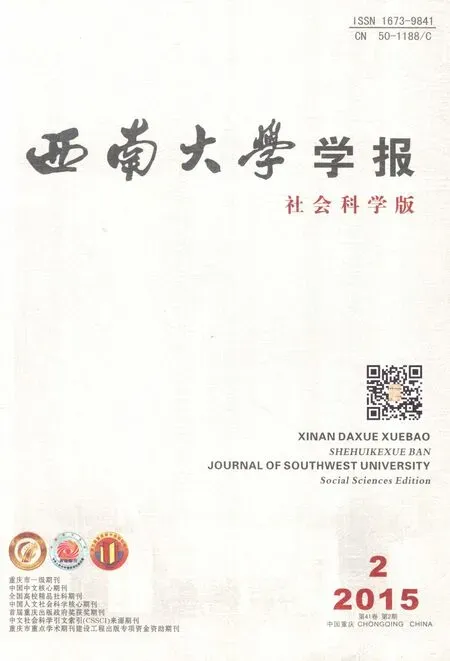先秦判決中的“誓”與“比”
鄒芙都,查飛能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重慶市400715)
先秦判決中的“誓”與“比”
鄒芙都,查飛能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重慶市400715)
誓與比在先秦司法判決中占據(jù)重要地位,誓是判決爭端時確立的契約關(guān)系,比用于比附判決。先秦時期按一定程序與儀式確立的具有契約法律性質(zhì)的誓規(guī)范著當事人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誓作為判決方式,主要依靠禮制下的權(quán)力保障其得以實施。比是一種特殊的司法判決方式,具有判例法性質(zhì),是先秦時期存在判例法的明證;在具體司法判決過程中,比體現(xiàn)出一定的判決技術(shù)與司法理念。先秦時期的誓與比蘊含“明德慎罰”思想,而在貫徹實施中禮的調(diào)控作用導(dǎo)致先秦刑罰出現(xiàn)“禮法合一”的特點,此應(yīng)為后世“禮法合一”立法指導(dǎo)思想的淵源之一。
先秦;判決;誓;比;契約關(guān)系;法理思想
誓與比作為先秦時期兩種主要的司法判決方式,對先秦及后世社會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但長期以來學界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以往關(guān)于“誓”的研究多集中在盟詛方面,雖然亦有學者對《匜》等銅器銘文中的誓作過探討,但均不同程度地把誓與法律等同,對判決之誓及其性質(zhì)則鮮有論述。比作為一種特殊的司法判決方式,相關(guān)研究更為少見。本文在參閱相關(guān)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從司法判決的視角,對先秦時期誓的性質(zhì)、比的司法內(nèi)涵及其對后世的影響等問題進行探討。
一、先秦判決中的“誓”
《禮記》云“約信曰誓”,鄭玄解釋為“約信,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為信也,若用言相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1]141。意即如果出現(xiàn)了糾紛,則當事人共同立誓以互相約束,如果當誓言也違背了,誓即成為一種判決方式。可見,誓是為了確立新的具有法律性質(zhì)的契約關(guān)系。但誓是否均具有契約法律性質(zhì)則應(yīng)當加以區(qū)分,先秦時期只有那些涉及爭端或利益關(guān)系無法劃分而立的誓才具有契約法律效力,或者是有代表國家維護奴隸主貴族權(quán)力的公證人在場的誓才有法律效力。一些因生活中瑣碎小事發(fā)的誓則不具備契約效力,更多只是屬于自我約束,這是我們應(yīng)該區(qū)別的。①如《衛(wèi)風·氓》:“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等“誓“就沒有契約效力,與自我約束有關(guān)。此外,《衛(wèi)風·考槃》中“永矢弗諼”、“永矢弗過”、“永矢弗告”,《論語·雍也》“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矢”皆為假借為“誓”,且都不是具有法律性質(zhì)的契約。同時,在先秦時期用牲所立的盟是具有判決意義的“誓”,《禮記》“涖牲曰盟”,鄭玄釋為“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1]141鄭玄釋盟與誓都強調(diào)信,不同的是盟需要用牲,而誓沒有用牲。然而在《秋官·司約》中則不同,鄭玄云“不信,不如約也。……謂殺雞取血釁其戶”[2]949。可能是誓不及盟重要所致。但是,無論盟或誓,都是為了防止和解決糾紛爭執(zhí)的,其內(nèi)容具有契約法律效力,規(guī)范著當事人(或邦國)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①在《禮記》中,盟誓連稱:“約信曰誓,涖牲曰盟”,鄭玄解釋為“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鄭玄解釋誓與盟都必須有“信”,可見在先秦典籍中誓、盟區(qū)別不大,都是為了確立新的契約,而在《左傳》中盟則主要是協(xié)調(diào)邦國之間的關(guān)系。總體來說,當出現(xiàn)糾紛時,發(fā)誓時的“信辭”可以作為判決的證辭,這是由于誓是有一定禮儀程序的,遺憾的是誓禮已不可詳考。
據(jù)文獻,“信”必須明著才具有契約性質(zhì),而用牲是其方式,說明“信”是作為契約被遵守的,若有違背將會受到神冥的懲戒。總體上,盟誓對象為神,整體過程如“北面詔明神,既盟,且二之”[2]881,即北面向神發(fā)誓,完成后把誓言記為劑,分兩份保存。我們從出土《格伯簋》可以證明西周時期誓言分兩份保存,銘文大意為倗生以“卅田”進行抵押向格伯購買良馬,并發(fā)了誓:
隹正月,初吉,癸巳,王在成周,格伯受良馬乘于倗生,厥貯卅田,則折(誓)。[3]280
郭沫若釋“折”為“誓”。楊樹達釋為“析”,即析券,“析券契而中分之,兩人各執(zhí)其一,故云析也。”[4]27析券即上文所說分為兩份的約劑。郭沫若認為的“折(誓)”與楊樹達釋“析”,字雖不同而意義卻一致。李學勤先生認為析券和立誓,在當時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若果違反了,便會受到法律的懲罰,見于《周禮》等書的記載[5]268-269。并說:“散氏盤末有一行:‘厥左執(zhí)要(約)史正仲農(nóng)’,即由名仲農(nóng)的史官保管契約一份。”[5]271稽查文獻,《秋官·司約》之下有“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2]947-949可見,劑是約信時的券書,根據(jù)事件輕重保存,這是西周時期與之前相比明顯進步的地方,因為一旦約信人有爭執(zhí)、糾紛不能解決,就可以查看藏于盟府的誓書,給予違背誓言者懲罰。因此,誓能夠像法律一樣具有約束力,可以用于司法判決。
誓形成一種約束,信則是約束當事人的契約之辭。《說文》:“誓,以言約束也。”段注:“凡自表不食言之辭皆曰誓。亦約束之意也。”[6]92《釋名》中誓為“制也,以拘制也”。因此,誓的約束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為誓能夠約束人們的行為,利于社會穩(wěn)定,所以先秦時期誓很普遍。吳榮曾先生認為:“無論《詩》、《書》,還是《左傳》,都多次提到盟詛之事,表明在西周、春秋時期的社會生活中,古老的對神發(fā)誓仍然對人與人的關(guān)系起到一定的作用……《周》春官之下有‘詛祝’,秋官之下又有‘司盟’,同屬主管盟詛的官吏而分設(shè)于禮官和刑官之下,這反映出當時禮和刑還沒有嚴格分開,兩者在發(fā)揮其社會功能時可以說是殊途同歸。”[7]事實上,在先秦時期向神發(fā)誓是判決是非曲直、約束當事人的一種方式,進入文明社會后它并不會很快消亡,而是殘留在刑罰規(guī)范中,今天我們偶爾也還會聽到“向神發(fā)誓”、“對天發(fā)誓”、“指天為誓”等,其原因就是人們相信天或神是公正的,當事人若對天或神有所隱瞞會受到懲罰。因此,盟誓也可以看成“宣誓神判”與“詛咒神判”,②宣誓神判指雙方爭執(zhí)不下時,由一方或雙方向神靈宣誓,若有盜騙或誣陷,事后將會受到神靈懲罰;詛咒神判指:雙方爭執(zhí)不休、各執(zhí)其理時,請巫為證人,向神發(fā)誓,對偷竊者或誣陷者詛咒。參見趙容俊:《殷商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術(shù)》(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2011年,第105~106頁。統(tǒng)稱為“誓審”,即借助人們對天的迷信而施行的一種判決方式。③西周民事訴訟中的誓審,由負責任一方在特定司法官主持下所發(fā),宣讀誓詞表示愿意承擔責任。參見張晉藩主編:《中國民事訴訟制度史》,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第18頁。吳榮曾先生所論從另一個側(cè)面反映,在西周、春秋及以前發(fā)誓更為普遍,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更為重要,且西周禮官與刑官同時出現(xiàn)于《周禮》中亦可知曉西周時期違反禮制也就違反了刑罰,就必然引起司法訴訟。
誓在西周、春秋時期也用于司法訴訟。西周、春秋時期有很多掌管誓、盟、詛、約的官吏,如司誓、司盟、司約、詛祝等。《秋官·司寇》之下有“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司盟職責之一即“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2]951-952又記“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2]963可見盟誓是普遍運用于司法判決中的。
發(fā)誓也可直接用于司法判決,形成一種新的契約關(guān)系,銅器銘文多有證明。《匜》銅器銘文記載了因為違背誓言引發(fā)的訴訟案件:
銘文內(nèi)容反映牧牛與自己長官爭訟而違背誓言,需要再次立誓,繳納罰金,形成新的契約關(guān)系。此篇銘文對探討西周司法判決意義重大,《中國法制史考證》甲編第一卷曾用一章的篇幅對其進行細致論述。論及“誓”時主要基于銘文內(nèi)容的處罰認為其是按國家規(guī)定的制度由當事人立的盟誓,以此作為法律形式及定刑量罪的依據(jù),強調(diào)誓的約束與規(guī)范作用。[9]162這一解釋有言過其實之嫌,誓只是具有契約法律性質(zhì)而已,不具有法律的普遍適用性特征,所以誓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法律。西周“民訴中的宣誓都是為了給審判過程中確定罪與非罪和進行定罪科刑尋找證辭”[10]113。銘文中牧牛被處罰的表面原因是與師爭訟,其深層原因則是違背了自己先前許下的誓言。在今天看來違背一個似乎微不足道的誓言就要處罰金,實在令人費解,然而與師(上級)爭訟已經(jīng)觸犯了奴隸主貴族的特權(quán)。實則誓言本身并不見得非常重要,只是奴隸主貴族的權(quán)威至關(guān)重要而已。銘文中誓已經(jīng)具有契約法律性質(zhì),保證奴隸主貴族的權(quán)威,這是導(dǎo)致此次訴訟發(fā)生的重要原因。
此銘文中攸衛(wèi)牧自己違背了自己租田時立下的誓言,導(dǎo)致雙方的契約未能實現(xiàn)而引起訴訟,最終借助王權(quán)判決,比與攸衛(wèi)牧重新訂立契約(誓)。
《散氏盤》銘文大意是夨國因為侵略散氏國而以田地賠償,并發(fā)誓作保證:
上述所引銅器銘文,過去學者們主要關(guān)注的是土地關(guān)系變動、交換關(guān)系出現(xiàn),對于誓的契約法律性質(zhì)則很少論述。從銘文來看,誓大致包含兩部分內(nèi)容。第一,宣誓一方明確提出并承諾遵守誓言(有可能是被迫的)。或是履行過去的誓言,或是確立新的契約關(guān)系。第二,違背誓言的處罰。這幾篇銘文中出現(xiàn)的違背誓言應(yīng)該得到的處罰,如鋝和墨刑,《尚書·呂刑》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是為證,鞭刑、放(流放)等也有記載,①《尚書·堯典》記“流宥五刑,鞭作官刑”及“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亦見李學勤主編:《周禮注疏》,第979頁。但“隱千罰千”則不見記載,可見誓辭存在凌亂與隨意的一面。以“隱千罰千”而論,雖見于銘文之中,且在此處也屬禮制規(guī)范之內(nèi),但卻是臨時約定的誓言。說明因契約有別、場合不同,誓與《周禮》等書記載不乏出入,其內(nèi)容可能并非完全能夠得到遵守與履行,也沒有像法律那樣規(guī)定固定的處罰條目。
事實上,誓與法律既有區(qū)別也有聯(lián)系。首先,誓表現(xiàn)為向神發(fā)誓,其約束力源于對神靈等神秘力量的盲目信從,立誓雙方所定的契約不具備廣泛的社會約束力,也就是說誓沒有得到社會承認的普遍公信力。然而隨著社會發(fā)展進步,誓逐漸產(chǎn)生兩種背離的趨勢,一是誓的約束力不斷擴大,由當事人雙方延伸到更廣闊的社會,誘導(dǎo)并促進社會契約性質(zhì)的法律產(chǎn)生;二是形成個人價值觀,產(chǎn)生道德約束力。而法律則不同,它具有廣泛的社會約束力,且一旦確立法律條款,它就不是隨意可改的。但是,誓與法的關(guān)系卻是相互的,誓的不規(guī)范性與履行的不可靠性促進了公共權(quán)力的產(chǎn)生,而誓又保證了公共權(quán)力的權(quán)威,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公共權(quán)力機構(gòu)的形成和法律制度的完善。[11]在成文法頒布之后,誓能夠約束一些法律無法管制的地方,甚至成為法律的補充。
其次,誓作為有法律性質(zhì)的契約,在判決時是可以有公證人的。《匜》中,牧牛再次立的誓言只有得到專、格、嗇、睦、五人的全部認可才能有效,方能繼續(xù)任職。[12]155而在《包山楚簡》中我們也可以找到類似的證據(jù),第137號簡記載判決“余慶殺人案”時,作為證人出證前需要宣誓自己所說的話是真實的,所以“執(zhí)事之人為之盟,凡二百人十一人。既盟,皆言曰……”[13]26-27,可見,在判決中不僅當事人需要發(fā)誓,證人也是需要發(fā)誓的。這與法律有相通之處,講究公正。
最后,從銘文中可見誓辭的實現(xiàn)與否依靠禮制下的權(quán)力保障。所引幾篇銘文中所立的誓,其共同點之一即誓出現(xiàn)的場合除《散氏盤》銘文外,均有周王及見證人在場。《匜》銘文中伯揚父直接向周王控訴牧牛,《比鼎》中比借助王權(quán)維護自己利益,《格伯簋》也是“王在成周”作為此次交換的見證。幾例銘文反映西周時期王權(quán)至高無上,一些重要案件的處理需要周王在場,甚至親自做出判決。周天子在場既說明誓在判決中的重要性,也說明周天子權(quán)威不可動搖,也正是這種訂立契約的場合增多,才使得法律也因此而逐漸產(chǎn)生,因此西周金文資料中的誓出現(xiàn)的場合,恰恰都是為了確立新的法律關(guān)系。[14]267然而金文資料中的誓不具備法律應(yīng)有的普遍適用特征,所以它還只是一種具有法律性質(zhì)的契約。
但是,從銘文亦可知曉誓辭與判詞等同,都有法律效力。周王或代表政府的官員在場則表明誓確實是有程序與儀式的。判決爭執(zhí)、訂立契約時誓本身已經(jīng)顯得不再重要,只是其內(nèi)容中協(xié)定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不可替代,原始的神意判決變?yōu)橐揽科跫s判決。周王參與立誓或判決更能證明誓是以強制力維護和保證其實施的,一些誓的程序與儀式是通過國家禮制確定其契約效力的,無論誓言違背與否,它的契約法律性質(zhì)不可變更。當然,春秋時期各國紛紛頒布成文法以致誓的契約作用式微,則另當別論,不可同日而語。
綜上,誓是由當事人按照一定程序與儀式所立的信,成文法頒布之前是定刑處罰的依據(jù)。作為解決糾紛的判決方式,“誓”在西周、春秋時期既是禮制的一部分,也是司法判決時的契約,誓辭對當事人能夠形成一種約束。出土資料表明,誓主要是針對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糾紛或訂立新的契約關(guān)系以防止爭議,以此規(guī)定當事人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總體上,法律性質(zhì)的誓包含約信之辭、處罰方式、維護誓言的權(quán)力機制等,故在禮制社會中,“誓”是具有法律性質(zhì)的契約是無可爭議的,但不能將其等同法律。
二、先秦判例中的“比”
(一)作為判例的“比”
“比”的判決例子難以詳考,然具有“比”的因素的例子最早記載可見于《左傳·昭公六年》。魯昭公六年(前536年)鄭國子產(chǎn)鑄刑書于鼎,晉國叔向遣使送子產(chǎn)書諫阻鑄鼎,“昔先王議事以制,不以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15]1274。關(guān)于叔向所言之“制”的具體含義,諸家所注,莫衷一是。李學勤主編的《十三經(jīng)注疏》標點本之《春秋左傳正義》:“臨事制刑,不豫設(shè)法也,法豫設(shè),則民知爭端。”[16]1225《尚書正義》:“《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以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不預(yù)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以刑書比附而罪之。”[17]551均認可“制”是指遇上案件時確立的一個判決標準,并言及“以刑書比附”。楊伯峻編著的《春秋左傳注》云:“儀,度也。制,斷也。謂度量事之輕重,而據(jù)以斷其罪。”[15]1274依楊伯峻之意則是判決的標準、尺度在先。楊一凡等認為先王之制的內(nèi)容即叔向詒子產(chǎn)書所言:“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9]347
按當時人叔向所言“議事以制”,可知“制”確實具有法律因素,但這里的制是具體案情或?qū)徟薪Y(jié)果,還是抽象的判決依據(jù)或司法原則,則不得而知。以叔向書的內(nèi)容為根據(jù)也不能明確界定“制”為何意。寧全紅博士的《春秋法制史研究》曾設(shè)《春秋時期“議事以制”初探》一節(jié)專門討論,最終認為“制”是“從某一案件審判結(jié)果中抽象出的判決依據(jù)或司法原則”[18]115。擱置爭論,諸家解釋“制”具有“比”的因素,或者影子,可以明見。
然而先秦時期是否存在“比”這種特殊的判例法依然未能解決,就目前而言尚有懷疑,甚至存有否定言論。劉篤才先生認為西方概念與中國實際之間存在差距,導(dǎo)致將古代例、條例、案例、判例混合,甚至將廷行事、決事比、法例、案例不加區(qū)別的等同[19]。事實上這一論點有用現(xiàn)代西方判例概念稽尋我國古代有無判例法之嫌。何勤華先生認為先秦時期只是判例法的萌芽階段,其真正形成是在審判組織發(fā)達、獄訟規(guī)范化的秦漢時期,而之前是習慣法時期[20]。楊師群先生則否定先秦存在判例的同時又有所保留,認為可能存在一些無法界定的判例被當成“故事”作為參考案例的司法樣式的萌芽[21]。
但是相關(guān)證據(jù)表明先秦時期是存在判例法的,并非習慣法。《荀子·大略》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推。”[22]453“類”即以判例為根據(jù)判決。清人沈家本論述“斷罪無正條”時曾考證先秦秦漢時期的“比”字,認為其意有:次、校、例、比方、類、類例、以例比況、比附及故事等。[23]1808武樹臣先生認為在西周時期出現(xiàn)了表示判例的“御事”一詞。[24]209-210又解釋“議事以制”為根據(jù)以往案例判決,認為西周春秋的法律樣式為判例法。[25]汪世榮先生也認為在《左傳》、《國語》中存在以案例判決的情況[26]5-7,且汪氏稱“從已經(jīng)出土的簡帛資料和青銅器銘文看,戰(zhàn)國以前的法律形式確實表現(xiàn)為判例法”,并認同《曶鼎》、《比鼎》、《匜》、《琱生簋》所記即為西周時期的判例[27]。事實上,汪氏所言是有道理的,作為司法判決的案例,它是以單獨的個案形式存在的,與漢代“比”一致。林劍鳴《秦史稿》舉《法律答問》一例說明作為判例依據(jù)的案例具有漢代“比”的性質(zhì):“律曰:‘斗夬(決)人耳,耐。’今夬(決)耳故不穿,所夬(決)非珥所入殹(也),可(何)論?律所謂,非從珥所入乃為夬(決),夬(決)裂男若女耳,皆當耐。’雖然解釋律文,但實際已超過律的本身內(nèi)容,因此,這種解釋就具有最高法律性質(zhì),而其中所舉的案例也就成為判例的根據(jù),具有漢代‘比’的性質(zhì)。”[28]182
在有關(guān)先秦時期歷史的典籍中,“比”(判例)確實存在。《周禮·秋官·司寇五·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憋之。”漢代經(jīng)學家鄭玄引鄭眾語:“憋當為弊。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弊之,斷其獄訟也。”[2]1326事實上,“邦成”之重點在于“成”,李學勤先生在《岐山董家村訓(xùn)匜考釋》一文中認為“成”是一個法律名詞[12]151,此說甚允。《周禮·秋官·士師》中有“掌士之八成”,鄭玄注:“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又“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2]922沈家本言:“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曰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弊之,斷其獄訟也。”[23]824沈家本之言與鄭玄之言相差無幾。此外,亦有“以官府之八成經(jīng)邦治……六曰聽取予以書契”[2]57-58。我們可以肯定“成”是法律名詞,“八成”即定國安邦的八種刑典或法律,“書契”即獄訟判決的根據(jù),可以是誓辭,也可以是以往的判例,都是“成”的一種。可見,“邦成”之“成”即為已有判例,鄭玄多次言及“邦成”類似兩漢時期“決事比”是不會有誤的①兩漢時期的“決事比”是一種特殊的司法判決方式,其判決理念與判決依據(jù)主要根據(jù)以往相似的案例,或者比附經(jīng)義(春秋決獄),為當下及以后判決提供標準與依據(jù),其本身即可看成具有比附、比照意義的判例。,而這種以判例為依據(jù)的判決方式其源流是可以上溯至先秦時期的。
《周禮》成書時間,雖然爭議較大,但其成書于戰(zhàn)國時期,在漢代最終定稿,則可定論,而且其反映周代社會的內(nèi)容也為越來越多的金文資料證實。李學勤先生也曾言:“《周禮》一書自從漢代即屢經(jīng)疑議,有人主張是‘六國陰謀之書’,有人以為是劉歆偽作。但近年新發(fā)現(xiàn)金文,卻有不少與《周禮》契合的地方。看來《周禮》至少是一部比較重要的先秦典籍,我們研究古代歷史文化,不能忽視它的意義。”[12]151因此,以《周禮》中的相關(guān)內(nèi)容作為判斷類似于兩漢“決事比”之“比”的判決方式出現(xiàn)于先秦時期是不會導(dǎo)致失誤的。只是現(xiàn)今我們不知道這些類似于兩漢“決事比”的判決方式在具體判決中針對的對象是如何區(qū)分的,是根據(jù)某些具體案例得出的判決結(jié)果作為指導(dǎo),還是根據(jù)以往判決人從具體案例本身提煉而出的法律精神?如果是前者,那么“比”就是已有判例;如果是后者,那么“比”就是法律精神,具有法理意義。然而,基于時代背景而言,法律精神的抽象總結(jié)不可能早于判例法而出現(xiàn),故前者可能性極大。
此外,《尚書·盤庚》中篇記有“非汝有咎比于罰”,是可以看出商代已存在判例法的最為明顯的證據(jù)之一。《盤庚》三篇歷來史料價值很高,很少有人認為是后世偽造。“有咎比于罰”即犯了過錯就根據(jù)已有案例比附判決(處罰)。武樹臣認為:“審理某一案件,經(jīng)過占卜,做出判決。以后再遇到同類案件便不再占卜,而直接參照成案判決之。……這種做法從某種角度而論已經(jīng)是‘判例法’了,盡管它僅作為某種例外而被籠罩在‘神意’的云霧之中。”[29]51從文意及武樹臣先生的觀點可知,“比于罰”的“罰”就是一種已有判例,而“比”則是比附判決,至于判決的思想則并未萌芽。商代迷信神鬼,對犯刑之人做出處罰前進行占卜是必須的,那么根據(jù)已有的占卜判決相似案例也是可以理解的,這種做法的確也就屬于“神意”判決。周初《康誥》也記載“茲殷罰有倫”與“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茲殷罰有倫”,孔穎達《尚書正義》云:“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即殷商時期若沒有刑書遵循,可以根據(jù)判例決斷。“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尚書正義》云:“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17]365則是直接指明殷商時期根據(jù)案例判決爭端,皆可說明殷商時期存在以案例為判決依據(jù)的情況。
《呂刑》中也提到“比”。據(jù)《史記》記載《呂刑》作于西周穆王時期,《周本紀》云:“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30]138-139文中“甫侯”即“呂侯”,“甫刑”即“呂刑”。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將《呂刑》作為西周史料引用,王世舜、王翠葉譯注《尚書》認為郭沫若“這種做法似可信從”[31]317。可見《呂刑》的價值是比較高的。《呂刑》中有“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王世舜、王翠葉注釋“制”為“制止,意思是說不再讓他們犯刑”。猶可商榷,依刑判決之“制”若只是簡單的“制止”,防止百姓不再犯刑,那么“刑”的意義無疑被降低了,恐怕“以教祗德”也將無從談起。故“制”釋“以刑預(yù)防或判決案件”更為妥當,至于判決形式則不可詳知,只是可以認為“制”當有“比”的因素,而此處“刑”則屬于判例。
上述《周禮》及《尚書》中有關(guān)“比”的討論,說明在先秦時期作為判決的“比”是存在的,也就是說先秦時期存在判例法。而我們從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一篇也可推測先秦時期存在判例法。
1975年12月,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一批秦簡,其中有《法律答問》一篇。綜合研究表明,《法律答問》是秦代解釋司法問題的專集,以問答的形式對相關(guān)的典型性案例進行解釋說明。《法律答問》一篇中出現(xiàn)了“廷行事”這一法律名詞,整理小組解釋為“法律成例”[32]102。清人王念孫《讀書雜志·六·漢書第十二》也有對“行事”的解釋:“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33]30另據(jù)《漢書·翟方進傳》記載:“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34]3412這里“自道”從文義而論當與漢代司法訟訴中的“自言”相當,即類似后世審判中的自我申訴與辯解,而“行事”無疑是“以往案例”。同時,王念孫注釋此句時引劉敞所言:“漢時人言‘行事’、‘成事’,皆已行、已成事也”。[32]31總之,“廷行事”一詞,可以定義為:根據(jù)已有的案例比附判決相似案件,與漢代“決事比”之“比”的判例意義相近。秦代“廷行事”的案例意義是大于從案例中總結(jié)出來的準則和理念的,即“廷行事”通常只是起指導(dǎo)判決作用的個案,具有普遍適用意義的司法判決原則并未體現(xiàn)出來。
秦代“廷行事”類似漢代“決事比”,其形成當有一段較長的時間進程,而與“比”有關(guān)的討論及“故事”、“成事”、“行事”等法律名詞,說明“比”這種以案例為依據(jù)的判決方式在先秦確已出現(xiàn)是無可置疑的,認為先秦時期判例的應(yīng)用只是判例法的萌芽,而其形成于秦漢時期則有失公允。[20]秦代的“廷行事”既然已經(jīng)整理成冊,即可說明它是一種較為成熟的判決方式,其判決技術(shù)就是以典型性案例作為指導(dǎo)。可以認為,《法律答問》是秦統(tǒng)一以前秦國部分法律條文合集,屬于判例法,處于草創(chuàng)時期,集合的是一些經(jīng)典判例,故整理小組認為是“商鞅時期制訂的原文”[32]93。
以秦代“廷行事”頻繁出現(xiàn),并且較為成熟,說明在先秦時期依靠已有典型性案例作為斷案判決的依據(jù)是存在的。先秦時期諸多典籍中與獄訟有關(guān)的“邦成”及注疏中所言的“故事”、“成事”、“行事”,其意就是已有判例。成文法頒布之前的時代里,法無明文,司法官可以用比附類推的方法,或用成例比附科刑[10]113。比附、比照的引用已有經(jīng)典案例判決案件就是具有判例法意義的“比”。而秦漢以前據(jù)案例判決的司法方式當有相當?shù)臍v史階段,就是到了漢代也仍然存在“決事比”的情況,說明抽象的法理、法律條律并未總結(jié)成書,這并不是否定法律存在,相較之下,反而更能說明先秦時期存在判例法。
(二)“比”的判決技術(shù)
目前對先秦時期“比”這一判決方式做出相對精確的定義較難,我們只可知曉“比”在先秦時期不僅具有判例法意義,也有一定的司法理念及判決技術(shù)。《呂刑》有言:“上下比罪,勿僭亂辟。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31]329“上下”指觸犯刑罰行為的輕與重,《呂刑》中的“比”適用性很強,要求司法官做出的判決,一定要做到與事實相符合,核實罪情根據(jù)刑罰辦事,講究判決合法、適度,禁忌“勿僭亂辟”。據(jù)文意而論,就是在判決中必須要注重對案例的考察、甄別,確定一個相對的標準,形成司法理念,指導(dǎo)類似案例的判決。
當然《呂刑》中的“比”也包含一定的判決要求與技術(shù)。“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者諸罰有權(quán)。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罪行輕重之別應(yīng)當臨時斟酌,不可輕易作出判決,或輕或重須做到上下皆服、有倫有要。上文“上下”至“有要”,王世舜、王翠葉譯注《尚書》分為了兩段,孔穎達《尚書正義》是作為一段來疏證,并曰:“此又述斷獄之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乃與獄官眾議斷之。……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為不能也”。在這里,“比”有適用性原則,如果確實不能作出判決,還可以“獄官眾議”,做出公平公正的審判、判決,使案子不出現(xiàn)“亂辟”情況。或者:“罪條雖有多數(shù),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并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yù)防之。……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17]550相反,這一解釋則指的是犯者的案例若沒有相應(yīng)的刑罰規(guī)定,就只能根據(jù)已有的案例(故事)“上下比方”做出判決,而且量刑上做到:重罪卻不是一慣觸犯,則可輕罰;輕罪卻是故意或經(jīng)常觸犯,則可重罰。
《禮記·王制》所載稍有不同,“凡聽五刑之訟,疑獄泛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鄭注:“大小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1]412孔穎達《禮記正義》:“‘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者,大小猶輕重也。比,例也。已行故事曰比。此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按舊法輕重之例,以成于事。”[1]415《正義》所言指不能確定是否觸犯刑罰的行為應(yīng)該給予赦免,或者按照以前相似的案例作出或輕或重的判決,當然我們應(yīng)該看到這是沒有法律可以依據(jù)的情況下而采取的比附判決。
“比”的案例意義大于從案例中抽象出來的準則和理念,但作為判決的指導(dǎo)案例其適用是有限制的,而正是其限制引發(fā)了是否有比附它律的爭議,上文《尚書正義》中對《呂刑》的解釋即是如此,存在法無此條則上下比罪之爭議,或依照案例比附判決,或依照其它相似律條比罪。沈家本則從孫奭《律音義》未有比附它律之說,沈氏認為妄為比附會導(dǎo)致挾仇陷害、酷刑興起,強為比附則法令不一,冤濫滋多。[23]1808-1809沈氏的見解是正確的,“比”最初的意思是比附案例進行判決,而不是比附它律,且從“比”的判決技術(shù)而言,我們也看不出存在比附它律的一面。
姑且不論沈氏所說比附它律的不利結(jié)果,但其沒有“比附它律之說”是深得其要的,律無明文則可以用例比附判決,并非依照它律比附輕重以作出判決,故比附它律之說很難成立。不可否認,“比即決事比之比,大小必察,亦即上下比罪之意”。[23]1809典籍及注疏中所見之“比”的確屬于判例,也有一定的司法判決理念、技術(shù)及原則因素,而較多的爭論也說明其有不完善的一面及判例與司法理念兩重因素。總體而言,先秦時期“比”的個案意義絕對大于法理意義則是無可爭辯的,其法理內(nèi)涵主要還是漢儒解經(jīng)而賦予的。
綜上,“比”在先秦時期是一種特殊的不完善的司法判決方式,其判決依據(jù)與判決技術(shù)具有一定的司法理念。先秦時期的“比”具有比附、比照的判例法意義及基于已有判例確立的相應(yīng)的判決標準和尺度(主要體現(xiàn)為上下比罪),然而具體的判例現(xiàn)今所見典籍已不可明確稽考。從傳世的《周禮》、《尚書》等典籍中我們只可以認定先秦時期存在判例法,也可推測用于指導(dǎo)判決之“比”的標準與尺度,即判決的理念。
三、誓與比蘊涵的法理思想
王國維云:“中國政治與文化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35]231刑罰思想亦然。在西周以前,中國刑罰更具野蠻性與殘酷性,殷墟卜辭中刑罰殘酷可見一斑,因此殷商及之前可稱“刑罰”,而不是“刑法”。西周建立之后這一情況有所改觀,西周刑罰中人文因素勝于之前鬼神因素,周人將道德與刑罰結(jié)合起來,貫徹德主刑輔的思想,以誓與比而言,判決中可見“明德慎罰”思想,周人具體貫徹“明德慎罰”思想時,周人利用了一系列禮樂模式進行調(diào)控,抵制濫用刑罰,則是后世“禮法合一”的淵源。
(一)明德慎罰思想
殷周之際天道觀念發(fā)生變化,人的作用突出。西周建立之后,審視殷商亡國教訓(xùn),隨之而來的是人文精神與理性主義興起,由之前徹底皈依鬼神逐漸轉(zhuǎn)向為重視自身行為的謹慎與努力。[36]285作為判決之誓也因西周建立而滲入新的內(nèi)涵,即融入了周初由周公旦等人抽象提煉的“明德慎罰”思想。“明德慎罰”是殷周鼎革之后,西周統(tǒng)治者反思殷商殘酷刑罰及其滅國教訓(xùn)而提出的。“明德慎罰”一詞出現(xiàn)于周初,見于《康誥》和《多方》,而德觀念卻見于殷周之際所有《尚書》各篇之中。①《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多方》:“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此外,《文侯之命》有“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殷末周初之際,《微子》、《洪范》、《酒誥》、《梓材》、《召誥》等所有《尚書》各篇均涉及“德”,周人重“德”可見一斑。“明德慎罰”的核心是“道德訓(xùn)誡,慎用刑法”,是對殷商末年暴刑的反動。慎罰是周代刑制的基本特色,在周代一些頗具代表性的刑法原則中得到了體現(xiàn)。[37]14本文所引《匜》銘文記載的判決是西周“明德慎罰”思想的具體實踐之一。
周人刑罰之德旨在規(guī)范品行、熏陶人格精神。西周立誓程序多由代表政府的官員引導(dǎo),所以,“盡管在一般情況下,立誓是由司法機關(guān)強制進行的,但立誓后遵守誓言的過程則是一個自我教育的過程,它使立誓者逐漸認識到遵守誓言就是避惡從善,從而自覺克制和矯正自己的行為”。[37]26很多時候,立誓者出于對懲罰的畏懼而嚴守誓言,這種自我教育的過程可能伴隨著不自愿的強迫性,但無論如何,誓言總會起到教育感化作用,以規(guī)范人們的言行。長此以往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必然“有恥且格”。[38]12《匜》銘文中體現(xiàn)的周人“明德慎罰”思想,其要旨是制度之德與精神品行之德,淡化了西周之前的天德與祖宗之德,不再過分依賴天與祖宗。這與西周建立后,提出“明德慎罰”思想,注重從品行上培養(yǎng)人文情懷,強調(diào)道德訓(xùn)誡有關(guān)。有學者認為西周時期德觀念逐漸擺脫了天道觀念影響而從天命神意的迷霧中走了出來,[39]而德觀念在殷周之際的變化正是因為周人重視人類自身品行的努力所致。
本文所引各篇銘文不見發(fā)誓用牲的記載,并不是否定誓在當時社會中大量存在的現(xiàn)象,反而更能說明西周看重人事的作用與影響。各篇之誓或有周王在場,或有重要官員出席,說明“天”的作用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被降低了。誓審只不過是利用人們對天還殘存的畏懼心理,把天作為一種工具加以利用罷了。[10]300也就是說,西周統(tǒng)治者把天作為一種工具運用于司法判決中,并結(jié)合自己的“德”觀念,形成了“明德慎罰”的刑罰原則。假如一味使人們畏懼刑罰,害怕因為違背誓言而“天理不容”,那么于注重道德訓(xùn)誡功能無濟,其結(jié)果只會導(dǎo)致“民免而無恥”,喪失道德內(nèi)涵與精神風貌。
而在比附及察“大小輕重之比”時,周人同樣堅持“明德慎罰”的思想觀念。具體來說,周人尚“中”的道德理念在立法與司法領(lǐng)域中體現(xiàn)為“中刑”原則。“中”本是周人的倫理觀念、道德準則,但周人也將其用于司法判決中,在比附判決時,“上下比附”的司法判決技術(shù),是做到量刑適中、罪罰一致的最好表現(xiàn)。如《禮記》記“附從輕,赦從眾”,注:“附,施行也。求出之,使從輕”。疏:“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也。”[1]411-413此外,《周禮》、《尚書》中有關(guān)“比”的注疏亦無不如此,這可結(jié)合上文“‘比’的判決技術(shù)”一節(jié)得知,此不贅述。總的來說,周人“上下比之”即堅持“中刑”原則,實踐時的具體要求則是公正適用,周人的“明德慎罰”思想在西周時期已經(jīng)融入刑罰之中了。
然而“中刑”如何實施在不同的場合可以因時制宜。對牧牛與攸衛(wèi)牧的處罰無不貫穿“中”的內(nèi)涵,對有疑慮的案件“上下比之”以后仍然不能判決者,則需“眾獄斷之”,也表明周人判決獄訟之時始終心存恪守公正、慎用刑罰的原則。誠然,“中刑”含有司法公正、量刑適中及罪刑相適應(yīng)的法文化意蘊,是周人“明德慎罰”觀念的核心。當然“中刑”只是周人貫徹“明德慎罰”思想所表現(xiàn)出來的,其慎罰的核心還是重視“道德訓(xùn)誡”。
(二)禮法合一思想
先秦時期禮、法對社會的規(guī)范與約束效力一致,誓與比蘊含的“禮法合一”特點,對后世“禮法合一”的立法精神影響深遠。魯昭公六年(前536年)鄭國子產(chǎn)鑄刑書于鼎一事,童書業(yè)云:“惟春秋前制刑,蓋藏之于官府,貴族守之,用于鎮(zhèn)壓人民。至此鄭、晉始明布刑律,即‘成文法’之公布也”。[40]207童書業(yè)所說不是否定之前沒有法律,而是沒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法律,成文法公布之前主要是指刑罰,它包含很多禮的因素。判決之誓之所以有契約法律效力,就是因為其程序符合先秦時期的禮制,觸犯禮的行為,無疑也觸犯了刑罰,以現(xiàn)在之語言之即“禮法難容”。換言之,誓是“禮法合一”的綜合體現(xiàn)。同樣,周人在比附判決時的“中刑”原則也含有禮的因素,比附輕重本身就包含人情因素,其核心即貫穿于禮樂教化中的“德”觀念。春秋后期孔子曾把禮置于刑罰之上,《論語·子路第十三》:“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38]132孔子指出禮是罰的核心,禮樂如若不能得到重視,作為對付被統(tǒng)治階級的刑罰也不會公正適當,自然統(tǒng)治者標榜的德政也就無法實現(xiàn)。周人看來,要解決這一問題,不外乎通過一系列禮樂模式對刑罰進行調(diào)控。
禮樂模式的調(diào)控功能在先秦社會中是一切禮儀得以維持的核心,而禮樂模式對刑罰的調(diào)控尤其重要,以致罰讓位以禮,退居次要地位,形成“禮法合一”的特點。①文中這一小節(jié)以后部分因先秦時期的“刑罰”在西周建立之后出現(xiàn)“慎罰”思想,處罰時滲入更多人的因素,野蠻和殘酷程度降低,為了行文方便,論及法律時用“刑法”一詞代替“刑罰”,“法”代替“罰”。“禮法合一”導(dǎo)致禮具有法的功用,既然發(fā)誓的過程屬于禮制領(lǐng)域,那么它確立的內(nèi)容也就是新的契約關(guān)系,而違背誓言也就不需要依靠神意判決,而是禮制下的權(quán)力。“禮制在法律關(guān)系創(chuàng)制中的意義表現(xiàn)在,通過嚴格的程序性禮儀形式確定雙方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起到對雙方行為進行約束的作用。”[14]266可見在我國古代法律確立的起始階段禮法是合一的。
在“明德慎罰”思想指導(dǎo)下,德教是根本,刑罰是補充。其表層是德與罰之間的關(guān)系,其深層則是禮與法的關(guān)系。因為禮與法有不同之處:禮是積極的正面規(guī)范,法則是消極的制裁性規(guī)范,所謂“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也。[41]218這就是說,法只是作為禮的補充而存在,是規(guī)范人們行為的最后防線,那么在禮法之間,“德”則成為兩種規(guī)范的核心元素。統(tǒng)治者將德、禮、法結(jié)合起來實行,以德為首,其次為禮,最后為刑。“上下比之”雖不見德與禮,而其處理技術(shù)卻見禮樂模式的調(diào)控作用與道德教育。雖然誓與比都有“禮法合一”的特點,卻也有一定的區(qū)別,誓同時含有制度之禮與抽象的禮的精神,比則主要是抽象的禮的精神。西周統(tǒng)治者規(guī)范人們言行,在強調(diào)德的同時,也需要有威嚴的刑,為了防止濫用暴刑,禮樂模式進行調(diào)控也就勢在必行,而禮樂模式的這種調(diào)控功能在成文法之前導(dǎo)致禮法區(qū)分不大,很多時候甚至可以等同。然而,先秦時期的“禮法合一”終究與兩漢之后還是有很大區(qū)別的。
在先秦時期,禮主要是制度之禮,實施過程中則指一些具體的符合當時社會規(guī)范的原則性儀式禮制。如《孔子世家》載孔子少時,“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shè)禮容”。《正義》云:“俎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云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也。”[30]1096-1097即孔子少時曾用俎豆演習禮。又孔子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楊伯峻言“灌”即禘祭的一部分,說明禘祭是由很多禮的程序構(gòu)成的。①楊伯峻注釋:“灌”,本作“裸”,是祭祀節(jié)目之一。古代祭祀用活人以代受祭者,活人一般為幼小男女,第一次獻酒使之聞到鬱鬯的香氣,叫做裸。《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26。又有人問孔子:管仲是否知禮,孔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38]31皆可說明先秦時期的禮有一些具體的要求與內(nèi)容,可以稱之為“制度之禮”,至于抽象的禮的精神則是孔門后學提煉總結(jié)的。這些也可推知,先秦時期誓所具有的禮制因素是一些程序,不是抽象意義上的禮,那么誓所推動的“禮法合一”進程也就是一個不斷融入新內(nèi)涵的歷史階段。誓在進入成文法時代后逐漸淡出司法判決領(lǐng)域,隱藏于社會生活中而作用微乎其微,但其蘊含的“禮法合一”則沒有終結(jié),并且隨著法律的進一步發(fā)展出現(xiàn)新變化,體現(xiàn)為“禮”是抽象的立法指導(dǎo)精神。相較而言,比的判決技術(shù)所體現(xiàn)出的抽象的立法精神則更為明顯。到了兩漢時期“春秋決獄”極大地推動“禮法合一”,并在唐代最終完成“禮法合一”,若深究其淵源,正是先秦時期誓與比這樣具有“禮法合一”特點的判決方式所推動的。
[1]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M]/李學勤主編.十三經(jīng)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M]/李學勤主編.十三經(jīng)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3]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1.
[4]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M].北京:中國科學院,1952.
[5]李學勤.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轉(zhuǎn)讓[G]//李縉云.李學勤學術(shù)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6]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吳榮曾.試論先秦刑罰規(guī)范中所保留的氏族制殘余[J].中國社會科學,1984(3):199-210.
[8]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9]楊一凡,主編.夏商周法制考[M]//中國法制史考證甲編第1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10]胡留元,馮卓慧.西周法制史[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8.
[11]杜文忠.誓與法[J].現(xiàn)代法學,2004(1):52-55.
[12]李學勤.岐山董家村訓(xùn)匜考釋[G]//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
[13]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14]王沛,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一輯)[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
[16]杜預(yù)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M]//李學勤,主編.十三經(jīng)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7]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M]//李學勤,主編.十三經(jīng)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8]寧全紅.春秋法制史研究[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
[19]劉篤才.中國古代判例考論[J].中國社會科學,2007(4):145-155.
[20]何勤華.秦漢時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點[J].法商研究,1998(5):133-142.
[21]楊師群.中國古代法律樣式的歷史考察——與武樹臣先生商榷[J].中國社會科學,2001(1):113-118.
[22]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荀子新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23]沈家本.歷代刑法考[M].北京:中華書局,1985.
[24]武樹臣.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25]武樹臣.中國古代法律樣式的理論詮釋[J].中國社會科學,1997(1):125-139.
[26]汪世榮.中國古代判例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27]汪世榮.判例在中國傳統(tǒng)法中的功能[J].法學研究,2006(1):125-134.
[28]林劍鳴.秦史稿[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29]武樹臣.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鳥瞰[M].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
[30]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31]王世舜,王翠葉譯注.尚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2.
[32]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33]王念孫.讀書雜志[M].北京:中國書店,1985.
[34]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5]王國維.觀堂集林(外二種)[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6]趙容俊.殷商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術(shù)(增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2011.
[37]崔永東.金文簡帛中的刑法思想[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
[38]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
[39]晁福林.先秦時期“德”觀念的起源及其發(fā)展[J].中國社會科學,2005(4):192-204.
[40]童書業(yè).春秋左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41]李學勤,主編.西周史與西周文明[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shù)文獻出版社,2007.
責任編輯 張穎超
K876
A
1673-9841(2015)02-0158-11
10.13718/j.cnki.xdsk.2015.02.020
2014-10-05
鄒芙都,歷史學博士,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商周金文字詞集注與釋譯”(13&ZD130),項目負責人:鄒芙都;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2007年以來新見殷周有銘銅器的整理與研究”(11CZS004),項目負責人:鄒芙都;中央高校基金項目“西周‘非對揚王休’銘文整理與研究”(SWU1509375),項目負責人:查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