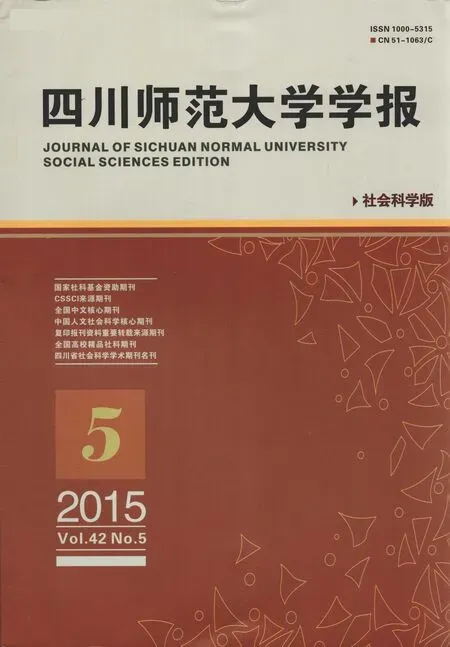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變遷的“差序格局”解讀——基于社會身份視角的探討
張必春,許寶君(華中師范大學(xué)a.政治學(xué)研究院,.湖北城市社區(qū)建設(shè)研究中心,武漢430079)
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變遷的“差序格局”解讀——基于社會身份視角的探討
張必春a,b,許寶君b
(華中師范大學(xué)a.政治學(xué)研究院,b.湖北城市社區(qū)建設(shè)研究中心,武漢430079)
摘要:費(fèi)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精準(zhǔn)地概括了傳統(tǒng)中國社會關(guān)系格局,然而,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jīng)濟(jì)的推進(jìn),學(xué)者們在“理論自覺”的過程中,進(jìn)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差序格局的內(nèi)涵,姻緣、感情、利益等新興要素全面滲透到差序格局中,傳統(tǒng)差序格局出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轉(zhuǎn)向。然而,對失獨(dú)父母而言,無論是傳統(tǒng)差序格局還是現(xiàn)代差序格局都無法對他們的社會關(guān)系選擇行為做出合理的解釋,因?yàn)樗麄兊纳鐣蛹炔皇茄壷鲗?dǎo),也不是利益主導(dǎo),而是身份主導(dǎo)。基于社會身份選擇,失獨(dú)父母的社會關(guān)系差序格局出現(xiàn)了選擇標(biāo)準(zhǔn)的更替、內(nèi)圈層的置換、重要要素的重組和差序格局的斷裂風(fēng)險,因此,筆者將此稱之為“非常態(tài)差序格局”。
關(guān)鍵詞:差序格局;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社會身份;非常態(tài)差序格局
許寶君(1989—),男,四川巴中人,華中師范大學(xué)湖北城市社區(qū)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基層治理、邊緣人群治理研究。
一 背景及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社會關(guān)系越來越成為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社會關(guān)系在社會學(xué)分析中,尤其是對社會結(jié)構(gòu)和社會行動的分析中具有很大的作用。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質(zhì)在其現(xiàn)實(shí)性上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1]78這明確告訴人們,社會關(guān)系是人本質(zhì)屬性的反映,同時,透過這一話語,我們足以看見社會關(guān)系于人、于社會的重大作用。近些年來,隨著新制度主義的興起,尤其是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的“嵌入性”(embeddeness)理論的提出,使得對社會制度和社會行動的分析,必須被重新置于對社會關(guān)系的分析的基礎(chǔ)上,社會關(guān)系在社會學(xué)分析中的作用重新受到學(xué)界的關(guān)注。就我國而言,社會關(guān)系研究也是學(xué)界最古老而傳統(tǒng)的研究課題之一,著名學(xué)者費(fèi)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可謂是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關(guān)系和社會結(jié)構(gòu)的全面總結(jié)和經(jīng)典概括,自此“差序格局”成為了學(xué)者分析我國社會關(guān)系的一個很有力的解釋概念和分析框架。
然而,社會關(guān)系不是一個靜態(tài)的概念,尤其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關(guān)系發(fā)生了巨大的變遷,傳統(tǒng)社會差序格局式的社會關(guān)系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我國許多學(xué)者將差序格局植根于我國當(dāng)前的社會實(shí)際,進(jìn)行
了一些有意義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diǎn)。如李沛良指出,在競爭激烈、成就動機(jī)高的社會里,該格局中的個體行動邏輯是工具理性,傳統(tǒng)文化資源不再被當(dāng)作至高無上的規(guī)則來遵守與指導(dǎo)行動,而是被當(dāng)作資源用于求利的目的,并提出了“工具性差序格局”的概念[2]76。林聚任提出差序格局的“裂變理論”,他認(rèn)為在涉及利益特別是直接的經(jīng)濟(jì)利益時,差序格局仍然具有一定的適用性,農(nóng)民仍然是按照親屬的遠(yuǎn)近來選擇關(guān)系的類型,但是在一般的情感交流中,差序格局已經(jīng)開始裂變,農(nóng)村是按照自身的興趣來選擇關(guān)系角色,交流感情;同時在信息傳遞方面,農(nóng)村符號網(wǎng)絡(luò)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特點(diǎn),已經(jīng)看不到差序格局內(nèi)的親屬和地緣的任何作用[3]121。這些理論刻畫了中國市場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后,人際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的變化都是隨著市場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而出現(xiàn)的,理論構(gòu)建結(jié)果增強(qiáng)了差序格局的適用性[4]。然而,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些理論都是立足于整個社會人群,從宏觀上建構(gòu)的一種“通用理論”,但是當(dāng)我們把研究對象立足于一些微觀群體,特別是一些特殊弱勢群體的時候,這些理論是否還具有“通用性”,能否有效地解釋這些群體的社會關(guān)系選擇行為?這仍是一個值得商榷和探究的議題。本文將以“失獨(dú)父母”①這一特殊的弱勢群體為研究對象,以差序格局為理論支撐,試圖探究這一群體的社會關(guān)系變遷路徑、選擇標(biāo)準(zhǔn)以及內(nèi)在結(jié)構(gòu)。
差序格局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關(guān)系的基本結(jié)構(gòu),以倫理為本位的差序格局有效地解釋了傳統(tǒng)社會人們的社會關(guān)系和社會行為,但是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jīng)濟(jì)的推進(jìn),我國社會關(guān)系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學(xué)者們在“理論自覺”的過程中,進(jìn)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差序格局的內(nèi)涵,傳統(tǒng)差序格局出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轉(zhuǎn)向。
經(jīng)典差序格局,準(zhǔn)確論述了我國傳統(tǒng)社會關(guān)系的基本結(jié)構(gòu)。費(fèi)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生育制度·鄉(xiāng)土重建》一書中刻畫了一幅傳統(tǒng)中國社會關(guān)系的圖景:“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fā)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fā)生聯(lián)系。”[5]27這就是所謂的差序格局。每個人的社會關(guān)系格局實(shí)際上就是一個同心圓的圈層格局,整個社會的關(guān)系格局就是無數(shù)個圈層相套、疊加,并不斷延伸出去的格局,其基本結(jié)構(gòu)特征是:第一,以血緣和地緣為互動邏輯[6],第二,以道德為基礎(chǔ)的人倫是其實(shí)踐特征[]。
隨著現(xiàn)代化的轉(zhuǎn)型,特別是我國處在農(nóng)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計劃經(jīng)濟(jì)向市場經(jīng)濟(jì)轉(zhuǎn)變的過渡時期,社會結(jié)構(gòu)和社會關(guān)系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口流動和交往的頻次增加,傳統(tǒng)差序格局的內(nèi)涵和外延都得以擴(kuò)大和深化,出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轉(zhuǎn)向,具體特征是:第一,行動單位由家族這種單一載體轉(zhuǎn)向家族、單位這種雙重載體[8],第二,選擇標(biāo)準(zhǔn)由血緣轉(zhuǎn)向血緣、姻緣、感情、利益等多種要素相交織[9]。
雖然隨著時代的變遷,我國經(jīng)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差序格局仍然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工具,被一代又一代學(xué)者用來分析社會現(xiàn)象。同時也正是由于社會的急劇變革,一代又一代的社會科學(xué)研究者對“差序格局”理論進(jìn)行了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延續(xù)了該理論的學(xué)術(shù)生命。同樣基于這種考慮,筆者試圖用差序格局理論分析失獨(dú)父母問題,一方面更加清晰地解剖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的變遷,另一方面,試圖通過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變遷的經(jīng)驗(yàn)案例分析總結(jié),繼續(xù)擴(kuò)展差序格局的理論內(nèi)涵。
二 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的現(xiàn)實(shí)狀態(tài)
社會關(guān)系就是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總稱,從社會關(guān)系的類型來講,社會關(guān)系包括個人與個人、集體、國家之間的關(guān)系。本文中的集體是個范疇,小到民間組織,大到國家政黨,都包含在集體的范疇內(nèi),進(jìn)行同類項(xiàng)合并后,社會關(guān)系就包括個人之間的關(guān)系和個人與集體(組織)之間的關(guān)系。再依據(jù)關(guān)系性質(zhì)的不同,個人與個人的關(guān)系又可分為個人與親屬、虛擬親屬和非親屬的關(guān)系,個人和組織的關(guān)系又可分為個人與他組織、自組織的關(guān)系。就失獨(dú)父母而言,其社會關(guān)系呈現(xiàn)出如下現(xiàn)實(shí)狀態(tài)。
(一)個人與親屬、虛擬親屬的關(guān)系:疏遠(yuǎn)
親屬是基于婚姻、血緣和法律擬制而形成的社會關(guān)系,包括血親、配偶和姻親。親屬關(guān)系是一種強(qiáng)信任關(guān)系,具有很強(qiáng)的穩(wěn)定性。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在分析現(xiàn)代工業(yè)經(jīng)濟(jì)時認(rèn)為中國文化中信任度低,人們普遍不信任與自己沒有親屬關(guān)系的人[10]86。因此,對中國人來說,即使兩個人彼此之間沒有交往,但只要有天然的血緣和地緣關(guān)系存在,就可以義務(wù)性地和復(fù)制性地確保他們之間的親密和信任關(guān)系。然而,對于失獨(dú)父母來講,失獨(dú)后,原本屬于強(qiáng)信任的親屬關(guān)系,也由于獨(dú)生子女的離開,而變
得“漸行漸遠(yuǎn)”。
材料一:我們跟我們的親戚當(dāng)中兄弟姐妹說實(shí)話也溝通不了,他們總是說他們的孩子怎么找到了好工作,怎么出國,怎么幸福之類,反正都是談的一些高興的事。我們聽到他們這些高興的事,心里就很不舒服,這其實(shí)就無意地傷害了我們。所以,一般情況下,我們都不會主動去聯(lián)系他們。(20101125SXR)②
材料二:盡管兄弟姐妹們,在我們孩子出了事之后,都會主動的來安慰我們,找我們聊天,但是說什么呢,無非是身體好不好,幾句話就完了,工作又談不上去,她做她的工作,我做我的工作,以前呢,更多的是在一起談?wù)労⒆?你談你的孩子,我談我的孩子,是吧,我們明顯地感覺到坐在一起,幾句寒暄的話說完了后,就沒有話說了,這是我們最大的問題。(20111104GSR)
從材料一中可以發(fā)現(xiàn),失獨(dú)父母常常會觸景生情——“看到人家的孩子,顧影自憐,想起自己的孩子,想起自己的處境”,從而把親屬的“幸福”當(dāng)成是勾起內(nèi)心的傷痛“刺激”,于是就選擇主動回避,以避免受到傷害。這樣孩子就成了失獨(dú)父母和親戚之間話題選擇中的“雷區(qū)”,這就出現(xiàn)了材料二中所描述的情形。因?yàn)楹⒆雍图彝ビ质俏辶畾q老齡人最主要的話題。然而,由于失獨(dú),他們和親屬要回避有關(guān)“孩子”、“死亡”之類的話題,從而失去了最主要的話題,因此失獨(dú)父母和親屬之間的交流也只能停留在寒暄的層次,問問對方身體怎么樣、吃飯情況、睡覺狀況、有沒有需要幫助,類似的話語和口氣,就連當(dāng)事人都覺得他們之間沒有話說,就如GSR告訴我們“說實(shí)話,說了兩三句,就不可能深入了”,往往形成一種“別扭”感覺。可見,失獨(dú)后,失獨(dú)父母和親屬之間共同話題消失,溝通頻次減少,溝通層次淺顯,這表明他們之前的關(guān)系由親密轉(zhuǎn)向疏遠(yuǎn)。
此外,失獨(dú)父母與虛擬親屬的關(guān)系也走向疏遠(yuǎn)。所謂虛擬親屬就是指模仿血緣關(guān)系或姻緣關(guān)系進(jìn)行交往而形成的社會親屬關(guān)系,主要包括“結(jié)拜兄弟”、“干親”等等,其也可以稱為“儀式性親屬”或“精神親屬”[11]193。這種“準(zhǔn)親屬關(guān)系”通常較親屬關(guān)系的信任程度要弱一些,穩(wěn)定性要差一些,在差序格局中虛擬親屬關(guān)系是靠近圓心的最內(nèi)層,是水波紋從內(nèi)向外得以推廣的第一媒介。除了親屬關(guān)系之間的信任外,虛擬親屬關(guān)系之間的信任感就是最強(qiáng)的。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虛擬親屬畢竟不是建立在血緣關(guān)系上的,因而這種疏遠(yuǎn)程度要大于其與親屬的疏遠(yuǎn)程度,其形成邏輯與親屬關(guān)系疏遠(yuǎn)的形成邏輯大致相當(dāng),所以筆者在這里就不再贅述。
(二)個人與非親屬、他組織的關(guān)系:斷裂
非親屬關(guān)系主要由地緣關(guān)系、業(yè)緣關(guān)系和趣緣關(guān)系構(gòu)成,這三種關(guān)系也可以依次簡化為“鄰里關(guān)系”、“同事關(guān)系”和“朋友關(guān)系”。需要說明的是,這些關(guān)系只被當(dāng)事人所認(rèn)可,卻未被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契約確認(rèn)和制度化,更多地體現(xiàn)了一種“自然結(jié)構(gòu)”[12]79;但是這種關(guān)系很重要,人們通常說“遠(yuǎn)親不如近鄰”、“同事關(guān)系是個人事業(yè)的催化劑”、“一生難得一知己”、“酒逢知己千杯少”等都是佐證。對失獨(dú)父母而言,由于獨(dú)生子女的死亡,這三種關(guān)系都趨向斷裂③。
材料三:同一個樓道上的同事,他們又都有個人的家庭,都幸福得不得了,這個娶媳婦,那個生孩子,放鞭炮什么的,我們兩個實(shí)在是受不了。……但是明顯這種交往不如以前,有種生怕別人另眼相待的感覺,怕別人瞧不起我們,認(rèn)為我們是“無后”之人。特別是怕和別人發(fā)生矛盾,一發(fā)生矛盾,有些不懂知識的人,跟你說你孩子都走了,你還這么壞,甚至有的人說,你這個斷子絕孫的人,你還搞什么搞呀,這對我們是極大的傷害。……最后我們也就都搬了家,我搬到現(xiàn)在這里來,我也不和別人打招呼,整天就低著個頭,進(jìn)進(jìn)出出,大多數(shù)是呆在家里,我看電視,他(SXR的丈夫)就成天“偷菜”(一種網(wǎng)絡(luò)QQ游戲)。(20111104GSR&SXR)
材料四:我是搞財務(wù)工作的,原來是單位的會計,孩子走后,人變得遲鈍,算不了賬,給人家找錢、報賬的時候,都給人家搞錯,幾千塊錢都搞錯了,后來只能提前退休。老公原來是單位的司機(jī),司機(jī)這種職業(yè),一分神,就容易出事,后來單位就給調(diào)配個工作。調(diào)換工作后,他還是受不了,完全無法與人溝通,一說話就嘴巴哆嗦,手也哆嗦,完全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做不了事情,最后也就退了休。(20101025SXR)
材料五:我原來是很喜歡唱歌跳舞的,自從我兒子走后,我就發(fā)誓,我再也不去唱歌了,晚上我再也不去跳舞了,很多以前的朋友叫我去,
我都拒絕了,因?yàn)槲矣X得,像我們這種人,就不應(yīng)該有快樂,我就成天把自己鎖起來,哪兒也不去。(20111105LML)
從材料三可以看出,失獨(dú)后,他們變得十分敏感,總是在想“如果不是自己的孩子走了,現(xiàn)在同樣也該考大學(xué)、找工作、結(jié)婚、生子了吧”,因此變得非常自卑,害怕因喪子被鄰居“另眼相待”,更怕因鄰里矛盾而被揭開“絕后”的傷痛,為了逃避,他們往往采取“搬家”或“自閉”的方式來緩解傷痛,從而地緣關(guān)系被迫阻斷。從材料四中可以發(fā)現(xiàn),失獨(dú)父母通過“提前退休”或“直接辭職”的方式,退出工作崗位,這就斬斷了他們的業(yè)緣關(guān)系維系的紐帶和機(jī)制,這表明失獨(dú)父母主動退出業(yè)緣關(guān)系。從材料五中可以發(fā)現(xiàn),受訪者所說“不再唱歌跳舞了”,表明失獨(dú)父母將自己的興趣愛好隱藏起來,不再按照興趣愛好行動,這就導(dǎo)致他們和趣緣關(guān)系成員聯(lián)系減少,互動頻次降低,久而久之,就導(dǎo)致他們的趣緣關(guān)系走向斷裂。一言以蔽之,由于獨(dú)生子女的死亡,失獨(dú)父母的地緣關(guān)系、業(yè)緣關(guān)系、趣緣關(guān)系都趨向斷裂,最終導(dǎo)致他們與非親屬的關(guān)系也幾乎走向斷裂。
此外,失獨(dú)父母與他組織④的關(guān)系也逐漸走向斷裂。就失獨(dú)父母而言,他組織主要是指社會上的經(jīng)濟(jì)組織(如企業(yè))、服務(wù)組織(如醫(yī)院)、福利組織(如養(yǎng)老院)、官方組織(如各級政府)、慈善組織(如志愿者協(xié)會)。這些組織的組織力并非來自于失獨(dú)父母,他們只是參與其中。正如費(fèi)老所言,中國傳統(tǒng)的社會關(guān)系是差序格局,而不是西方的團(tuán)體格局,個人堅持的是“自我主義”而不是“集體主義”,因此個人很難產(chǎn)生集體歸屬感和認(rèn)同感。對于失獨(dú)父母而言,更是如此。其原因有兩點(diǎn):一方面,獨(dú)生子女死亡后,失獨(dú)父母疏遠(yuǎn)了地緣關(guān)系、業(yè)緣關(guān)系和趣緣關(guān)系,而他組織關(guān)系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上述關(guān)系建立,因此說失獨(dú)父母與他組織關(guān)系走向斷裂;另一方面,獨(dú)生子女死亡改變了他們原來的訴求內(nèi)容(現(xiàn)在主要是精神慰藉),而這些都是他組織所無法兼顧到的,因此二者之間缺乏交集,這就加劇了相互疏遠(yuǎn)的步伐,最終導(dǎo)致失獨(dú)父母與他組織關(guān)系的斷裂。
(三)個人與自組織的關(guān)系:親密
“協(xié)同學(xué)”的創(chuàng)立者哈肯(H.Haken)提出了“自組織”的概念,他認(rèn)為自組織獲得空間、時間或功能的結(jié)構(gòu)過程中,沒有外界的特定干預(yù)[13]29。就是說,自組織不是依靠外部命令,而是依靠內(nèi)部的某種默契,成員之間合作形成的組織。失獨(dú)父母的自組織就是指在失獨(dú)父母精英引領(lǐng)和其他成員的協(xié)助下,為了搭建失獨(dú)父母交流溝通的平臺,減少失獨(dú)父母的傷痛,而成立的一種公益組織,我們簡稱為“失獨(dú)組織”。該組織具有“自發(fā)性、自組織性、排他性和團(tuán)隊(duì)化”的特征[14]。就武漢市而言,目前主要有“WXGW”、“LXJY”、“YWQQ”三家較大的失獨(dú)組織。
按照人們傳統(tǒng)的行為邏輯,個人對集體公共事務(wù)是漠不關(guān)心,而更加關(guān)心自己的私人事務(wù),因而在傳統(tǒng)理念中,個人不愿參與集體(組織)事務(wù),兩者之間是一種疏遠(yuǎn)的關(guān)系。就失獨(dú)父母而言,他們與失獨(dú)組織關(guān)系卻異常親密,甚至超越了與親屬的親密程度。這一方面是由于“失獨(dú)身份”是其共同的特征,他們對自己的認(rèn)知、理想、價值觀念等都會因?yàn)楠?dú)生子女死亡這一共性特征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從而產(chǎn)生較強(qiáng)的群體意識;另一方面,失獨(dú)組織慰藉效果好,責(zé)任感強(qiáng)。失獨(dú)組織以“跨越苦難,自助助人”為目標(biāo),其會員具有相同的經(jīng)歷、相似的命運(yùn),彼此擁有共同的話題、共同的情感,因而他們之間能夠相互慰藉,且慰藉效果好;同時,組織成員責(zé)任感強(qiáng),他們這樣認(rèn)為,“沉溺于痛苦中不如做點(diǎn)事,既自救也幫助別人”⑤。
材料六:王爹爹稱,他之所以要成立這個組織,源于自己痛失愛女。他說:“親人丟了,生活還要繼續(xù)。”他決定將后半生獻(xiàn)給所有和他有著同樣遭遇的不幸家庭,給他們送去溫暖。目前,與他結(jié)盟的7位志愿者骨干,均是失獨(dú)父母。該組織的辦公室設(shè)在漢口花橋街三眼橋三村社區(qū)的“WXY”,成立于2006年5月10日。活動經(jīng)費(fèi)均是志愿者自己出,不索取任何報酬。⑥
材料七:“這個地方來一趟,就離不了。”每來一個新成員,WAW總要跟他們相互傾訴:“每講一次,心里就輕松一些。她說,失去孩子的痛苦,只有經(jīng)歷過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在這里,大家可以一遍遍的講這樣的痛苦,沒有人會認(rèn)為你是祥林嫂。”⑦
通過上述材料可以發(fā)現(xiàn),失獨(dú)父母與失獨(dú)組織之間有著親密的關(guān)系,這是兩者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就失獨(dú)父母而言,一方面,他們的參與程度高,和在他組織中的“工作層次參與”相比,失獨(dú)父母參與失獨(dú)組織的頻率較高,且是一種深度參與,他們不是被
動的參與組織活動,而是主動參與,以主人翁的態(tài)度參與到組織的運(yùn)營管理活動中來(詳見材料六);另一方面,會員的組織依戀、共同經(jīng)歷使他們之間相互吸引和相互認(rèn)同,因此失獨(dú)父母普遍對自組織存在很強(qiáng)的依戀情結(jié)。正如材料六中的受訪者所說:“來這個地方一趟就離開不了。”就失獨(dú)組織而言,一方面,組織的精神慰藉效果好,這是因?yàn)樽越M織成員和組織的目標(biāo)對象都是失獨(dú)父母,同樣的人生經(jīng)歷、同樣的情緒體驗(yàn),使得自組織對失獨(dú)父母精神慰藉的效果超出其他任何組織;另一方面,組織的責(zé)任感強(qiáng),由于自組織是失獨(dú)父母自發(fā)組織的純公益性組織,組織成員沒有摻雜經(jīng)濟(jì)誘因,志愿將自己的余生奉獻(xiàn)給其他有著同樣不幸遭遇的組織成員,因此富有極強(qiáng)的責(zé)任感。正如材料七中的受訪者所說:“決定將后半生獻(xiàn)給所有和他有著同樣遭遇的不幸家庭,給他們送去溫暖。”由此可見,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失獨(dú)父母和組織之間建立并保持了親密的關(guān)系。
三 失獨(dú)父母的社會關(guān)系格局:非常態(tài)差序格局
獨(dú)生子女死亡后,失獨(dú)父母的社會關(guān)系發(fā)生更新和重組,并且這種重組的機(jī)制已經(jīng)和費(fèi)孝通時期發(fā)生了本質(zhì)的改變。
(一)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的更新和重組
論述至此,讀者可以發(fā)現(xiàn)獨(dú)生子女死亡后,失獨(dú)父母的社會關(guān)系大致可以分為三種變遷路徑,借用費(fèi)孝通先生社會關(guān)系同心圓結(jié)構(gòu)可以表示如圖1:

圖1.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變遷圖
首先,親屬關(guān)系和虛擬親屬關(guān)系向外推出。在一般社會關(guān)系的同心圓結(jié)構(gòu)中,親屬關(guān)系居于核心圈層,但是在獨(dú)生子女死亡后,失獨(dú)父母與親屬關(guān)系因?yàn)榉N種原因而逐漸疏遠(yuǎn),從社會關(guān)系同心圓結(jié)構(gòu)的核心圈層退讓到次外圈層,親屬關(guān)系不再是失獨(dú)父母最親密的關(guān)系;同時,虛擬親屬關(guān)系也出現(xiàn)一定程度的退讓。原本虛擬親屬關(guān)系居于同心圓結(jié)構(gòu)的中間圈層,但是獨(dú)生子女死亡后,已經(jīng)退出到次外圈層,處于距離中心點(diǎn)較遠(yuǎn)的位置。換句話說,對于中心點(diǎn)而言,虛擬親屬關(guān)系再也不是除了親屬關(guān)系之外最親密的關(guān)系類型,而是被邊緣化了。由于獨(dú)生子女死亡后,親屬關(guān)系和虛擬親屬關(guān)系具有同樣的變遷方向,因此筆者把這兩種關(guān)系類型放到一起,構(gòu)成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的一種流動趨向。
其次,非親屬關(guān)系和他組織關(guān)系從同心圓中結(jié)構(gòu)退出。在一般社會關(guān)系的同心圓結(jié)構(gòu)中,非親屬關(guān)系和他組織關(guān)系是居于外圍圈層,雖然居于外層,但中心點(diǎn)仍然和他們發(fā)生一定的聯(lián)系,然而獨(dú)生子女死亡后,失獨(dú)父母基本上斷絕了與非親屬和他組織的交往,也就是說這兩種關(guān)系幾乎退出了失獨(dú)父母的社會關(guān)系范圍。
最后,自組織作為新興組織躍入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的核心圈層。在原來的同心圓圈層結(jié)構(gòu)中,沒有自組織這一要素。這一要素是獨(dú)生子女死亡后,失獨(dú)父母自發(fā)建立的社會關(guān)系類型。從發(fā)展路徑來看,這一關(guān)系要素進(jìn)入社會關(guān)系的體系沒有遵循常規(guī)的路線,不是循序漸進(jìn)地從外圍圈層到中間圈層再到內(nèi)核圈層,而是直接躍入內(nèi)核圈層。這是因?yàn)槭И?dú)父母的自組織關(guān)系建立恰恰是發(fā)生在失獨(dú)父母自我認(rèn)同重構(gòu)、社會關(guān)系重組的關(guān)鍵時期,這期間他們對社會關(guān)系要素進(jìn)行重新認(rèn)識、重新排列,因此失獨(dú)父母的自組織關(guān)系在建立之初就能以極強(qiáng)親密的姿態(tài)占據(jù)其社會關(guān)系同心圓結(jié)構(gòu)的核心圈層。
總而言之,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的更新與重組向我們揭示了兩個事實(shí):一方面,原本十分親密的親屬關(guān)系(這里將虛擬親屬關(guān)系也看成是一種特殊的親屬關(guān)系),并沒有得到失獨(dú)父母的信任,而是逐漸淡出失獨(dú)父母的社會關(guān)系體系;另一方面,失獨(dú)父母的自組織得到他們的信任,而且在出現(xiàn)之初就進(jìn)入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核心圈層。
(二)變更和重組的內(nèi)在機(jī)制:社會身份
正如文章開篇所言,傳統(tǒng)差序格局運(yùn)行的內(nèi)在機(jī)制是血緣,而隨著社會的變遷,差序格局由傳統(tǒng)轉(zhuǎn)向現(xiàn)代,其運(yùn)行機(jī)制也演變?yōu)檠墶⒁鼍墶⒏星椤⒗娴纫氐慕徊娼M合,差序格局的關(guān)系選擇機(jī)制也由單一轉(zhuǎn)向復(fù)合。但是,就失獨(dú)父母的社會關(guān)系變遷而言,無論是傳統(tǒng)差序格局還是現(xiàn)代差序格局都無法很好的作出解釋⑧。因?yàn)槭И?dú)父母的社會關(guān)系格
局之所以能發(fā)生如此翻天覆地的變遷,恐怕是對關(guān)系選擇機(jī)制進(jìn)行添加所無法達(dá)到的,它所遵循的是一種特殊的機(jī)制——社會身份。
一方面,從社會關(guān)系吸引機(jī)制的角度講,“身份關(guān)系”主導(dǎo)差序格局。費(fèi)孝通先生認(rèn)為,傳統(tǒng)中國社會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是以“己”為中心,按照血緣關(guān)系的遠(yuǎn)近向外擴(kuò)展的親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jìn),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的確立,經(jīng)濟(jì)利益導(dǎo)向機(jī)制的形成,社會成員的利益觀念和行為得以展現(xiàn),社會關(guān)系在血緣差序上的遠(yuǎn)近實(shí)質(zhì)上演變?yōu)槔骊P(guān)系的遠(yuǎn)近。如折曉葉明確指出:“利益原則已經(jīng)成為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交往的一個重要砝碼”[15]339。
然而,對于失獨(dú)父母而言,獨(dú)生子女死亡后,失獨(dú)家庭社會關(guān)系的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劇烈的變化,很多失獨(dú)父母幾乎將“利益”剔除出他們的關(guān)系調(diào)適機(jī)制,并且弱化“血緣”關(guān)系調(diào)適機(jī)制,同時以強(qiáng)勁的方式引入“身份”關(guān)系調(diào)適機(jī)制。如有些失獨(dú)父母說,“我一般都是不攢錢”,“子女死亡后,我轉(zhuǎn)讓利潤高達(dá)數(shù)百萬的生意,賦閑在家,不再和以前生意上的朋友來往”等等,這些都是淡化人際關(guān)系中“利益”紐帶的表現(xiàn)。與此同時,他們和其他失獨(dú)父母建立新的聯(lián)系,并且在新關(guān)系建立的過程中,他們之間的經(jīng)濟(jì)地位被明顯弱化,失獨(dú)身份被得到強(qiáng)化,百萬富翁也可以與低保戶結(jié)為朋友,互述衷腸。這表明,“身份”已經(jīng)成了失獨(dú)家庭社會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的主要調(diào)適機(jī)制。
此外,他們也將傳統(tǒng)的血緣關(guān)系弱化。由上文失獨(dú)父母的社會關(guān)系的重組和更新可知,失獨(dú)父母(同命人)進(jìn)入他們差序格局的核心圈層,而親屬關(guān)系則退出核心圈層,被排擠到中間圈層,而非親屬和他組織在差序格局中則被繼續(xù)向外擠出,有時候甚至完全沒有被納入失獨(dú)父母的人際交往范圍。由此可見,獨(dú)生子女死亡后,失獨(dú)父母的社會關(guān)系調(diào)適機(jī)制已從“血緣+利益”轉(zhuǎn)向“身份為主,血緣為輔”。
另一方面,從互動對象選擇機(jī)制的角度講,失獨(dú)父母的社會認(rèn)同從“單位認(rèn)同”、“社區(qū)認(rèn)同”轉(zhuǎn)向“身份認(rèn)同”。社會認(rèn)同指的是“行動者對其群體資格或范疇資格積極的認(rèn)知評價、情感體驗(yàn)和價值承諾”[16]143-172。通過社會認(rèn)同,行動者把群體分為內(nèi)群體和外群體,并通過自我歸類(self-categorization)將自己歸于某一群體,然后內(nèi)化該群體的價值觀念,接受其行為規(guī)范。
社會認(rèn)同理論告訴我們,一般人的身份和資格都源于單位、社區(qū)和家庭,因此他們的認(rèn)同更多的是單位認(rèn)同、社區(qū)認(rèn)同、親屬認(rèn)同。然而,獨(dú)生子女死亡后,失獨(dú)父母獲得了新的身份——“失獨(dú)父母”,因此獲取了新的認(rèn)同,即“身份認(rèn)同”。同時,通過單位、社區(qū)、家庭與失獨(dú)父母之間的比較,他們發(fā)現(xiàn),和同命人之間可以更加自由的溝通,完成精神慰藉;相反,與單位中的同事、社區(qū)的鄰居、家族的親屬進(jìn)行溝通,要么會缺乏共同話題,要么會勾起自己的傷心往事,要么就是彼此都很敏感難以放開交流,正如失獨(dú)父母所說“(和親戚、同事、鄰居)感覺總是隔著一層”。綜上所述,失獨(dú)父母就認(rèn)為失獨(dú)父母屬于“內(nèi)群體”,而同事、鄰居和朋友就退出“內(nèi)群體”而變成“外群體”,這表明失獨(dú)父母的社會認(rèn)同從單位認(rèn)同、社區(qū)認(rèn)同、親屬認(rèn)同逐漸轉(zhuǎn)向“身份認(rèn)同”。
(三)實(shí)質(zhì):非常態(tài)差序格局
行文到這里,讀者可以發(fā)現(xiàn),獨(dú)生子女死亡后的失獨(dú)父母的人際關(guān)系格局不同于費(fèi)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差序格局。具體而言,失獨(dú)父母人機(jī)關(guān)系的選擇標(biāo)準(zhǔn)、要素構(gòu)成、分裂風(fēng)險等等都是該群體的獨(dú)有特征。正是基于這種考慮,筆者認(rèn)為失獨(dú)父母的社會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呈現(xiàn)“非常態(tài)差序格局”。
由上文分析可知,失獨(dú)父母的社會關(guān)系選擇標(biāo)準(zhǔn)已由“血緣”轉(zhuǎn)向“身份”。但這里尤其要說明的是,這里的身份實(shí)際上指的是“同命人”,不是傳統(tǒng)文化中的“身份等級”。傳統(tǒng)文化中的“身份”實(shí)際上是帶有一種等級意識;而這里的“身份”帶有的只是一種類別意識,因此不同于有些學(xué)者所講的“傳統(tǒng)差序格局仍將主導(dǎo)現(xiàn)代社會人際關(guān)系格局,社會將再度重返到身份等級主導(dǎo)的血緣、倫理格局”[17]。它不是遵循的傳統(tǒng)的差序格局,而是遵循的一種特殊的差序格局。
此外,這種特殊性還體現(xiàn)在失獨(dú)父母的社會關(guān)系格局的“要素構(gòu)成”中。在傳統(tǒng)差序格局中,首先遇到的是親屬關(guān)系,而后是擬親屬關(guān)系,最后是非親屬關(guān)系,這三種關(guān)系不僅構(gòu)成了中國社會關(guān)系的結(jié)構(gòu),而且在長期的互動中已經(jīng)達(dá)到相對平衡。但是,這種平衡是相對的,任何外力都可能打破這種平衡。對于失獨(dú)父母而言,這個外力就是獨(dú)生子女死亡,這個“大事件”打破了失獨(dú)家庭中原先的社會關(guān)系平衡機(jī)制,破壞了他們的社會交際圈。在失獨(dú)父母特殊的差序格局中,首先遇到的是自組織關(guān)系,而后是親屬關(guān)系和虛擬親屬關(guān)系,非親屬和他組織關(guān)系幾乎
中斷,其基本上退出了失獨(dú)家庭的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由此可見,獨(dú)生子女死亡后,失獨(dú)父母的社會關(guān)系要素出現(xiàn)顛覆和重組。
最后,這種特殊性還體現(xiàn)在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格局的“高風(fēng)險性”上,即存在斷裂的風(fēng)險。失獨(dú)父母在篩選交往對象時純粹遵循“二分法”,即是失獨(dú)父母,或者不是失獨(dú)父母,沒有第三種答案。這種簡單化的二分法會造成差序格局這個連續(xù)統(tǒng)的斷裂,即使失獨(dú)父母在社會關(guān)系選擇的時候并沒有完全放棄親屬標(biāo)準(zhǔn)和虛擬親屬標(biāo)準(zhǔn),但是這兩種標(biāo)準(zhǔn)的作用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低于身份標(biāo)準(zhǔn)。在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同心圓結(jié)構(gòu)圖中,我們可以將親屬關(guān)系和虛擬親屬關(guān)系命名為“過渡地帶”,研究發(fā)現(xiàn),這個過渡區(qū)不是與內(nèi)圈層和外圈層分類體系并列的層次,而只是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系統(tǒng)外圈層的子層次,所以筆者稱之為“次外圈層”。從這一點(diǎn)上看,失獨(dú)父母的人際關(guān)系系統(tǒng)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二分化的局面,即一邊是自組織成員,另一邊就是非親屬關(guān)系成員和他組織成員,簡單地說就是“內(nèi)核”和“外圍”的二分,沒有所謂的過渡地帶。由此可見,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中的差序格局出現(xiàn)斷裂的趨勢。
四 結(jié)論
費(fèi)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精準(zhǔn)地概括了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中的社會關(guān)系格局,這種格局是以血緣關(guān)系為互動邏輯,以道德人倫為實(shí)踐特征,并以“己”為中心而將社會關(guān)系向外推進(jìn)和延伸。但是,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jīng)濟(jì)的推進(jìn),我國社會關(guān)系也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學(xué)者們在“理論自覺”的過程中,立足于我國當(dāng)前社會的實(shí)際,進(jìn)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差序格局的內(nèi)涵,姻緣、感情、利益等新興要素全面滲透到差序格局中,特別是利益在人們社會關(guān)系選擇中的地位日益提升,這就突破了傳統(tǒng)差序格局以血緣為中心的單一的社會關(guān)系選擇機(jī)制,而是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復(fù)合化。這些理論的建構(gòu)結(jié)果都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了傳統(tǒng)差序格局的適用性,傳統(tǒng)差序格局出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轉(zhuǎn)向,逐步走向“工具化”和“理性化”。
無論是傳統(tǒng)差序格局還是現(xiàn)代差序格局都是立足于一般人群所建構(gòu)的一種“中層理論”,隨著社會學(xué)研究的“精細(xì)化”和“本土化”,很多特殊的弱勢群體逐漸進(jìn)入學(xué)者的研究視野,而對于這些群體,無論是傳統(tǒng)的差序格局還是現(xiàn)代的差序格局都無法很好地解釋他們在社會關(guān)系中的選擇行為,因?yàn)樗麄兊纳鐣P(guān)系互動既不是血緣主導(dǎo),也不是利益主導(dǎo),而是身份主導(dǎo)。
對失獨(dú)父母而言,獨(dú)生子女死亡后,他們原有的差序格局式的社會關(guān)系格局被打破,在其社會關(guān)系格局的同心圓結(jié)構(gòu)中,各要素的排列標(biāo)準(zhǔn)從親屬姻緣標(biāo)準(zhǔn)轉(zhuǎn)向社會身份標(biāo)準(zhǔn),原有的要素出現(xiàn)了更新和重組。但是,這一過程的主要依據(jù)是身份,因?yàn)樯矸葜挥惺腔虿皇莾煞N可能,因而這就純粹是“二分法”。這種區(qū)分方法會造成差序格局這個連續(xù)系統(tǒng)的斷裂。簡而言之,失獨(dú)父母的社會關(guān)系差序格局出現(xiàn)了選擇標(biāo)準(zhǔn)的更替、內(nèi)圈層的置換、重要要素的重組和差序格局的斷裂風(fēng)險,故而筆者稱之為非常態(tài)差序格局。
社會身份是人類自我概念社會化過程的產(chǎn)物,同時又是個體在情境中所獲得的一種意義,它可以較好地解釋行動者自我概念和社會行動選擇之間的觀念,它在社會關(guān)系分析中也具有獨(dú)特的作用路徑:一方面,社會身份通過社會行動影響社會關(guān)系;另一方面,社會身份直接影響社會關(guān)系。正因?yàn)槿绱?社會身份的分析路徑可以克服結(jié)構(gòu)主義和個人主義二元對立的局面。本文就是立足于嘗試運(yùn)用社會身份視角對失獨(dú)父母社會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的變遷進(jìn)行分析。對于失獨(dú)父母而言,失獨(dú)父母是他們的社會身份,他們就是在獨(dú)生子女死亡后形成了新的自我觀念,認(rèn)為自己是“苦命人”、“祥林嫂”[18],建構(gòu)出社會生活中與其他人的沖突和矛盾,從而主動調(diào)整和不同群體的交往策略,最后導(dǎo)致人際關(guān)系的“非常態(tài)變遷”。由此可見,社會關(guān)系的變遷脫離不了社會身份的影響,社會身份是分析社會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變遷的一個重要變量。
注釋:
①失獨(dú)父母指失去獨(dú)生子女的父母。根據(jù)計生部門的統(tǒng)計,本文中“失獨(dú)父母”需要具備四個條件:第一,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第二,女方年滿49周歲;第三,只生育一個子女或合法收養(yǎng)一個子女;第四,現(xiàn)無存活子女。據(jù)中國衛(wèi)生部發(fā)布的《2010中國衛(wèi)生統(tǒng)計年鑒》顯示,全國失去獨(dú)生子女的家庭已經(jīng)超過百萬,每年新增7.6萬個“失獨(dú)家庭”;人口學(xué)家預(yù)計,我國失獨(dú)家庭未來將達(dá)到一千萬,失獨(dú)父母將達(dá)到兩千萬。
②本文中收集的語音材料均來自于2010-2012年筆者完成湖北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委托課題《獨(dú)生子女死亡家庭扶助機(jī)制研究》和筆者博士論文調(diào)研中的訪談資料,訪談錄音的編碼方式為:20101025XXX,其中20101025代表時間,XXX代表受訪者姓名的首字母。
③這里的“斷裂”只是為了說明失獨(dú)父母與非親屬和他組織的關(guān)系變遷的一個整體趨勢,而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失獨(dú)父母與他們就沒有發(fā)生任何關(guān)系,事實(shí)上,他們之間也會發(fā)生一些聯(lián)系,只是從總體上講,這種聯(lián)系很少。
④他組織強(qiáng)調(diào)的是組織系統(tǒng)內(nèi)部各成員在系統(tǒng)外部力量強(qiáng)行驅(qū)使下所形成的一種組織結(jié)構(gòu)。簡言之,他組織是自上而下進(jìn)行的,具有某種強(qiáng)制性。
⑤資料來源:《星星港的故事》,載《瞭望東方周刊》2006年第37期,http://news.sina.com.cn/c/2006-09-08/20/47/0959926. shtml.
⑥資料來源:《武漢首現(xiàn)喪子安慰志愿者團(tuán)體》,新浪網(wǎng)2006年8月3日,http://news.sina.com.cn/s/2006-08-03/ 10359647332s.shtml。
⑦資料來源:《武漢誕生“溫馨苑”——孩子走了,他們相依前行》,載《楚天都市報》2006年6月13日。
⑧筆者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失獨(dú)父母群體是社會中的一個特殊群體,用特殊來論證一般肯定會犯簡單化論的錯誤;然而,需要交代的是,筆者并不想說明社會關(guān)系的整體性變遷趨勢,而是應(yīng)用“差序格局”這一理論工作來研究和分析這一特殊群體由于其特殊經(jīng)歷所發(fā)生的社會關(guān)系的新變化。
參考文獻(xiàn):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李沛良.論中國式社會學(xué)研究的關(guān)聯(lián)概念與命題[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3.
[3]林聚任.社會信任和社會資本重建:當(dāng)前鄉(xiāng)村社會關(guān)系研究[M].濟(jì)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
[4]徐曉軍.內(nèi)核—外圍: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的變動——以鄂東鄉(xiāng)村艾滋病人社會關(guān)系重構(gòu)為例[J].社會學(xué)研究,2009, (1):64-95.
[5]費(fèi)孝通.鄉(xiāng)土中國·生育制度·鄉(xiāng)土重建[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1.
[6]卜長莉.“差序格局”的理論詮釋及現(xiàn)代內(nèi)涵[J].社會學(xué)研究,2003,(1):21-29.
[7]任敏.現(xiàn)代社會的人際關(guān)系類型及其互動邏輯——試談“差序格局”模型的擴(kuò)展[J].華中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9, (2):50-56.
[8]翟學(xué)偉.中國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的平衡性問題:一項(xiàng)個案研究[J].社會學(xué)研究,1996,(3):78-87.
[9]楊善華,侯紅蕊.親屬,姻緣,親情與利益[J].寧夏社會科學(xué),1999,(6):51-58.
[10]〔美籍日人〕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chuàng)造經(jīng)濟(jì)繁榮[M].彭志華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11]王景海.中華禮儀全書[M].長春:長春出版社,1992.
[12]王詢.文化傳統(tǒng)與經(jīng)濟(jì)組織(修訂本)[M].大連:東北財經(jīng)大學(xué)出版社,2007.
[13]哈肯.信息與組織:復(fù)雜系統(tǒng)的宏觀方法[M].郭志安譯.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14]張必春,柳紅霞.失獨(dú)父母組織參與的困境、內(nèi)在邏輯及其破解之道——基于社會治理背景的思考[J].華中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14,(6):31-39.
[15]折曉葉.村莊的再造:一個“超級村莊”的社會變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7.
[16]方文.學(xué)科制度和社會認(rèn)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8.
[17]谷家榮.差序格局:從身份到理性——以廣西大瑤山下古陳村坳瑤人的婚姻為例[J].山東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 2007,(2):92-96.
[18]張必春,江立華.喪失獨(dú)生子女父母的三重困境及其扶助機(jī)制——以湖北省8市調(diào)查為例[J].人口與經(jīng)濟(jì),2012,(5):22-31.
[責(zé)任編輯:張 卉]
作者簡介:張必春(1982—),男,江蘇江都人,博士,華中師范大學(xué)政治學(xué)研究院講師、湖北城市社區(qū)建設(shè)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基層治理、邊緣人群治理研究;
基金項(xiàng)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xiàng)目“失獨(dú)父母邊緣化的內(nèi)在邏輯及其社會再融入的社會工作干預(yù)研究”(14CSH060);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青年基金項(xiàng)目“加速老齡化背景下身邊無子女老人的社會支持系統(tǒng)建設(shè)研究”(13YJC840048);中國博士后科學(xué)基金第七批特別資助(2014T70713)。
收稿日期:2015-03-20
中圖分類號:C913.9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0-5315(2015)05-006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