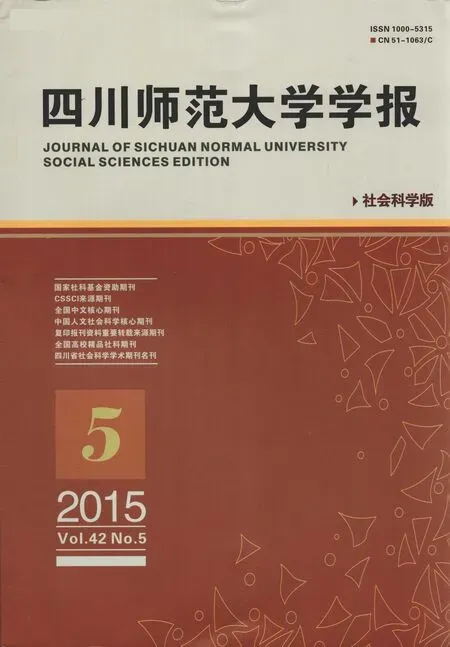古代小說語-圖互文現象初探——以插圖本《三國演義》為例
王 凌(1.西安工業大學人文學院,西安710021;2.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西安710062)
古代小說語-圖互文現象初探——以插圖本《三國演義》為例
王 凌1,2
(1.西安工業大學人文學院,西安710021;2.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西安710062)
摘要:明清小說插圖的繪圖者們熱衷于通過對最具“孕育性”頃刻的把握、特殊的時空分割方式以及獨具意蘊的靜態繡像描畫以達到最真實、準確再現文字信息的目的;而插圖對故事場景進行的帶有情感傾向的取舍、圖題的褒貶寄寓以及有意無意的圖、文不符現象,又表明繪畫者試圖對小說作出符合自身審美習慣解讀的努力。在插圖本小說中,文字與圖像之間呈現一種特殊的互動關系。明清以來各插圖本《三國演義》,正是明清插圖小說語-圖互文規律的代表。
關鍵詞:明清小說;語-圖互文;《三國演義》;小說插圖
一
在我國傳統文化之中,圖像與文字的關系密切,“圖”、“書”二字的正式結合在《史記》中已有表現,“左圖右史”、“左圖右文”是古代書籍早已采用的表現形式[1]132。有學者曾將我國插圖藝術的起源追溯至戰國秦漢的帛書插畫[2]17;而木刻版畫的出現,則一般以晚唐《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扉畫為開端①。具體到小說插圖,學界普遍認為唐代的佛教活動——“變相”對其產生了直接推動[3]93-105。胡士瑩先生認為,“變文中的圖畫,往往在故事情節關鍵處加以提示,圖,顯然是為了加強故事氣氛而展開”,表演者“指出某‘處’畫面讓觀眾看,同時開始將畫上的情景唱給觀眾聽,加深了觀眾的印象。這對話本中散文敘事之后,插入一些駢語和詩詞來描繪景物,是有直接影響的,而后世小說插圖的來源和意義,也可以從這里得到一些啟示”[4]34-35。文與圖的關系如此密切,只因在傳遞信息、表達情感、創造意境等方面各有優勢,二者結合方能讓讀者獲得最為豐富的閱讀體驗。自20世紀魯迅、鄭振鐸等學者開始關注文學插圖以來,學界對明清小說的插圖研究已經積累相當成績;不過,對傳統插圖研究多從我國版畫發展史或書籍出版印刷史角度展開②,集中從小說文本意義及接受視角切入插圖的研究還是相對晚近的事。西方敘事學、圖像學理論的引入為傳統小說研究帶來新的活力,“讀圖”作為近年流行起來的文化視野也推動了小說插圖研究的繁榮景象③。不過,我們對語言與圖像之間的相互作用所涉及的一個重要命題——互文性仍然所論不多④;有學者甚至認為“中
外學者幾乎都忽略了中國古代敘述中這一十分明顯而獨特的現象”,而這“不僅有違中國古代敘述的原初形式與閱讀交流狀況,而且也難以全面揭示中國古代敘述獨特的敘述原則與敘述風格”[5]。
程錫麟將互文性理論分為以熱奈特為代表的狹義互文觀和以克里斯蒂娃及羅蘭·巴特為代表的廣義互文觀,他認為,前者將互文性界定為一個文本與可以論證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之間的關系;后者則將互文性內涵擴展至任何文本與賦予該文本意義的知識、代碼和表意實踐之總和的關系,這些知識、代碼和表意實踐形成了一個潛力無限的網絡[6]。互文性涵蓋文本的意義生成與意義接受兩個維度,是文學研究中難以回避的理論話題。互文性理論否認文本邊界的存在,認為每個文本都向其它文本開放,作品意義的生成及解讀完全依賴于文本之間的相互作用。在這種泛文本化的互文視野中,“其它文本”既有可能是完全獨立于該作品之外的另一部具體作品,也可能是與作品有著密切聯系,甚至本身從屬于作品的特殊部分(如插圖)。插圖是畫家在忠于作品的思想內容基礎上進行的創作,是“用圖畫來表現文字所已經表白的一部分意思”的藝術[7]3,“是對文字的形象說明,能給讀者以清晰的形象概念,加深對文字的深刻理解”[8]234。盡管古代小說的文字文本與圖像文本出現各有早晚,但二者作為共時存在呈現給當代讀者卻是不爭的事實,語言敘事與圖像敘事之間相互參照、互為背景的特殊關系因此也就成為小說讀者了解作品的必然途徑。對于文學作品中文字與插圖之間的關系,熱奈特曾將其歸入“跨文本性”中的特殊類型——“副文本性”⑤。事實證明,作為插圖的副文本不僅能為閱讀“提供一種氛圍”,從而引導讀者的接受,而它本身也表現出對小說作品的獨特理解。文字與圖像之間究竟是“因文生圖”還是“以圖解文”?也許只有“互文”這一“中西結合”的特殊概念才足以囊括這種奇妙關系的全部所指。本文就以明清以來的插圖本《三國演義》為具體考察對象(《三國演義》的不同版本有不同名稱,在此為方便起見,故統一稱號),對古代小說中的語-圖互文現象作一嘗試性探討。
作為明清時期最重要的白話長篇之一,《三國演義》擁有該時期小說的典型文本呈現特點。明代出版業的繁榮曾對小說的創作、傳播造成巨大影響,二者之間形成良性互動,插圖本(繡像本)的出現便是出版商針對讀者趣味作出迅速反應的表現之一。萬歷年間的小說出版已達到“無書不插圖,無圖不精工”的程度[9]51。這些以營銷為直接目的的插圖本小說,不僅以其形象、直觀的優勢成功吸引了讀者眼球,還通過圖像的敘事、抒情功能從不同角度引導著后續讀者把握文字內容,同時也從另一側面向我們傳達了以繪圖者為代表的讀者群對作品的理解,成為我們了解小說接受情況的重要參考資料。《三國演義》的故事內容歷來深受大眾歡迎(從說書活動的繁榮即可見端倪),而出版商更希望迎合讀者口味來獲得更大利潤,因此在插圖上頗用心思,也就造成了大量插圖本存世的局面。現存插圖本《三國演義》中,葉逢春本(《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出現最早,該本采用常見的上圖下文版式,每頁一圖(現存1500余幅),內容詳盡;湯學士本(《新刻湯學士校正古本按鑒演義全像通俗三國志傳》)插圖形式與之類似,也是上圖下文;周曰校本(即萬卷樓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為雙面連式對葉大圖(每則一圖,存160幅),插圖標題書于右側,此外插圖左右各有圖題一句,根據圖中所題刻畫者姓名可知插圖屬金陵版畫。此外,李卓吾評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存圖200幅;英雄譜本(《二刻英雄譜》)為崇禎年間建陽雄飛館所刊,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合刻本,插圖形式為半葉大圖,共100幅,《三國演義》62幅。諸如此類,不可遍舉。
文字敘事依賴語言符號,讀者通過閱讀文字生發聯想與想象,在腦海中勾勒出故事情景,由此完成對作品的理解;而圖像敘事則具體可感,它通過線條、圖形、色彩等直接訴諸視覺,為讀者帶來感官體驗。萊辛在《拉奧孔》中論及詩與畫的界限,認為詩敘述的是“時間上先后承續的動作”,而畫則描繪“空間中并列的物體”[10]222。有學者因此指出,“圖像敘事是敘事媒介由時間藝術向空間藝術的轉變”[11]174。在表現故事時間性(或情節性)方面,文字敘事頗占優勢;而在表現故事的空間性上,圖像敘事亦擁有獨特方便。
以萬卷樓本《三國演義》圖16為例,該圖配合連環計王允謀董卓情節,繪圖者選取了最精彩的呂布戲貂蟬片段,插圖右側為仙鶴古樹掩映之下的董卓雙手扶冠,左側為呂布與貂蟬在亭中纏綿,畫戟被置于呂布身后,雙頁合并,畫面場景的空間感極強,兩個分鏡頭并置,呈現突出的戲劇性效果:太師入后園
之前先正衣冠,庶幾暗示其對貂蟬的用心;而貂蟬與呂布的私會則對此形成解構(見圖一[12]146-147)。

圖一
文字敘述遵循線性時序,先述呂布趁董卓與獻帝議事而入后堂尋貂蟬,后述貂蟬與呂布在鳳儀亭私會,再述董卓因不見呂布在側而生疑遂入園尋找。帶給讀者的是清晰的時間—因果線索。而插圖的優勢不在于交待故事發生的因果邏輯,而是通過對瞬間場景的捕捉為讀者呈現一個富于張力的意義世界。如果說直觀的自然環境畫面營造出的是撲面而來的現場感,那么人物微妙卻又復雜的神態表情卻傳達出無比豐富的內心世界,引發讀者的想象和思考。
二
小說插圖原為配合文字內容而來,表達的是“特定文本中的特定故事”[13],因此天生具有依附性。“因文生圖”也就成為古代小說語-圖互文關系中最基本的層次。明袁無涯《忠義水滸全書發凡》曾針對小說插圖有云:“此書曲盡情狀,已為寫生,而復益之以繪事,不幾贅乎?雖然,于琴見文,于墻見堯,幾人哉?是以云臺、凌煙之畫,《豳風》、《流民》之圖,能使觀者感奮悲思,神情如對,則象固不可以已也。”[14]可見,插圖的首要功能是配合文字內容,通過圖像的直觀性感染讀者。那么,如何有效地捕捉小說的文字信息,并將之以生動可感的畫面呈現,不同的繪圖者會作出不同的選擇。
(一)挑選“孕育性的頃刻”
在將文字敘述的時間藝術轉化為圖像符號的空間藝術過程中,繪圖者必須首先對內容作出選擇。萊辛指出,“(繪畫)藝術由于材料的限制,只能把它的全部摹仿局限于某一頃刻”,因為“最能產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讓想象自由活動的那一頃刻”[10]18。最富于“孕育性的頃刻”并非故事情節的高潮,而往往是事物到達高潮之前的某一瞬間,這是因為事物“到了頂點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遠的地方去看,想象就被捆住了翅膀”[10]19。而透過最富“孕育性的頃刻”,讀者則可以充分發揮想象,推測、認識事物的前后語境。



圖二
在眾多《三國》版本之中,插圖的密集程度各不相同。有每頁配圖者(稱“出相”),如采用上圖下文版式的葉逢春本每三百左右文字配合插圖一幅,密度極大。在鳳儀亭呂布戲貂蟬一段情節之中,單是呂布與貂蟬在太師府中相見情景,葉逢春本就配有三幅插圖:一幅繪貂蟬初入府中為呂布所窺(卷一圖58左:呂布于簾外偷望,梳妝中的貂蟬似有所覺,遂轉身做憂郁狀與呂布眼神互動);一幅為呂布與貂蟬在董卓榻前眉目傳情(卷一圖59右:呂布于董卓榻前張望,貂蟬則掀開帷帳一角與之迎合,嬌媚之態盡顯);一幅為呂布與貂蟬鳳儀亭幽會(卷一圖59左:呂布在亭邊右手執戟,左手似作推阻之勢,而貂蟬于亭內身體左傾,大有追扯呂布之勢)。三幅插圖皆著意摹仿和再現文字內容,且排列密集,故能相對完整
的表現故事情節,呈現出與連環畫類似的連貫動態效果(見圖二[15])。按小說所述,呂布擔心董卓發覺而急于離開鳳儀亭,而貂蟬則欲鞏固矛盾,故以柔情激怒呂布。貂蟬為離間董卓父子而表現出的心思細密,呂布惑于女色而應對的愚笨無謀,皆在這段文字中得以發揮。然而,插圖仍然無法復制人物之間的對話,它只能選取一個特殊的情景片段表現所有。第三幅插圖以呂布將去未去、欲留不得的瞬間為中心描述,人物的動作、神情成為刻畫重點。呂布的留戀之態表現了勇夫的好色單純,而貂蟬的挽留之舉卻暗示了殫精竭慮的謀略心機。圖像與文字在此表現出一種上下呼應、相與闡發的共存互動關系。同一情景在湯學士本中以呂布與貂蟬二人親熱攜手瞬間為構圖中心,雖可見呂布對貂蟬之迷戀,卻難見呂布之無謀與貂蟬之韜略(見圖三[16]83),在意蘊的豐富程度上與葉逢春本尚存差距。

圖三
萬卷樓本240幅雙面連式對頁大圖(稱“全圖”或“全相”[17]33),平均每圖配合萬字左右內容,其畫面所需承載的信息量更高,也就對繪圖者選擇和把握“孕育性頃刻”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說上圖下文版式插圖側重于幫助文化層次不高的讀者理解故事情節,其主要功能尚在敘事,那么整版插圖則除了敘事功能之外更具審美意味。以“長坂坡趙云救主”為例,插圖以趙云為護阿斗而與敵軍奮戰為中心:畫面一側趙云懷抱阿斗挺槍于戰馬之上,槍頭所及一人撲倒于戰馬上奄奄一息,一人已身首異處,另一人則頸部流血不止(見圖四[12]784-785)。該本插圖表現戰場景象多采用交戰雙方各一戰將對峙交手的構圖形式。人物周圍亦有刀劍林立、軍士混戰痕跡。該回文字從眾人誤會趙子龍投奔曹操敘起,至張飛掩護趙云撤離結束,環境涉及正面戰場及后方,場景甚廣。選擇怎樣的瞬間既能充分傳達戰爭信息又強調主人公的英勇形象,成為繪圖者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從細部觀察,插圖中趙云腰間佩劍,時機當在殺夏侯恩奪曹操“青釭”寶劍之后;又阿斗被趙云庇護在懷,當為晏明、張郃追趕趙云之時。其實,在此段混戰中,最驚險的瞬間發生在趙云為張郃追趕連人帶馬顛入土坑之時,紅光罩體的寶馬發揮神力從土坑中躍起方使趙云擺脫困境。插圖選擇了高潮發生的前段,使讀者既對故事發展有充分認識,又有后續的緊張情節可供聯想,頗具意味,而子龍的忠心護主與神勇難擋也在這一簡單的畫面中得以傳神表現。

圖四
(二)共時性敘事:時空場景的分割
古代小說在敘事視角選擇上習慣采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以此可居高臨下、事無巨細地講述情節發展的方方面面,對此前人論述已多。與這一特點頗相契合的是,我國古典繪畫藝術在構圖中也擅長使用所謂“散點透視”原則,即通過移動視點(或謂多視點)進行觀察,將各個不同立足點上觀察所得全部組織到畫面中來⑥。正因為這種與西方“焦點透視”不同的處理技巧,古人才能繪出如《清明上河圖》、《富春山居圖》之類的宏篇巨制。相對來說,“散點透視”不追求與描述對象的形似,而更求神韻與意境。這種傳統繪畫技巧自然影響到小說插圖的繪制,在時空表現形式上,既有對小說情景“一時一地”的反映,更有利用簡單的線條、山石、云團、屋宇等作為分割界線,以表現“同時異地”、“同地異時”以及“異地異時”的場景[18]。運用巧妙的處理技巧,就可輕易完成文字無法實現的共時性敘事,不能不說是圖像的神奇之處。當然,明清小說的插圖繪制也經歷了一個由簡單、樸拙到復雜、精致的過程。在早期上圖下文版式中,畫面空間窄仄,人物與景物多在同一高度,構圖效果極為平面化,敘事信息量有限,也難有意境可言⑦。但隨著插圖制作藝術的改良,尤其是
單頁或對頁大圖的出現,使得畫面空間開闊,畫工們更有條件合理安排構圖,除了通過對象的高低錯落營造立體效果之外,還可通過將不同場景進行濃縮和融合以增加敘事信息量,并配合文字內容創造特殊意境。
萬歷雙峰堂刊本《三國志傳評林》圖“周瑜喝斬曹公來使”將周瑜斬使的場景由“大帳”移至“船上”,目的就是為了將曹操遣使渡江送書與周瑜斬使兩個場景同時容納到畫面中來。崇禎雄飛館《英雄譜》本赤壁之戰一節插圖則囊括孔明借箭、蔣干中計、曹操賦詩以及闞澤詐降四個經典場景,時間、空間的跨度更大。清兩衡堂刊本《李笠翁批閱三國志》八十一回插圖中既有范疆、張達躡手躡腳進入張飛寢室的情景,亦有二人靠近張飛床前行刺的瞬間;一百五回插圖“魏拆長安承露盤”亦將馬鈞建議曹叡拆取承露盤與馬鈞帶領軍士于柏梁臺拆取銅人金盤兩個場景合二為一,皆是按照時間流動表現情節進程的實踐(見圖五[19]163,212)。這些插圖通過獨特技巧盡力體現時間和空間的延展性,其根本的目的仍是更加真實、傳神地再現文字信息的內容。

圖五
(三)自然環境、繡像的靜態表現
除以上所論動態色彩較強的出相、全相插圖之外,《三國》小說中還存有少量的靜態環境插圖,由于不表現具體情節,其主要功能不在敘事。如葉逢春本6卷第63圖(左)描繪“曹操御園”景致,畫中僅有神鹿、仙鶴及參天古樹等自然風物,全無人物,亦無情節信息可言,所配合的文字內容卻是許芝向曹操介紹管輅善卜之事(見圖六[15])。緊隨其后的六十四圖(左)亦繪曹操宮室殿宇之貌,文字內容卻仍敘管輅神算救人。這可能是因為管輅生平事跡內容繁多,又屬情節次敘述層,加之63圖(右)已繪許芝推薦管輅情景,畫工為避免重復才以自然景物作為描繪對象。當然也不排除繪圖者的個人喜好等因素。又“耿紀韋晃討曹操”一節,文字乃敘耿紀、韋晃二人飲酒密謀討操之事,插圖則配殿宇宮室嚴整之狀。庶幾因為單頁篇幅有限,文字敘述信息量較少,緊接此頁又有表現“耿紀、韋晃、偉德論操”之畫面,則此圖亦為避免重復所設?類似情形還出現在“曹兵殺主簿楊修”一節,前四圖分別對楊修猜中曹操“雞肋”之意、楊修命軍士做撤退準備以及楊修破解曹操“門活而闊”之謎題進行了刻畫,第五幅插圖(6卷89圖左)則僅繪曹操駐兵之地斜谷溪山之自然風貌。不過,將這山峰、松樹所構成的清冷之境置于楊修之死的文字之側,是否也暗示了畫工對楊修命運的些許悲傷與惋惜?此外,還有4卷圖49(左)、圖56(左)等也屬類似情形。這類景物插圖一般多出現在圖像密集的版本之中,從整體上來看也能起到調節和舒緩敘事節奏的作用。

圖六
人物繡像插圖(主要人物肖像)多在小說正文之前或之后集中出現,此類作品在清代大量涌現,如清光緒年間刊印的《增像全圖三國演義》、《三國演義圖畫》等,書中皆有近百個人物繡像。與一般情節性插圖不同,繡像插圖的敘事功能下降,有時甚至連人物所處的環境背景也被省略,僅凸顯人物的服飾裝扮、樣貌體態。有學者認為,繡像插圖的大量出現,實際是出版商節省出版成本的結果。因為插圖雖能招徠顧客,但畢竟耗費成本,而人物在插圖中又無論如何不能省略,于是只好獨存人物要素,“謀求最小限度上‘俱全’的插圖本”[20]47。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繡像插圖的大興實則是版畫發展走向低潮的表現。繡像在表現人物時具有“類型化”特征,人物容貌神態多有雷同,能使形象之間區別開來的重要標示是衣著武器等外在裝備,畫工一般會依據小說的描述選擇最能代表人物特征的裝束表情,或者根據經典場景為人物安排動作。如在清貫華堂《四大奇書第一
種》、光緒桐蔭館刊本《三國畫像》以及光緒同文書局《增像三國演義全圖》中,孫夫人都是一身戎裝、手執寶劍造型,以此對應小說對其颯爽英姿的描述。而個性迥異的糜夫人在《三國》畫像中則多是懷抱阿斗的慈母之態(如貫華堂本、光緒同文書局本等),顯然是針對她舍身護子的犧牲之舉。這類插圖雖然其本身的藝術成就有限,卻能直觀地反映小說人物在當時的接受情況,具有一定的文學研究價值。
三
小說插圖雖力圖對文字信息進行全面的模仿再現,但兩種不同藝術形式在轉換中仍不可避免地出現信息的遺漏、溢出或錯位等情況,這正是學者所指出的圖-文轉化過程中不可忽略的意義“縫隙”[21],實則也是語-圖互文關系中的另一層面。這種“縫隙”很大程度由繪畫者主體意識所致——插圖是經過繪圖者主觀視角過濾的小說信息,是繪圖者首先作為普通讀者對小說進行個體解讀的結果,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插圖是對小說文本的二度創作。這種二度創作對后期小說讀者能產生直接影響,插圖在此就對原始小說文本形成了一種反向互動。
(一)場景選擇與審美取向
陳平原先生曾認為,“(小說插圖)的功能并非只是便于民眾接受;選擇什么場面、突出哪些重點、怎樣構圖、如何刻畫等,其實隱含著制作者的道德及審美判斷”[22]136。繪圖者的主觀意識決定了插圖的價值取向及審美風格,我們可從不同階段的《三國》小說插圖中得到印證。
以對曹操形象的表現為例,葉逢春本插圖總是選擇對人物有利的觀察視角或場景瞬間進行描繪,即便作品內容對曹操有明顯的貶斥之處,繪圖者也會避重就輕。比如針對曹操殺呂伯奢情節,繪圖者故意將表現時機安排在“曹操陳宮見呂伯奢”瞬間,將曹操行兇的場景輕輕抹去(見圖七[15])。又小說曾述曹操征討袁術過程中下令軍士不得踐踏麥田,百姓因此感戴之事,雖然在作品中只是一筆帶過的簡單敘述,但在插圖中卻得以大力表現:曹操等一眾軍馬行過,百姓虔誠跪拜,感戴之情流露于神色舉止之中,插圖題曰“百姓感激曹操遮道拜送”,更強化了曹操受百姓愛戴的仁主形象。又陳宮被殺情節之側小說配圖,一為“曹操差使討陳宮家小”,一為“陳宮父母見曹操”,皆為表現曹操寬仁之心。與葉逢春本情況不同的是,湯學士本插圖對曹操的態度就沒有如此寬容,殺害呂伯奢的血腥場面就得以強調和特寫:曹操拔出的長劍尚未回鞘,呂伯奢已身首異處(見圖八[16]40)。這樣的描繪雖與文字內容略有出入,但卻恰好透露了繪圖者有意表現曹操兇殘之用心。更有意味的是畫面中僅有曹操和呂伯奢而不見陳宮,顯然出于對這位不屑與曹操為伍者的維護。此外,周曰校本插圖也對曹操許田射鹿、重勘吉平、縊死董妃、杖殺伏后等場面進行了正面特寫(尤其是對吉平、董妃、伏后臨刑之際血肉模糊慘狀的刻畫足令觀者動容),貶斥之意自不待言。有學者將各本插圖對曹操的表現進行對比,指出葉逢春本插圖對曹操的態度是維護和美化,而誠德堂本插圖對曹操不褒不貶,雙峰堂及明后期各刊本插圖則極盡指責與批評[23]。這也可見不同時期讀者對小說人物的看法和態度。

圖七
如果說對曹操形象的不同描畫反映的是繪畫者們并不一致的價值取向,那么對“龐統理縣事”情節的不同表現則告訴我們繪圖者們還擁有各自不同的觀察視角和審美習慣。針對這一內容,葉逢春本、周曰校本、李漁評本(兩衡堂刊本)等插圖皆以龐統審案現場為表現重點:堂上正中坐龐統,旁坐張飛、孫乾,堂下跪二至三名涉案人員,另有衙役伺候在側。畫面表現出典型的明清公案風格,繪圖者將小說對人物才能的籠統描寫具體場景化,試圖通過一個特定案件的庭審現場再現龐統的過人才智⑧。不過,與其他各本正面表現龐統才能不同的是,在湯學
士本中,此段情節所配合的插圖卻是“張翼德怒責龐士元”,顯然是以先抑后揚的方法從側面反襯人物的才智。湯學士本的這一處理方式不僅不會讓讀者感到意猶未盡,相反表現出更多的戲劇意味。因為緊連于此的前兩幅插圖分別表現的是龐統在孫權處遭冷遇以及在玄德處遭疏遠,再加上在張飛處遭責罵,恰好形成一個小小的沖突高潮,為接下來的情節逆轉做好了充足的鋪墊。除繪圖者本身的價值取向、審美習慣之外,時代風尚也對小說插圖的繪制產生一定影響。如有學者研究發現,明中期之后的小說插圖在構圖形象上表現出對園林文化的熱衷、對人居環境的關注等特點,而這都與當時社會風尚的浸潤不無關系⑨。總之,不同風格的插圖代表了不同時代的《三國》解讀視角和審美取向,插圖不僅是小說文字內容的鏡像反映,更是繪圖者在解讀文本基礎上的二次創作。
(二)圖題的褒貶寄寓
圖像之側用簡短文字對畫面內容進行概括介紹或補充說明,是白話小說插圖的另一重要特點,如“孔明百箭射張郃”、“孔明出師”、“將星墜孔明營”(見《全相平話三國志》)等。圖題雖以文字形式表現,但直接配合畫面而來,仍屬插圖范疇。圖題由產生之初的四字短語或五字、七字單句,發展至整齊的雙句對偶,經歷了一個緩慢過程。相對而言,短語或單句圖題的敘事功能較突出,而對偶詩句則更偏重于意境、氛圍的渲染。圖題的發展促成了章回小說回目的形成,在章回小說文體成熟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此已有學者進行深入討論[24]。圖題之間的關系復雜:一方面,插圖的直接目的是為方便讀者理解作品,以直觀的空間形象訴諸讀者視覺,使其通過不同的感觀體驗在瞬間了解故事信息;但另一方面,插圖本身也可能存在“圖不達意”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插圖在表現時間過程上受到諸多限制所致),事實也證明確有許多小說插圖離開圖題而令人費解⑩。這也就是說,插圖的表意功能并不一定超越文字,它有時仍需文字對其進行直觀的意義補充或說明。如此一來,小說語—圖之間就絕非簡單的誰影響誰,誰解讀誰,而更多是彼此依存、相互參照或互為補充的特殊互動。

圖九
早期圖題比較強調敘事功能,其主要目的僅限于為插圖提供信息補充,而字數的限制也妨礙了繪圖者主觀意識的表達。隨著圖題的表現趨于自由(比如周曰校本圖題內容就發展為兩大部分:一是概括小說內容信息的單句,二是表現繪圖者針對情節所作褒貶評價或感慨的對偶詩句),繪圖者主觀意識的傳達也就更加靈活方便。如周曰校本“呂子明智取荊州”插圖,圖題“計出陰謀犬吠雞鳴非將帥,兵行詭道獐頭鼠耳豈男兒”(見圖九[12]1414-1415),明白透露著繪圖者對東吳白衣渡江軍事行動的不滿。其實,亂世之中戰爭的正義與否本來就很難界定,兵不厭詐簡直就是各軍事集團為求生存所應具備的基本素質,更何況當初劉備奪荊州同樣也是諸葛亮的智謀巧取,繪圖者在此若不是出于對關羽之死的惋惜而遷怒于東吳驕兵之計的制定者,又何至于厚此薄彼?盡管關公的大意輕敵才是呂蒙與陸遜計劃成功的關鍵,然而關羽形象在民間已成為神化的偶像,繪圖者作為一般小說讀者只能通過自己獨特的方式表達對于英雄的追念與嘆息。又如“董卓議立陳留王”一圖,畫面僅列舉董卓等人席間飲酒交談的場景,讀者本來難以窺見繪圖者的主觀意圖,但加上“輕議立君建極殿前云氣慘,妄謀廢主溫明園內鳥聲凄”的圖題,讀者便能很強烈地感受到繪圖者對王室衰微的同情、感慨,以及對董卓悖行逆失的憤怒、譴責[25]。與周曰校本情況不同的是,上圖下文版式的湯學士本圖題形式古拙、重于敘事,在褒貶寄寓上表現得較為客觀和含蓄。同是針對呂蒙、陸遜計取荊州畫面,其分別題為“孫權封呂布為都督”、“呂蒙用白衣人搖櫓”、“荊州百姓迎接呂蒙”等。這些圖題并未表現出對失敗英雄的惋惜留戀,從敘述語氣來看似乎還流露出對呂蒙妙計的默默贊許。圖題經過發展逐漸與小說回目合一,也是白話小說版本發展中的重要現象[24]。清兩衡堂刊本《李笠翁批閱三國志》的圖題
除在個別字詞上與回目略有出入之外,基本與回目一致;而文英堂刊本圖題則完全取回目上半句。以上兩個版本皆屬毛本系統,毛氏父子極力提倡擁劉反曹的立場,經其修改的回目用于圖題,進一步豐富了插圖的褒貶寄寓。
(三)圖文不符的背后
插圖的最初目的既然是“用圖畫來表現文字所已經表白的一部分的意思”[7]3,那么首先應該忠實地傳達作品內容。但兩種不同的表意符號各有擅長,在轉化過程中無法完全做到一一對應;又或者是繪圖者認識、理解能力有限,甚至是繪圖者的某種主觀愿望,都容易造成局部的圖文不符。有學者甚至指出“圖像敘述的圖形變形程度越大,其表現的敘述主體意圖就會越明顯”[26]。這些特殊的圖文不符現象,反映的也許是繪圖者對小說文本的某種“誤讀”,但也可能對后續讀者產生某些“歪打正著”的影響。小說文本中的圖文不符,主要存在以下幾種情況。
其一,人物的更改。如葉逢春本卷四圖47(右)“孔明見孫權以問曹操事”,描繪孔明與孫權對坐商議、魯肅等人侍立在側場景,但實際該圖對應的文字內容卻是魯肅勸說孫權聯合劉備以抗曹操,插圖將文字內容中的關鍵人物魯肅改換為孔明;而緊接于此的“孫權與孔明同行誠問智略”插圖,其對應文字內容則為張昭言挑孔明,插圖將主要人物張昭改換為孫權,亦與小說內容不符。可能是繪圖者意識到孫權與孔明在決定戰、和問題上的關鍵作用,因此將二人之間的互動作為構圖中心反復表現。這一更改看似無意,卻能對讀者造成一種閱讀導向,加深其對情節重點的理解。當然也不排除有的更改是繪圖者的粗率大意所致。如葉逢春本四卷圖3(左)題為“玄德問牧童臥龍何往”,畫面中卻顯示中年農夫;又四卷圖18(右)“張顧欲殺甘寧,孫權自休”,改凌統為張顧,是很明顯的理解錯誤。若不仔細閱讀原文,讀者也可能被插圖的直觀印象所誤導。
其二,場所的變換。多屬繪圖者的有意為之,往往能反映其獨特的敘事習慣及審美取向。如周曰校本將關云長刮骨療毒的場所由帳中改為亭閣間,初看似無意,細較之下我們就會發現這實際是周曰校本插圖普遍重視環境描繪,并追求室內裝飾的審美習慣所致。相比早期上圖下文版式中插圖的狹窄局促,周曰校本的雙面對頁大圖顯然為繪圖者提供了更多發揮的空間,而繪圖者趨于精細化的創作態度和審美追求也成為該本插圖重視場景氛圍的直接因素。此外,還有的場景更換是為了整合敘事信息。如雙峰堂本《三國志傳評林》將“周瑜喝斬曹公來使”的發生地從帳中移于船上,目的是將兩個情節片段(曹操遣使渡江與周瑜斬使)同時容納于畫面,也是繪圖者為發揮圖像的共時敘述功能而采取的特殊手段。對此上文已有分析,此不贅論。
其三,時序的錯亂。如葉逢春本卷五圖1(左)表現“孔明令魯肅造七星壇”景象,而實際對應文字內容卻是周瑜因顧慮火攻無法實施而吐血犯病,孔明造七星壇祭風情節當在后兩頁位置,插圖將敘述時序進行了調整。而此前的圖1(右)“周郎山頂觀風”則直接承接上卷“曹兵被風吹折旗幟”而來,是典型的延遲敘述。兩幅插圖一緩一快拉長了讀者對情節的體驗過程,同時也強調了東風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實際是為諸葛亮的多智形象進行渲染。又熊佛貴刊本“關羽獨行千里”插圖繪關羽騎馬荷刀造型,實際當為前兩頁內容,也是典型的插圖預敘。
其四,細節的錯漏。如葉逢春本五卷圖74(左)表現“韓遂與曹操敘舊”場景,畫面中二人對面站立交談甚歡,身后則有貼身侍衛牽馬等候。插圖看似正常,實則背離了小說原意。按小說所敘,曹操特意邀請韓遂“輕衣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語”,只有在馬上的位置、距離,才最適合曹操對韓遂進行各種含糊的問候,而旁無他人的私密性更足以引起馬超的疑心。插圖將情節原意按個人理解直觀化,卻在最關鍵的細節上出現了漏洞。又卷一圖75(右)繪“李相求見孔融”,實際文字內容卻敘孔融求見李膺,且孔融此時年僅十四,不應是圖中所示中年模樣。這應當為繪圖者大意所致。這些錯漏說明繪圖者對小說作品的理解是有限的,而插圖也確實無法做到與文字敘述完全同步。
“因文生圖”反映的是插圖對小說文字文本的直觀再現,是同一內容在兩種符號之間的轉換,在這個維度上,插圖是文字直接作用的結果,處于被動地位。在形形色色的《三國演義》插圖中,繪圖者們通過挑選“孕育性頃刻”、特殊的時空分割方式以及頗具意蘊的靜態繡像描畫,試圖達到最真實、準確再現文字內容的目的。“以圖解文”則指向插圖對文字文本的主觀解讀,插圖既反映小說在畫工群體中的接受情況,同時也對后續讀者產生引導,進而影響小說在更大范圍內的接受和傳播,因此,它又具有某種主
體性。從插圖表現出的對故事場景的挑選取舍、插圖圖題的褒貶寄寓以及有意無意中流露的圖文不符等現象中,我們也感受到小說插圖繪制者試圖對文字文本作出自身解讀的努力。本文雖僅以明清以來插圖本《三國演義》為重點關注對象,但根本的目的卻是以此切入明清插圖小說的整體規律。
注釋:
①但鄭振鐸先生則認為該畫“是相當成熟時期的作品,決不是第一幅的作品”,版畫出現的時間應該更早。對此學界尚無確論。參見: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上海書店2010年版,第12頁。
②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阿英《中國連環圖畫史話》(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版),以及線裝書局《古本小說版畫圖錄》(1996年版)等皆屬此類。
③新世紀以來涉及古代小說圖像主題的專業論文不下百篇,宋莉華《插圖與明清小說的閱讀與傳播》(《文學遺產》2000年第4 期)、汪燕崗《古代小說插圖方式之演變及意義》(《學術研究》2007年第10期)、程國賦《論明代通俗小說插圖的功用》(《文學評論》2009年第3期)、陸濤《圖像與敘事——關于古代小說插圖的敘事學考察》(《內蒙古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劉文玉等《圖像時代下的中國古代插圖研究》(《廊坊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等可為代表,其中又以顏彥《中國古代四大名著插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及金秀玹《明清小說插圖研究》(北京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論述最為系統。
④直接以語-圖互文現象切入明清小說研究的論文不足十篇,代表作有張玉勤《論明清小說插圖中的語-圖互文現象》(《明清小說研究》2010年第1期)、陸濤等《明清小說插圖的現代闡釋——基于語圖互文的視角》(《集美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明清小說出版中的語-圖互文現象》(《魯東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等。除陳平原《看圖說書——小說繡像閱讀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對古代小說語-圖關系有所論述之外,目前尚無此方面專著。
⑤熱奈特認為副文本性是指“一部文學作品所構成的整體中正文與只能稱作它的‘副文本’部分所維持的關系組成,這種關系一般來說不很清晰,距離更遠一些,副文本如標題、副標題、互聯性標題;前言、跋、告讀者、前邊的話等;插圖;請予刊登類插頁、磁帶、護封以及其他許多附屬標志,包括作者親筆留下的或是他人留下的標志,他們為文本提供了一種(變化的)氛圍”。參見:〔法〕熱拉爾·熱奈特《熱奈特論文選·隱跡稿本》,史忠義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頁。
⑥“散點透視”與“焦點透視”是兩種繪畫結構方式,前者是指“在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視點狀態下,人們對景物的綜合透視觀察方法和表現方法,也稱多點透視。它是相對于一個視點的焦點透視而言的”。參見:李峰《中國畫構圖法》,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
⑦但也有例外情況,如《三分事略》圖24表現督郵問責劉備太守被殺之事,盡管畫面狹長逼仄,但仍用線條分隔出兩個空間,同時表現室內和室外情景。《三國志平話》沿襲《三分事略》,插圖亦與此同。
⑧在1994年拍攝的《三國演義》電視劇中,龐統理縣事也通過一個具體的審案過程加以表現(借用民間流傳的包公審案故事),可見將文字概述轉化為具體情節,是插圖和影視改編藝術中比較通用的處理技巧。對此筆者已另撰《<三國志演義>影視改編的互文性策略》(《西安工業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一文進行說明,此不贅述。
⑨顏彥認為,《三國演義》早期上圖下文式插圖,“往往以微觀寫實的手法再現戰爭中身首異處的暴戾場面,體現戰爭的血腥性與殘忍性,而對戰爭以外的生活常態的描繪則大而化之。發展到單頁大圖,圖像在描繪戰爭場面的同時,亦對人居環境的刻畫給予了極大關注”。參見:顏彥《明清小說中的社會風尚影響——小說文本中插圖形象的演變解讀》,《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⑩比如葉逢春本卷四圖63(右)表現周瑜與劉備對坐、云長侍立在側的場景,配合的是周瑜設鴻門宴欲殺劉備,但因顧慮云長而最終取消暗殺計劃的情節。插圖雖對三個重要人物皆有描繪,但本應特加強調的人物表情卻表現平平,三人神情淡定且非常雷同,根本談不上反映各人暗自盤算的復雜心理。這種插圖的表現效果顯然不夠精彩,但加上“周郎欲害玄德,云長輔佐莫能”的圖題,就相當于將讀者無法從畫面中一眼獲知的情節信息以另一種更加直接的方式補充傳達出來,及時彌補了插圖的不足。
參考文獻:
[1]程國賦.論明代通俗小說插圖的作用[J].文學評論,2009,(3).
[2]祝重壽.中國插圖藝術史話[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3]〔美〕梅維桓.唐代變文[M].楊繼東,陳引馳譯.北京:中國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4]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M].北京:中華書局,1980.
[5]于德山.中國圖像敘述學:邏輯起點及其意義方法[J].社會科學戰線,2004,(1).
[6]程錫麟.互文性理論概述[J].外國文學,1996,(1).
[7]鄭爾康.鄭振鐸藝術考古文集·插圖之話[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8]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9]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M].上海:上海書店,2010.
[10]〔德〕萊辛.拉奧孔[M].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11]陸濤.圖像與敘事——關于古代小說插圖的敘事學考察[J].內蒙古社會科學,2011,(6).
[12]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G]//古本小說集成.影萬卷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3]王遜.論明清小說插圖的“從屬性”與“獨立性”[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6).
[14]《李卓吾批評忠義水滸傳全書》[G]//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影袁無涯刻本.臺北:天一出版社,1974.
[15]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史傳[M].影西班牙皇家修道院本(葉逢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6]羅貫中.《三國志傳》[G]//古本小說集成.影湯學士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7]魯迅.連環圖畫瑣談[M]//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18]顏彥.明清小說插圖敘事的時空表現圖式[J].中國文化研究,2011,(春之卷).
[19]李笠翁批閱三國志[M]//李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20]金秀玹.明清小說插圖研究[D].北京:北京大學,2013.
[21]張玉勤.“語—圖”互仿中的圖文縫隙[J].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
[22]陳平原.看圖說書:小說繡像閱讀札記[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23]張玉梅,張祝平.明代《三國》版畫對曹操的褒與貶[J].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11,(6).
[24]李小龍.試論中國古典小說回目與圖題之關系[J].文學遺產,2010,(6).
[25]胡小梅.論周曰校本《三國志演義》插圖的情感傾向[J].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
[責任編輯:唐 普]
[26]于德山.“語—圖”互文之中敘述主體的生成及其特征[J].求是學刊,2004,(1).
Preliminary Study on Text-Image Intertextuality of Ancient Novels:Taking the Illustrated Edition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s an Example
WANG Ling1,2
(1.School of Humanities,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021;
2.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062,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illustrations in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drawers are found to re-appear text information through holding a moment,special spatio—temporal segmentation, and painting static tapestry portrait.Their choice of story scenes for illustrations,judgments on images and titles,and intentional or unintentional discrepancies between illustrations and texts all demonstrate drawers’efforts to interpre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ovel with their own aesthetic habits.Novels’illustrated editions present a special kind of interaction between words and pictures.Illustrated editions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 gdom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perfect examples of text-image intertextuality of illustrated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ext-image intertextuality;Romance of the Three Kin gdoms;Illustrations
作者簡介:王凌(1980—),女,湖南常德人,文學博士,西安工業大學人文學院講師,陜西師范大學古代文學博士后流動站博士后研究人員。
基金項目: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明清小說互文性研究的專題分析與體系構建研究”(15XZW013);2015年度陜西省教育廳專項基金項目“互文性視閾下明清奇書小說文本與接受研究”(15JK1359)。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5315(2015)05-0153-10
收稿日期:2014-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