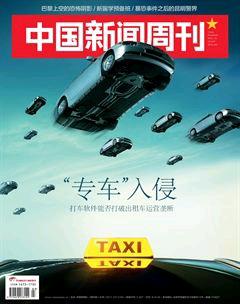伊春“小社區、大社會”
王全寶+王曉丹+解培華

(資料圖片)王愛文。圖/CFP
伊春市偏居黑龍江省東北部,與俄羅斯隔江相望。這個城市有世界上面積最大的紅松原始林,號稱“天然氧吧”,被譽為“祖國林都”。
近年來,社會管理創新成為一項重要的改革。從三年前開始,伊春市就開始了社區治理改革的探索。作為林區,社會管理問題與其他地區既有共性也有差異。王愛文發現,街道辦事處作為區級政府的派出機構,充當了區政府和社區之間“二傳手”的角色,職能定位不明確、機構臃腫、辦事效率低。于是,如何有效解決人浮于事、脫離群眾、重管理輕服務等諸多問題,擺在了伊春市委書記王愛文的案頭。
2005年3月,王愛文由原勞動保障部規劃財務司司長調任黑龍江省委政法委副書記。2008年,他又調往伊春市,先后任職市長、林管局局長。2011年6月30日,王愛文出任中共伊春市委書記。
中國新聞周刊:伊春市探索建立新型社區治理模式引起社會關注,請介紹一下社區改革的背景?
王愛文:可以說,伊春市社區治理改革與整體社會結構變革是緊密聯系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越來越多的“單位人”變成“社會人”,原有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已不能完全適應群眾日益多樣化的訴求,原有的社會治理體制已經不能適應當前復雜的形勢,改革勢在必行。
特別是近年來,黨和政府惠及人民群眾的政策越來越多,而人民群眾的“主體意識、民主意識、自我管理意識”日益增強,如果不選好的機制去解決利民惠民政策分配問題,就會產生新的分配不公,將好事辦壞,引發新的不穩定因素。
中國新聞周刊:伊春市新型社區治理模式具體內容是什么?
王愛文:伊春市市轄區15個區、(局)全面開展了社區管理體制改革。市轄區內30個街道辦事處全部予以撤銷。以每個社區2000戶至3000戶為標準,將原有155個社區整合為102個,以每個網格100至200戶居民為標準,重新劃分居民網格2372個。
改革之初,我們就要求將“民事民管、民政民理、民利民定”定為改革的核心。我們創新了社區民主自治新模式,建立了《社區居民代表選舉制度》,居民代表由社區網格內居民差額選舉產生。居民代表在工作中,履行居民代表、居民小組長、平安網格長“三位一體”工作職能。
我們還創新了社區民主決策的機制,涉民事務由原來居委會拍板定事、相關部門審核審批,轉變為涉民事務由居民代表會議民主決策,將低保、醫保、就業等涉民事務的議事權和監督權交給群眾,把原來的部門審批代辦轉變為居民自治議決,使社區實現了民事民管、民事民議、民事民辦,真正將涉民事務通過居民自治來解決。
中國新聞周刊:在推進社區改革過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王愛文:改革之初,遇到兩個最大的困難:一是有些部門不愿意放權,改革是要動誰的奶酪問題。從實踐來看,這個問題必須是一把手親自來抓,不換腦筋就換人。起初這項工作由政法委來負責牽頭做,但是費了很大的勁,很難推動。
為了推進改革,破除阻力,我們要求關于改革的各個部門聯合下發的文件都要上常委會,讓市委辦督辦。按規定這些文件是不需要常委會來定的,但是沒辦法。通過高壓辦法推進改革,現在回過頭來看,效果還是不錯的,一些部門觀念開始慢慢轉變過來。
另一個困難是社區代表沒有積極性的問題。一開始社區代表沒有實際權利,大家都不愿意干。我們通過改革賦予社區代表權利之后,居民代表就有了參政的積極性。這些權利包括社區代表參與福利分配,以及參與派駐社區干部的考評。
中國新聞周刊:撤銷街道辦后,一些政策如何貫徹下達到社區?
王愛文: 過去是各個部門指揮街道辦,街道辦主任和社區主任忙得像“木偶”,天天忙著填表,接受檢查,結果是街道辦主任天天疲于應酬上面各個部門,對于社區群眾服務則就沒有時間了。
我一召開座談會,街道辦主任就發牢騷,后來我在社區工作上做了一條規定,凡是任務要下達到社區,并且到社區進行檢查的,區里一把手要來親自定這件事情,否則就不能往社區下達任務。不能把社區當做下屬機構來看。
坦誠講,這件事目前做得也不是太規范,有些部門還經常偷偷給社區派活,指揮社區做很多事情。我認為,下一步社區還要減負。
現在社區行政化的影子還是有的,距離社區居民真正自治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中國新聞周刊:街道取消后,伊春與上級部門的對外銜接是否存在問題?
王愛文:這個問題是存在的,比如人民武裝部,之前按照規定是有街道人武部,現在街道這級取消了,不過也沒產生什么負面影響。又比如,過去司法調解機構也是依托街道辦來設立的。在改革之初,有些部門都來找我,問以后這些部門該怎么處理。我說,先掛在大的社區運行一段再說。
有些部門,在街道辦掛上牌子,街道辦主任身兼多職,街道只有兩三個人,有些工作根本就做不了。街道辦盡管牌子多,實際上卻沒有起到作用。
實際上,有些機構沒有必要設到這么底層,設在區一級就可以的。當初各個部門攬權,要自留地,把手伸得太長,這些都是政府職能不能轉變的結果。
像伊春人口這么少,設置那么多街道辦沒有意義。大家都成干部了,養這么多干部,群眾負擔就會很重,“雞多了不下蛋,人多了瞎搗亂”。
現在要就行改革,很多事項就要與上位法發生沖突,如果完全按照上位法改革,那么許多改革都將無法推動。實際上,改革這兩年,也沒有發生什么問題。要推進改革,有些法律就要突破。
中國新聞周刊:在社區治理改革過程中,如何保證政府不會過多干預社區事務,保證社區自治?
王愛文:如何實現政府行政控制與共治之間的平衡,以及如何把握政府與社會的邊界,一直是我們考慮的問題。
我們提出了“小社區,大社會”“強政府,好社會”的改革思路。在操作層面上,凡是社會能夠做的,政府就不再介入。我們開展的社區居民自治改革,就是要清晰界定政府行政行為與社會共治的一種探索和實踐。通過涉民事務居民自治,實現政府的簡政放權,最終實現統合公共資源,提升為群眾服務的能力。
我要求,社區居委會換屆直選率要達到100%,社區群眾有選舉權的居民參選投票面要達到80%以上,下派社區的部門工作人員要參加選舉。
為此,我們實行社區工作績效評議制度,定期召開居民代表大會,對社區“兩委”工作和社區工作人員表現進行評議,罷免表現不佳的社區工作人員。
例如,公安部門還推行警務機制改革,把社區警務工作的評價權和監督權交給社區群眾,如果駐社區民警被社區群眾否決,他不僅不能派駐社區,就連晉升資格都失去了,這大大增強了民警的服務意識。
為此,改革之初我們就建章立制,以免背離改革初衷。
中國新聞周刊:社區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平臺,日益成為各種政策和各類組織的落腳點、各種利益的交匯點、各種矛盾的集聚點。那么社區自身能否協調這些利益訴求?這些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訴求在居民區層面是否能得到解決?
王愛文:實踐證明,社區完全可以協調群眾在社區層面發生的矛盾,可以運用人民調解的方式解決;如果調解不成,社區會引導群眾用法律渠道解決群眾的訴求。
我們主要做了兩方面的嘗試。第一個在機制層面上,建立《兩級社區周例會制度》。各社區每周定期召開由黨支部書記、居委會主任組織的例會,參會人員是社區內的居民代表(網格格長、居民小組長)、居委會成員,會議議程主要對上周社區各網格內居民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集中梳理、分析原因、整改完善、集中解決。
對于社區層面解決不了的城市棚戶區改造、基礎設施建設、道路交通維護、涉法涉訴案件等方面的問題,提交區委、政府召開的區級社區事務周例會,主要是解決社區處理不了的涉民事務和群眾訴求。
第二個層面上,是通過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由綜治委孵化建立“百姓百事咨詢中心”這個群眾性自治社會組織。
中心的工作人員是司法、醫療、社保、建筑、公安等單位退休或二線的威信較高、為人正直、熟悉政策法規、熱心公益事業的部門領導和業務骨干,為百姓義務答疑解惑、反饋意愿,既能隨時化解一般性矛盾糾紛,又能引導群眾從合法的渠道表達訴求,減輕了信訪部門的工作壓力。
中心實行“一單式”接待,無償性服務。對于群眾需要解決的集體事務、家庭矛盾、鄰里糾紛、土地征用、城市拆遷、企業改制、醫療事故等糾紛訴求,咨詢類的由工作人員當場給予解答;需要政府有關部門解決的,由中心反饋到相關涉事單位、部門協調解決。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看來,目前我國是否已經具備真正實現居民自治的條件?
王愛文:我認為,目前我國已經具備真正實現居民自治的基礎條件。
我國現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是1989年頒布,1990年開始實施的。之所以成效不顯著,就是因為沒有隨著時代的變化,根據變化了的條件尋求其有效的實現形式。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的問題,很多條款規定過于宏觀籠統,缺乏操作性,對居委會自治權利的保障等缺乏詳細說明。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依法治國”,為我們進一步開展社區居民自治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居民自治作為制度和行為,不但需要法律依據去支撐,還需要群眾的參與和支持,進而才能探索有效的實現形式。
首先,將居民自治相關機制、細則,用立法程序加以固化,全面推進居民自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使開展各項自治工作有法可依、有據可查。
其次,隨著我國民主法治建設的不斷加強和完善,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普遍增強。特別是參與意識、監督意識的增強,為我們深化居民自治提供了良好的先決條件。
為此,我們要切實保障社區居民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監督權,廣泛調動廣大群眾參與社區自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只有群眾積極廣泛的參與,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區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