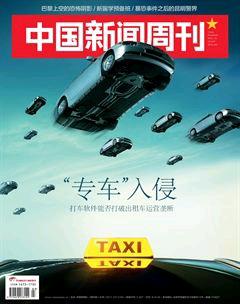梅村:一曲二胡新演繹
齊元
搜索“中國二胡藝術”的版圖,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20世紀以來的二胡名家、名曲、名琴師,大都指向了同一個地方——無錫。而距無錫市中心12公里,無錫新區轄內、素有“至德名邦”美譽的梅村,更因為二胡而聲名遠揚。
從2011年起,兩年一度的中國二胡演奏領域最高規格賽事——“中國音樂金鐘獎”二胡比賽落戶無錫。2012年,全國第一家集二胡歷史文化、生產工藝、演奏廳及培訓與活動基地等功能于一體的“二胡文化園”在梅村落地開放。
據無錫新區宣傳部負責人介紹,目前,梅村具有一定規模的二胡生產企業有10多家,從業人員300多人,年產各類二胡4萬余把,占全國中高端二胡市場份額的25%左右,年產值3000多萬元,梅村二胡制作工藝已列入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二胡文化產業也已成為梅村的特色產業。
單從經濟數據的角度,梅村二胡產業的產值與無錫新區重點打造的IC、光伏、軟件外包、傳感網等數百億級的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相比,或許難以相較。但這個面積僅有15平方公里的街道,卻以幾代人的文化傳承與發展,推動了二胡制作技藝的提升,豐厚了無錫二胡文化的內涵和底蘊,支撐起了“中國二胡之鄉”的金字招牌,成為國內各地新區開發中少見的一抹文化亮點。
一首曲,二胡情
在無錫,與二胡有關的名人軼事頗多,其中最為人傳唱的,莫過于一曲《二泉映月》。
1978年,小澤征爾應邀擔任中國中央樂團的首席指揮。其間,他指揮演奏了勃拉姆斯的《第二交響曲》和弦樂合奏《二泉映月》。這一天,小澤征爾并沒有說什么。
第二天,他來到中央音樂學院,專門聆聽了二胡演奏的《二泉映月》。曲終,這位享譽世界的著名指揮家老淚縱橫,被二胡的旋律深深震撼了。“‘斷腸之感這句話太合適了”,他說,“如果我聽了這次演奏,我昨天絕對不敢指揮這個曲目,因為我并沒有理解這首音樂,因此,我沒有資格指揮這個曲目……這種音樂只應跪下來聽。”
這是1978年9月7日,日本《朝日新聞》刊登的一篇文章——《小澤先生感動的淚》。自此,二胡演奏的《二泉映月》聲名遠播,成為中國民樂曲目中歷久彌新的經典。
熟悉《二泉映月》的人都知道,這首曲目是無錫籍盲人樂師阿炳(華彥鈞)創作的。他一生顛沛流離,他在道觀中被寄養多年,才被父親相認。父親去世后又沾染病致盲,最終流落街頭賣藝。
歷盡人間冷暖,阿炳在無錫惠山泉邊成就此曲,訴盡起伏跌宕的“命運交響”。曲調沉郁婉轉,仿佛一個人哽咽著傾訴生之怨憤與抗爭。著名二胡理論研究專家趙硯臣對此曾這樣總結:“行弓沉澀凝重,力感橫溢,滯意多,頓挫多,內在含忍,給人以抑郁感、倔強感,表現了一種含蓄而又艱澀蒼勁的美。”

梅村二胡文化園。
這種美感,或許只有通過二胡演繹,才尤為撩撥心弦。正所謂“東音凄涼、西音懷鄉、南音思親、北音離別”,來自馬尾弓毛與琴弦交織出的每一次或粗糲或纖細的顫音,都仿佛在訴說人性深處的暗流激蕩。
在“梅村二胡文化園”的二胡歷史展廳,我們找到了二胡魅力的原點。
一千多年前,中國北部的少數民族區域以“胡地”代指,“胡地”的拉弦樂器也被稱為“胡琴”。唐代詩人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的名句“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便是一例。宋代學者沈括也曾在《夢溪筆談》中記載“馬尾胡琴隨漢東,曲聲猶自怨單于。”
“胡琴”,這種源自苦寒之地的樂器,自誕生之日起便伴生了兩種主題——塞外邊關的生活之艱與戰火連天的亂世之難。由此,便不難理解千百年來它為何擅長演繹憑欄傷懷的曲風與情愫,也回答了《二泉映月》以二胡演奏更勝一籌的理由。
在進入中原的過程中,“胡琴”衍生出了多樣的變種,有秦腔、豫劇需要的板胡,京劇、漢劇需要的京胡、京二胡,河南墜子需要的墜胡,廣東粵劇需要的高胡等等。而到了無錫,由周少梅、劉天華加以改革,形成了現代二胡。他借鑒了西方樂器的演奏手法和技巧,將二胡定位為五個把位,又確定了二胡的高音,擴充了二胡的音域范圍,創作了10首獨奏曲,47首練習曲,并將二胡納入到專業音樂教學之中,使其成為音樂會上經常獨奏的樂器。這些都奠定了今天二胡文化藝術事業在無錫、乃至全國的起點。
接下來的一百年間,現代二胡藝術經歷了從初創到成熟繁榮的歷程,其中為之貢獻最多的二胡名家中,周少梅、劉天華、楊蔭瀏、劉北茂、蔣風之、儲師竹、閔惠芬、王建民、鄧建棟……無錫籍的藝術家占據了大多數。
在1992年“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的入選曲目中,二胡獨奏共選了5首,除劉文金創作的《豫北敘事曲》外,其余4首都是來自無錫音樂家的作品,包括阿炳的《二泉映月》和劉天華的《病中吟》 ?《空山鳥語》 ?《良宵》。
而作為“梅村二胡形象大使”的無錫籍著名二胡演奏家鄧建棟,曾于2008年與著名的捷克國家交響樂團合作,成功舉行了“《二泉映月》鄧建棟二胡獨奏音樂會”,成為首位在維也納金色大廳舉行獨奏音樂會的中國演奏家,開創了中國器樂獨奏音樂會的先河。
在無錫,二胡音樂家、演奏家的不斷涌現,得益于當地二胡文化氛圍的熏陶和給養,而為了尋得一把稱心如意的二胡,更多愛好者又將目光鎖定在了梅村。
匠心有道,產業于錫
從“梅村二胡文化園”駛出,在梅村宣傳辦楊偉新的引領下,我們來到了一片類似木材倉庫的建筑前,水泥裸露的外墻上,寫著四個宋體大字——“古月琴坊”。
不了解的人很難想象,這個貌不驚人的地方,是很多二胡演奏家們選琴必到之處。它在行業里的地位之高,使得這里的簡樸甚至有了朝圣的意味。
琴坊的主人,是年近八旬的萬其興,他是當代著名的制琴大師,也是梅村的傳奇之一。
1953年,年僅15歲的萬其興赴蘇州袁順興樂器店學習制作二胡。由于天資聰慧,18歲就出師,成為當時最年輕的琴師。1965年,他回鄉參與創辦了無錫第一個社辦廠——梅村樂器廠,開啟了梅村制作二胡的歷史。半個世紀中,廠子經歷過斗資批修的冰冷、關停改制的困頓、市場經濟的洗禮,幾經沉浮起落。1999年,他“二次創業”開辦了“古月琴坊”,并得到了二胡制作大師呂偉康的精心指導,廣采百家之長,最終制成了享譽海內外的“萬氏琴”。
“‘萬氏琴最要緊的就是選材”,萬其興說。“古月琴坊”用材只選明清時代的紅木舊料、印度的紫檀等高檔材質,以提高琴桿的耐用性和琴筒的共鳴音質。而蒙皮一步,從蟒皮選材到前期干燥處理,再到蒙皮松緊和后期調音,是二胡制作工藝的核心技術,也是制琴師功力火候的最大考驗。“音色是不能見的,全憑感覺”,萬其興說。蒙蓋在琴筒上的蟒皮,對花紋、厚度亦有要求,一張蟒皮四五米長,最好的只有尾部一段,適合做精品琴的蛇皮往往幾百張里都選不到一張。
在選材、時間、工藝、火候、手感等各種機緣全部滿足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得出一把好二胡,“萬氏琴”自然價格不菲。2010年,一把參賽獲獎的“萬氏琴”市場售價已高達18萬元。
但這并不能阻擋二胡演奏家和愛好者們來“古月琴坊”選琴的熱情。《戰馬奔騰》的創作者、二胡演奏家陳耀星每年都要來梅村,與萬其興切磋選琴,他相信萬師傅是“人品好,琴才好”。
的確,萬其興從業60多年來,無私傳授二胡制作技藝。前來學藝的二胡制作師來自全國各地,臺灣地區和日本也有愛好者慕名而來學習。目前在梅村開辦二胡廠的卜廣國、熊建、張連均等二胡制作師都是他的高徒。“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習語,在萬其興這里仿佛失去了效力,取而代之的,是一代制琴大師寬厚坦蕩的胸懷。“徒弟自己在外邊開二胡店,經營得好師傅臉上也有光。”萬其興用樸實的話,成就了梅村二胡制作史上的佳話。

二胡制作大師萬其興。
今天,以“古月琴坊”為代表的梅村二胡生產企業,仍舊保留著父傳子、師傳徒的傳統手工作坊模式,這種古樸的形制確保了每一把二胡的精工細作與價值考量,但也面臨著市場供給不足的問題。
據琴坊第二代傳人卜廣軍(萬其興女婿)介紹,目前,琴坊的訂單不止來自國內二十多個省市,更來自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及歐美地區,其中,日本市場上80%的二胡都來自“古月琴坊”。2014年12月底,“古月琴坊”誕生的國內最大的可演奏二胡,也是由臺灣一家民樂團專門前來定制。
因此,分工細化、服務外包以滿足不同層次的市場需求,便成了包括“古月琴坊”“林生樂器”“金波樂器”等在內的梅村二胡工藝產業升級發展的必由之路。
據了解,為扶持二胡特色文化產業的發展,無錫新區特制定了二胡文化產業規劃,計劃逐步把處于分散狀態的作坊式二胡企業及其配套企業聚集起來,引入現代企業制度,從而提升二胡制作企業的生產能力、管理水平和整體形象。同時配以一系列優惠扶持政策,招引周邊地區的二胡企業集聚,著力讓梅村成為全國最有影響的二胡的生產基地和集散地,并以此帶動無錫新區文化旅游、餐飲住宿、休閑娛樂、教育培訓等相關產業的發展。
產業之外,無錫新區更注重區域文化軟實力的提升,新區坐擁無錫吳文化資源遺存的80%以上,轄區內吳文化博覽園也已成型。而今,梅村二胡文化的傳承與技藝的革新,正在成為無錫活態文化不斷延伸的生長點,以一把二胡、一首新曲演繹無錫的城市新名片。
二胡藝術的梅村之旅,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