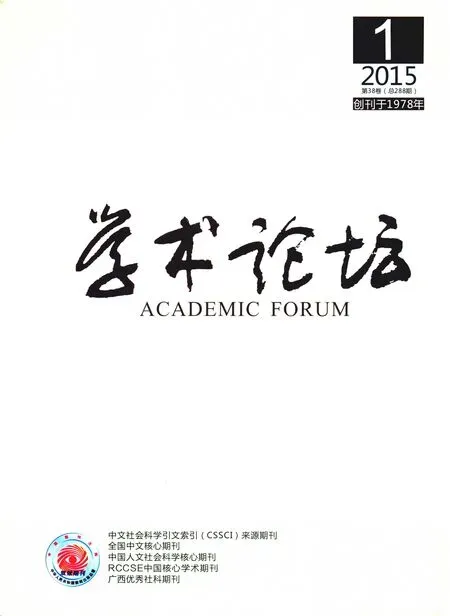對中國律師職業信任問題的分析與解決思路
——以法律職業社會學為考察視角
董進,韋冰一
對中國律師職業信任問題的分析與解決思路
——以法律職業社會學為考察視角
董進,韋冰一
當前我國律師職業界存在公共形象低以及公眾不信任的問題,從職業社會學理論來看,公眾對律師職業的信任是現代律師職業生存與發展的前提性要素,公眾對律師職業的不信任的存在將會給我國法律職業化目標的實現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該問題的產生有著文化傳統、職業化發展道路、律師業結構等多方面的背景,要解決該問題,必須立足于職業信任所產生的理論基礎,通過加強律師職業的職業責任來進行。
律師職業;公共信任;職業責任;職業信任
在我國法律職業化的發展進程中,律師職業化的進程一直是實現法律職業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近20年的改革中,我國的律師職業化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律師開始成為當前法治社會中的重要力量。但在這個發展過程中,當前律師職業界存在著律師公共形象下降的因素,并直接導致了公眾對律師職業不信任問題的出現。如何分析和解決這些問題,成為了實現律師職業化目標的重要抓手。本文擬從法律職業社會學的視角來審視目前我國律師職業信任危機的來源,以比較的方法來為提升我國職業律師公共信任度提供合理的參考性意見。
一、我國律師職業發展中的職業信任危機
我國的律師職業群體在近20年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在法治建設中發揮出了重要作用,律師的職業身份得到了確立,拋棄了原有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界定,成為了利用自身專業知識在市場中提供專業法律服務的人員[1]。律師開始走向政治舞臺,在國家立法以及法律監督方面成為了一股重要的力量[2]。但是,在目前我國律師業迅速發展的進程中,對我國律師群體的懷疑之聲也日益高漲,我國律師職業群體的信任危機開始呈現。根據美國學者麥宜生對新興的中國律師職業群體的研究,當前中國律師的公共形象處于一個非常低的水平上,公眾認為律師更多的時候是通過非官方的“關系”的手段來解決案件。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律師辦理案件過程中存在著眾多違法行為,從而出現了眾多防礙司法公正的事件。普通民眾對中國律師群體的敵對感處于非常高的水平[1],著名律師張慶曾經在《中國律師》上發文指出,“一段時期以來,由于職業道德教育的放松和競爭的加劇等主客觀原因,造成了整個律師行業的公信力下降,律師的社會形象遜于以往,從而導致了對律師的社會評價降低”[3]。由此可見,我們的律師目前確實無法做到讓公眾信任。因此對當前我國在律師職業發展中遭遇到的律師信任危機,值得學術界的關注和討論。
按照法律職業社會學發展的脈絡,律師職業是作為最典型的職業群體在社會結構中存在,其職業特性上決定了律師必須要同其客戶在一個相對保密的空間里面開展相關的個別化服務活動[4]。該特點也同時在客觀上決定了律師職業的運作需要有客戶對律師的信任機制作為前提性支持,客戶基于對律師職業的信任而提供自己的隱私信息讓職業律師知曉,而職業律師也必須在職業倫理上擔負起保密的義務,否則一切相關的法律服務工作將很難順利進行。在律師職業發展過程中,公眾對其的信任是隨著法律職業化的進程不斷完善的。公眾對律師的信任應該理解為對“律師職業”的信任,這種信任來源于律師職業的自身品性以及其內在的職業倫理、職業責任以及律師在社會結構中的職業定位,它與普通意義上的信任有一定的區別。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從法律職業社會學的發展來解讀其基本屬性。
二、律師職業信任的理論來源
從法律職業社會學來看,對律師的公眾信任來源于迪爾凱姆所創立的社會分工理論。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社會分工也隨之細化,各個行業間存在著工作性質上的差異,但是又因為社會的復雜性而需要相互的依賴,這就需要一個特殊的紐帶將各個行業聯系在一起,以保證社會機器的正常運傳。按照迪氏的觀點,行業內部以及行業之間是通過所謂的“有機團結”(Organic Solidarity)來進行互相協調進而保證社會整體的順利運轉的,有機團結成為了現代社會結構以及社會分工的重要維護者。在迪氏的觀點中,有機團結主要運用于協調各個工種之間的協作性,保證了社會中的個人能夠順利來完成自己所負責的工作。那么在社會結構中什么是實現“有機團結”相關功能的媒介呢?在其劃時代著作《社會分工論》中,迪氏指明了有機團結承載于職業團體之上,通過職業團體來發揮其功能。在有機團結機制的作用下,社會中的個人需要在職業團體中生活。在職業團體內部,個人將以團體的整體目標為中心,所有個人都需要合理地分擔自己在團體中的責任,同時應該信任在職業團體中個人的行為,也信任在職業團體中形成的職業倫理以及團體整體的行為模式,使得團體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有效力量。在這個時期,信任開始作為有機團結機制中的重要內涵存在,成為了有機團結得以維系社會運作的主要功能,可以說有機團結型社會的出現,是以信任作為前提條件[5]。
迪爾凱姆的社會功能觀點,在以帕森斯為代表的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在以帕森斯為代表的社會功能主義者看來,迪爾凱姆在社會研究中強調以職業團體為代表的次級團體在社會結構中的重要作用,承擔著連接個人與社會整體的功能。職業之所以建立,其目的是為了維系社會結構的完整性且實現社會團結的功能而存在的。在資本主義高速發展的時期,新的社會規范性秩序以及管理組織也在形成過程中,這需要將先進的知識融入社會并且轉化為實際的運用能力去推動社會發展[6]。法律和醫學的職業化轉變就是知識轉化的最典型例子,相關的配套改革也陸續開展,二者都采用職業化的教育模式,以區別于其他的學科人才培養,都建立了職業協會來實現對職業群體的管理,形成了資格授予機制來保證職業群體的職業特性[7]。在這個過程中,律師群體已經和其他的社會工種開始區分開來,其在社會結構中的職業功能得到了確認,基于知識服務社會的理念,律師需要與客戶形成勞動市場上的彼此間的真實而且有效的溝通方才能夠實現這一目標,職業律師與客戶之間的關系,并非其他工作(occupation)般的雇傭與被雇傭關系,而是一種基于法律職業特殊性的信托關系(Trusteeship),這種關系對律師職業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要求職業律師在工作中不能夠僅僅提供法律技術層面的支持,而是必須要具備職業倫理,且在該職業倫理的支持下促使律師的職業知識和客戶的法律需要相結合。這個結合不是在一個公開場合進行的,而是要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工作環境,要求職業律師必須提供專業的知識服務于客戶,而客戶也應該出于對律師服務以及律師職業品質和倫理的信任,提供真實的背景材料,按照律師建議展開工作,方能保證案件的成功解決[8]。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信任機制的形成來自于職業化的初期,律師工作和信任概念在職業化之初就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聯系,信任機制是律師職業得以作為一門職業而非普通工作在社會結構中得以存在的前提性條件。
三、當前困難的成因
由于中國法律職業化進程的獨特性,使得我國律師職業的發展不同于西方法律職業發展的軌跡。從當前我國法律職業化的發展進程來看,司法考試的確立以及法學人才培養體系的建設是非常重要的法律職業化成果,但是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當前法律職業化目標仍然沒有得到完全的實現,特別是在職業律師工作環境中,律師職業化應該具備的職業傳統、職業身份以及職業品格都存在著結構性的問題[9],這些問題的存在是導致我國律師職業信任問題的根本原因。
從歷史傳統上看,中國的律師職業發展同西方社會相比較有著明顯不同的軌跡,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法律職業化的進程要遠遠晚于西方主流法系,因此我們的職業化進程缺乏可以倚賴的深厚文化土壤,在職業化萌芽階段并沒有出現迪爾凱姆所認為社會分工系統的自然細化過程,反而在長期以來,法律職業化的發展是在政府主導下的、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運動。在改革之前的相當長時間內,我國的律師職業都是建立在國家行政體制管理之內的非自治性團體,律師的身份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隸屬于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受政府的管理和規制[1],這就導致了律師職業的形成與發展相對滯后,律師缺乏職業的身份,因此對律師職業的信任感也就無從培育。
同時,從傳統觀念上看,中國傳統社會的信任體系中缺乏職業信任。中國傳統的信任體系,按照著名學者季衛東的觀點,更多的是強調信任主權者的權威以及儒家的教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信任處于相對無序的狀態,沒有形成普遍意義上的法律信任觀念[10]。此外,在傳統法律文化研究中,中國傳統社會中存在著深厚的厭訟文化,從而導致了對律師職業有著文化傳統層面的負面印象,雖然中國傳統社會并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法律職業特別是律師職業,但是存在類似于律師的訟師等非國家法律工作人員,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法律服務的職能。由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厭訟意識,使得民眾對這種從事訴訟服務的工作者有著天然的排斥感,在傳統法律體系中的承擔律師角色的“訟師”往往處于邊緣性的地位,在中國法律史中一直處于被打擊的對象,被認為是擾亂法律秩序的主要群體[11]。這種傳統使得我國民眾從文化內涵上對律師職業有著天生的不信任心理。
從當前律師服務結構上看,隨著法律職業化在中國的展開,律師職業在中國逐漸成型,中國律師職業化確實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通過司法考試以及律師考試制度選拔律師已經初步建立了職業律師體系。但是,我們在確立律師職業身份的同時,并沒有和西方法律職業體系中那樣讓律師職業獲得相應的市場地位,相反由于當前法律服務工作市場復雜,職業律師在法律服務市場上存在著為數眾多的競爭者。按照美國社會學家麥宜生對中國律師群體的研究,當前中國除了通過國家律師考試或者司法考試而正式擁有執業資格的律師之外,還存在著眾多其他形式的類似律師的工作人員,他們可以被稱之為“馬路律師”、“黑律師”、“土律師”等等,他們在案件代理中所占的比率達到了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這些非職業律師的存在往往在給當事人在辦理案件中存在眾多非職業甚至違反法律以及律師倫理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律師整體的公眾形象[12]。在大眾的觀念中對于“職業”概念模糊不清,往往將法律職業理解為以法律為營生的人所構成的行業[13]。基于職業身份的公眾信任感被這種魚龍混雜的法律工作市場所分解,民眾無法真正理解律師作為職業群體存在之特性,這直接導致了民眾對律師的信任程度的降低。
同時,律師職業發展中存在著過分注重商業利益而忽視社會公益和正義的特點,也使得民眾對于律師職業充滿不信任。在西方律師群體職業化的開端,社會公共利益和正義確實是律師職業本身屬性的主要組成部分[14]。但是,隨著法律職業化進程的深入,律師的公共利益屬性和實現正義的倫理目標遭到了弱化,在律師實踐中很難得到具體實現[15]。根據美國著名法學家理查德埃貝爾(Richard Abel)的研究,在律師職業化與商業結合之后,律師職業被作為市場壟斷的工具,律師被定義為出賣自身服務給富人的工具而不是為了實現社會正義的群體,律師職業群體內部也被指責職業獨立性降低,律師變成了為富人說話的工具,律師職業藍圖(professional project)因此落空[16],法律在商業和職業倫理之間存在的這種緊張的關系,使得律師職業中的公正性受到公眾的懷疑,律師的公共形象因此降低,從而帶來的是公眾對律師職業的低信任度,根據美國對美國民眾律師信任的調查,美國民眾對律師信任程度在21世紀初僅為35%[8],民眾普遍也將律師職業理解為賺錢的工具。法學院畢業生也往往會選擇經濟效益好的大型律師事務所開始其職業生涯,以公共利益實現為目標的法學院畢業生占到很低的比重[17]。
在中國律師職業化進程中,美國所出現的上述問題,在我國也有一定的顯現。在相關中國律師調查報告中顯示,目前我國絕大多數的律師將律師事務所定位為營利性機構,國內的學者們將這個問題理解為中國律師職業倫理的缺失。由于長期以來律師地位是從屬于國家的工作人員,因此律師自身倫理的培育工作并不是十分的積極,當前的律師職業倫理采用國家主導的方式來進行培育,無法賦予律師職業更多的獨立性和凝聚力,因此無法能夠真正建構律師職業倫理[18]。有學者將商品性列為職業律師的特點之一,但忽略了律師倫理中所蘊涵的社會公益屬性以及維護社會正義的職能[19]。在這種語境之下,律師僅僅作為一個從事服務類型的商業組織,和當事人之間是簡單的客戶與服務人的商業關系,客戶通過支付金錢以獲得律師所提供的各種服務,原有的社會公益屬性無法體現,實現社會正義的職能被金錢交易所遮蔽,律師的公共形象因此降低,從而弱化了民眾對律師職業的信任。
四、律師職業信任危機的克服路徑設計
在上一個部分中,我們已經分析了當前律師職業信任危機存在的內在原因,這個危機的存在并非是中國法律職業化所獨自面對的問題。根據之前的論述,在法律職業化起步較早的美國,其職業律師群體同樣也面臨著信任危機,由此可見信任問題是法律職業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要解決該問題也應立足于法律職業化的相關理論與實踐。
在中國法律職業化繼續展開的大背景下,解決問題的著眼點在于強化律師自身的職業責任,特別是職業責任中所具有的公益服務屬性,形成職業律師的公益服務文化,以公益的形象來提升律師職業的正面形象,并進而贏得公眾的信任。無論是在我國法律傳統上,還是近20年來的法律職業化進程中,律師的職業責任特別是其中的公益性一直被我國專家學者所忽視。因此,為了克服當前的危機,我們需要在中國法律職業化的發展道路中注重職業責任建設,強調律師職業服務社會、實現社會正義的職業責任,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通過律師職業文化與制度層面的建設。在律師職業文化層面,應該加強對律師職業的公益文化建設,要在律師職業中形成服務社會的公益文化,律師職業不僅僅是商業主體而更應該是社會公益的提供者和社會正義的維護者。在職業律師群體中,律師事務所要擔負文化建設的任務,要加強對職業律師的職業文化培養,要讓他們意識到律師職業所蘊含的公益服務屬性。要形成與律師職業相適應的公益服務文化氛圍,促進當前職業律師職業文化的進一步轉型,通過文化的培養,減少律師職業群體中的過分強調經濟利益、忽視社會公益活動的行為,將職業律師與傳統意義的訟師以及現今存在的黑律師等非職業律師從自身言語和行動上明顯區分開來,從而讓公眾真正感受到職業律師在社會中維護社會正義的根本品性。
職業文化的培育需要制度建設來得到具體實現,美國律師職業界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20世紀70年代的水門事件讓美國職業律師界開始意識到美國律師職業責任處于一個低水平層面。在該政治丑聞中,幾位主要參與者都是美國著名法學院的畢業生,這讓美國律師職業的聲譽降到了歷史最低點,也同時讓美國律師職業界開始重新重視對于律師職業責任的培養[21]。為了能夠重新喚起職業律師的職業責任意識,在美國律師協會的主導下,美國律師職業界開始了眾多的改革措施,目的是為了強化美國職業律師的職業責任感,這些改革措施力圖在文化層面將恢復律師職業倫理中所蘊涵的致力社會公益與實現社會正義作為核心要素。首要的措施是通過法學教育的變革來培育正確的律師職業文化,通過職業倫理文化教育來強化律師的職業責任。1986年美國律師協會要求美國所有法學院都要將鼓勵學生從事公益法律援助活動作為法學院的教育目標。到了2007年,有大約150余所法學院開始將從事公益法律援助的實踐活動納入法學院學分授予體系或者作為法定的畢業要求,并且建立了完備的公益法律學習體系[20]。
在職業律師實務界,為了挽回職業律師的公共信任程度以及公眾形象,美國的律師事務所在進入21世紀之后加大對公益法律援助活動的投入,從組織形式上改變了以往美國公益法律援助活動無體系無秩序的特點,開始走上機構化公益法律援助的軌道。美國律師協會開始要求律師每年必須要完成一定數量的公益法律活動。在美國律師模范規則的第6條第1款中明確規定律師有從事公益法律活動的職業責任,并且要求律師每年至少從事公益法律活動的實踐最低50小時。以此為基礎,美國各地的律師協會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規章以及專門的組織機構對律師的公益活動進行監督、評估、引導和管理。律師協會的努力帶動了美國律師事務所,代表美國精英職業律師階層的大型律師事務所也開始將公益法律活動制度化和有組織化,具體表現是在律師事務所中設立專門的從事公益法律活動的部門和委員會,并對此給予專門的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支持,并制定律所規章制度來將公益法律活動規范化(Formality)
[21]。很多著名的律所開始將規定的公益法律援助時間作為年輕律師開始職業生涯的必經實踐道路,公益法律援助的多少以及質量逐漸成為了評價一個律師事務所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14]。這一變革對美國職業律師的整體社會結構帶來了很大的沖擊,從目前形勢來看,通過市場方式,由職業律師主導的公益法律援助行動已經在美國成為了關于法律職業責任建構的重要議題,并且在對美國律師職業形象的重塑和公共信任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社會作用。有數據表明,自該運動開展以后,美國從事公益法律活動的律師數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長,律師的公眾形象也在隨之改觀[14]。
相比之下,我國在提升法律職業人職業責任的努力并不是不存在,但是目前處于一個相對無序化、個別化的局面,缺少一個系統的制度加以有效的引導,更多的是個別機構的行為,沒有提升到宏觀制度或者政策的高度。在法學教育方面,在當前的課程體系中,法律職業倫理課程抑或公益法律課程沒有被列為國家法學教育的14門核心課程之一,在研究生層次的教育體系中,也沒有系統地將這方面的課程納入教學計劃之中,沒有形成一個普遍系統的公益法律與法律職業倫理觀的教學體系。在律師職業規范方面,2008年新頒布的律師法中,并沒有任何關于律師從事公益活動的法律規范,而中華律師協會所頒布的律師行為準則雖然在第10條中規定“律師協會倡導律師關注、支持、積極參加社會公益事業”,但是該條文規定得過于簡單抽象,缺乏在具體操作層面的明確指引,律師事務所無法進行實際的操作。在地方律師協會的行為準則中,僅有極少數律師協會將從事公益活動列入律師行為規范之中。在司法部最新頒布的《律師事務所年度檢查考核辦法》中,已經把律師事務所從事社會公益活動納入考核的標準,這一點確實有利于促進律師從事社會公益活動,但是如何評價律師參與的公益活動數量以及質量仍然存在模糊之處,對于從事公益活動在評估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對整個律師事務所最終評估結果影響的方面還需要一個細化的標準加以配套,這些都應該通過建立完善的律師公益活動行為規范來解決這一問題。
[1]M ichelson Ethan,Unhooking from the State:Chinese Law yers in Transition[M].Ph.D.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Soci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2003.
[2]朱國泓,史建三.上海律師業發展戰略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3]張慶.盡快建立律師誠信體系[J].中國律師,2002,(8).
[4]李學饒.法律職業主義[J].法學研究,2006,(2).
[5]Durkheim Em ile.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M]. Free Press,1997.
[6]Events Julia.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ism [J].International sociology,2003,(2).
[7]劉思達.分化的律師業與職業主義的建構[J].中外法學,2005,(4).
[8]李學饒.法律職業主義[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
[9]CarlrosW ing-Hung Lo,ED Snape,Lawyers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 Study of Comm itment and Professionaliz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2005,(53).
[10]季衛東.法治與普遍信任[A].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
[11]俞飛.訟棍與訟師[N].檢察日報,2011-09-23.
[12]劉思達.割據的邏輯: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的生態分析[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
[13]張文顯,盧學英.法律職業共同體引論[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3,(6).
[14]Granfield,Robert&L.Mather.Pro bono,The Public Good,and the Legal Profession:an Introduction[A]. Granfield,R.and L.Mather(edit),Private Law yersand the Public Interest:The Evolving Role of Pro Bono in the American Legal Profession[C].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5]Boucher Steven.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o Bono In large Law Firms:Trends and Variation across the Am law 200[A].Granfield,R.and L.Mather(edit),2009.Private Lawyer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The Evolving Role of Pro Bono in the American Legal Profession[C].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6]李學饒.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職業藍圖的落空:評埃貝爾的法律職業矛盾[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
[17]Granfield,Robert,Making Elite Lawyers:Visionsof Law at Harvard and Beyond[M].New York:Routledge,1992.
[18]郝凱廣.當代中國律師“公益性”職業倫理之缺失:基于李莊案的思考[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0,(5).
[19]徐卉.重新認識律師職業:律師與社會公益[J].中國司法,2008,(3).
[20]Adcock,Cynthia.Shaped by Educational,Professional,and Social Crisis:The history of Law Student Pro Bono Service[A].Granfield,R.and L.Mather(edit),2009. Private Law yer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The Evolving Role of Pro Bono in the American Legal Profession[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21]Cumm ings Scott,The Politics of Pro Bono[J].UCLA Law Review,2004,(52).
[責任編輯:劉烜顯]
董進,法學碩士,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韋冰一,理學學士,中南民族大學統計學專業畢業,湖北武漢430074
D926.5
A
1004-4434(2015)01-01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