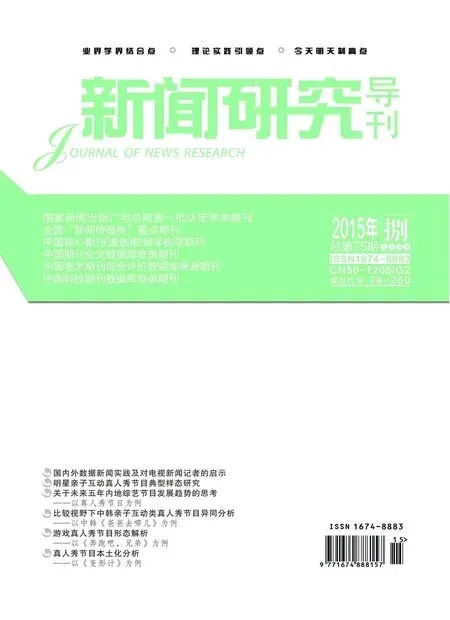我國電視綜藝節目傳播效果的社會因素分析
黃兆函
(中國傳媒大學 播音主持藝術學院,北京 100024)
縱觀2015上半年綜藝節目收視情況,《奔跑吧兄弟》第二季以收視率4.714%的成績位列榜首,其他同類綜藝節目收視表現也可圈可點。相比之下,影視劇的表現卻較為低迷,2015上半年只有《武媚娘傳奇》一部電視劇以2.959%的收視率達到了2%以上的收視率,就連2014年口碑極佳的《北平無戰事》單集收視率最高也只有1.6%,遠不比劉燁今年參加的《爸爸去哪兒》第三季的單集收視。綜藝節目在最近兩年取得的良好收視效果背后的社會原因值得關注和分析。
一、節目模式的海外引進
節目模式的引進已經成為我國綜藝節目生產的成熟模式,也正是因為這些節目曾經擁有在海外非常成功的案例,它們向中國市場的移植才更具說服力。眾所周知,浙江衛視購買了韓國sbs的熱門綜藝《running man》并將其改造為中國化的《奔跑吧兄弟》,備受觀眾喜愛的撕名牌環節也是在韓國原版中實踐了五年之久依然人氣超高的游戲內容;《中國好聲音》的靈感來自于同一模板的荷蘭之聲、愛爾蘭之聲、美國之聲等;湖南衛視引進了韓國mbc《爸爸!我們去哪兒?》做成了《爸爸去哪兒》;除此之外《爸爸回來了》《我是歌手》《極限挑戰》等不少時下熱門綜藝均是引進了外國的優秀節目從而一炮而紅。成熟模式的借鑒和海外制作團隊的參與,使得這些節目從一開始就擁有比較高的起點,從而為收視率的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明星的日常化
成功的綜藝節目都擁有著一些相同因素,其中難以忽視的一點就是它們都展示了明星普通人的一面。明星真人秀節目嫁接紀錄片的形式展現了在明星身上不常見而在百姓生活中常見的場面,讓觀眾找到了認同感。例如,《爸爸回來了》就展現了大明星們“奶爸”的一面,節目基本上只是采用半記錄的形式來展現明星和萌娃之間的日常生活,卻備受觀眾喜愛。此節目更是讓在影視表演領域反響平平的賈乃亮一躍成為備受大家喜愛的“神經奶爸”。看爸爸們在與孩子相處中的真實狀況,觀眾們得以摒棄對明星一貫的仰視心理,而有了平視的姿態,自然帶來良好的收視體驗。
對于很多藝人來講,參加綜藝節目也是一件雙贏的事情,增加了節目的可看性也助長了自己的名氣,不管是以奶爸的身份照顧萌娃,還是放棄偶像光環“滾泥潭,都可以盡情地展現自己的性格,讓很多影視演員在熒幕上回歸了本真狀態。而觀眾看到明星的身上更多可貴可愛的特質后,也成為明星的支持者,并將自己納入偶像消費的環節。
不過,拋開節目的成功營銷和話題,單從明星自身來講,參與綜藝節目其實更像是一把雙刃劍,因為明星制在某種程度上是以神秘感作為重要的營銷手段的,而如今明星過度地在節目中呈現自我,消費自我,也有可能產生想負面的效果。例如,范冰冰以美貌感染觀眾,但這種美得力于電影中分毫不差的鏡頭語言,但參加真人秀《出彩中國人》坐在評委席上的范冰冰卻受到了輿論的批評。再比如周冬雨在近期參加的綜藝節目《極限挑戰》中就因為對同期嘉賓表現的傲慢無禮,在節目播出后被觀眾倍加詬病,曾經清純透明的謀女郎形象仿佛一夜間蕩然無存。相較于上文提到的讓明星走下神壇展現普通人的一面,這也是另一種走下神壇,對偶像的神秘感的破壞,一如本雅明所說的“靈韻”的消逝,也可能對整個偶像工業產生顛覆性的影響。
三、讓普通人戴上明星的光環
選秀類綜藝是目前影響力最大的綜藝節目形態,剛剛開播的《中國好聲音》第四季就以5.455%的收視穩居首。從最初的“快女”、“超男”到現在的《中國好聲音》,選秀類節目一路火爆,其原因大抵就是因為,觀眾得以通過節目看到普通人實現自己夢想的過程,從而產生一種虛擬的代入感與體驗感。包括看到明星導師之間因為搶奪一個選手進行爭辯等環節,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令觀眾產生心理滿足。當然,選秀類綜藝節目不同于明星真人秀節目或游戲競技類的節目那樣可以設計各種各樣的形式以及豐富的內容,此類綜藝節目一旦形式被熟知了內容也不會有更多的懸念,這也是為什么類似的綜藝節目總是不停更換擁有一定知名度的導師來吸引觀眾的目光,或是不斷的制造話題選手、明星學員的原因了。
在節目的制作上,綜藝節目時常結合自身節目特點,進行取舍。也有一些節目因為沒能把握好明星化的分寸而導致收視慘敗,如浙江衛視推出了一檔《我不是明星》的欄目,意在吸引“星二代”們來參加選秀節目,這些星二代有的子承父業,有的做著其他普通的職業。每一期節目展示個人特長,依據現場觀眾投票來進行排名。節目第一季反響頗為熱烈,節目同樣也是利用了觀眾對于明星生活的好奇心,但顯然節目并沒有找到一個準確的定位,這些星二代并不算明星,無法吸引固定的收視人群;并且他們的個人特長遠不如選秀節目中的選手耀眼,最終節目也是草草收場。
四、良好互動與觀眾加強情感
綜藝節目的互動主要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首先是屏幕外和屏幕內的互動,即節目與觀眾的互動。以選秀節目為例,普通人參賽使參賽者變成了大眾的代言人,他的成功與否會直接牽動觀賞者的心,他們的成功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實現觀眾的夢想。節目也經常采取觀眾投票的形式來增強與觀眾的互動,觀眾們也更愿意看到因為自己各種形式的支持而獲得成功的選手,覺得他們的命運與自己息息相關。也正是因為這樣,曾經有一段時間的電視選秀節目開始了競相比“慘”,最初總是深深的讓觀眾為其動容,但看久了也就屢見不鮮。這些都是綜藝節目為保證節目看點而采取的敘事手段,但現在看起來未免簡單粗暴。
第二種互動是電視與網絡的互動。在這個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我們很難說得清楚究竟是電視帶動了網絡還是網絡帶動了電視,往往微博就是人氣最直觀的體現,在一部綜藝節目熱播之前官博會推出各種各樣的預熱信息,讓觀眾對其保持一定的好奇與期待;前期不斷進行話題營銷,也是節目保證收視率的一種手段。并且在節目熱播后網絡上都會形成一定的熱度,有些是觀眾自發的,有些是主辦方發起的,總之,在節目播出后依然可以使其熱度維持一段時間,以此吸引更多的沒有在第一時間關注的觀眾和網民。如果說過去電視節目是“制造業”,現在則是純粹的“服務業”,往往在電視之外所留下的選擇更多。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觀眾主宰了屏幕。到底是應當引導還是迎合,是文藝創作常年探討的問題,而很明顯現在的主導者是觀眾,迎合的是藝術。
五、總結
我國綜藝節目的成長大體分為三個階段。最初的節目以夾敘夾議的形式呈現,如《綜藝大觀》等;后來出現的以“解惑”為主要功能的綜藝節目如《開心辭典》《幸運52》等,旨在娛樂的過程中給人們知識,使知識趣味化,節目也更加的有價值;而現在的綜藝節目可以被歸結為“解渴”性質的節目,其主旨在于為觀眾提供純粹的娛樂。在藝術創作中有感性和理性兩種思維,如果說兩種思維都是如平行線般并駕齊驅永不相交,那如今的綜藝節目中所秉承的便是游戲思維,而游戲思維更像是一條曲線,使節目的內容和文化自然地在感性和理性中過度,讓人感覺到即不是過分的嚴肅,又不是過分的煽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往的沉悶的,同時也開創了一種更加新穎輕松的形式,使節目的可看性大大提高。雖說游戲思維增添了節目的娛樂性,但也正是源于這種思維,節目得以用更加刺激的視覺來吸引人們的眼球;用更加開放的行為來增加人們的興趣。我們注意到現在的綜藝節目都會或多或少的展現一些矛盾,這便是 “解渴”性使然。這也是為什么前一段時間的《花兒與少年》第二季,并沒有依靠剪輯來規避嘉賓們的爭吵,反而是依靠各種手段夸大了這種沖突性。但依靠這樣的方式來提高關注度,雖然解了觀眾的渴,或許是飲鴆止渴。
依靠著國內外的優秀制作團隊,以及對明星制的利用,綜藝節目的成功有著方方面面的因素。但歸根結底,有生命力的節目應當是藝術和文化相互依存的結果。大眾媒體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觀眾現階段藝術欣賞的水平與能力,但任何藝術形式,包括電視綜藝節目,依然需要推陳出新并擁有自己的文化品位,這才是綜藝節目的影響力得以延續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