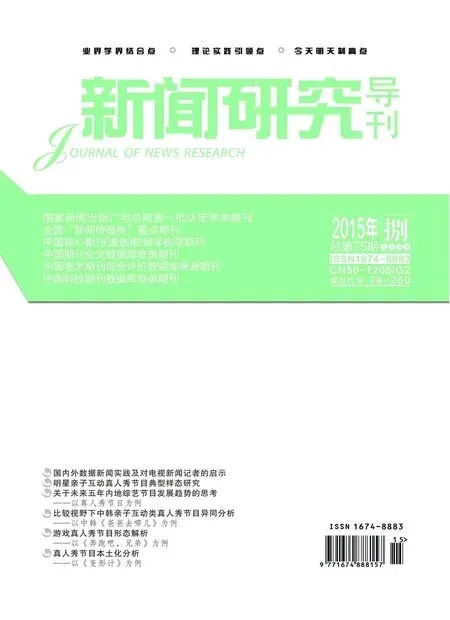人物報道的新媒體寫作
黃宏春
(右江民族醫學院,廣西 百色 533000)
人物報道的新媒體寫作
黃宏春
(右江民族醫學院,廣西 百色 533000)
隨著媒介融合時代的到來,作為內容生產的人物報道,不僅要符合新媒體的傳播特點,也要符合讀者的信息需求和閱讀習慣,才能達到其傳播效果,傳遞社會正能量。
人物報道;新媒體;新聞寫作
隨著的媒介融合的不斷深入,作為內容生產形式的人物報道,要主動尋求符合新媒體的傳播特點,才能發揮它的傳播目的,才能永葆它的生命力。傳統的人物報道在選題上大多以“典型”為重,在寫法上以有“意義”的內容為重,在表達上著重引導性的語氣,在篇幅上講究大篇章。而以“草根”選題,貼近讀者生活;人情味價值取向,觸動讀者心理;故事化敘述,吸引讀者;短小精煉的篇章,滿足讀者閱讀習慣,是新媒體傳播環境中的人物報道的寫作特征,
一、以“草根”選題,滿足讀者的信息需求
隨著傳播環境的空前開發,以民間為“草根”的現象盛行,這種“一地雞毛”式的生活方式,得到公眾追捧。人物報道的選題,應該符合時代的需求,符合讀者的信息需求。國內傳統人物通訊報道的對象都是“高、大、全、強”,被報道的人近乎是一種“神話”。這個人物為工作而六親不認,七親不顧;為了某項事業而廢寢忘食,甚至積勞成疾乃至獻出生命。當然,特定的社會環境下,我們不可否認這種以意識形態為內容,以宣傳為目的的報道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在新媒體的到來,傳播手段多樣,傳播環境開放,帶來是讀者信息需求的多元。這種“高、大、全、強”的人物寫作受到質疑。那些近乎“神話”的典型人物、受到讀者的詬病。
然而,在當前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突發,利益分化嚴重,人們價值取向多元的情況下,讀者更易于接受“草根”選題。人是社會現實生活中的人,“眾”形象意義就是很多人搭起來的,所以這個社會離不開一個個獨立的人,既要有頂天立地的偉人,也有普通平凡的人。在這個空前開放的傳播環境下,社會不僅需要偉人,同樣也需要“草根”人物。媒體作為文化的傳承和社會價值觀的維護者,自然就應該用鏡頭用筆頭面對這些人群。那些有感人的經歷的、有普通意義的人物是人們更多關注的對象。以“草根”人物選題,讓人物報道回歸社會現實,能接近讀者的生活,讓讀者可見、可知、可感。
縱觀近幾年來中國新聞獎的獲獎人物報道,人物報道“草根”選題出現了新氣象,一年一度的央視的“感動中國”節目,吸引全國觀眾,因為這些人物多是從民間發現的,他們的事跡并不“偉大”,但是他們來自讀者周圍,能打動讀者的心靈。第22屆中國新聞獎中獲獎作品《宿管阿姨800字致辭 被掌聲打斷11次講哭畢業生》在南信大當了10年的宿舍管理員的吳光華阿姨,《小胡同走出大記者——“張剛現象”啟示錄》普通記者張剛,這些人物是生活在我們身邊的普通人,他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為自己生活、為別人服務。從讀者的角度來說,那是自己的故事。
只有報道回歸現實,以我們寫“我們”,以自己寫“自己”才能情真意切,才能感染別人,這恰恰是我們媒體的社會功能之所在。符合媒體貼近群眾、貼近生活、貼近實際的原則,符合“走轉改”的報道思路。近些年來我們看到人物“草根”選題的新氣象。央視的東方時空欄目的標語是“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是與普通老百姓生活中的那些感人的人物、那些具有教育警示意義的人物故事。《南方人物周刊》副主編徐列認為,他們所報道的人物大致分兩類人:一類是對生活、對社會的進步具有推動作用的人;另一類是在與命運的抗爭中所體現出來的具有向善力量和人性魅力的人。[1]
二、人情味價值取向,觸動讀者內心
人情味是新聞價值構成要素之一,指的是新聞人物接近讀者,能在讀者心理產生共鳴。這就要求我們改變以往以“意義”來寫人物報道,要遵循新聞的發展規律,以“新聞”來寫人物報道。以“情”字為核心來報道。這不僅要展示一個人有“意義”的一面,也展示一個“人”的真實的情感,當靈感相同,感受相同的時候,才能引起共鳴。分析國內外人物報道,我們發現,國內的新聞人物主要寫作特征是人物的主要事跡、主要成績等等。而國外則是人物的故事,國內的人物報道注重“意義”。國外的新聞人物關注“人情味”。他們寫人物報道就是把一個人當成一個完整的人,不管是達官顯貴還是街頭小販或司機,在寫作上能融入這個人物的正常的日常生活,展現一個正常人所具有的特征。人之所以成為高級動物,是因為他具有社會屬性。所以,人物報道中也是需要讓人物回歸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
《我要做一個有誠信的人》講述了已經74歲高齡的老人吳蘭玉,為了還清為兒子治病而欠下的10多萬元的費用,用9年的時間,依靠撿破爛攢錢還債。這一義舉,贏得了讀者的尊敬,也打動讀者的心,體現中國傳統文化誠信的優良品質。《吳菊萍:勇敢的媽媽,偉大的媽媽》講述的是一個女童從10層樓高地方掉下來,是這個與她素不相識的吳菊萍,伸出雙手接住了她。《“最美司機”吳斌:普通人的創造“愛的奇跡”》,當面對突如其來的災禍時,這些普通人,為了別人,毫無顧慮地行動起來,這么一個舉動卻感動人們。這些人物雖然不偉大,卻做出“偉大”的事,相比那些“高、大、全、強”的人物,他們充滿人情味的事件,切合時代的價值觀,體現一個時代的精神實質。能喚起社會的良知,傳遞了社會的正能量。
一個有人情味的人物報道有助于讀者在心理上的接近與共鳴,能夠賦予新聞報道“活”的靈魂。[2]人情味的人物報道是體現了人文關懷,在一個崇尚以人為本的社會,我們的人物報道的人情味應該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選擇。
三、故事化敘述,吸引讀者閱讀興趣
故事化產生視覺化,在這個“讀圖時代”,一張圖勝過萬千字,作為傳統的文字,故事化的文章才能夠引起讀者的興趣;新媒體時代的讀者習慣“淺讀”,故事性的文章才能讓讀者“潛讀”,扣人心弦,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文章才能拴住讀者,無論是黨報還是都市類的報紙,唯有“寓教于悅”才能起到報道的目的。
在外國的新聞學里,新聞是“story”,這不僅說明外國新聞要以事為新聞,而且是以故事來寫新聞,一則新聞就是一個故事,或者說是以故事的形式來講述一則新聞。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有人就有故事。人物報道也因為故事而引人,也因故事的代表性而成為報道的對象。在國內的人物報道中,我們看是模式化的、鑒定式的、簡介式的寫法。寫一個盡職的優秀干部,都寫他整天忙著到基層調研,走破多少雙鞋子,吃冷飯,感冒生病也不醫治。寫一個優秀教師,都是為學生著想,冬天里給學生送衣服,熬夜批改作業等等,其實不然,一個人的性格、一個人的興趣愛好、一個人的個性都與這個人的為人處世有關。
斯諾的故事化寫法值得我們借鑒。在《西行漫記》一書中他用故事化的講述,中央蘇區的領導人、蘇區的生活情況,國共當時的形式對比等等,故事化強。在斯諾筆下的寫毛澤東、徐東、彭德懷等中央蘇區的中共領導人,每個人物活靈活現,栩栩如生。這是因為他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運用多種寫作手法,講述了這些偉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體現的“偉人”的性格。例如,寫毛澤東的一個細節,“突然間,他們兩個都俯過身去,看到一只飛蛾在蠟燭旁邊奄奄一息地死去,高興得叫起來。這確是一只很可愛的小東西,翅膀是淡淡的蘋果綠,邊上有一條橘黃色和玫瑰色的彩紋。毛澤東打開一本書,把這片彩色的薄紗般的羽翼夾了進去。……”這樣的人會是真的在認真地考慮戰爭嗎?一個偉人以日常的細節來描寫,在中國的人物報道史上極為鮮見。
新聞是建構,而不是記錄。筆者認為,記者是巧婦而不是魔術師,巧婦是在有米的條件下才能做飯,做飯是巧婦的技能。魔術師是制造無中生有,脫離現實的表演;記者是建筑設計師而不是化妝師,建筑設計師用真實的材料通過巧妙的設計展現建筑的美,而化妝師可以把美化得更美,丑也能化成美,掩蓋事物的本來面目。所以新聞作品是行為藝術而不是表演藝術。新聞的本源是事實,記者的本事是講故事。記者可以在現有的事實上,通過自己的對事件的理解,為讀者講述一則故事。這就要求記者要有小說家的思維,有散文家的情感,有詩人的靈氣。在寫作人物報道時基于報道對象的事實,圍繞所要表達的內容。有故事情節、有散文化描寫、有詩歌造句。一篇故事化人物躍然紙上。
四、篇幅要短小,滿足讀書閱讀習慣
周蔚華通過后現代讀者的閱讀習慣研究發現,后現代的閱讀是以讀者為中心的閱讀,是感性的、享受的閱讀是非線性的、跳躍式的、破碎的閱讀。是海量的、瀏覽性的淺閱讀,是調侃的、消解(解構)和顛覆傳統的,是多元化的、時尚的,充滿著不確定性。我行我素、率性而為的,是偷懶的、具有惰性的,是趣味指向型的,是交互的、互動的、對話式的。篇幅短小符合新媒體的傳播要求,我們的新聞媒體要適應新媒體的傳播的渠道,我們改變過去長篇大論或鴻篇巨著,精品化成為我們報道的改革方向。
中國的傳統人物報道是長篇巨著,是創世詩,筆者做過統計《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正文不含空格共13,356字,《黨的好干部 人民的貼心人——追記新時期領導干部的楷模、優秀少數民族干部牛玉儒》不含空格共計9,529字,這些收錄在《人民日報60年優秀通訊》的人物報道,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中國人物報道的典范。我們不可否認的是這么長的人物通訊在中國的某一個歷史時期所起到的傳播效果,但是我們也可以想一想,擱在現在的閱讀習慣和在沒有行政指令要學習的情況下,會有多少人去認真讀一讀這樣的人物報道。難怪業界也有說,很多報道是“寫誰誰讀,誰寫誰讀”的幾乎是“自娛自樂”的現象。第23屆中國新聞獎人物報道的特等獎的獲獎作品《老紅軍和他的三個兵》記空格在內才1,755字。這篇文章不僅篇幅小,行文中大量引用直接引語,新聞現場感強。我們應該提倡這樣的人物報道。
篇幅短小符合新媒體時代的閱讀習慣。符合時下“悅讀”和“淺閱讀”的時代。那些上萬字的報道,如果按照一般人的閱讀速度平均為(200~500)字/分鐘,大概需要20分鐘的時間。上班族中有多少人靜下一點來讀這樣一篇報道(除了有目的的讀者外)。更何況,這樣的文章放在手機里,有多少人樂意去點擊翻看下一頁。時代的要求和讀者的閱讀習慣要求我們寫精品人物報道。我們的記者和編輯人員要從讀者的角度出發去考慮新聞采寫,盡量縮短篇幅。一篇短文的人物報道,讀者一口氣讀完,引起讀者對這個人物的思考。
五、結語
新媒體的到來引起了傳統媒體的轉型,這種轉型最關鍵的是如何把傳統的新聞寫作更適應新媒體的傳播特性,也更符合讀者“眾口難調”的信息需求和閱讀習慣。作為傳遞社會正能量人物報道,如何在信息時代發揮它的傳播效果,激發它的生命力,需要媒體從業人員從思想上要改變過去的寫作思維,在傳播技巧上要改變過去的行為方式。唯有新媒體寫作特點的人物報道才能符合信息時代的要求,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
[1] 南方人物周刊對話北大學子:我們時代的青年領袖[DB/ OL] . http://news.Sina.com.cn/c/2005-06-03118156838670. shtml.
[2] 周蔚華.后現代閱讀方式的興起與出版轉型[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2).
[3] 白貴,彭煥萍.當代新聞寫作(第1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17.
[4]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版)[M].三聯書店,1979:88.
G212.2
A
1674-8883(2015)15-0210-02
黃宏春,右江民族醫學院新聞中心主任,研究方向:新媒體,新聞寫作,傳播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