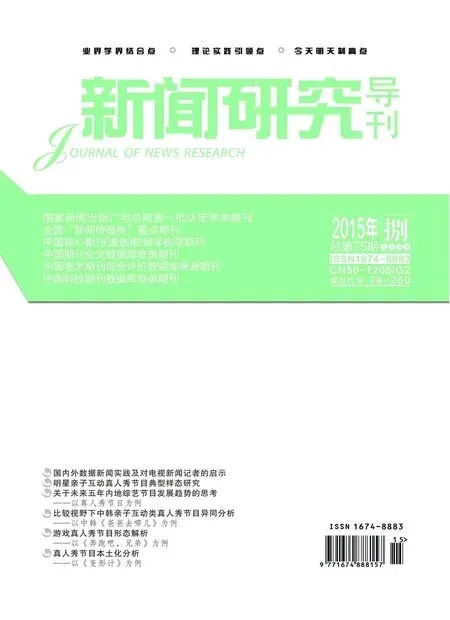健康傳播視角下的控煙傳播研究綜述
劉婷婷 劉欣娟
(中國傳媒大學,北京 100024)
一、控煙傳播的現(xiàn)實情況
全世界每年因吸煙死亡達250萬人之多,煙是人類第一殺手;而中國,是煙草生產、消費大國,吸煙者達到3億多人,占世界吸煙總人數(shù)的三分之一……所以說,控煙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個人習慣問題,而且已經(jīng)演變?yōu)橐粋€備受各界關注的社會問題。
(一)控煙傳播主體廣泛,權責不明晰
控煙的主體非常廣泛,相應地,控煙傳播也是多元主體,大到國際組織、國家有關部門,小到家庭、個人。控煙的信息到處都能找到,街道的標語條幅,火車站的禁煙廣播,媒體上的控煙信息……其中尤以媒體上控煙信息最為關鍵:在眾多的控煙傳播主體中,媒體影響范圍廣、可信度較高、觸及時間長,對公共議題的報道和健康理念的傳播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理應承擔起“瞭望員”的作用。
(二)社交媒體將成控煙傳播主力
近年來,隨著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的迅猛發(fā)展,人們的媒介偏好發(fā)生了大幅度的遷移:從傳統(tǒng)的報紙、雜志、廣播、電視切換到了電腦、Pad和手機,今年以來幾大運營商的“提速降費”更助推了這種趨勢。像其他所有議題一樣,控煙傳播的主陣地,將逐漸從傳統(tǒng)媒體轉移到影響范圍更廣、效率更高、黏性更強、影響力更大的社交媒體——在這個時候研究社交媒體控煙傳播,無疑會為以后的實踐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
2015年4月21日,“無煙北京”微信公眾號正式上線,市民不僅可以借此平臺了解戒煙知識和戒煙案例,還可以對違法吸煙行為進行舉報和曝光。同時,北京市控煙協(xié)會發(fā)布了待選的三個控煙勸阻手勢,市民可以通過投票的方式,最終確定今后在北京市通用的“控煙手勢”,你、我、他,都將成為公眾場合控煙的一份子。
(三)“控煙”的網(wǎng)絡熱度長期處于低位
控煙從來不是社交網(wǎng)絡上的火熱話題,這一點從一直處于低位的百度指數(shù)就可以窺見一斑,“控煙”這一關鍵詞近幾年來的平均熱度為200左右,2012年1月創(chuàng)了最低搜索指數(shù)62,在2015年達到高峰。觀察近7日的百度指數(shù)則不難發(fā)現(xiàn),該搜索詞在2015年6月1日,即“最嚴控煙令”出臺當日達到頂峰,搜索指數(shù)為2020,后來逐漸回落,3日回落到882。
新浪微博的“微指數(shù)”在這一時間段內的統(tǒng)計結果與百度指數(shù)一致,2015年6月1日微指數(shù)達到峰值,為91931,6月3日則跌落到15211。
雖然目前的數(shù)據(jù)并不樂觀,但是我們的媒介接觸習慣從紙質媒介、電腦轉移到了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社交網(wǎng)絡上的控煙內容只要內容得當,傳播得法,必將衍變?yōu)榭責熤髁Α?/p>
二、控煙傳播研究現(xiàn)狀
從傳播學角度看,控煙問題的研究漸漸成為政府行政學者、醫(yī)學社會學者和健康傳播學者共同關心的重點話題,但因為研究視角的差異,不同學者的關注點也各有不同。政府行政學者側重于控煙政策的研究;醫(yī)學社會學家偏重于對吸煙人群生理機能的研究,而大部分健康傳播學研究則從大眾傳播的角度入手,著眼于大眾傳播在控煙的相關傳播中扮演的角色、設置的議題、構建的框架……其中健康傳播學者的控煙傳播研究,是我們本次文獻分析的重點,他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一)宏觀層面的控煙研究
目前研究多借鑒健康傳播理論、風險傳播理論及框架理論的研究成果,描述我國目前的控煙現(xiàn)狀,并結合控煙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例如,張文燦的《框架理論視野下我國控煙報道的新聞框架探析》,抽取《人民日報》《南方周末》2001年以來的71篇文章,用質化量化相結合的方法,得到了我國媒體控煙報道的大致框架。
在這一類的研究中,其研究對象不僅局限在控煙的新聞報道,還涉及煙草廣告。例如,李玉青、曹遠、劉秀榮的《91種平面媒體煙草廣告及控煙報道刊出情況》,就監(jiān)測并統(tǒng)計分析了91種平面媒體在2013年5月13日至19日所有版面的刊出內容,對其刊登的控煙報道進行了記錄、分析和比較。
(二)中觀層面的控煙研究
這個層面多為兩個國家或兩個媒體的控煙報道比較,比較維度涵蓋議題建構、傳播策略等多個層。例如,蘇州大學顧燕的《健康傳播視角下主流網(wǎng)絡新聞媒體的控煙報道研究——以新浪網(wǎng)、人民網(wǎng)為例》,吉林大學趙微的《中美控煙報道議題建構比較研究——以〈人民日報〉和〈紐約時報〉為例》,李瑩《控煙微博的傳播策略研究——以三家控煙微博為例》等。其中李瑩的作品選取了“上海控煙”、“衛(wèi)生部控煙傳播活動”、“控煙集結號”三個控煙微博,重點分析了控煙微博的傳播策略,并指出微博在控煙傳播中存在的問題,最終為控煙微博傳播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議。
(三)微觀層面的研究
控煙報道方面研究成果最為豐富的,還是微觀層面的研究,它們著眼于一地、一報的控煙傳播,試圖從歷時性的分析中得出相應的結論,其中以一報的控煙傳播為研究對象的占絕大多數(shù)。前者如楊秀杰《2008-2012年云南控煙報道研究》,對各大媒體有關云南控煙的新聞報道作品進行內容分析,指出云南控煙議題目前在云南的實施背景、現(xiàn)實狀況、主要特點、突出問題等,倡導媒體向民眾傳達“吸煙有害健康”的信息,構造“戒煙可以減少對健康的輿論氛圍,從而推動云南控煙行動的總體進步;后者如西北大學2012年的碩士論文,《控煙報道研究——以2000-2011年〈中國青年報〉為例》,聚焦媒介控煙報道的文本內容,對控煙報道是否到位進行求證和闡釋,認為該報的報道階段性、事件性現(xiàn)象嚴重,消息來源采用不平衡,對政府作為過度呈現(xiàn),忽略了其他控煙力量,控煙措施流于空洞。
微觀研究層面另一篇值得提及的論文是陳虹、郝希群的《恐懼訴求視角下看媒體的控煙報道——以〈人民日報〉控煙報道為例》,以“煙”為關鍵字,搜索出2006年到2011年6年來的165篇報道,進行內容分析,得出了“恐懼訴求整體水平偏低,說服效果不佳”的結論,為以后的控煙傳播提供了借鑒。
其實除了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來對目前的控煙傳播研究進行歸類,還能用國內和國際兩個維度進行分類。和傳播學的其他重要議題類似,控煙傳播也是從其他國家興起,引發(fā)學者關注,在國內掀起研究高潮的。
國際上較為知名的研究控煙傳播的學者,如hye-jin paek教授,她從事控煙傳播研究多年,議題涉及青少年控煙。例如,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adolescents attend and respond to antismoking media campaigns吸煙的社會規(guī)范相關研究,如impact of norm perceptions and guilt on audience response to anti-smoking norm psas:the case of korean male smokers,媒體主張研究,如media advocacy,tobacco control policy change and teen smoking in florida。
國內的研究除了我上面提到的那些,集中度較好的是復旦大學的健康傳播研究所。例如,錢海紅/王帆/孫少晶等人的《媒介素養(yǎng)的視角:上海市中學生吸煙的知信行研究》,分析了2009年對上海市中學生有關媒介素養(yǎng)和吸煙的知信行問題的調查數(shù)據(jù),從媒介素養(yǎng)的視角為控煙工作做出努力。
三、研究缺失
(一)對傳播效果的研究有所缺失
在控煙傳播中,許多研究者把著眼點放在媒體“做了哪些”上面,簡單地呈現(xiàn)事實,而缺少媒體“做得怎么樣”,即除了議題選擇和話語分析外,很少把關注點聚焦在這些控煙傳播產生了什么樣的效果。
當然,這部分研究的缺失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傳播效果的測量很難像其他社科類研究一樣只采用文獻分析法,而要加入控制實驗法,但控制實驗法較難把控。表面上看來,將控制實驗的對象鎖定在高校的吸煙學生或都市的吸煙白領身上,已經(jīng)很大程度上縮小了調查范圍,降低了研究難度,但是整個實驗過程,既要保證問卷前后受訪者的一致性,又要反復確認他們關注了指定的微博賬號和微信公眾號,以保證數(shù)據(jù)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實在不是一項輕松的工作。
(二)研究廣度有待拓寬
在目前的控煙報道研究文獻中,除《中美控煙報道議題建構比較研究——以〈人民日報〉和〈紐約時報〉為例》外,尚未發(fā)現(xiàn)深入探究國外控煙報道的例子,尤其是幾乎沒有涉及國外社交媒體的控煙現(xiàn)狀和經(jīng)驗借鑒,沒有從橫向的角度對控煙報道進行系統(tǒng)的、全面的分析,研究視野過于狹隘,缺乏一定的廣度。因此,筆者希望能通過本研究,提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見解和建議。
控煙問題由來已久,報道歷時較長,隨著人們健康意識的逐漸加強和對控煙法令的支持度提升,媒體對這一議題的報道也越來越豐富,在對資料進行收集時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與時間,如何準確充分的對媒體的報道進行收集整理就成為本次研究中又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