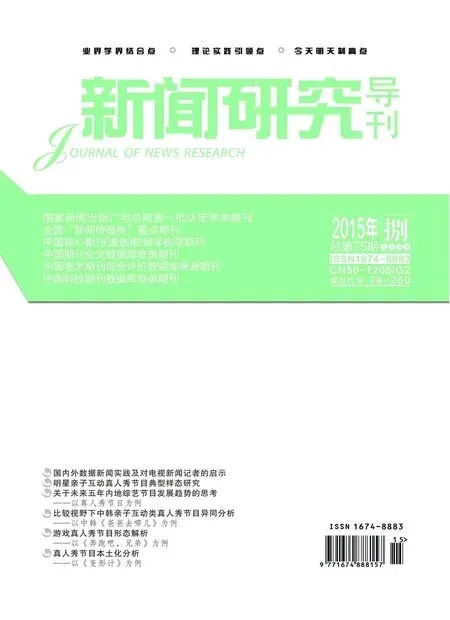淺析網絡暴力成因
吳 偉
(河海大學,江蘇 南京 211100)
網絡暴力,起源于貓撲網首創的一種搜索方式——人肉搜索,可追溯到2006年的“踩貓事件”甚至更早。關于網絡暴力的定義,學界并未給出一致的看法,我們姑且從一些經典事件中粗略總結:所謂“網絡暴力”,可以理解為在虛擬網絡空間中,對某種不符合社會道德標準的行為,采用網絡黑客的手段,[1]披露受暴者隱私,形成某種源于網絡、作用于現實的輿論壓力,對受暴人的心理和生活產生影響和制約的行為。其本質在于利用網絡和輿論的力量影響現實,但是由于網絡信息多源性,造成了對是非判斷的扭曲,加上輿論力度的控制不當,網絡暴力逐漸暴露出其“暴力”本質。
網絡暴力為何從一種揭露不道德,規范社會的手段,變成了一種暴力的工具?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虛擬社會的各種特征為網絡暴力提供了有利的生長環境。互聯網是一個開放的空間,它打破了時空限制,突破了國與國的界限,互聯網的發展使得人們的交往范圍逐漸擴大,為信息的擴散提供了更廣的方向。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信息的傳播速度加快,從而增強了輿論的力量。網絡又是一個自由的空間,當今網絡環境中,UGC逐漸取代了以往被動接收傳媒新聞的模式,網民對于信息的選擇和發布有更多的選擇性和更大的靈活性,可以自行進行信息把關,不同的教育背景和認知水平使人們對同一事件會做出不同的判斷。加之網絡的匿名性,網民可以利用一個終端隨意隱藏自己的身份以及與現實有關的個人信息,更多情況下不需要為自己的言論承擔責任,信息選擇和發表言論的隨意性也催生了網絡暴力。
其次,“把關人”理論在網絡空間中的失效。所有的信息都會經過媒介的把關,被過濾、選擇之后傳播給受眾,被過濾的事件無論其本身會造成多大的影響,都不會為受眾所知。而這些,僅僅發生在互聯網出現之前。一方面,“用戶生產內容”是網絡社會發展至今的一個特點和仍在延續的一種趨勢,信源的增加使得傳播中關鍵的一環逐漸消失,即由“把關人”把持著的信息“流動關口”,[2]信息能夠直接從信源傳給受眾,即使傳統媒介不加以報道的事件也能夠很快的通過網絡得以流傳;另一方面,網絡的開放性、自由性使得網絡信息變的海量、良莠不齊,這也決定了在網絡空間中媒體只能引導,“把關”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互聯網時代,“把關人”的威力大大減弱,一些低俗、惡劣的信息進入到網絡傳播中,如隱私揭露、謠言、偏激的輿論、攻擊和謾罵等,網絡信息的權威性和可信性大打折扣,網民的討論建立在錯誤的信息之上,網絡輿論自然很容易演變成一種網絡暴力。
第三,網民對言論自由的錯誤解讀。基于網絡的匿名性和自由性,不少網民將網絡虛擬環境中的言論自由誤解為不受限制的絕對自由,這種對虛擬社會言論自由的錯誤解讀致使網民在言論甚至行為上都逾越了自由應有的界限,演變為一種非理性的表達。例如,在網上看到的帶有侮辱性質、攻擊性質的言論等,有些甚至超出了法律劃定的邊界造成了對公民權利的侵犯,其中最常見的是對名譽權和隱私權的侵犯。我們所生活其中的現實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往往相互熟悉,掌握著彼此的身份信息,每個人都生活在“熟人”的監督之下,因而社會道德、法律規范等對個人起到強大的制約效果,人們在表達意見時基于各種顧慮會遵循這些道德與法規,在某些問題上婉轉表述甚至保持沉默。而進入到網絡虛擬空間,就脫離了人際關系、利益關系等“熟人社會”種種因素的制約,只能靠個體的自覺來維護規范,每個個體都只是一個表達意見的“符號”,法律規范等難以監管,個體就很容易沖破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去發表一些未經核實的非理性言論,在這個匿名世界中,為言論負責的觀念被大大淡化,偏激而失實的帖子早已見怪不怪。
最后,網絡暴力是一種網絡失范,甚至會衍生出一些網絡犯罪,如網絡侵權和引發一些現實中的暴力活動等。失范是由于沒有規范,犯罪是因為沒有法律的制約,網絡暴力,實則影射著網絡倫理的缺失和法律法規的不健全。一方面,人類社會所建設的一切倫理體系都是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進行的,[3]而網絡是在極度自由的環境中建立起來的,其傳播的交互性、虛擬性以及跨越時空等特點,都決定了一定的倫理體系建設所需要的時空范圍在網絡中是不確定的,因而迄今為止也未能建立起被一致認可的規范;另一方面,針對網絡空間的管理尚未有一套健全的法律,網絡的匿名和自由加大了網絡監管的難度,違法行為無法從根本上規避。法律的不完善也使得網絡暴力的受侵害者無從尋求維權的途徑,某種程度上只能忍氣吞聲,也助長了網絡“施暴者”的氣焰。虛擬社會的特性將人心底無法發泄的部分釋放出來,網絡暴力實際上只是放大了人的道德缺陷,這些缺陷在現實生活中得以被法律和規范制約,在網絡空間倫理和法律的缺失情況下,只能演化為促進網絡暴力生長的沃土。
網絡暴力是互聯網發展的一次“脫軌”或“走偏”,網絡輿論本應成為普通公眾表達意見和維護社會道德的手段,卻由于網絡自身的特性、網民的觀念偏差以及監管不力等諸多因素成了造謠、攻擊、侮辱、宣泄情緒的舞臺。但網絡暴力的出現并不意味著網絡輿論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的絕對負面因素,對癥下藥,正確利用互聯網的特性、引導受眾傳播正能量、健全相關規范和法律,網絡暴力同樣可以回歸其正常的輿論監督功能,成為造福社會的利器。
[1]張婷.從“人肉搜索”看網絡暴力[J].東南傳播,2009(3):30.
[2]李媛.虛擬社會的非理性表達——“網絡暴力”初探[D].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3]杜駿飛.網絡傳播概論(第四版)[M].福建人民出版社,第2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