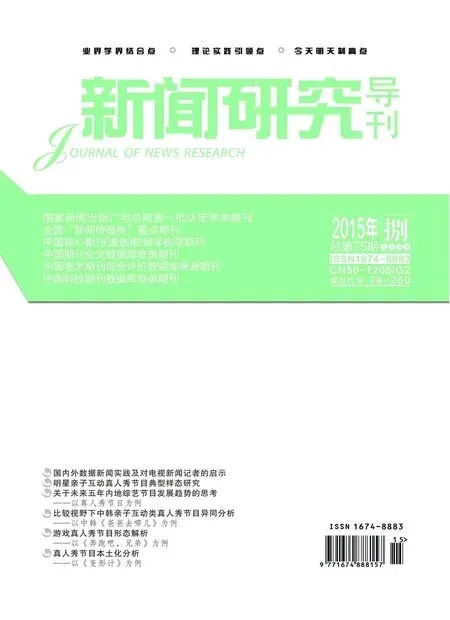網絡謠言擴散動因及應對策略研究
彭麗華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四川 成都 610000)
一、網絡謠言擴散動因分析
近年,網絡謠言治理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打擊的同時,新的謠言也不斷涌現,它們以裂變式的傳播方式在微博、微信、論壇等網絡平臺瘋轉。網絡謠言迅速擴散主要由社會因素、技術因素以及社會心理因素三個方面共同促成的。
(一)社會因素
(1)網絡時代的信息不對稱。網絡謠言產生擴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公眾沒有掌握充分信息。信息不充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信息不公開,公眾無法獲得相關信息或得到的信息較少;另一方面,信息公開,但公眾因選擇性接收信息而不能掌握全面信息。這兩種情況會導致掌握信息的一方與不掌握信息或掌握部分信息的公眾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造成公眾對事件的曲解,容易滋生謠言。[1]
盡管網絡信息時代,信息獲取的機會越多、渠道越便捷,公眾利用網絡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任何信息,從這方面來看,信息不對稱現象有所緩解。但公眾根據年齡層次、文化水平等偏頗吸收自己需要的信息,忽視其他信息,也不能全面掌握事件信息,仍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
(2)社會公信力危機。社會公信力危機表現在多個方面。例如,政府公信力、媒體公信力下降,公眾對發布權威信息的政府部門不信任、對報道事實真相的主流媒體不信任。
市場經濟條件下,媒體的經營管理關系到其生存與發展。媒體經營活動滲透到新聞策劃、報道、制作的全過程,導致假新聞泛濫。[2]一些媒體為了獲得更多經濟效益,一味迎合受眾獵奇心理,盲目追求時效性,將沒有核實真假的信息發布出去,出現了更多假新聞。部分媒體從業者違反職業道德,搞虛假新聞和有償新聞,長此以往,媒體的可信度必然遭到質疑。這種環境為謠言提供了傳播空間。
(3)社會不安全感。中國的發展進入了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是社會矛盾的凸顯時期。眾多輿情事件觸及了中國現階段社會安全、利益分配等問題,現實生活中的矛盾積壓,網絡輿論激化了社會矛盾,引發了網絡群體性事件。
風險社會中各種危機隨時可能發生,當出現了某類事件的謠言時,處于不安全社會中的公眾無法做到置身事外,出于確保安全的目的出發轉發信息,卻沒有求證信息真偽,形成了謠言的群眾基礎。
(二)技術因素
自媒體時代,每個人都成為信息發布者,個人話語權放大,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媒體輿論場成為公眾發表意見、表達觀點的平臺。網絡匿名性使部分網民自以為可以擺脫道德約束和法律制約,不必對網絡言論承擔任何后果,因而隨意發布匿名信息,炮制網絡謠言。而網絡把關人缺位使沒有經過甄別、篩選的信息不受限制地發布到網絡上,網絡謠言因此有機會進入公眾的視野。
網絡謠言的受眾群體龐大,在網民轉發和評論過程中,其影響力也急劇擴散。當謠言通過網絡媒介傳播時,它從傳統的人際傳播領域走向大眾傳播渠道,披上了“信息”的外衣,增強了偽裝性和欺騙性,[3]具有不可控性。
網絡信息監管技術落后使得謠言信息不能被及時刪除清理,對其治理也相對滯后。“關鍵字過濾”等信息過濾、屏蔽技術手段只能對已經在網絡擴散的謠言有一定的控制作用,而新的謠言內容在缺少把關人環節的網絡信息傳播中繼續發酵。
(三)心理因素
在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得不到解決,滋生了公眾的不滿情緒和心理,網絡謠言迎合了公眾心理,調動了公眾情緒,起到了很好的傳播效果。
(1)從眾心理。個體是社會群體中的一員,其判斷、認識、行為等都受到社會群體中其他成員的影響,在社會群體壓力下,大部分個體會產生從眾心理,與群體中大多數人的意見保持一致,只有少部分人能保持獨立性。群體中的主流意見在大多數人的支持下越來越強勢,持不同于主流意見的少數人群在強大的群體壓力下,害怕被社會孤立,他們要么改變原本持有的意見轉而支持主流意見,為主流意見發聲,擴大主流意見的影響力,要么選擇沉默,不再發聲,形成“沉默的螺旋”效應,其他意見的沉默從反面增強了主流意見的呼聲。在群體壓力下,公眾依附群體意見,逐漸弱化獨立思考、自我判斷能力,盲目跟風輕信謠言,信謠群體擴大,形成流瀑效應。
(2)泄憤心理。公眾對現實生活的不滿情緒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得到解決,他們迫切需要一個發泄情緒、釋放壓力的空間,網絡的低門檻、匿名性等特征成為他們的首選平臺。[4]當網絡謠言體現社會不公時,就能使網民產生心理認同,引起他們的憤怒情緒。在情緒感染下,公眾變得不理性,他們不再在乎謠言是否真實可信,只要能發泄心中的不滿情緒,他們就會轉發并用激烈的言論評論謠言信息,使謠言再次擴散。
(3)窺私心理。窺私是對他人隱私的好奇感和偷窺欲。人們總是對越私密的事越好奇,甚至會隱私窺私行為,但由于受道德規范約束,公眾在現實生活中的窺私欲被壓制,而網絡的匿名性和便捷性放大了公眾的偷窺欲,從網絡獲知他人的隱私信息,并將其放于網絡傳播,網絡謠言由此產生。一般而言,公眾人物、明星藝人的私生活和高層人士的“秘聞”類的網絡謠言正是抓住、迎合了受眾的窺私心理。[5]網絡謠言中包含的個人隱私信息能引起公眾對其的好奇心、偷窺欲,想要探究其真實性或深入了解隱私內容,謠言也就擴散開來了。
二、網絡謠言治理的應對策略
謠言經過傳播后,盡管被證偽,但其危害已經顯現。網絡謠言無法根除,但可以防治。針對謠言擴散的原因采取行之有效的針對性措施,對網絡謠言治理有積極意義。
(一)及時公開事件信息
網絡謠言的出現,“滿足了處于信息不對稱狀態下的公眾對信息的渴求,緩解了信息缺乏引起的緊張不安心理”。[6]因此,在網絡、電視、報紙等媒體上及時公布事實真相,建立一套信息發布機制和辟謠機制,提高信息透明度,滿足公眾對信息的需求,有利于抑制網絡謠言的擴散。
(二)提高網絡信息監管技術
網絡的匿名性、把關人缺位、網絡監管技術落后是網絡信息監管的短板。盡管我國已經開啟網絡實名制,但一直存在爭議,沒有完全落實。因此,有必要有效落實網絡實名制,當公眾以真實身份在網絡發言,網絡謠言將有所下降。同時,設立網絡把關人,利用技術手段對網絡信息進行篩選和過濾,及時發現、刪除網絡謠言信息,使網絡謠言無法進入傳播渠道。
(三)加強公眾媒介素養教育
媒介素養包括社會公眾認知媒介、使用媒介、參與媒介的能力。[7]針對網絡謠言治理,更重要的是提高公眾對媒介的參與能力,他們不僅要接受、處理信息,還要生產信息,這就要求公眾在網絡上要謹慎發言,不要嘩眾取寵,發表不當言論。利用網絡、報紙、電視等媒介資源開展媒介素養教育,對在校生開設媒介素養課程,有利于普遍提高社會公眾媒介素養,培養公眾的理性發表網絡言論的習慣。
(四)加強網絡法制建設
隨著《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專門法規相繼出臺,傳播網絡謠言的嚴重性受到網民重視,這對惡意發布、傳播謠言信息的造謠者、傳謠者有一定威懾作用。但還存在“法律體系不完善、法律的針對性不強、可操作性不高”等諸多問題,[8]而現有法律對造謠者、傳謠者的懲罰力度不大,傳播謠言犯罪成本低代價小使得造謠者有恃無恐。針對這些問題,必須加強網絡法制建設。一方面要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嚴厲打擊造謠者和傳謠者;另一方面要加大對造謠者的懲罰力度,提高其犯罪成本,使造謠者不敢編造惡意謠言。
三、結論
網絡謠言的擴散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社會環境因素和網絡技術因素是網絡謠言的助推手,公眾復雜的心理因素支配其行為,推動著謠言擴散,在這種環境下每一位互聯網用戶都可能成為謠言信息的傳播者。新媒體時代網絡謠言具有傳播速度快,波及范圍廣,隱蔽性強等特點,較傳統媒體時代而言社會危害進一步加深,因而必須采取相應措施治理網絡謠言。例如,及時公布事件信息,讓公眾了解事件真相,扼殺謠言生成空間等。
[1]匡文波,郭育豐.微博時代下謠言的傳播與消解——以“7.23”甬溫線高鐵事故為例[J].國際新聞界,2012(02).
[2]陳陽.重塑媒體公信力[J].視聽界,2013(06).
[3]肖紅慧.治理網絡謠言[DB/OL].人民網,http://media.people.com.cn/n/2012/0703/c346003-18435241.html.
[4]孟鴻,何燕芝.受眾心理分析視角的網絡謠言治理[J].重慶社會科學,2012(10).
[5]邱少明.規避五種心理以遏制網絡謠言[DB/OL].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118/c40537-23577425.html.
[6]陳強,方付建,徐曉林.網絡謠言擴散動力及消解——以地震謠言為例[J].圖書情報工作,2010(22).
[7]李靜宇,高雪.新媒體語境下公眾媒介素養的提升途徑[J].新聞世界,2013(06).
[8]孟鴻.比較與借鑒:網絡謠言治理的路徑探索[J].前沿,20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