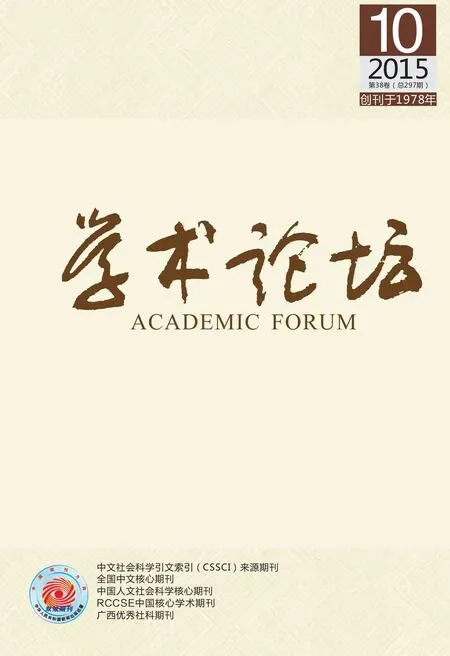倫理世界“預(yù)定的和諧”與生態(tài)文明
牛慶燕
倫理世界“預(yù)定的和諧”與生態(tài)文明
牛慶燕
一部生態(tài)文明史,就是一部“沖突”與“和諧”對立與角逐的歷史,然而,生態(tài)倫理文化的精神基地和價值目標(biāo)應(yīng)當(dāng)是“和諧”。唯有通過對生態(tài)價值世界“和諧”的預(yù)設(shè),實(shí)現(xiàn)“生命過程”的和諧,才能夠應(yīng)對“生態(tài)困境”,推進(jìn)生態(tài)自然世界“和諧”的落實(shí)。透過倫理實(shí)體之間“預(yù)定的和諧”,能夠塑造家庭、民族、生態(tài)自然世界的生態(tài)道德教育的實(shí)體“基地”;透過倫理規(guī)律之間“預(yù)定的和諧”,能夠開啟情感與理性相互融通的生態(tài)道德教育模式;透過倫理個體與倫理實(shí)體之間“預(yù)定的和諧”,能夠推動生態(tài)實(shí)踐個體向道德“主體”提升。這是走出“生態(tài)困境”的可能性前提,也是生態(tài)文明哲學(xué)新的理論基點(diǎn)和價值歸宿。
倫理世界;預(yù)定的和諧;倫理實(shí)體;倫理規(guī)律;倫理個體
在漫長的生態(tài)進(jìn)化史中,“沖突”與“和諧”的對立與角逐從未止息,然而,生態(tài)倫理文化的精神基地和價值目標(biāo)應(yīng)當(dāng)是“和諧”,并且唯有“和諧”才是生態(tài)文明世界的“應(yīng)然”與“歸宿”。因此,指向“和諧”、歸依“和諧”是倫理精神的文化本性,這是生命的文化“解釋系統(tǒng)”為人的“生命過程”建構(gòu)的文化同一性和“價值承諾”,唯有通過對生態(tài)價值世界“和諧”的預(yù)設(shè),實(shí)現(xiàn)“生命過程”的和諧,才能夠應(yīng)對“生態(tài)困境”,推進(jìn)生態(tài)自然世界“和諧”的落實(shí),進(jìn)而為當(dāng)下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實(shí)踐推進(jìn)和新時期環(huán)保規(guī)劃的落實(shí)提供深層的理論依據(jù)和政策建議,重構(gòu)生態(tài)文明哲學(xué)的理論基點(diǎn)。
一、“和諧”與“生態(tài)和諧”
在現(xiàn)實(shí)的生態(tài)自然世界,存在人與自然的對立和沖突的“現(xiàn)實(shí)”,克服“生態(tài)困境”,走出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是揚(yáng)棄沖突、實(shí)現(xiàn)辯證和諧的“生態(tài)”過程。“和諧”并不是否認(rèn)差別和對立,并非是矛盾雙方的絕對同一,而是包含著對立面的雙方相互聯(lián)系、相互依存、互惠互利、互補(bǔ)互促的思想,強(qiáng)調(diào)平衡、動態(tài)、協(xié)調(diào)與合作,因而是哲學(xué)精神層面的“包容萬物”和“兼收并蓄”,在面對沖突、協(xié)調(diào)矛盾的過程中實(shí)現(xiàn)多樣性的統(tǒng)一。因此,“和諧”是精神價值體系中倫理世界和道德世界的“文化本性”和“文化本務(wù)”,唯有通過倫理精神的“解釋系統(tǒng)”的努力才能夠?qū)Ω丁吧胬Ь场保M(jìn)而創(chuàng)造“善”的精神價值世界,“釋善”是為“致善”,透過“致善”的倫理生態(tài)實(shí)踐,進(jìn)而推進(jìn)生態(tài)“和諧”價值目標(biāo)的落實(shí),揚(yáng)棄“生存困境”,實(shí)現(xiàn)“生命過程”的和諧,最終推動“人—自然—社會”生態(tài)和諧世界的建立,實(shí)現(xiàn)生態(tài)自然世界與精神價值世界“和諧”的辯證復(fù)歸。
在文化“解釋系統(tǒng)”中,“生態(tài)和諧”必定要被“精神地”規(guī)定、把握,并被“精神地”實(shí)現(xiàn)和完成,作為人類生命的最高價值指向的“和諧”是“精神自由”的顯現(xiàn),同時也是意識與意志、認(rèn)知與沖動、知與行的辯證統(tǒng)一。因此,作為生命的文化“解釋系統(tǒng)”應(yīng)當(dāng)為人的“生命過程”建構(gòu)某種文化同一性,當(dāng)面對“生存困境”與“生態(tài)和諧”的兩難進(jìn)行價值選擇時,首先應(yīng)當(dāng)在價值直覺的基礎(chǔ)上設(shè)定某種價值承諾和價值目標(biāo),即在具體的自然生命世界建構(gòu)倫理世界“預(yù)定的和諧”。
二、倫理世界:“真實(shí)”的精神世界
倫理世界在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中被認(rèn)為是“真實(shí)”的倫理精神實(shí)體。實(shí)體的本質(zhì)是“精神”,精神是“單一物與普遍物的統(tǒng)一”,即作為“單一物”的個體通過行為向作為“普遍物”的人的生命的普遍意義和終極目的歸依。“倫理是一種本性上普遍的東西”[1](P8),實(shí)體是超越了個體和整體的“共體”與“公共本質(zhì)”,因而倫理實(shí)體是“單一物”與“普遍物”的統(tǒng)一,只有在“精神”中被把握,并只能被“精神地”認(rèn)同和接受,此時,“倫理行為的內(nèi)容必須是實(shí)體性的,換句話說,必須是整個的和普遍的;因而倫理行為所關(guān)涉的只能是整個的個體,或者說,只能是其本身是普遍物的那種個體”[1](P9)。由于“精神”具有外化自身的能力,因而“倫理實(shí)體”能夠外化為現(xiàn)實(shí),具有個別化了的具體的、現(xiàn)實(shí)的存在形態(tài),是“單一物”與“普遍物”統(tǒng)一形成的現(xiàn)實(shí)的“整個的個體”,“實(shí)體,一面作為普遍的本質(zhì)和目的,一面作為個別化了的現(xiàn)實(shí)”[1](P5)。所以,諸倫理個體與倫理元素作為“個別化的現(xiàn)實(shí)”與普遍的精神本質(zhì)和目的統(tǒng)一,形成了世界的多樣性的存在形態(tài),便構(gòu)成了“真實(shí)”的精神世界,即“倫理世界”。
“精神自由”的實(shí)現(xiàn)有其自然的“生命過程”,“倫理世界”是“生命過程”中重要的環(huán)節(jié)。現(xiàn)代社會的理性主義消解了倫理世界“和諧”的真義,從現(xiàn)實(shí)的倫理生活世界到整個道德哲學(xué)體系,“沖突”“對立”與“緊張”現(xiàn)實(shí)地存在著,“和諧”與“預(yù)定的和諧”被消解和遮蔽。
然而,倫理世界的文化本性與文化本務(wù)應(yīng)當(dāng)是、也必定是“和諧”,無論作為倫理實(shí)體存在形態(tài)的家庭與民族之間、作為倫理世界的兩種勢力的“神的規(guī)律”與“人的規(guī)律”之間還是個體與實(shí)體之間,都存在相統(tǒng)攝、過渡與融會貫通的“和諧”本性,并且“和諧”是揚(yáng)棄道德哲學(xué)內(nèi)部倫理精神“沖突”的必然途徑,只有通過倫理世界“預(yù)定的和諧”的文化解釋才能夠超越生態(tài)實(shí)踐主體的“生存困境”,克服人類在現(xiàn)實(shí)的生態(tài)自然世界遭遇的“生態(tài)困境”難題。
三、倫理世界“預(yù)定的和諧”與生態(tài)困境的超越
倫理世界“預(yù)定的和諧”是走出“生態(tài)困境”的可能性前提,也是生態(tài)文明哲學(xué)新的理論基點(diǎn),表現(xiàn)為倫理世界中諸倫理實(shí)體之間、倫理規(guī)律之間以及生態(tài)倫理個體與倫理實(shí)體之間“和諧”的價值預(yù)設(shè)與價值承諾。
(一)倫理實(shí)體之間“預(yù)定的和諧”
黑格爾在其“精神現(xiàn)象學(xué)”理論中提出了兩種倫理實(shí)體存在形態(tài),即家庭與民族,在“法哲學(xué)原理”中提出了家庭、市民社會與國家三種倫理實(shí)體存在形態(tài),不同的倫理實(shí)體存在形態(tài)之間存在差異、對立和矛盾。然而,對立與沖突并不是“倫理世界”的本質(zhì),沖突的背后“預(yù)定”了倫理世界的實(shí)體性“和諧”。如果說,“家庭”是生態(tài)道德教育的自然實(shí)體“基地”,“民族”或者說市民社會與國家是生態(tài)道德教育的最大的實(shí)體“基地”,那么,二者之間互補(bǔ)共生,“生態(tài)自然世界”則成為融“家庭”與“民族”命運(yùn)于一體的生態(tài)道德教育的最高的實(shí)體“基地”,這是生態(tài)自然世界中倫理實(shí)體之間“預(yù)定的和諧”。
首先,家庭作為自然的倫理實(shí)體,凸顯的是作為“單一物”的家庭成員與作為“普遍物”的家庭倫理實(shí)體之間的關(guān)系,即自然倫理的生命關(guān)聯(lián),是生態(tài)道德教育的自然實(shí)體“基地”。家庭體現(xiàn)了不可動搖的“普遍性”,“在這里,個人把他冷酷無情的人格揚(yáng)棄了,他連同他的意識是處于一個整體之中”[2](P43)。作為家庭成員的個體在向家庭倫理實(shí)體提升的過程中能夠不斷揚(yáng)棄自身的主觀任意性、偶然性以及冷漠的“個別化”的趨向,并通過“愛和感覺”的形式獲得家庭普遍的倫理精神,“作為精神的直接實(shí)體性的家庭,以愛為其規(guī)定,而愛是精神對自身統(tǒng)一的感覺”[2](P175)。“愛”與“感覺”訴諸某種不需加以反思的直接性,因而是一種自然的倫理情感,“所謂愛,一般說來,就是意識到我和別一個人的統(tǒng)一,使我不專為自己而孤立起來”[2](P175)。同時,“家庭”是人生旅途的第一站,同時也是個體接受道德教育的第一所學(xué)校,因?yàn)椋彝サ赖聝r值教育關(guān)涉人的生存的終極性問題,比普通的技術(shù)理性教育具有優(yōu)先性,傳統(tǒng)“修齊治平”的邏輯進(jìn)路以及“家國一體,由家及國”的發(fā)展路徑都從側(cè)面證明了家庭作為生態(tài)道德教育出發(fā)點(diǎn)的可能性與合理性。
其次,隨著家庭內(nèi)部子女的成長,原初的自然家庭在倫理上開始解體,其倫理普遍性在家庭成員的“反思”中以“假象”的形式映現(xiàn)出來,原初的自然家庭自然而然地分裂為眾多的家庭,它們之間“相互見外地對待著”,于是,開始向“民族”的倫理實(shí)體存在形態(tài)過渡,民族、市民社會與國家成為生態(tài)道德教育最大的實(shí)體“基地”。因此,民族倫理實(shí)體的形成有其共同的自然淵源與和諧的自然基礎(chǔ),“和諧”是其公共本質(zhì),作為“單一物”的民族公民向作為“普遍物”的民族倫理實(shí)體和國家倫理實(shí)體歸依與提升,普遍性的倫理精神在國家中達(dá)到了現(xiàn)實(shí),“成為國家成員是單個人的最高義務(wù)……由于國家是客觀精神,所以個人本身只有成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理性和倫理性”[2](P174)。由此,生態(tài)實(shí)踐主體唯有走出家庭、走進(jìn)社會、走向民族與國家,才能夠在更普遍的意義上接受、認(rèn)同生態(tài)道德教育,通過社會組織、社團(tuán)的教化接受科學(xué)的生態(tài)知識教育,運(yùn)用公共媒體和網(wǎng)絡(luò)的強(qiáng)大輿論導(dǎo)向和制約作用對危害環(huán)境的行為予以揭露和抨擊,對有效保護(hù)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行為加以提倡并弘揚(yáng),從而營造良好的生態(tài)道德教育氛圍,提高全民的生態(tài)意識,建構(gòu)普遍的生態(tài)道德教育“基地”。
最后,無論自然的家庭倫理實(shí)體中的家庭成員,還是民族倫理實(shí)體中的民族公民,經(jīng)過家庭的生態(tài)情感的熏陶教化與社會、國家的生態(tài)理性教育后,應(yīng)當(dāng)把內(nèi)化的生態(tài)理性認(rèn)知運(yùn)用于具體的認(rèn)識自然、改造自然的生態(tài)實(shí)踐行動中,于是,走入具體的生態(tài)自然世界,通過對復(fù)雜、生動的“生態(tài)困境”的體認(rèn),深化自身的生態(tài)理性認(rèn)知,克服人類自身生產(chǎn)生活方式的非合理性,緩解“生態(tài)困境”。因此,具體而生動的生態(tài)自然世界融家庭、民族與整體人類的命運(yùn)于一體,并且是對生態(tài)實(shí)踐主體進(jìn)行生態(tài)道德教育的最為深刻和最高的倫理實(shí)體的“基地”。
(二)倫理規(guī)律之間“預(yù)定的和諧”
倫理世界中各倫理實(shí)體所依循的倫理規(guī)律不同,“實(shí)體成了一種自身分裂為不同方面的倫理本質(zhì),它分裂為一種人的規(guī)律和神的規(guī)律”[1](P5)。“神的規(guī)律”是家庭自然倫理實(shí)體及其家庭成員的行為所遵循的規(guī)律,“人的規(guī)律”是民族倫理實(shí)體及其民族公民的行為所遵循的規(guī)律,兩種規(guī)律的作用方向不同,從而造就了家庭成員與社會公民兩種倫理精神的矛盾。然而,“神的規(guī)律”與“人的規(guī)律”并非存在某種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超越差異與對立,應(yīng)當(dāng)發(fā)現(xiàn)二者之間“預(yù)定的和諧”,從而推動統(tǒng)一的倫理世界的“共生和諧”。在“神的規(guī)律”的引導(dǎo)下能夠訴諸“愛”的情感化的生態(tài)道德教育模式;在“人的規(guī)律”的啟發(fā)下能夠訴諸社會公民的生態(tài)道德法則的“理性”教育模式;“神的規(guī)律”與“人的規(guī)律”辯證契合,進(jìn)而訴諸保護(hù)自然生態(tài)家園的情感與理性相互融通的生態(tài)道德教育模式,并遵從“自然生態(tài)規(guī)律”,這是生態(tài)自然世界中倫理規(guī)律“預(yù)定的和諧”。
首先,“神的規(guī)律”是家庭自然倫理實(shí)體的規(guī)律,同時也是家庭直接的倫理精神的規(guī)律。作為“單一物”的家庭成員及其自我意識服從“神的規(guī)律”的支配,它訴諸于某種不可更改的家族血緣倫理關(guān)系,依靠某種毋需加以反思的“愛”的情感和感覺加以維系,在“神的規(guī)律”的引導(dǎo)下和家庭直接性的“愛”的情感的啟發(fā)下,生態(tài)道德教育能夠訴諸情感化的教育模式。情感直覺力與倫理沖動力在走向生態(tài)實(shí)踐過程中具有無可比擬的優(yōu)越性,“但愛是感覺,即具有自然形式的倫理”[2](P175)。在自然之“愛”的導(dǎo)引下,生態(tài)實(shí)踐主體能夠向作為“普遍物”的人的“類本質(zhì)”提升,意識到人類與作為“生命之源”的生態(tài)自然世界的一體相依性,從而對自然生命系統(tǒng)產(chǎn)生“愛”的依戀之情,珍惜生命、熱愛自然。
然而,無論是家庭中的“愛”還是生態(tài)世界的“情感”心性教育都具有自身局限性,它們都建立在“生命直覺”基礎(chǔ)上,具有不確定性。生態(tài)實(shí)踐主體只有在作為民族實(shí)體的關(guān)系中,在作為社會公民和國家公民的意識中,才能獲得自我確證,“因?yàn)橐粋€人只作為公民才是現(xiàn)實(shí)的和有實(shí)體的,所以如果他不是一個公民而是屬于家庭的,他就僅只是一個非現(xiàn)實(shí)的無實(shí)體的陰影”[1](P10)。當(dāng)家庭向民族提升時,理性反思便代替了直接性的情感,“人的規(guī)律”便取代了“神的規(guī)律”,因此,生態(tài)道德教育不能否定“理性化”的道德教育方式。
其次,“人的規(guī)律”是民族倫理實(shí)體或者市民社會與國家倫理實(shí)體的“規(guī)律”,它決定民族、市民社會、國家倫理實(shí)體及其內(nèi)部個體的意識與行為。作為民族國家的公民具有一種理性的反思意識,以對民族或社會與國家倫理實(shí)體的普遍本質(zhì)的歸依、認(rèn)同與維護(hù)為真義,這種實(shí)體性的“精神”意識滲透于個體并通過實(shí)踐行為進(jìn)行外化,便凝結(jié)為“民族精神”。于是,在“人的規(guī)律”的啟發(fā)下,生態(tài)道德教育應(yīng)當(dāng)彌補(bǔ)“情感”心性教育的不足,訴諸情理主義的道德教育方式。生態(tài)道德教育在民族、國家倫理實(shí)體范圍內(nèi)的落實(shí)應(yīng)當(dāng)兼顧契約精神、權(quán)利與義務(wù)對等精神以及社會正義理念等,在生態(tài)道德法則的教化中締造民族公民的生態(tài)道德素養(yǎng),“理性的道德教育是完全可能的”[3](P7),“當(dāng)?shù)赖麻_始成為理性化的道德時,并未失去其基本要素;通過世俗化這一事實(shí),道德反而會變得更豐富,獲得新的要素”[3(P14-15)]。因而,理性能夠?yàn)榈赖陆逃峁┐賱恿Γ鷳B(tài)道德教育在民族公民的倫理進(jìn)路中能夠通過生態(tài)倫理道德法則的教化,把生態(tài)道德規(guī)范和自然世界理性化的規(guī)范倫理精神傳達(dá)給生態(tài)實(shí)踐主體,構(gòu)建民族公民個體合理性的生命秩序與社會生活秩序,培養(yǎng)公民健全的生態(tài)意識與生態(tài)人格,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生態(tài)理性知識與道德價值信仰、認(rèn)知導(dǎo)向與價值構(gòu)建相統(tǒng)一的公民生態(tài)道德教育范式,當(dāng)理性的道德灌輸與社會公民的心性價值相交融,融入生態(tài)實(shí)踐主體的意識深層時,便能夠產(chǎn)生巨大的生態(tài)實(shí)踐效應(yīng)。
最后,“自然生態(tài)規(guī)律”決定自然生命世界及其整個人類的命運(yùn),尊重生態(tài)規(guī)律、保護(hù)自然生態(tài)家園的生態(tài)道德教育應(yīng)當(dāng)訴諸“理性”與“情感”相互契合的教育模式。在“自然生態(tài)規(guī)律”的導(dǎo)引下,生態(tài)道德個體走出家庭,走進(jìn)社會、走向國家和民族,在具體的生態(tài)自然世界進(jìn)行生態(tài)道德教育,應(yīng)當(dāng)建構(gòu)“理性”與“情感”整合的道德教育模式,體現(xiàn)客觀約束性與主體能動性、外在規(guī)范性與內(nèi)在主體性的辯證統(tǒng)一,實(shí)現(xiàn)生態(tài)道德認(rèn)知導(dǎo)向與生態(tài)價值構(gòu)建、理性教育與情感教育的統(tǒng)一。在理性與情感、主體性與規(guī)范性之間,理性主導(dǎo)情感、情感承載理性,外在規(guī)范性制約個體主體性,個體主體性承載外在規(guī)范性,其終極價值指向是在遵循“生態(tài)自然規(guī)律”的前提下,善待生命、保護(hù)自然,實(shí)現(xiàn)人與自然的“生態(tài)和諧”,推進(jìn)人的自由與全面發(fā)展。
(三)倫理個體與倫理實(shí)體之間“預(yù)定的和諧”
在倫理世界中存在個體與實(shí)體之間的矛盾,個體是構(gòu)成實(shí)體的原素。“在考察倫理時永遠(yuǎn)只有兩種觀點(diǎn)可能:或者從實(shí)體性出發(fā),或者原子式地進(jìn)行探討,即以單個的人為基礎(chǔ)而逐漸提高。后一種觀點(diǎn)是沒有精神的,因?yàn)樗荒茏龅郊喜⒘校癫皇菃我坏臇|西,而是單一物和普遍物的統(tǒng)一。”[2](P173)因此,“從實(shí)體性出發(fā)”與“原子式地進(jìn)行探討”的實(shí)踐方式能夠帶來不同的實(shí)踐結(jié)果,這是二者的差異和對立,但同樣存在二者關(guān)系中的“預(yù)定的和諧”。作為“單一物”的生態(tài)實(shí)踐個體具有向倫理“實(shí)體”歸依的可能性與必然性,無論是家庭成員向家庭倫理實(shí)體的歸依、民族公民向民族倫理實(shí)體的歸依還是生態(tài)實(shí)踐個體向自然生命共體的歸依,都體現(xiàn)出“單一物”與“普遍物”統(tǒng)一的本質(zhì)性。個體只有向?qū)嶓w歸依,實(shí)現(xiàn)“單一物”與“普遍物”的統(tǒng)一,獲得個體的“實(shí)體性”,才能夠克服自身的偶然性與主觀任意性,進(jìn)而克服倫理世界的“倫理—道德”悖論,建構(gòu)生態(tài)和諧世界。
在倫理世界中,“諸倫理本質(zhì)以民族和家庭為其普遍現(xiàn)實(shí),但以男人和女人為其天然的自我和能動的個體性”[1](P7)。“神的規(guī)律”與“人的規(guī)律”,最后落實(shí)到“男人和女人”兩種不同的倫理性格和實(shí)踐個體。在具體的生態(tài)自然世界存在無數(shù)作為“單一物”的生態(tài)實(shí)踐個體,生態(tài)實(shí)踐個體只有向作為“生命之源”的生態(tài)自然世界歸依,在對自然生命實(shí)體不斷地反思與踐行中才能夠克服自身的主觀任意性、盲目性與偶然性,不再是飄忽的“陰影”,成為真實(shí)的自然生命實(shí)體。生態(tài)實(shí)踐個體向自然生命共體歸依的這種“普遍性”和“悲愴情素”,是“滲透個體的整個存在的、決定著他的必然命運(yùn)的一種感情因素”[1](P27)。由此,生態(tài)實(shí)踐個體獲得了自然生命共體的“實(shí)體性”,明確了自然作為人類的“生命之源”與人類作為“自然之子”的倫理信條,便從道德形上的意義層面獲得了生態(tài)“倫理精神”,在“類本質(zhì)”的精神感召下,體現(xiàn)自然生命共體的普遍本質(zhì),向道德“主體”提升,最終走出生態(tài)困境,走向生態(tài)自然世界的“綠色和諧”。
[1]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下卷)[M].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6.
[2]黑格爾.法哲學(xué)原理[M].范揚(yáng),張啟泰,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6.
[3]愛彌兒·涂爾干.道德教育[M].陳光金,等,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責(zé)任編輯:胡彩芬]
牛慶燕,南京林業(yè)大學(xué)江蘇環(huán)境與發(fā)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學(xué)博士,江蘇南京210037
C91
A
1004-4434(2015)10-0021-04
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青年項(xiàng)目“發(fā)展中國家的生態(tài)文明理論研究”(12CZX066);國家重大招標(biāo)課題“現(xiàn)代倫理學(xué)諸理論形態(tài)研究”(10AZX004);江蘇高校優(yōu)勢學(xué)科建設(shè)工程資助項(xiàng)目“環(huán)境科學(xué)與工程”(11SJB05)
- 學(xué)術(shù)論壇的其它文章
- 建立現(xiàn)代農(nóng)產(chǎn)品物流與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結(jié)構(gòu)
——基于西方發(fā)達(dá)國家農(nóng)產(chǎn)品物流分析 - 關(guān)于我國現(xiàn)當(dāng)代出版業(yè)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問題的思考
- 中國文化軟實(shí)力的內(nèi)容架構(gòu)及提升路徑探究
- 房價指數(shù)、CPI與社會消費(fèi)水平
——基于脈沖響應(yīng)和方差分解的一個解釋 - 大學(xué)生創(chuàng)業(yè)帶動就業(yè)的時滯效應(yīng)研究
——基于數(shù)學(xué)建模方法 - 需求、資源與能力:旅游開發(fā)致貧效應(yīng)的機(jī)理分析
——基于贛瓊兩個旅游村的實(shí)地調(diào)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