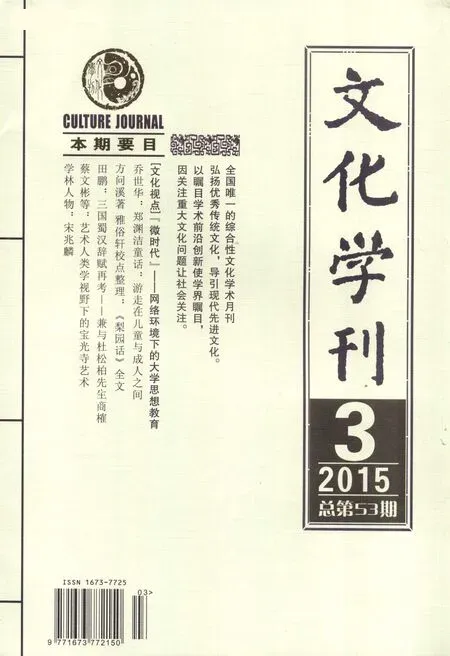論中國古代的舉止禮儀
彭孝軍 李永超
(河北大學歷史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論中國古代的舉止禮儀
彭孝軍 李永超
(河北大學歷史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每個人的身體作為客觀存在,不僅指生理層面的肉體,還包括歷史、文化、思想等社會、精神層面的因素。身體是自我認知以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溝通的起點和基礎,在任何時代,身體問題都是一個人,一個社會,乃至一個國家和民族所關注的基本問題。作為文明發展的階段性產物,中國古代的舉止禮儀全面、系統地詮釋了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修身理念,本文將以古代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坐立行走禮為主要研究內容,探討古人如何在舉手投足之間踐行舉止禮儀,實現以禮正身的目標,進而挖掘古代舉止禮儀所蘊含的巨大文化價值和社會實踐功能。
舉止禮儀;坐立行走禮;價值和功能
起源于商周時代的古禮文化源遠流長、包羅萬象、博大精深,可以說“禮”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高度凝練和概括。禮儀制度自古以來就是“立國經常之大法”“揖讓周旋之節文”,具有社會政治規范和道德行為規范的雙重作用,舉止禮儀則是古禮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舉止禮儀就是指古代禮典所規定的,人們在人際交往的各種場合中的身體行為規范。與融合了西方元素的現代禮儀大不相同,流傳兩千余年的中國古代舉止禮儀于揖讓進退之間無不展現著底蘊深厚的華夏品格和倫理道德觀念。隨著先秦兩漢時期禮學的重構與不斷完善,《儀禮》《禮記》等儒家經典和官方禮典對舉止禮儀做出了明晰的分類和闡發,使舉止禮儀不斷系統化、精細化。后世禮制規范則多有流變,尤其是魏晉以降“胡風”傳入后,舉止禮儀以及稱謂、服飾穿戴等禮俗為之一變。因此本文主要以先秦兩漢時期的經典以及這一時期的考古資料作為主要參考內容,通過這些中華元典更能真切地解讀傳統禮儀文化的內涵與核心精神。
一、“坐”的禮儀
“舉止”一詞最早見于《漢書·五行志中之上》所記載的“舉止高,心不固矣。”顏師古注:“止,足也。”[1]止的本義就是腳趾,這里的“舉止”就是“舉足”的意思,后來“舉止”引申為行動、舉動之意。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身體舉動不外乎坐立行走,然而古代對坐立行走的定義和禮儀規范與現代大相徑庭。首先來看“坐”的禮儀,中國古代的坐姿經歷了從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的轉變。先秦兩漢時期,“跪坐”于席上為正式坐姿,這種坐姿臀部坐在腳跟上,腰背挺直,男子的手平行放于兩膝之上,女子的手交叉放于身前,這種傳統坐姿給人一種端莊優雅、安適和諧的美感,也是一種很好的修身方式。魏晉以降,北方游牧民族的“胡床”、椅子等坐具傳入中原,至唐宋以后這些新式坐具得到普遍使用,垂足而坐的坐姿也逐漸取代了傳統的“跪坐”,本文要介紹的坐姿正是傳統的“跪坐”及其變體。
西漢長沙王太傅賈誼在其著作《新書》中細致地描述了古代的坐姿規范。書中把坐姿分為四類,分別為經坐、共(恭)坐、肅坐和卑坐。四種坐姿的基本要求大體相同:臀部坐于腳跟之上,身體重心落于腳面、腳踝和小腿上。“坐以經立之容,胻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2]這四種坐姿的差別在于頭部姿勢和視線落點,經坐(圖一)即正襟危坐,水平目視前方,姿態端莊,時刻關注對方的舉動,以便與之交流;共(恭)(圖二)時頭微俯,大致目視對方膝蓋,以示恭敬。卑坐(圖三)時則需低頭垂肘,更顯謙卑;肅坐雖然是仰首而視,但是也要有一定的限度。

圖一:陜西臨潼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秦坐俑(經坐)

圖二:秦代坐俑(共坐)

圖三:卑坐

圖四:漢代坐俑(跽坐)
除以上四種常規坐姿外,古代還有許多變體坐姿,如跽坐、箕踞、趺坐等。如圖四所示,跽坐與經坐類似,但與之不同的是,跽坐時臀部要離開雙足,挺直上身,兩膝著地,亦稱“長跪”。由坐而跽的坐姿變化,多表示對對方的敬意或情感上受到震動,如鴻門宴上,樊噲得知沛公有難,帶劍擁盾闖入軍門,瞋目而視項王,“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3]顯然對于樊噲突然闖入帳中,項羽頗為震驚,心生警惕,所以才“按劍而跽”,坐姿由放松而緊張,描述頗為形象。又如戰國時期著名政論家范雎由魏入秦,期望得到秦昭王的賞識,然而他起初并未像蘇秦、張儀那樣鋒芒畢露,而是對秦昭王謹言慎行,三緘其口。“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4]秦王向范雎賜教,范雎不置可否,唯唯再三,在“宮中虛無人”的情況下,秦王以帝王之尊“跪”“跽”而與范雎言,充分表現了他對范雎求教心切的心情。現代社會中如有尊長、客人駕臨,我們都要由座位上起身以示敬意,也緣于“由坐而跽”的傳統禮儀觀念。

圖五:秦箕踞姿陶俑

圖六:商代貴族箕踞白石雕
箕踞是一種輕慢不雅、不拘禮節的坐姿,如圖五、圖六所示,臀部著地,伸開雙腿,狀如簸箕;或兩腿彎曲,以足底著地。這種坐姿通常表達了輕視、傲慢,甚至仇視的情感,如《莊子·至樂》記載“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前來吊唁莊子亡妻,莊子卻“箕踞鼓盆而歌”,既不近人情,又不合禮數,由此展現了莊子超脫的生死觀。又如《史記》中記載:“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5]眾所周知,劉邦是一個玩世不恭、不拘禮節的人,謀士酈生請見劉邦,劉邦卻踞坐洗腳而與之言,很失禮,被酈生駁斥后方以禮相待。劉邦在做了皇帝之后,甚至由于“箕踞”招來殺身之禍,《史記·田叔列傳》記載:“會陳豨反代,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嚙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于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6]由于漢高祖箕踞而罵趙王,因此趙王的臣下們認為主公受辱,怒不可遏,意欲犯上作亂,遭到趙王駁斥后,以貫高為首的大臣們決定私自行刺高祖,幸而陰謀提前敗露,高祖才幸免于難。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古人對于舉止禮儀十分看重,而箕踞的坐姿顯然是對他人的不敬甚至是侮辱,由于箕踞失禮甚至會造成嚴重的矛盾沖突。
此外,還有一種坐姿稱為“趺坐”,姿勢為兩足交叉,盤腿而坐,類似于佛教參禪打坐的姿勢,所以又稱“跏趺坐”。從史料記載來看,此種坐姿的稱呼出現較晚,大體在隋唐以后,“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無義理。’于是訓令改之。”[7]隋文帝認為倭王風俗信仰怪異,聽政時居然“跏趺坐”,“此太無義理”,勒令其改正,可見“跏趺坐”也是一種輕慢、不合禮數的坐姿。
以上介紹了幾種基本坐姿,然而在古代具體的人際交往過程中,還有更為細致的“坐”的禮儀規范,成書于先秦兩漢時期的“三禮”(《周禮》《儀禮》《禮記》)是古代禮樂文化的理論形態,其中《禮記》對禮法、禮義作了最權威的闡發,對歷代禮制的影響最為深遠。《禮記》中所記載的不同社交場合中的坐立行走禮非常全面、豐富,不僅涉及到舉止規范,還包括與之相配合的言語、儀容規范。
《禮記》中“坐”的禮儀強調“莊重”“敬讓”,主要體現在“侍坐于長者”時,如“侍坐于所尊敬,無余席。……上客起”[8]“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9]“虛坐盡后,食坐盡前。”[10]侍坐于尊長,要就近而坐,“狎而敬之”,表現出對長者的親近和尊敬。尊者有其他客人前來拜訪,侍坐者也要起身表示敬意。作為晚輩,坐時不能選擇室中西南隅和中席,因為那是尊者的位置。吃飯進食要盡量往前坐,避免飯菜掉落,玷污坐席,非進食時要盡量靠后坐,以示謙恭。侍坐于長者時,除了要注意以上身體規范外,與之相應的言語、儀容規范也同樣重要,“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剿說,毋雷同,……侍坐于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11]坐時要鎮定自若,長者未提及的話題不要東拉西扯地說。聆聽老師教誨時要虔誠,表情要端莊,要等老師把話講完再回答,插嘴或隨聲附和都是不可取的。向老師請教書本知識要起立,請老師進一步詳細講解也要起立,以示對老師的尊重。除了“侍坐于長者”,在公共場合與人同坐也要表現得莊重,并且不妨礙他人。“若夫坐如尸”[12]“并坐不橫肱”[13]坐時要像代死者受祭的人那樣矜莊,與人同坐不要橫起胳膊,以免妨礙他人。
以上介紹了古代幾種主要的坐姿以及不同社交場合中“坐”的禮儀,從容端莊的坐姿展示了雍容、優雅、包容的華夏品格,舉手投足間也詮釋了“尊親”“尊師”“敬長”“禮讓”的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觀念。

圖七:秦陵立將軍俑

圖八:漢初陶立俑(共立)

圖九:石磬
二、站立和行走的禮儀
賈誼在其著作《新書》中將站姿分為四類,分別為經立、共(恭)立、肅立和卑立,“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14]經立時目視前方,腰部挺直,肩部放平,兩臂環抱,自然下垂,猶如抱鼓。雙腳站立時相隔二寸,衣帽整齊,頭和身體不能亂動。如圖七所示,秦兵馬俑就是標準的經立姿勢,此種站姿給人一種莊重、從容之感。石磬作為古代的一種打擊樂器常與編鐘配套出現,“微磬曰共立”,共(恭)立(如圖八)時稍稍彎腰,比圖九所示石磬的彎曲程度稍減。而肅立則與石磬的彎曲程度相當,大致為135度,顯然所表達的禮數也更重,一般古代大臣覲見國君和諸侯時才采用這種站立姿勢。最為謙卑的站立方式是“卑立”,古人腰間常戴玉佩,“卑立”時要讓腰間玉佩垂直落下才算合乎標準,身體大致要彎曲呈90度。
上述不同站姿主要通過身體彎曲程度加以劃分,不同的身體語言所傳達的尊崇、敬讓也有輕重等差。《禮記》中對站立的禮儀有更為具體的規定,如“立如齊”[15]“立毋跛”[16]“立必正方,不傾聽”[17]“立不中門”。[18]站立時要像參加祭祀或典禮一般恭敬,雙腳并立,不要將重心偏于一足之上。與人站立交談,身體要端正,不要斜著身子聽人講話,那樣是不尊重對方的表現。站立時不要立于當中的門口,因為那是尊者所過之處,晚輩當避讓。可見,在與人交往過程中,莊重得體的站姿表現著一個人的品格修養和對對方的尊重,因此古人十分看重。
得體的舉止禮儀是為了表達莊重、敬讓的內心情感,如果并非發自內心而只是程式化地遵守站立的禮儀規定,則會變成“僵立”,會給對方一種不自然、不真誠的感覺。不能踐行禮義的舉止規范只可稱為“儀”,只有在具體舉止儀節中真誠貫徹禮義,才能傳遞給對方真情實感,并實現身心整體的修養與升華。
古代的行和走與現代的行走含義不同,“步,行也,趨,走也……步徐,趨疾”“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說文解字》)可見古代在不同場合的行和走有著嚴格的緩急之分。古代的行走禮儀規范包括腳步的輕重快慢、體態儀容等,如古籍中對人物行走的描述經常出現“趨”“翔”兩個字,“趨”為快步行走之意,書中人物往往是因為身處莊重場合,要表達自己敬畏、謹慎的內心情感,因此才“趨進”“趨退”“趨走”,而“翔”是指行走時像鳥張開翅膀一樣張開雙臂,通常是為了表達一種輕松愉悅的心情。
《禮記》中對于“與長者同行”以及于祭祀場所、朝堂之上等莊重場合的行走禮儀多有規定,首先是與長輩同行時的行走禮儀,“為人子者……行不中道”[19]“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20]“從于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21]道分左中右,作為晚輩,不要于中道行走,因為中道是尊者行走之處,晚輩當避讓。路遇同自己父親年齡相仿的長者,應禮讓對方先行;遇到與兄長年齡相仿者,并行稍后,按輩分次序排列而行;即使是同輩朋友,行走時也不可爭先。與老師同行,不能私自跑到路的另一邊與人交談,那樣會顯得冷落、不尊重老師。路遇老師,要快步上前,拱手正立,這樣才顯得恭敬、莊重。此外,在不同的正式場合中,對行走的姿態、步頻等也有要求,“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22]由于堂上空間狹小,玉器貴重,在堂上或手執玉器時都不宜行走過快,在堂上應當細步而行,堂下正步而行。室內空間狹小,不宜張開手臂大搖大擺地行走,以免妨礙他人。此外,在婚喪嫁娶、慶典儀式等場合也有具體的行走禮儀規范,如舉行祭祀儀式時,“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23]舉行秋嘗之祭時,孔子端著祭品獻于親人的靈位時,走路很快,步子急促,體現了祭祀儀式上的孔子莊重、敬謹的體態和內心情感。以上主要介紹了與長者同行、路遇長者以及祭祀儀式上的行走禮儀,這些行走禮儀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古代宗法制等級觀念,但其中所蘊含的尊親、敬長、尊師等良好道德品質仍有很大借鑒價值。
《論語·鄉黨》篇記錄了孔子在朝廷、宗廟、鄉學等不同場所行走時的體態儀容:“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24]朝廷公門本來非常高大,而孔子卻曲身進入,好像公門不能容身一樣,形象地描述了孔子過公門時畢恭畢敬的身姿。走側門而非中門,因為中門專為國君出入開放。不踩門限,因為那是失禮的舉動。無論國君在與不在,路過國君所在的位置時都要正色快行,謹小慎微,以此表達對國君的敬畏和尊重。上堂時兩手要提起衣服的下擺,以免腳踩摔倒,有失禮容。下堂后面色才和緩放松,輕快地行走,回到原位站立,仍然保持踧踖(恭敬)之貌。隨著不同場景的的變換,孔子行走時時而謹慎莊重,時而愉悅放松,把舉止禮儀演繹成了身體的藝術,頗具美感。這種外在舉止儀容的變換既是內心情感的表達,反之又由外而內強化著“誠敬”的道德理念,是一種身心互動的身體修行。
三、舉止禮儀的文化價值與社會實踐功能
中國是傳承數千年的禮儀之邦,“禮”作為事實上的不成文法,維護著歷代王朝的統治階層和整個社會的秩序。時至今日,作為身體行為規范的舉止禮儀,其政治功能已不復存在,然而其所蘊含的巨大文化價值和社會實踐功能則不容忽視。
首先,中國古代舉止禮儀的內容之豐富,價值之巨大,對于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古代舉止禮儀“緣人情而作”,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在“身體”上的具體展現,每一個致力于成為“謙謙君子”的中國人都于舉手投足之間踐行著“文質彬彬”的舉止規范,彰顯著雍容典雅的禮儀風貌。舉止禮儀不僅是個人修養的展現,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不同于西方文化所宣揚的,主張縱欲的“酒神精神”,中國傳統文化崇尚“禮樂精神”,強調“發乎情,止乎禮”,要求適時地控制身體的感性欲求,“強調感性中的理性,自然性中的社會性。”[25]認為通過對人的動作、行為、言語、儀容等外在身體活動進行規訓,能使人的內心情感更加成熟,更具“人性”與社會性,“無過無不及”。可以說,中國古代的舉止禮儀既在一定程度上由外而內地塑造了華夏兒女的民族性格,又是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外化表現。正是通過舉止禮儀來不斷踐行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具有華夏品格的文化印記才代代相傳。當前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綜合競爭力顯著增強,而文化軟實力則有待進一步加強。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若想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彰顯特色鮮明的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而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的構建決不能與傳統割裂開來。中國古代的舉止禮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標志,蘊藏著巨大的文化價值,我們應當本著理性、辯證的態度,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將底蘊深厚的中國禮文化轉化成每個人舉手投足間的禮儀風度展示給全世界。
此外,作為古禮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舉止禮儀以每個具體的社會成員為載體,揖讓進退之間詮釋著“敬讓”“忠孝”“仁義”“長幼有序”等中華傳統美德,其中所蘊含的修身養性、教化民眾的社會實踐功能不容忽視。“從禮產生、發展的邏輯順序看,對作為獨立個體的人的道德完善與人性培養,以及作為群體成員的人的理性教化和社會性規范是禮最早、最基本的功能。”[26]翻閱史書,古代社會生活中循禮與失禮之間的爭論和矛盾沖突屢見不鮮,可見禮儀規范在古代社會具有不可替代的風俗教化作用。當今社會在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道德滑坡狀況嚴重,出現了個人價值觀扭曲、公共場所秩序混亂、誠信缺失等不良現象。《大學》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27]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雖令不從。”[28]孟子也說:“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29]要實現社會的和諧有序,歸根到底是解決人的問題,得體的舉止禮儀不僅能完善自我,提升個人文化修養,更能減少社會交往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沖突,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實現社會安定和諧,因此,重新樹立正確的個人價值觀,重塑社會成員的舉止行為規范就顯得尤為重要。作為時代發展的產物,中國古代的舉止禮儀大多已不適用于現代社會,然而其中所包含的儒家思想中修身養性、教化民眾的古禮精神則依然與中國本土文化相契合,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和作用。如何借鑒古禮精神的道德教化和社會性規范功能,重新制定符合中國當代社會文化土壤的舉止禮儀規范,事關每個社會成員精神素養的提升和整個社會精神文明的進步,是一個亟待解決的文化課題。
禮文化堪稱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能否將其發揚光大,關乎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衰。中國古代的舉止禮儀作為一種“形體美”“身體的藝術”,是禮文化的重要載體和表現形式,文化價值與社會實踐功能巨大,有待于我們進一步去發掘,去弘揚!

泥模藝術——落馬湖
[1][東漢]班固.漢書·卷二七中之上志第七中之上[M].北京:中華書局,1962.1356.
[2][14][西漢]賈誼.閻振益,鐘夏校注.新書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0.227-228.227.
[3][西漢]司馬遷.史記·卷七·本紀第七[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3.313.
[4][西漢]司馬遷.史記·卷七九·列傳第一九[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3.2406.
[5][西漢]司馬遷.史記·卷八·本紀第八[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3.358.
[6][西漢]司馬遷.史記·卷一百四·列傳第四十四 [M].北 京: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社,1963.2775-2776.
[7][唐]魏征等.隋書·卷八十一·列傳第四十六[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2.1826.
[8][9][10][11][12][13][15][16][17][18][19][20][21][22][23][清]朱彬.禮記訓纂[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7.20.11.19.19-20.3.17.3.21.13.11.11.208.13.17.704.
[24][27][28][29][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3.112.5.135.260.
[25]李澤厚.華夏美學·美學四講[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16.
[26]張自慧.禮文化的價值與反思[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194.
【責任編輯:周 丹】
K892.9
A
1673-7725(2015)03-0194-07
2014-11-20
彭孝軍(1988-),男,河北唐山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清史、中國古代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