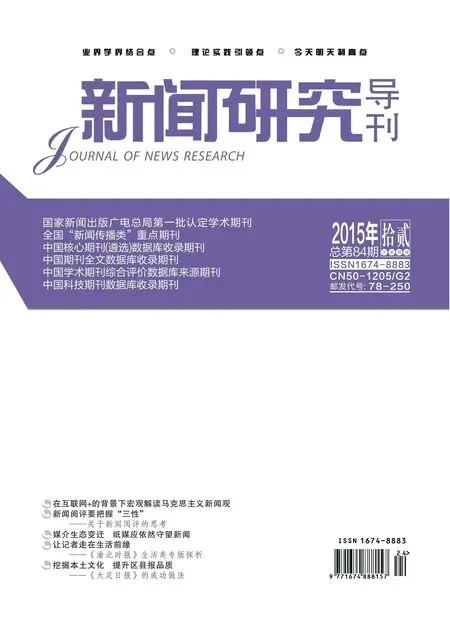女大學(xué)生被殺事件的系列化呈現(xiàn)問題分析
向 可
(華東政法大學(xué),上海 200042)
女大學(xué)生被殺事件的系列化呈現(xiàn)問題分析
向 可
(華東政法大學(xué),上海 200042)
本文以女大學(xué)生被殺案的輿論熱潮為視角,透視新媒體時(shí)代網(wǎng)絡(luò)熱點(diǎn)事件系列化呈現(xiàn)問題,并對(duì)其呈現(xiàn)路徑、傳播機(jī)制及其負(fù)面影響進(jìn)行剖析,為類似事件的呈現(xiàn)與報(bào)道提供借鑒。
傳播機(jī)制;刻板印象;二次傷害
2014年8至9月,短短的三十幾天里,網(wǎng)上接連曝出多起女大學(xué)生被殺事件引發(fā)關(guān)注,一時(shí)間輿論風(fēng)起云涌。這一系列事件的出現(xiàn)揭示了伴隨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的來臨,熱點(diǎn)事件由過去的孤立存在逐步走向關(guān)聯(lián)化的現(xiàn)象,并形成了以主體、主題、情緒等為關(guān)聯(lián)要素的輿情集和輿情簇?fù)怼#?]相較于網(wǎng)絡(luò)熱點(diǎn)事件的形成規(guī)律、輿論監(jiān)督與引導(dǎo)等話題的炙手可熱,系列化呈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鮮少有人問津。本文則以女大學(xué)生被殺事件為切入點(diǎn),對(duì)系列化呈現(xiàn)的相關(guān)問題進(jìn)行分析。
一、女大學(xué)生被殺案系列化呈現(xiàn)
網(wǎng)絡(luò)熱點(diǎn)事件是公民行使民主權(quán)利、媒體發(fā)揮自身職能、政府監(jiān)測社會(huì)環(huán)境、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徑。近年來,網(wǎng)絡(luò)熱點(diǎn)事件的呈現(xiàn)由過去的孤立零碎化轉(zhuǎn)向集中系列化,熱點(diǎn)事件不再單獨(dú)出現(xiàn),更多的是以“批量化”和“同類復(fù)制”的方式集中展現(xiàn)在公眾的視野中。有學(xué)者將這種系列化的呈現(xiàn)歸納為“同標(biāo)簽型系列事件、同主體型系列事件、同類別型系列事件、同時(shí)段型系列事件”四種類型。[2]本文所探討的女大學(xué)生被殺案系列化呈現(xiàn)現(xiàn)象更接近于“同時(shí)段型系列事件”,即事件具有共同特點(diǎn),且發(fā)生時(shí)間相隔較短具有連續(xù)性,事件本身具有奇異性、暴力性、破壞性等特征。[2]系列女大學(xué)生被殺事件的特點(diǎn):
(一)事件框架與呈現(xiàn)方式的重復(fù)性
恩特曼指出:“框架包含了選擇和凸顯兩個(gè)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認(rèn)為需要的部分挑選出來,在報(bào)道中特別處理,以體現(xiàn)意義解釋、歸因推論、道德評(píng)估等”。[3]一般來說,當(dāng)前面的事件受到關(guān)注與熱議時(shí),為了延續(xù)輿論熱潮,媒體與公眾便會(huì)主動(dòng)在社會(huì)范圍內(nèi)搜尋與吸納類似事件,選擇性忽略事件差異,借助主體、主題等類似要素對(duì)事件進(jìn)行框架處理,從而營造出事件接連發(fā)生的現(xiàn)象。女大學(xué)生被殺事件中“女大學(xué)生”、“離奇失蹤”、“慘遭殺害”等成為議題呈現(xiàn)中的高頻詞匯,搶眼的標(biāo)題與聳人聽聞的細(xì)節(jié)成功地吸引了公眾注意,實(shí)現(xiàn)輿論聚焦。
(二)情緒易點(diǎn)燃性
在充滿爆炸性、碎片化信息的網(wǎng)絡(luò)海洋中,孤立事件要獲得關(guān)注,得以擴(kuò)散傳播,演變成系列化事件,其概率并不亞于中彩票。有研究針對(duì)2007~2012年《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輿情分析報(bào)告》所評(píng)選出的120件網(wǎng)絡(luò)輿論熱點(diǎn)事件進(jìn)行了梳理,結(jié)果顯示網(wǎng)絡(luò)輿論熱點(diǎn)議題主要集中于八大領(lǐng)域,其中法治類和社會(huì)類議題占比最重,[4]由此可見,涉及公共利益、具有反常態(tài)性的法治事件和社會(huì)事件更能吸引公眾的視線。女大學(xué)生連續(xù)失蹤被殺事件作為極端惡性的刑事案件,暴力性與社會(huì)傷害性凸顯,其所攜帶的公共性與公共利益更是毋庸置疑,因此可以在短時(shí)間內(nèi)實(shí)現(xiàn)情緒點(diǎn)燃,引發(fā)公眾關(guān)注與討論。
(三)引發(fā)互動(dòng)性
互動(dòng)性主要是“話題與人的互動(dòng)”,所謂話題與人的互動(dòng)指某個(gè)特定話題是否能在最廣泛程度上激起人們的共鳴。女大學(xué)生被殺作為社會(huì)安全事件與公眾存在著天然的聯(lián)系,尤其是在矛盾交織的轉(zhuǎn)型期社會(huì)中,極易激發(fā)公眾對(duì)生命權(quán)利的捍衛(wèi)和對(duì)社會(huì)公平正義的追求,引發(fā)輿情共振。僅9月5號(hào)央視官微發(fā)布的一條“女大學(xué)生張某失聯(lián)被殺”博文,在短短24小時(shí)內(nèi)便收到了6000多條回復(fù),轉(zhuǎn)發(fā)更是高達(dá)14000多次。在人與話題間不斷地互動(dòng)角力中賦予其持久的生命力,推動(dòng)著系列事件持續(xù)升溫,成為地區(qū)性乃至全國性的公共“議題”。
二、系列化呈現(xiàn)背后的傳播機(jī)制
從近年來產(chǎn)生的網(wǎng)絡(luò)熱點(diǎn)事件系列化呈現(xiàn)現(xiàn)象并非單純地由媒體或受眾的某一方造成,其背后的動(dòng)力機(jī)制更真實(shí)表現(xiàn)為:社會(huì)問題激增的新媒體環(huán)境下網(wǎng)民、媒體等多種力量的交織作用。
(一)系列化根植于事件本身
輿論是特定時(shí)空里,公眾對(duì)特定社會(huì)公共事務(wù)公開表達(dá)的基本一致的意見或態(tài)度。[5]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環(huán)境中,較短時(shí)間內(nèi)惡性事件連續(xù)發(fā)生是造成輿論熱點(diǎn)事件系列化呈現(xiàn)的根源。所謂無風(fēng)不起浪,8月~9月內(nèi),社會(huì)上女大學(xué)生被殺事件接連發(fā)生的現(xiàn)實(shí)是造成事件系列化的根本因素。暴力惡性公共事件連發(fā)的奇異現(xiàn)象是導(dǎo)致輿情簇?fù)砼c井噴的根本緣由。
其次,事件的公共屬性強(qiáng)化了事件的話題性。女大學(xué)生被殺事件之所以能夠在短時(shí)間內(nèi)突出重圍、迅速發(fā)酵、廣泛地聚焦公眾視野,正是與其作為惡性兇殺事件所具有的社會(huì)損害性和攜帶的公共利益密不可分。女大學(xué)生頻繁被害違背與沖擊著社會(huì)倫理道德與法律底線,持續(xù)震撼與刺痛著網(wǎng)民神經(jīng)。這種涉及生命傷害的血腥事件必然會(huì)廣泛地激起網(wǎng)民的正義感和權(quán)益感,吸引公眾的密切關(guān)注。
除此之外,女大學(xué)生主體身份的特殊性也是事件延續(xù)、關(guān)聯(lián)化呈現(xiàn)的重要因素。西方新聞價(jià)值觀認(rèn)為,一起事件的新聞價(jià)值往往在于該事件與某種規(guī)范之間存在的負(fù)面比較關(guān)系,換言之,即所謂的事件沖突性。[6]女大學(xué)生作為一種身份認(rèn)知符號(hào),是清純、青春與知識(shí)素養(yǎng)的代名詞,而事件本身的血腥性和暴力色彩與之形成了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與反差,不言而喻的沖突性導(dǎo)致事件的話題度猛增。加上長久以來媒介報(bào)道構(gòu)建出的扭曲與污名化的女大學(xué)生形象,使得女大學(xué)生被殺事件相較于其他類別的暴力事件更具話題效應(yīng),一經(jīng)曝光便可引發(fā)公眾關(guān)注,掀起輿論風(fēng)暴。
(二)媒介議程設(shè)置的作用機(jī)制
(1)新媒體環(huán)境下媒體議程設(shè)置的作用機(jī)制。在系列化事件的形成過程中,議程設(shè)置作用體現(xiàn)在媒介將某類引起網(wǎng)民熱議的事件作為線索,刻意地在現(xiàn)實(shí)中尋找類似版本從而集中展示出來。勒龐認(rèn)為:“影響民眾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實(shí)本身,而是它們發(fā)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7]事實(shí)上,這段時(shí)間內(nèi)發(fā)生女大學(xué)生被殺事件是否就比其他時(shí)段更多或更集中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媒介借助議程設(shè)置將零散分布在社會(huì)中的類似事件串聯(lián)起來、集中呈現(xiàn),營造出此類社會(huì)事件廣泛存在、極為緊迫的表象,成功激發(fā)了網(wǎng)民的勾連想象,造成輿情的累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媒介議程設(shè)置并非在所有話題上都可以實(shí)現(xiàn)如此大的作用,議題屬性的差異會(huì)對(duì)媒介議程設(shè)置效果起到放大或限制的作用。長久以來,公眾對(duì)女大學(xué)生抱有的“性別歧視”與負(fù)面印象是媒介在女大學(xué)生被殺事件上成功實(shí)現(xiàn)顯著性轉(zhuǎn)移的重要原因。有調(diào)查顯示,在新聞報(bào)道中女大學(xué)生消極形象明顯多于積極形象,占整體數(shù)量的68.24%,女大學(xué)生的研究樣本中涉及“性”的占30.59%。[8]女大學(xué)生在新聞報(bào)道中多被塑造為“被害者”形象,且多于“性”、“暴力”等帶有隱性色彩的話題聯(lián)系在一起。正如李普曼曾提出的“多數(shù)情況下我們并不是先理解后定義,而是先定義后理解。”[9]與一般的社會(huì)治安問題相比,社會(huì)對(duì)女大學(xué)生固有的非正面認(rèn)知與印象強(qiáng)化事件的奇特性與暴力性,賦予了其更多娛樂化色彩與隱晦意味,使得事件一經(jīng)曝光便會(huì)激發(fā)媒介與公眾對(duì)系列化事件進(jìn)行挖掘的熱情與積極性。
(2)系列化議程設(shè)置的深層次原因。信息爆炸式增長,媒體間的競爭演化成對(duì)注意力資源的聯(lián)合競爭,話題變更速度加快,導(dǎo)致信息冗余和注意力稀缺這對(duì)矛盾更為凸顯。因此,媒體不得不著眼于轟動(dòng)效應(yīng),借助規(guī)模化、關(guān)聯(lián)化的報(bào)道方式來持續(xù)吸引公眾注意。在輿情邊際成本遞減和邊際收益遞增的經(jīng)濟(jì)規(guī)律驅(qū)使下,媒介將不同地點(diǎn)、不同時(shí)間點(diǎn)發(fā)生的熱點(diǎn)事件關(guān)聯(lián)化呈現(xiàn),利用規(guī)模效應(yīng)、連鎖效應(yīng)有效地吸引公眾注意,[2]在滿足公眾信息需求同時(shí),為自己創(chuàng)造經(jīng)濟(jì)利益。其次,媒介組織間議題相互模仿也是導(dǎo)致輿論熱點(diǎn)事件系列化呈現(xiàn)的直接因素之一。社會(huì)心理學(xué)家塔爾德提出的模仿理論認(rèn)為,模仿是最基本的社會(huì)現(xiàn)象,是社會(huì)學(xué)習(xí)的重要形式,模仿也是人們互相影響的重要方式。[10]當(dāng)前,在你爭我奪激烈的眼球經(jīng)濟(jì)競爭中,媒介組織間議題模仿成風(fēng),模仿議程創(chuàng)新者成為獲得關(guān)注,實(shí)現(xiàn)注意力經(jīng)濟(jì)的便捷途徑。相較于新創(chuàng)議題將公眾注意力從一件事情轉(zhuǎn)移到另一件事上的不確定性,依靠輿論熱度延續(xù)、獲取關(guān)注則來得更為穩(wěn)妥。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在生存壓力與經(jīng)濟(jì)效益面前媒體的職業(yè)價(jià)值的追求無力,創(chuàng)新動(dòng)力與社會(huì)責(zé)任被蠶食。
(三)公眾推波助瀾
截至2014年12月,我國網(wǎng)民規(guī)模達(dá)6.49億,其中手機(jī)網(wǎng)民規(guī)模達(dá)5.57億,在總體網(wǎng)民中的比例達(dá)85.8%。[11]手機(jī)等移動(dòng)終端的發(fā)展為公眾構(gòu)建了信息交流和自由表達(dá)的空間,使自我議題設(shè)置成為可能。
(1)公眾參與和自我議程設(shè)置的驅(qū)動(dòng)作用。新媒體時(shí)代,傳統(tǒng)傳播格局被顛覆,在話語機(jī)會(huì)與權(quán)利的爭奪中,公眾逐漸擺脫弱勢地位成為自我議程設(shè)置的主力。通常情況下,越是能產(chǎn)生道德震撼,激發(fā)對(duì)弱者同情的事件越有可能會(huì)成為網(wǎng)民議程設(shè)置的議題。女大學(xué)生被殺事件作為涉及弱勢群體、帶有救助性、人性關(guān)懷,故事性較強(qiáng)的事情無疑會(huì)激發(fā)網(wǎng)民議程設(shè)置的熱情。因此,當(dāng)社會(huì)中同類型事件勾起公眾的特定記憶時(shí),無所不在的“公民記者”便會(huì)通過自己手中所掌握的社交媒體,以自我熟悉的框架和方式將其傳到網(wǎng)上,實(shí)現(xiàn)議題設(shè)置,從而造成熱點(diǎn)事件不斷地衍生,輿論聲勢持續(xù)擴(kuò)張。
(2)公眾框架構(gòu)建需求與獵奇心理為其營造生存空間。網(wǎng)民自身有將事件“標(biāo)簽化”、“類別化”的偏好基礎(chǔ)。當(dāng)前,信息碎片化與淺閱讀習(xí)慣,培養(yǎng)出了受眾對(duì)快速獲悉信息的期許,縮減了受眾在信息獲取上愿意為之付出的時(shí)間與精力。因此,網(wǎng)民需要媒體用最易識(shí)別、最節(jié)約時(shí)間的框架對(duì)事件進(jìn)行構(gòu)建。[12]系列化呈現(xiàn)借助標(biāo)簽化、類別化構(gòu)建同類型事件,將具有共同特點(diǎn)的事件進(jìn)行概括,簡單直接地傳遞給公眾,在節(jié)省時(shí)間與精力的同時(shí),迎合了淺閱讀時(shí)代受眾的信息消費(fèi)方式。另外,公眾具有極強(qiáng)的獵奇心理,相較于嚴(yán)肅性、政治性較強(qiáng)硬的新聞報(bào)道,這種集中發(fā)生、飽含故事性、趣味性的報(bào)道更能吸引公眾的注意力,強(qiáng)烈的沖突色彩與娛樂色彩能極大地激發(fā)與滿足公眾的好奇心。
三、系列化呈現(xiàn)行為的反思
女大學(xué)生被殺事件作為惡性刑事案件,媒體報(bào)道使其環(huán)境監(jiān)測功能的充分展現(xiàn)。種系列化呈現(xiàn)在引發(fā)相關(guān)政府部門重視社會(huì)治安問題,提高女大學(xué)生自我保護(hù)意識(shí)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這其中存在的缺陷與弊端同樣不容忽視。
(一)引起社會(huì)恐慌
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中提出每個(gè)人的行為依據(jù)的都不是直接而確鑿的知識(shí),而是自己制作的或別人給他的圖像。[9]媒體的系列報(bào)道所營造出惡性事件不斷發(fā)生的景象極易讓公眾產(chǎn)生一種威脅即將逼近的錯(cuò)覺。9月5“央視新聞”官微發(fā)布的一條“女生防身小貼示”博文,轉(zhuǎn)發(fā)量高達(dá)14500多次,其中“女生出門注意安全啊”、“不敢出校門”等類似充滿恐懼情緒的評(píng)論更是層出不窮。由此可見,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時(shí)空限制的打破讓受眾更清晰地“感知”事件的發(fā)生,而過度的負(fù)面信息傳播無疑會(huì)造成恐慌,徒增社會(huì)的無望與焦慮。因此,媒體應(yīng)把握報(bào)道的平衡性,避免同類事件的不斷演繹給社會(huì)穩(wěn)定造成沖擊。
(二)固化刻板印象,造成二次傷害
中國長期處于父權(quán)統(tǒng)治模式,對(duì)女性的弱勢、附屬地位的認(rèn)知根深蒂固,即使是在當(dāng)前相對(duì)民主開放的社會(huì)中,這種性別差異的思維方式仍未沖破樊籬,并且可以從新聞報(bào)道中女性形象的建構(gòu)上窺見一斑。在新聞報(bào)道中女性多被塑造為軟弱無知、易受侵害的形象,即使是高知群體的女大學(xué)生,仍無法擺脫社會(huì)對(duì)女性這一刻板認(rèn)知的限制與束縛。在新聞報(bào)道中關(guān)于女大學(xué)生的報(bào)道大多涉及暴力、權(quán)色交易等,相較于負(fù)面報(bào)道,對(duì)其正面形象塑造的報(bào)道幾乎寥寥無幾。
女大學(xué)生被殺事件的系列報(bào)道看似講述的是女大學(xué)生遭受的不幸,呼吁女性提高安全意識(shí),但卻在無形中加重了公眾對(duì)女大學(xué)生“無知”與“輕浮”印象,存在報(bào)道失衡的問題。另外,在對(duì)女大學(xué)生被殺事件的微博評(píng)論中充斥著“穿著如此成熟一看就不是好學(xué)生”、“看韓劇看傻了吧”等帶有侮辱性、貶低性意味的評(píng)論。這不僅固化與加深公眾對(duì)女性的刻板印象,使本就受損的女性形象雪上加霜,更會(huì)因?yàn)榫W(wǎng)絡(luò)傳播中的語言暴力和對(duì)悲劇事件的娛樂化解構(gòu)給受害者及其家屬、女大學(xué)生群體帶來二次傷害。
同其他社會(huì)群體一樣,女大學(xué)生群體存在負(fù)面消息在所難免,但是媒介作為具有專業(yè)素養(yǎng)的組織應(yīng)該注意把握信息的平衡與全面,在還原事實(shí)真相的同時(shí),把握正確的輿論導(dǎo)向,避免成為落后思想的助推者。
(三)媒介報(bào)道中娛樂化傾向嚴(yán)重
媒介作為社會(huì)公器,必須服務(wù)于公共利益。尤其是在眾生喧嘩的時(shí)代,媒介組織更應(yīng)該堅(jiān)守其作為理性捍衛(wèi)者的角色。但現(xiàn)實(shí)情況卻令人擔(dān)憂,很多時(shí)候?yàn)榱双@得轟動(dòng)效應(yīng),相較于對(duì)深層次問題的追問,媒介往往選擇捕捉那些最具社會(huì)情緒點(diǎn)燃性的新聞點(diǎn),[13]以此實(shí)現(xiàn)眼球效應(yīng)。就如此次女大學(xué)生系列事件報(bào)道中,媒體一邊倒地將報(bào)道側(cè)重點(diǎn)集中在“性”、“缺乏安全意識(shí)”等煽動(dòng)性話題上,不僅忽視了作為理性輿論引導(dǎo)者所應(yīng)承擔(dān)的責(zé)任,反而成為話題炒作的始作俑者,使悲劇性事件的嚴(yán)肅性被娛樂性吞噬。
四、結(jié)語
女大學(xué)生被殺事件系列化呈現(xiàn)是新媒體環(huán)境所孕育出來的一種獨(dú)特現(xiàn)象,且近來輿論事件的這種系列化呈現(xiàn)方式不斷涌現(xiàn)。它的產(chǎn)生是媒體、公眾等各方力量交錯(cuò)糾纏的結(jié)果。因此,媒介、公眾和政府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zé)任。為了充分發(fā)揮輿論熱點(diǎn)事件在監(jiān)測社會(huì)環(huán)境、表達(dá)民意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并有效避免系列化呈現(xiàn)的負(fù)面效應(yīng),媒體要做到審慎議程設(shè)置,堅(jiān)守專業(yè)主義信念,加強(qiáng)輿情把關(guān),自覺擔(dān)任理性輿論的引導(dǎo)者。公眾則要主動(dòng)適應(yīng)新媒體環(huán)境,合理使用自身權(quán)利,避免標(biāo)簽化認(rèn)知,做到謹(jǐn)言慎行。而政府則要居于領(lǐng)頭羊位置,還原事實(shí)的真相,營造有序的公共環(huán)境與表達(dá)空間,引導(dǎo)輿論熱點(diǎn)參考文獻(xiàn):
事件朝著健康有序的方向發(fā)展。以此避免熱點(diǎn)事件中的跟風(fēng)與模仿,娛樂性吞噬公共性,輿情累加威脅社會(huì)穩(wěn)定等問題的出現(xiàn)。
[1]王國華,鄧海峰,王雅蕾,馮偉.網(wǎng)絡(luò)熱點(diǎn)事件中的輿情關(guān)聯(lián)問題研究[J].情報(bào)雜志,2012(7).
[2]肖林,方付建,王國華.網(wǎng)絡(luò)輿情熱點(diǎn)事件“系列化呈現(xiàn)”問題研究[J].情報(bào)雜志,2011(2).
[3]張洪忠.大眾傳播的議程設(shè)置與理論關(guān)系探討[J].西南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1(10).
[4]劉艷婧.網(wǎng)絡(luò)輿論熱點(diǎn)議題的信息架構(gòu)分析[J].現(xiàn)代傳播,2013(12).
[5]李良榮.新聞學(xué)導(dǎo)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47.
[6]嚴(yán)利華,高英波.從個(gè)案激情、話題互動(dòng)到公共理性[J].當(dāng)代傳播,2015(1).
[7]古斯塔夫·勒龐(法).烏合之眾[M].戴光年,譯.新世界出版社,2012:67.
[8]李薇.新聞報(bào)道中的大學(xué)生媒介形象[J].新聞界,2008(3).
[9]沃爾特·李普曼(美).公眾輿論[M].閻克文,江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7,18.
[10]呂菁.論網(wǎng)絡(luò)熱點(diǎn)事件的傳染性及其啟示[J].傳播與版權(quán),2013(7).
[11]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信息中心(CNNIC).第35次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發(fā)展?fàn)顩r統(tǒng)計(jì)報(bào)告[R]. 2014.
[12]王斌,李詩瑤.新媒體環(huán)境下職業(yè)記者角色爭辯[J].新聞戰(zhàn)線,2012(10).
[13]李向陽.試論傳媒轉(zhuǎn)型的陷阱[J].南方電視學(xué)刊,2014(2).
課題項(xiàng)目:本論文為2015年度浙江萬里學(xué)院研究性教學(xué)改革示范建設(shè)課程項(xiàng)目“《新聞評(píng)論》課程建設(shè)”的階段性成果
G206.3
A
1674-8883(2015)24-0028-02
余顯仲,浙江萬里學(xué)院文化與傳播學(xué)院新聞系講師。
作者簡介:向可(1992—),女,安徽鳳陽人,華東政法大學(xué)社會(huì)主義法制教育與傳播專業(yè)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社會(huì)法制新聞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