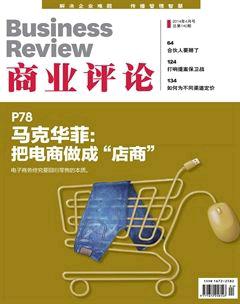給大腦留白
蘭剛
入冬的上海,大霧連連。此刻,我正與羅總坐在金茂大廈凱悅酒店的大堂吧里,開始我們的月度對話。
隨著太陽逐漸露出笑臉,晨霧開始消退。從酒店的落地窗望出去,陸家嘴那些形態各異的高樓大廈宛若云海中的群山,鱗次櫛比,光彩照人。羅總輕輕嘆口氣說:“若不是有霾搗亂,此情此景,也堪稱仙境呢!”
我拉回話題:“最近在忙什么呢?”
羅總想了想:“這一年又快過去了,我們正在思考未來的戰略部署。但感覺這幾年經濟形勢撲朔迷離,行業格局變幻莫測,越來越難以把握,有時真想不清該如何下手。”
我點點頭:“是啊,不確定性將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旋律,要學會駕馭它,需要我們深刻改變自己的思維模式才行。”
羅總好奇地問:“要怎么改?”
我答:“我們過往習慣的思維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條件反射,一是目標導向。條件反射其實是對思維的簡化處理,對于外界發送給我們的各種信號,依據我們以往的經驗,快速做出分析、判斷與回應。”
羅總笑著說:“我過去常常就是這樣,看到一個問題馬上處理。但我發現公司做大以后,反應速度太快也有問題,有時病根沒找對的話,解決了一個問題,反而衍生出更多的問題。”
“你說得很對,條件反射就像飛機的自動駕駛系統,能簡化信息分析的過程,提高大腦的敏捷度,節省能量。但遇到系統性的復雜問題,好比飛機遭遇氣流,就不能再自動駕駛了,人工干預很有必要。”我回應道。
“不過,對于我們做企業的人,目標導向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目標導向是現代管理學宗師彼得·德魯克最先提出來的,在促進管理的專業化、系統化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相當于為所有管理活動找到了一個‘綱。一切的管理行為最終都是為了達成一個特定的目標,當組織明確了這個一致的方向后,協同效應就產生了,大海航行就不會迷失方向。”
“但是,”我話鋒一轉,“今天企業身處的競爭環境與德魯克時代最大的區別在于—— 一切都變得越來越難以預測,很多時候我們甚至都弄不清楚目標在哪里。比如我們越來越重視創新,但創新的最終成果會是什么樣子,我們出發的時候并不清楚。”
羅總表示認同:“喬布斯曾說,在福特發明汽車之前,你如果去問消費者想要什么交通工具,他們一定會說,一輛更快的馬車,因為他們只見過馬車。只有當汽車出來以后,他們才會意識到,這是我們想要的。所以在開發iPhone的時候,喬布斯跟研發人員說,我也不知道最終的iPhone應該是什么樣,但只要你們把正確的產品放在我眼前,我就知道了。”
我擊節叫好:“你舉的這個例子太經典了。這就是今天企業常常面對的情境:我們出發時不知道要去哪兒,但到達正確的地方時,我們都知道我們到了。”
羅總一臉茫然:“我們總得有個指南針吧,要不然真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我肯定地說:“當然,但這個指南針不在外面,而是藏在你的心里。學習型組織的開山鼻祖彼得·圣吉在與國學大師南懷瑾深度對話后,總結提煉出了U型理論。過去我們的思維模式是先‘外觀,再行動,造成了很多不可持續的問題。U型理論指出,在這兩者之間,我們還需要一個高質量的‘內觀環節,之后的行動是由‘心驅動的,而非目標。這樣的行動才是強有力的,具有改變世界的能量。”
羅總心中存疑:“‘內觀有什么要訣呢?”
“圣吉的《第五項修煉·心靈篇》專門談U型理論。我認為內觀有三個要點:首先是‘知止,讓躁動的思緒停止下來。隨著移動互聯的快速發展,我們所有的碎片時間全都被各種各樣的資訊填滿了,好比你的大腦雷達上充斥著各種噪音信號,自然就接收不到來自內心的訊息了。所以要給大腦留白,尤其對于你這樣的企業一把手來說,留出獨處和靜默的時段非常必要。”
“其次是‘放下,要放下我們習慣的思維模式和經驗判斷。在我們的首屆外灘CEO培練營中,我反復向學員們強調守住培練位置的重要性,告誡他們要放下評判欲、控制欲和教導欲,守在我們稱之為‘有意識的無知位置上。德魯克也曾經說,當我給客戶做咨詢時,我常常提醒自己,忘掉過去的思維框架,認真傾聽,不做評判,因為這些所謂的經驗往往已不再適用。”
羅總插話道:“我們這些極端自信的人,不經常提醒自己,真不行!”
我強調說:“但只有這樣,才能到達我們想要的第三階段——‘精思,高質量的內省和思考。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彩虹?!這就好比禪學中的頓悟,是需要修煉才能獲得的。這時的思考我們稱之為‘思想的結晶,才是真正閃著智慧光芒的思想成果。這樣的思想指導下的行動,才是由內而外,由心而發,充滿力量和韌勁的。”
談笑間,窗外的大霧已徹底散盡,陽光萬道灑滿了浦江兩岸,天地一下子明亮起來。羅總興奮地說:“蘭兄,你提的這三個詞:知止、放下、精思,就好比借了我一雙智慧眼,讓我透過迷霧,看到了這片新天地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