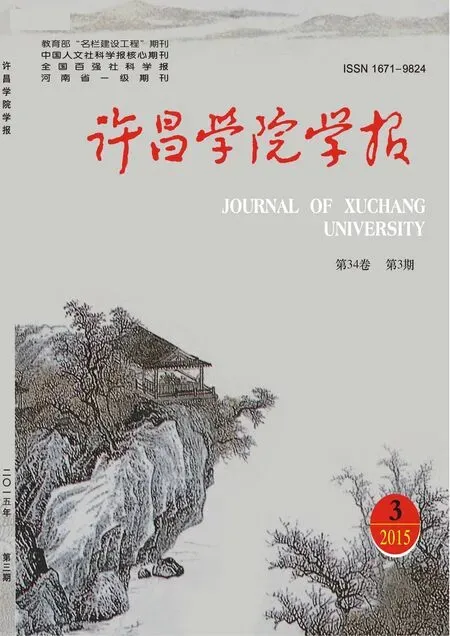曹叡崇文觀儒學文化傳播考論
張蘭花
(許昌職業技術學院 人文系,河南 許昌 461000)
?
曹叡崇文觀儒學文化傳播考論
張蘭花
(許昌職業技術學院 人文系,河南 許昌 461000)
在梳理曹魏三祖尊儒貴學慣常態度的基礎上,文章選取曹魏青龍四年曹叡設立的崇文觀為考察視窗,通過對崇文觀主要成員文化思想的考辨,以及曹叡系列如新訂明經課考選拔制度、組織儒生整理經學典籍、將經學與文學并重傳播等諸多尊儒篤學活動,論證曹叡在樹立儒學正統思想觀和復興儒學方面的諸多貢獻,以此糾正學界有關因曹魏三祖不重儒學而導致儒學走向衰落的錯誤觀點。
三國曹魏;曹叡;崇文觀;復興儒學;文化貢獻
因董仲舒等對天人之際的創建性探討得到漢武帝的大力支持,儒學在漢代獲得了“獨尊”的正統地位。但有學者認為,之所以儒學自漢末建安以降,隨社會動蕩、政權更迭而呈逐步衰落趨勢,“曹魏統治者對儒學不重視的態度,是魏晉儒學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1]深層原因是“曹操重文辭、倡通脫,不恪守儒家禮法。”[2]而且“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3]1544等,進一步推助了儒學的衰落。但是,倘若翻檢史籍,從曹魏統治者推行的尊儒貴學政策到對儒學傳播的實際作用諸方面考察,上述論點,顯失允當。
一、曹魏三袓對儒學的態度
《魏略》記載了漢末儒學漸衰的景觀:“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茍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4]420面對這種局面,開創曹魏基業的曹操在建安元年迎漢獻帝遷都許昌,待政局稍稍穩定之后,便在建安七年(202)春正月下達了置學令,建安八年(203)又下達了修學令:
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生之道不廢,而有以益于天下。[4]24
在戰亂的年代里,曹操固然重才能、嚴刑法,但總體施政原則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即武力征討與文治教化并舉。這一點還可從《三國志·武帝紀》中曹操尊儒重學的諸多事例中得到驗證。比如,漢末儒士多避亂荊州,荊州遂成為全國儒學教育中心。曹操平定荊州之后,禮待并重用北遷許都和鄴城的儒士,為曹魏中后期儒學文化的復興奠定了基礎,這正是荀彧“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圣真,并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4]317-318思想的落實。建安二十二年(217)五月曹操在鄴城所置“泮宮”①泮宮:原指西周諸侯所設大學。《漢書·郊祀志》有:“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93頁。即是曹魏太學的前身。在教育子女方面,曹操要求他們多讀儒家經典,且選聘當時名儒為太傅,灌輸他們儒家學說。還曾特別訓誡喜武的曹彰要讀《詩》《書》:“汝不念讀書慕圣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4]555對儒學有成者,曹操總是竭力贊賞,樹為楷模,如為已故的名儒盧植修繕墳墓時云:“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禎干也……孤到此州,嘉其余風……敬遣丞椽修墳墓,并致薄酸,以彰厥德。”[4]650-651突出地標榜了盧植的儒宗地位,如此等等。
總體來講,曹操的基本思想是以儒家為核心的,不僅施政措施多以儒學為主,而且在重新定制雅樂、恢復禮制、復興漢代太學和儒家家教思想諸多情形來看,曹操對儒家思想的尊崇是史實俱在的,學界對此也多所肯定。如張作耀在《曹操尚禮重法思想述論》中列舉了曹操“尚仁重德、倡禮嘉義”的大量事實后,認為“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響很深,其根基屬于儒家思想范疇,尚仁義禮讓,并試圖以仁義、道德、禮讓教民和行政。”[5]
曹操的兒子曹丕從小就喜歡儒家經典,“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4]90公元220年,曹丕以儒家禪讓禮儀的方式接受了漢獻帝的退位,避免了因易代戰爭而造成的大量傷亡。曹丕稱帝后,繼承乃父尊儒貴學之風,吸取歷朝覆滅的教訓,全面改革創新,極力推廣儒家文化教育。比如黃初元年(220)“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4]420擴大儒學招生范圍,使洛陽太學規模快速恢復到“弟子數百人”,并“集諸儒于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4]88曹丕執政后第二年,又頒布了正史首見的尊孔詔書《追崇孔子詔》,這是東漢以來樹立尊孔崇儒的第一面大旗。同年,在大儒孔羨的家鄉,他“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于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4]78這種既為孔子修廟祭祀,又為儒學學者建專館以供其進行文化交流和傳播的行為,在史書上尚屬首例。黃初五年(224)夏四月,曹丕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4]84要求拓展儒學課程,還令官吏課考儒家六藝,“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余篇,號曰《皇覽》。”[4]88《皇覽》包括五經群書,共八百多萬字,開了我國編纂大型類書的先河,有力地推動了儒學文化的發展。在教育子女方面,他選大儒鄭稱作曹叡的老師,“學亦人之砥礪也。(鄭)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耀明其志。”[4]59突出強調學習內容是儒家經學,等等。
在曹丕有條不紊的選拔制度、重振儒學政策以及重用儒士等系列尊儒重教的推動下,整個社會風尚有明顯轉變,這直接影響到士人人生價值的取向,仿佛一夜之間,士人們研究學習儒學的熱情受到激發,“興復辟雍,州立課試,于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4]685甚至出現“黃初中,儒雅并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亢散里巷”[4]486的崇儒思潮,世風較漢末為之一變。
在恢復儒學文化傳播方面,“曹魏三祖”*“三祖”指太祖曹操、高祖曹丕、烈祖曹叡。胡應轔《詩藪》云:“詩未有三世傳者,既傳而且煊赫,僅曹氏操、丕、睿耳。”胡應轔《詩藪·外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37頁。之一的曹叡也有特殊的貢獻。盡管文學家鐘嶸認為“叡不如丕”,把他的詩歌列入下品,現行的文學史對他也略而不提或一筆帶過,而更多的史學家則又集中批評他生活奢淫,認為是他“改變了曹操以來的節儉政策,形成了奢淫風尚。……加深了曹魏的危機。”[6]但學者往往忽略了他對儒學文化傳播的突出成就。
史書簡略記載有曹叡曾設“崇文觀”,但學界對此極為忽略,這是導致誤解曹叡儒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環節。現以“崇文觀”傳播儒學文化的史實為考察中心,考論他尊儒貴學的系列活動,由此窺見曹叡時期儒學非但沒有停滯、衰落,而且在傳承經學和儒學復興方面有著卓越的貢獻。
二、曹叡崇文觀主要成員及文化思想
史載青龍四年(236)“夏四月,置崇文觀,征善屬文者以充之。”[4]107“(王)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4]416“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群才,迭相照耀。”[7]405上述文獻標明,崇文觀領導人物是經學家、常侍領秘書監王肅,何晏、劉劭等。因資料欠缺,崇文觀中具體人員名字無法詳考,但史載青龍四年前后,名儒侍中高堂隆、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秦靜*《三國志·高堂隆傳》云,“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并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由此知蘇林、秦靜和高堂隆一并為當時享有盛名的大儒。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17頁。,盧植推薦的孫邕和鄭沖*據《三國志·高堂隆傳》:“毓舉常侍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于是用邕”可知。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51頁。,作品傳世且追隨曹叡創作的骨干成員衛覬、邯鄲淳、繆襲、韋誕、卞蘭、夏侯惠等,應該均為崇文觀成員。粗略算來,也是“文士輩出”[8]28了。
梳理崇文觀重要成員的存世作品,顯見他們鮮明的儒學文化色彩。
王肅(195-256年):字子雍,東海郡郯人,有《孔子家語解》存世。在序中他認為因鄭學“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9]527,從而形成了迥異于大儒鄭玄的“王學”經學派。正因為王肅深知儒學傳播的重要性,故對掌管文化傳播工作的秘書職責十分重視,他強調要提高秘書地位:“秘書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典謨,與中書相亞,宜與中書為官聯。”[10]224在《論秘書丞郎表》中又提議提高秘書丞郎的待遇,以彰顯“陛下崇儒術之盛旨”,由此可知他從事的秘書具有“儒術”文化內核。
從傳世至今的作品來看,王肅有多篇論述樂舞規制者,如《議祀圓丘方澤宜宮縣樂八佾舞》中強調“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10]227的禮樂文化等級制,并倡導“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的樂理文化思想。由此可斷定,王肅是典型的儒家學者、經學家。
何晏(?-249年):字平叔,南陽宛人。善于談理,主要著作有《論語集解》《道德論》等。從今存《論語集解》《無名記》《無為論》和《景福殿賦》等作品來看,他的思想兼具儒道,儒本道末。比如,他在《奏請大臣侍從游幸》中所談治國修身的言論則完全屬儒家學說,許多語言直接取自《論語》:
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可自今以后,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10] 408
以他為主編,孫邕、鄭沖、曹羲、荀轍等人參與對諸家訓注進行編撰的《論語集解》,是我國首部“集解體”專著,也是迄今最早的一部《論語》注本,匯集了當時《論語》研究的重要成果,對儒學文化的傳承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劉劭(186?—249年?):字孔才,廣平邯鄲人。黃初中受詔搜集《五經》群書,參與編纂《皇覽》。曹叡即位后封劉劭為陳留太守,他尊儒重教,受到百姓稱贊。青龍元年(233)三月,魏下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散騎侍郎夏侯惠推薦了劉劭。劉劭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律略論》《都官考課》《說略》《上都官考課疏》《祀六宗議》《樂論》等。以為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還聽命曹叡作《趙都賦》《許都賦》《洛都賦》《龍瑞賦并序》《嘉瑞賦》等。今存《人物志》十二篇,論辯人才,分別流品,對人性、才能和形質等諸方面剖析詳盡,是人物品鑒的代表作,對當時地方察舉和品鑒之風均有一定的影響。從他在法治、考課、德育和用人四個方面的學術成就可以看出,他雖兼具法、道諸家,但儒家是其核心思想。
高堂隆(?-238年):字升平,泰山平陽人。建安中為丞相軍議掾、歷城侯相,黃初中除堂陽長,明帝初,為給事中博士、散騎常侍。青龍中遷侍中,領太史令。景初初遷光祿勛。主要著作有《魏臺雜訪議》卷三、《雜忌歷》二卷、《張掖郡玄石圖》一卷,有文集十卷。
高堂隆是當時大儒,懂經典,常議禮制,精通天文,常受詔推校歷法。平素也常依經典進諫,有輔臣之節。如在《詔問漢武厭災對》中建議“圣主睹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10]314在《諫用法深重疏》進諫“宜崇禮樂,班敘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10]316即使在重病將亡前,還口呈《疾篤口占上疏》,勸諫曹叡要吸取大造宮室的前代之鑒,提防當下有“鷹揚之臣于蕭墻之內”[10]319的危機。當曹叡聞其亡故,長嘆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4]717
王基(?—261年):字伯輿,東萊曲城人。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太和中擢中書侍郎,遷安平太守,后因公事免職。王基為官正直清廉,治理江夏時,“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4]752曾寫《上明帝疏諫盛修宮室》對曹叡大興土木進行勸諫,撰《時要論》抨擊曹爽專權導致時風大壞。在學術上,王基尊崇儒家學派的鄭玄學說,對王肅改易鄭玄舊說的行為頗為不滿,常以鄭玄學說與王肅展開辯論,影響很大。史載他有《毛詩駁》《東萊耆舊傳》《新書》等文章傳世。由此顯見,他是位具有軍事才能且德才兼備的儒學思想家。
此外,當時比較活躍的儒學人物還有曹丕《典論》中曾提到的蘇林。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4]621另外,《王肅傳》有以董遇、賈洪、邯鄲淳、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為儒宗的記載。其它還有與何晏共同編撰《論語集解》的曹羲、鄭沖、孫邕、荀顗等,他們也是曹叡時期著名的儒學文化傳播者。
三、崇文館尊儒活動及文化貢獻
黃初七年(226)夏五月,曹丕病危,立曹叡為皇太子。不久,曹丕去世,曹叡即皇帝位。據《三國志》記載,曹叡“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4]91可知他從小跟隨曹操,家學及曹操的儒法思想對他思想的成型影響頗深。查文獻可知,曹叡繼位后繼續光大儒學,先后采取了多種推廣經典、復興儒學的措施。
(一)崇道篤學、明經課考,樹立儒學正統思想觀
儒學的復興,得益于統治者在選官制度上的推行和引導。曹叡在承襲曹丕時推行的九品官人法的同時,也采取了其它選官途徑,其中策試規定至少要“學通一經”,明確了曉習儒家經典為重要選拔標準。同時,他還在繼位第二年(太和二年六月)頒布《貢士先經學詔》,明確提出“尊儒貴學”、“經學為先”[10]90的儒學正統思想觀,為士人進取確定了努力方向,強化了儒家經典的突出地位。
由于當時推行的是九品官人法,評議者多為儒學大族,為進一步突顯重視儒家經典,特制定了“四科”課考法。“四科”以漢代儒學、文吏、孝悌、從政等四條為參考選取標準,使儒學提升到法制維護的地位。據《三國會要》所云,定立此法,是為禁錮廢黜以“夏侯、諸葛、何、鄄之儔”等四聰八達為首的浮華之風所設。又在太和四年(230)二月追加《策試罷退浮華詔》,重申“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后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4]97曹叡倡導儒學,詔令警示“浮華”之風,彰顯了他推崇儒學的堅定決心和實際行動。
不僅如此,曹叡對武將推薦儒士的行為也大加贊賞。比如,在太和四年(230)征西車騎將軍張郃推薦一位明經修行的同鄉卑湛時,就立即得到曹叡的支持:“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4]527不僅下詔提拔卑湛為博士,還稱贊將軍喜愛儒生的行為,彰顯了對軍人儒士的贊賞。
對那些經義大儒,曹叡還特別關注他們對儒學文化的傳承作用。景初中,大儒高堂隆、蘇林、秦靜等年事己高,曹叡頗為憂心:“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4]717-718擔憂之際,特下令選派三十名年輕儒生跟隨大儒學習。這既是曹叡對儒學大師的尊重,也是他崇尚儒學的真情表露。如此豐富多樣的傳播方式,無疑對促進儒學的復興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二)重視太學教育和經學典籍整理
太學及儒學教育是儒學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曹操穩定北方之后,建安二十五年(220)在鄴城設立了“泮宮”,曹丕稱帝后在洛陽恢復太學,曹叡即位后又下詔復興太學等,這些均表明“曹魏三祖”對恢復太學的重視和力圖光大太學教育的努力。
從理論上講,儒家最重要的治國理論核心就是崇尚道德與禮制。六藝經典作為儒家價值體系的本源文獻,對儒者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曹叡十分重視禮樂教化。他在位期間,曾特設國家圖書編撰機構,熱心傳播文化。比如,衛凱曾與王粲并典制度,到魏明帝時又受詔典著《魏官儀》數十篇。
在機構設置方面,他新置了秘書監、著作郎、佐郎等職位,足見他編纂史書所傾注的心力。其中秘書監始置于東漢桓帝延熹二年(159),主掌圖書保管及考訂古今文字,因內容有一定機密性,故曰“秘書”。桓帝、靈帝時因政局動蕩曾一度廢除,到獻帝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在府內設秘書監,劉放、孫資為秘書郎。秘書監除收集整理或保管圖書典籍之外,尚有“典尚書奏事”的功能。曹丕在黃初年間,下令改秘書為中書監,又新立秘書監“掌藝文圖籍之事”。新置秘書監,大體是專職管理圖書典籍的國家編撰出版機構。到了明帝景初(237—239)前后,秘書監脫離了少府而成為獨立職官機構,當時王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由于圖書典籍管理者要求文化素養較高,故多由博學多識之士擔任秘書監,如曾任職于秘書監的王肅、劉放、杜摯、薛夏等人,均為飽學宿儒。正如王肅上表所稱,秘書監政治待遇的高低,體現著國家對文化教育事業的重視程度,也反映皇帝尊崇儒學的核心思想。比如曹丕令大儒王象領秘書監,于延康元年(220)召集諸儒撰集經傳,經數年編纂成我國古代第一部類書《皇覽》。曹叡時以大儒鄭默為秘書郎,考核舊文,刪省浮穢,校訂整理官府藏書,撰成魏宮府藏書目錄《中經》,這部修成于青龍二年(235)的目錄書編目準確,打破了六分法體例,開創了我國圖書分類的四分法,對圖書典籍的整理、編撰和傳播更為有益。諸多經籍的整理,為保存和傳播儒學文化奠定了文獻基礎。
(三)經學與文學傳播并重
六藝經典可視為文學作品,垂范后世,傳道留名。儒士的文學創作也必然會展示其儒家的人格理想、價值觀念等。曹叡出生在喜愛文學的家庭,承其祖其父文學遺風,特別留心于經典書籍。據他自稱,“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總公卿之議。”[10]97他本人對文章及文學作品有著獨特的認知。在青龍四年(236)所下《選舉詔》中云:“欲得有才智文章,謀虛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10]96這是第一次明確將“才智”、“文章”并列為重要地位的詔令,足見曹叡發揚曹丕“文章經國之大業”的觀點,進一步把“文章”視為輔國強族的教化工具了。由此就更容易理解他詔令將《典論》刊刻成石碑,與石經同立于太學,使文學與石經并存于世之舉的深層動因了。
曹叡的文學作品有很多儒學宣教色彩,從他傳世的18首詩歌全是可唱樂府詩即可窺知一二。如《短歌行》有“歸仁服德,此雄頡頏。”《步出廈門行》中“嗟哉夷叔,仲尼稱賢。”《月重輪行》中“圣賢度量,得為道中。”《棹歌行》中“文德以時振,武功伐不隨。”等等。不僅他的樂府有濃重的儒家禮教風格,即使是詔令,也多有直接表達崇尚儒學或儒家治國理想的內容。如太和三年(229)六月《議追崇處士君號謚詔》就張揚了儒家“德”、“孝”為本的經學詩教大旗。
除整理圖書典籍之外,曹叡還加強禮樂著作的編撰工作,劉勰《文心雕龍·時序》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7]405這既是對“曹魏三祖”文學成就的肯定,同時也點明了崇文觀有“制詩度曲”的功能,是朝廷創作詩曲樂舞的文化傳播機構。
有關曹叡設置崇文觀,因“其后無聞”而未引起學界的重視,或僅認為它開啟后世“文館”先例而一筆帶過。倘若進一步深入梳理研究,不難看出,此舉不僅是曹叡承繼曹魏二祖文學發展進入到新階段的標志,也是他振興儒學文化的重要標志。
[1] 郝虹.從曹氏三代人對儒學的態度看魏晉儒學的衰落[J].管子學刊,2005,(4):95-98.
[2] 王永平.世族勢力之復興與曹叡顧命大臣之變易[J].揚州大學學報,1998,(2):19-23.
[3](唐)魏徵.令狐德棻.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4] (晉)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
[5] 張作耀.曹操尚禮重法思想述論[J].東岳論叢,1998,(3):67-75.
[6] 王永平.略論魏明帝曹叡之奢淫及其危害[J].江漢論壇,2007,(7):92-97.
[7] 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9] 王肅.孔子家語序[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10](清)嚴可均.全三國文[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責任編輯:熊偉
2015-01-27
河南省教育廳2013年度人文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三國文人區域遷移與曹魏文學嬗進”(2013-GH-557)。
張蘭花(1963—),女,河南許昌人,博士,許昌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許昌學院魏晉文化研究所兼職教授,研究方向:三國文化研究。
K236.1
A
1671-9824(2015)03-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