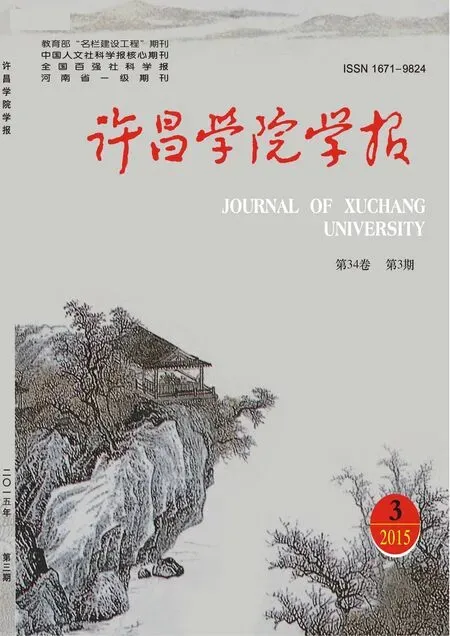“兩極化”創作背后的分野與暗合
——《阿Q正傳》與《邊城》之比較
黃 高 鋒
(許昌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河南 許昌 461000)
?
“兩極化”創作背后的分野與暗合
——《阿Q正傳》與《邊城》之比較
黃 高 鋒
(許昌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河南 許昌 461000)
《阿Q正傳》和《邊城》分別是魯迅和沈從文的經典代表作。通過細讀文本可以發現,《阿Q正傳》重在“審丑”,凸顯出魯迅對國民性批判的深刻思索;《邊城》重在“審美”,凝聚著沈從文對人性美的永恒追求。兩部經典之作“兩極化”書寫的背后,是兩位作家思想觀、文學觀、審美觀的差異與分野。
審丑;審美;“兩極化”書寫
“丑”和“美”相對而存在,如果說美是人與客觀事物在社會實踐中歷史地形成的一種肯定性關系的話,它所喚起人們的是一種肯定性審美體驗,那么,丑則是一種否定性關系,它喚起人們的則是一種否定性審美體驗。審丑和審美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從廣義上來講,審丑實質上只是審美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而已。著名美學家蔣孔陽認為,“審丑歷來都是人們審美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歷來的文學藝術都有表現奇丑怪異的杰作。原始藝術和現代主義藝術……充滿了以丑為美的審美現象。”[1]373審丑,就對象而言,所審的丑,可以是具體的人,可以是具體的自然事物,可以是現象和場景,也可以是抽象的人性惡,甚至是丑惡的社會“浮世繪”。審丑,重在“審”,即創作主體的態度、立場和價值判斷。審丑的目的就是通過對“丑”的感知、判斷、分析和評價而獲得正確的美丑觀,從而提高審美水平。“文學審丑的意義在于,人們在作品展示的種種丑陋之中認識了世界的丑陋及人類自身靈魂的丑陋,在否定性的評價中感覺到羞恥、痛苦、恐懼、負罪,并通過認識丑來為丑定罪,引起‘對自身的不滿’,從而‘以文化的美學的方式實現對生命沖動的壓抑、限制、修正’,最終到達美的境界”。[2]66作為一種藝術生命體驗活動,無論審美,還是審丑,都是作家獨特思想追求與審美理想的直接或間接個性表達。
上世紀末,《亞洲周刊》推出了一項影響深廣的百年文學經典評選活動,即從20世紀全世界范圍內用中文寫作的小說中遴選出中文小說一百強進行排名。結果耐人尋味:魯迅以小說集《吶喊》位列排名榜榜首,沈從文的小說《邊城》則位居第二。但如果以單篇小說計,《邊城》則屬第一。今天,我們把兩部經典作品放在一塊仔細比較,從中可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兩部作品呈現出鮮明的“兩極化”創作傾向。一個偏重“審丑”,一個偏重“審美”。在這種“審丑”與“審美”經典書寫背后,帶給我們的是深沉的思索。
一、《阿Q正傳》:一個“審丑”的未莊世界
《阿Q正傳》最初連載于《晨報副刊》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小說主要塑造了一個核心主人公阿Q形象。除了阿Q形象之外,還塑造了趙太爺、舉人老爺、假洋鬼子等眾多形象,所有的形象共同構成了一幅黯淡的“群丑圖”。
阿Q是一個從外表形象到內在精神都十分丑陋的形象。外在形象方面,破衣爛衫,舊氈帽,“瘦伶仃”,黃辮子,滿身虱子,最突出的就是阿Q頭上的“癩頭瘡”。長“癩頭瘡”到也無可厚非,但阿Q卻十分敏感忌諱。因為他忌諱說“癩”以及和“賴”相近的讀音,后來推而廣之,諸如“光”“亮”,甚至連 “燈”“燭”等等字音都很敏感,很避諱。對于犯諱者,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到后來變為怒目而視了。面對未莊閑人們的嘲笑,他認為別人還不配,藉以尋求心理安慰。《阿Q正傳》突出表現了他的精神勝利法:不敢正視現實,盲目自大,自輕自賤,欺軟怕硬,健忘,忌諱缺點,以丑為榮,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虛幻的精神勝利之中。小說還表現了阿Q性格里的諸多復雜因素,他主觀、狹隘、思想封建保守,既有農民式的樸質與愚蠢,也不免粘染上些游手之徒的狡猾與無賴。他還受到封建思想的影響,如嚴守“男女之大防”,排除異端等,他的性格是一個復雜矛盾體。近代中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不斷入侵,封建統治階級日趨沒落,阿Q可以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環境中培育出的一個“文化怪胎”。
小說除了批判了阿Q的落后、麻木和精神勝利法之外,還揭示了周圍“看客”們的靈魂丑陋。同時,小說也塑造了具有“獅子似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的趙太爺父子以及地主階級出身的資產階級革命投機分子假洋鬼子等眾多丑陋形象。小說既鞭撻了趙太爺之流的兇殘卑劣,也戳穿了假洋鬼子投機鉆營的嘴臉,還譴責了知縣大老爺、把總、“民政幫辦”等人的反動本質,揭示了他們人性的陰暗丑陋。
從整體上,《阿Q正傳》給讀者展示了一個生存環境之丑的“未莊世界”。“未莊世界”是一個封閉愚昧的世界,也是一個等級森嚴的世界。作者在審視故事發生的環境時,著重強化其“丑惡性”,猶如聞一多筆下的一潭“死水”。在這里,“凝滯的時間,封閉的地域,愚昧落后殘忍的人物,一起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社會思想環境”。[3]102“未莊世界”是辛亥革命時期貧困愚昧中國的一個縮影。在這個世界里,充斥著各色人等,有作為上層統治者、剝削者的地主鄉紳,有混跡革命隊伍的政客、投機者,有幫傭、無業游民,也有尼姑等。辛亥革命除了給未莊帶來“大不安”之外,并沒有絲毫質的改變,一切照舊。在這片封閉的地域,生活著一群“可恨之獸”和“可憐之蟲”,在他們身上,魯迅深刻洞悉到了國民劣根性。《阿Q正傳》“審丑”傾向的背后,寄予著魯迅對于國民性問題的深思憂慮。
二、《邊城》:一個“審美”的湘西世界
《邊城》于1934年初在天津《國聞周報》上連載,同年10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是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上的又一部經典之作。小說除了翠翠形象之外,還塑造了天保、儺送、老船夫、船總順順、楊馬兵等眾多形象。所有的形象共同構成了一個鮮亮美麗的湘西世界。
翠翠是愛與美的化身,從小在邊城茶峒小鎮青山綠水中長大。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在陽光雨露的沐浴下,作為“自然之子”的翠翠,皮膚黝黑健康,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天真無邪、活潑可愛的性格惹人愛憐。她有著一顆美麗善良、至真至純的心靈,對于愛情充滿著期待和幻想,單純、執著而又癡情。小說結尾面對不可知的渺茫未來,翠翠選擇執著地等待,人性美熠熠閃光。除了翠翠形象之外,其他如純樸厚道的老船夫,豪爽慷慨的船總順順,豁達大度的天保,專情篤情的儺送,熱誠質樸的楊馬兵……作家筆下的每一個人物身上都閃耀著真善美的高潔品質。《邊城》的“審美”,不僅僅表現在人性美,而且還表現在自然美和風俗民情美。幽碧的遠山、清澈的溪水、美麗的白塔、翠綠的竹簧,河里連接如織的船只,沿河垂直的吊腳樓等,為讀者呈現了一個澄明空靈的世外桃源。對民俗風情美如端午節龍舟競賽,水中捉鴨子等生動逼真的描寫,也引人入勝。
湘西世界不是現實中“原生態”的湘西世界,而是一個與都市世界相對照和互補的世界,是一個經過過濾帶有理想化色彩的湘西世界,是一個寄寓著沈從文人性美追求的湘西世界。沈從文的湘西世界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態。《邊城》里沒有等級貴賤,沒有剝削壓迫,沒有虛榮嫉妒,沒有貪婪自私,人人都是那么和善,那么自足,豪俠重義,古道熱腸,生活猶如一首田園牧歌。“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紳士還更可信任”。總之,這里“一切莫不極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樂土”,與他筆下異化病態的都市世界大異其趣。
沈從文試圖要給讀者注入的是一種審美精神。他企圖用優美的文字建構一個充滿了人情人性美的湘西世界,由此喚起人們麻木的感覺,遲鈍的想象,異化的精神,“慢慢的陶冶我們,啟發我們,改造我們,使我們習慣于向遠景凝眸”,重新去感觸生活,冥悟生命,憧憬未來。沈從文站在審美現代性立場,通過構筑一個詩意的、感性的、自然的充滿了“夢”與“真”的審美湘西世界,企圖對現代性進行修復與救贖,從而實現人性、生命和民族品德的重造,其用心良苦。
三、魯迅與沈從文創作的分野與暗合
《阿Q正傳》和《邊城》分別為讀者創造出了兩個迥異的藝術世界。一個是灰暗丑陋的未莊世界,一個是鮮亮美麗的湘西世界,一個偏重“審丑”,一個偏重“審美”,兩個作家的創作呈現出鮮明“兩極化”的傾向。“兩極化”書寫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兩位作家思想追求、審美理想、藝術個性和創作動機的差異與分野。
魯迅一生致力于國民性問題的思考,所秉持的是一種啟蒙文學觀。沈從文是一個自由主義作家,他一生致力于人性探索,所秉持的是一種人性文學觀。如果說“啟蒙”是我們解讀魯迅的一把鑰匙,那么“人性”則是我們解讀沈從文的一把鑰匙。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闡發了他的文學動機和目的:“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4]512他又在《〈吶喊〉自序》中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沈從文則說:“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的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5]228“人性”在沈從文的文學觀念里是神圣的。在文學創作上,沈從文絲毫不避諱“人性”立場,旗幟鮮明的打出了“人性”的旗幟,并以人性作為其創作出發點和落腳點,孜孜不倦地執著于人性探索。在他看來,一切優秀偉大的作品,都蘊含有一種表現人性的真切欲望,評價一部作品成功與否,也要以人性作為基本準則。可以說,“人性”是沈從文創作思想的支點,是其美學理想的基石,更是其作品的精髓和靈魂。魯迅側重于對國民劣根性不余遺力地批判,對負面、黑暗、丑陋、險惡一面的揭露,而沈從文側重于對人性真、善、美的追求,對人性素樸、美好、善良、純真的張揚,并且,魯迅更注重啟蒙的社會意義,反對抽象的“人性論”。這一點在二十年代與梁實秋等人關于人性論的論爭可窺一斑。而沈從文的人性探索,更注重人性的自然意義,所秉持的是一種自然人性觀,由此形成了二人啟蒙文學觀和“人性”文學觀的分野。
就具體兩部作品而言,魯迅在談及創作《阿Q正傳》的成因時,說他要畫出這個“未經革新的古國”的“國民的魂靈”來,在《偽自由書·再談保留》一文中又指出要“暴露國民的弱點”。沈從文在談到創作《邊城》動機時,則說自己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由此可見,二者的創作動機并不相同。魯迅一生都在關注和思考國民性問題,他以筆為刀,冷峻犀利,深刻解剖著中國人的病態靈魂,對民族痼疾給予徹底地暴露和批判。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魯迅的著眼點不在國人身上的閃光之處,而專注于其“紅腫之處”、“潰爛之時”,即且不論其“美”,而只論其“丑”,恰如醫生之于病人,只論其病變的肌體。[6]73魯迅給我們展示了觸目驚心的國民劣根性:精神勝利法、吃人、奴隸性、“瞞與騙”、“中庸之道”、“面子”、守舊、復古、迷信等。《阿Q正傳》正是國民劣根性的集中展覽。劉再復認為,“魯迅是堅決主張暴露生活中的丑的,并在藝術實踐中無情地撕毀丑惡的假面,他也是一個具有深刻的審丑力的對于丑惡的大審判家”。[7]187而在沈從文的作品里,對人性美的探索與追求從未間斷,一以貫之。人性美作為一種人生理想、價值追求和審美傾向,在沈從文的生命意識里早已根深蒂固。即便是那些描寫都市人生的小說,盡管也揭露和鞭撻人性異化和人性惡,但最終指向仍是對于人性美的執著追求和無限憧憬。
文如其人,一個作家的人格、個性和氣質必然會或顯或隱地浸潤到自己的作品里。魯迅是一個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的人,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魯迅具有憎惡、剛烈、韌性、開放等人格特征,這種人格特質決定了他在作品中更多地描繪了丑陋、病態、畸形和低劣這些否定性審美范疇內的東西,對社會生活中各色各樣的丑態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形成了魯迅作品風格內容上鮮明的審丑取向”。[8]258而沈從文則是一個純樸和藹、謙遜仁慈的人,看似柔弱的外表下,卻有著一顆倔強的靈魂。沈從文這種外柔內剛的氣質,就如同他筆下充滿靈性和智慧的水一樣,是一種“水”的氣質,又不乏“水”的力量。早年的他見慣了殺人砍頭、權力濫用等社會丑象,反而促使他一生不懈致力于追求人性的真善美。
1926年,《晨報》副刊發表了梁實秋的《文學批評辯》一文。梁實秋把“人性”作為文學批評的標準,并認為“人性根本是不變的”。在《文學與革命》、《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等文中,提出“偉大的文學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對于梁實秋的人性論調,魯迅針鋒相對,予以反擊,他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中逐一予以批駁。無獨有偶,沈從文也是一個人性論者。魯迅和沈從文不同的思想追求、審美理想、創作動機和藝術個性,一個注重“審丑”,一個注重“審美”,但是否就意味著二人大相徑庭,迥然不同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沈從文的人性文學觀里還包含著更為深廣復雜的內涵。在以《邊城》為代表的湘西世界作品里,他懷著復雜的感情,試圖通過對“這個民族過去偉大與目前墮落處”的不斷對比和反省,進而探求“民族道德消失與重造”,帶有功利性色彩。作為一個有著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來講,沈從文旨在探求“中國應當如何重新另造”這樣沉重的話題。應該說,這和魯迅的“國民性改造”思想有暗合之處,只是選取的角度不一樣,兩人殊途同歸。魯迅著力于國民性批判,是一種“批判式啟蒙”;沈從文執著于追求人性美,是一種“歌頌式啟蒙”;前者以破為主,破中有立,后者以立為主,立中有破。
[1] 蔣孔陽.美學新論[M].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2] 葉繼奮.理性的失落與潘多拉魔盒的傾翻——20世紀文學審丑現象詮釋[J]. 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0(3):62.
[3] 馮光廉等.中國新文學發展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4] 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4)[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5] 沈從文.沈從文選集(5)[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6] 朱慶華.論〈吶喊〉、〈彷徨〉的“審丑”話語[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03(3).
[7] 劉再復.魯迅美學思想論稿[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8] 陳昕、朱慶華.論魯迅人格對其文格的制約[J].蘭州學刊,2005(2):73.
責任編輯:石長平
2014-09-28
黃高鋒(1980—),男,河南襄城縣人,講師,碩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I207
A
1671-9824(2015)03-005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