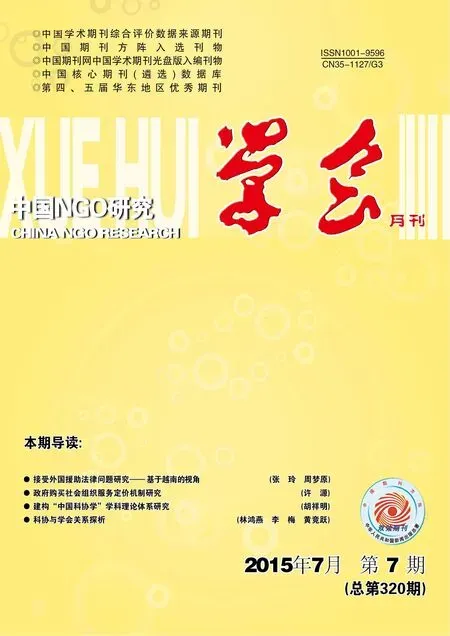政府購買教育服務的源頭之問
董圣足
政府購買教育服務的源頭之問
董圣足
當前,各級政府正圍繞如何推動包括教育領域在內的“政府購買服務”活動,制定規劃、出臺規定、開展試點,有的地區(如上海浦東、北京海淀、廣東深圳、浙江溫州等地)已經先行先試,并在實踐中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就教育領域總體而言,政府購買服務工作尚處于探索階段,還沒有形成成熟的模式,建立起完善的機制。筆者以為,要深入推進教育領域政府購買服務,使之能走上制度化、規范化、經常化軌道,必須從源頭上解答和把握以下三個問題:
一、為什么要購買服務和購買什么樣的服務?
(一)重在促進教育行政職能的轉變
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便是要推進教育行政職能的轉變,促使教育主管部門全面、正確地履行政府職能,杜絕“越位”、“錯位”、“缺位”并存的現象。實踐證明:強化公共服務職能,推行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教育服務,對于促進管、辦、評分離,推動簡政放權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各級政府部門從過去“大包大攬”式的行政管理和繁瑣的事務性活動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強化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的制定和實施,有效地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和各類公共服務的提供。
(二)擴大教育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
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樣化教育服務需求相比,教育領域的公共服務存在質量效率不高、規模不足、發展不平衡和選擇性不強等突出問題,迫切需要創新教育服務供給模式,有效地動員社會力量,構建多層次、多方式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提供更加方便、快捷、優質、高效的教育服務。政府通過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向社會力量購買教育服務,將有助于擴大教育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克服供需矛盾,更好地滿足社會需求。
(三)購買的應是基本公共教育服務
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不可能是一個萬能的政府,其所能向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必然受到自身財力的約束,只能是其力所能及的基本公共服務。就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而言,各級政府能夠提供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按社會公益性(正外部性)大小排序,依次應為義務教育、學前教育、中等職業教育、普通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和社會緊缺的教育培訓服務。其中,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無疑是重中之重,應予優先確保。
二、向誰購買服務和以怎樣的方式購買服務?
(一)明確購買服務的主體和客體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3〕96號)明確規定了政府購買服務的主體主要是各級行政機關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事業單位;而承接政府購買服務的主體,則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門登記成立或經國務院批準免予登記的社會組織,以及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業主管部門登記成立的企業、機構等社會力量。同時,還就“社會組織”及“社會力量”的資質條件做出了相應的規定。因此,不是所有機構和個人都可承接服務,必須守住門檻。
(二)堅持公開、規范、擇優、效能原則
國外政府購買教育公共服務的方式及案例不少,常見的有:購買整體學校教育服務,如法國的“合約學校”;購買教育機構入學位置,如美國的“教育券”計劃;購買項目式教育服務,如加拿大的新移民培訓項目;公私合作基礎設施建設,如英國的私人機構資助計劃等。國外政府購買教育服務,一般都遵循如下基本流程:確認購買內容-公示-競爭或談判-簽訂合同-公布結果-評估-政府付款-審計,并體現“公開、規范、擇優、效能”原則。這些方式及原則,可以也應該為國內教育領域所借鑒和效仿。
(三)如何才能逾越政府購買服務存在的誤區
1、購買服務要防止政府推卸責任。推行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教育服務,其根本目的在于深化教育領域改革,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整合利用社會資源,增加教育服務供給。需要警惕的是,過度的“購買服務”也可能會導致一些政府部門“行政不作為”,對一些本該由自身履行或不能完全由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職能(如義務教育),也“一買了之”,從而造成市場監管缺位和公共福利損失。
2、購買服務不能演變為雙重管理。現實當中,一些教育行政部門通過向自身所屬的事業單位或內設機構也采取所謂的“購買服務”方式,委托或轉包部分設立審批、評估驗收、行政監管以及業務檢查等職能,而這些接受委托的單位或機構,實際履行的則是“代甲方”、“二政府”職能。如此一來,不僅沒有做到簡政放權,反而增加了對所服務對象的干擾,加重了基層的經濟負擔,這個問題必須要克服。
3、購買服務須杜絕公共權力尋租。理論上,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教育服務,也應遵守基本的市場原理,做到貨比三家、質優價廉。而實際當中,接受基本公共服務的對象,則經常感受不到良好的“性價比”。究其原因,乃是一些公共部門及其當事者的權力尋租,導致購買服務過程中存在暗箱操作、灰色交易和寡頭壟斷等不規范行為,破壞了公平交易規則。這不僅造成公共資源流失,也影響了政府良好形象,亟須從制度層面上加以研究解決。
(來源: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