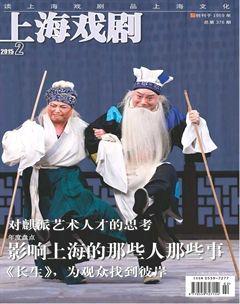對麒派藝術人才的思考
馬博敏
中國戲曲是以演員為主導的舞臺藝術,表演人才(角兒)是戲曲最顯著的征象。一位優秀的戲曲演員除了得體的外在條件,還必須具備嗓音天賦、演唱技巧、表演才能……簡言之,就是唱、念、做、打的全面技能缺一不可。京劇尤甚。其中,麒派藝術對演員自身能力的要求更高。作為南派京劇的一面旗幟,麒派藝術在發展過程中面臨人才斷層、青黃不接的艱難局面令人憂心。因此,建立健全麒派藝術人才培養體系、抓好麒藝人才梯隊建設迫在眉睫。
麒派藝術是動態的傳承
遙望皮簧鼎盛的年代,麒派藝術風靡大江南北。崇拜周信芳的弟子眾多,私淑者更是不可勝數。周信芳本人非常重視人才培養,他始終不渝地以培養后輩為己任。建國前,號稱“麒門十大弟子”的有:程毓章、高百歲、陳鶴峰、王瀛洲、于宗瑛、王富英、李如春、王少樓、徐鴻培與楊寶童。其中多是各團“頭牌”。此外,著名的麒派傳人還有:陳筱穆、王椿柏、劉文魁、劉澤民、孫鵬志、小王桂卿、陳鶴昆、李桐森、錢麟童、卞韻良、張銘聲、呂君麟等。一度,南方京劇老生幾乎形成“無生不麒”的局面。
1949年以后,周信芳又分批收了15位學生。他們是:李少春、李和曾、張學海、蕭潤增、逯興才、管韻華、徐敏初、曹藝斌、董春柏、沈金波、童祥苓、孫鵬麟、明毓昆、李師斌與霍鑫濤。其中,有不少“京朝派”與“關外派”著名演員。周信芳之子周少麟,后來也“子承父業”,成了有名的“麒派老生”。此時,可謂麒派藝術的全盛時期。
其后,經過“文革”的沖擊,周信芳先生和麒派藝術飽受摧殘,麒派劇目絕跡舞臺,麒藝人才培養也被迫中斷。周信芳先生的過早離世,更使麒派藝術雪上加霜。到上世紀80年代初,“麒藝飄零”,原先遍布各地的麒門弟子大多垂垂老矣,或衰弱病故、或隱退梨園,能夠重上舞臺者寥寥無幾。最為嚴峻的是,這一代人之后,后繼者嚴重匱乏。人走藝絕!周信芳先生創演的六百余出麒派劇目,如今能夠上演的不過十余出……
所幸的是,從政府到社會,眾多有識之士充分意識到麒派人才的危機,為搶救這一民族藝術瑰寶做了大量努力。經過8年艱苦籌備,周信芳研究會與上海京劇院聯手編纂的《周信芳全集》大部分圖書將正式出版。《全集》16冊300萬字,包括《劇本卷》、《曲譜卷》、《文論卷》等,對麒派藝術成就作了最全面、最系統的梳理與總結。
但是,與文學、繪畫、雕塑、建筑相對凝固的藝術門類不同,京劇表演是一門“活”的藝術。表演藝術的真正傳承,在于舞臺生命的延續和接班人才的不斷涌現。藝在人身,藝隨人走,師徒相授,代代傳承,是以京劇為代表的戲曲藝術得以傳承和發展的基本途徑。這是任何一種書面復制、實物保存、甚至錄影留聲都無法替代的動態傳承!
麒派藝術,一旦離開麒門傳人與麒派劇目,就將被請進博物館,供后人遠遠地觀望、追憶、嘆息。這決非我們所愿!
麒藝現狀不容樂觀
上世紀80年代以后,周信芳先生親授的38位弟子僅存10余人,當時一些在世的麒門弟子,如李如春、徐鴻培、呂君樵、孫鵬志、劉澤民、李桐森、董春柏、小王桂卿、蕭潤增、小趙松樵等,也曾多次示范演出,并在歷屆“麒藝班”擔任教師,傳承麒派藝術。高難度的藝術傳承并非幾個研習班教學所能完成,現狀難以令人樂觀。作為麒派藝術大本營,“文革”后,上海京劇院十余年間無麒派老生,直到上世紀90年代從湖南引進陳少云,尷尬局面才得以扭轉。
記得上世紀 80年代末,在不足20名的第三代麒派傳人中,陳少云、裴永杰二位堪稱佼佼。后來陳少云繼承了大量傳統麒派劇目,基于對麒派藝術的準確理解與把握,他已形成“外樸內秀”的表演風格,成為當今麒派藝術的領軍人物。除繼承了一批麒派名劇外,陳少云創演的《貍貓換太子》、《成敗蕭何》、《金縷曲》、《宰相劉羅鍋》等新編戲受到廣泛歡迎,得到藝術界的高度評價。
歷史上,武漢是麒派藝術頻繁活動的第二重鎮,裴永杰自加盟湖北京劇院后發展勢頭令人興奮,他排演的《牛子厚》、《楚漢春秋》等劇目得到業內認可,受到當地麒迷觀眾的熱捧。
再往下,能得到社會公認的新一代麒藝傳人就屈指可數了。在歷年為青年京劇人才提供展示平臺的“青京賽”、“學京賽”等賽場上,麒派老生缺位數屆。目前,新生代演員中,上海的魯肅、郭毅、于輝等青年麒派演員通過前輩的悉心教導,業務皆有長進,總算在第七屆青京賽上取得一金二銀的好成績,為麒派藝術爭了一口氣。但他們畢竟還很稚嫩,一時難挑大梁。在京津及其他地區,“小演員”難以引起重視。
麒派藝術,這份標志著近代京劇藝術高峰的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何能夠薪火相傳,不被湮沒?責任誰擔?
麒門薪火任重道遠
事實上,努力一直在進行。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有關部門的推動下,上海舉辦過三次麒派藝術研習班:
1984年的“麒派藝術進修班”。主教老師是張信忠、李如春、徐鴻培、李伯麒、張泰華、趙曉嵐、劉斌昆等麒派弟子以及長期與周信芳先生同臺合作的老伙伴,計鎮華、王全熹、周公謹、小趙君甫等25名學員來自全國12個省、市、自治區的18個京、昆院團,繼承學習了《徐策跑城》、《蕭何月下追韓信》、《斬經堂》、《明末遺恨》(《夜訪》《撞鐘》)、《烏龍院》、《清風亭》等劇。該班于當年9月開班,為期三個月。
2001年“麒派藝術研修班”。主教老師徐鴻培、劉澤民、小王桂卿、蕭潤增、張信忠等,為陳少云、王全熹、裴永杰、奚中路等來自全國5個省、市,6個京、昆院團及戲校的15名學員傳授了《未央宮》、《唐太宗馬陷淤泥河》等劇目。該班于當年7月開班,為期兩個月。
2008-2009年的“周信芳藝術傳承研習班”。主教老師小王桂卿、趙麟童、張信忠、蕭潤增、楊建忠(小麟童)、王全熹、周公謹、陳少云等,裴永杰、朱玉峰、范永亮、傅希如、田磊等20名學員學習、演出了《四進士》、《戰潼臺》(《闖圍》《救駕》)、《打鑾駕》等劇目。
值得稱道的是,在總結前兩屆“麒藝班”經驗基礎上,2008-2009年的“研習班” 打破了以往短訓班的辦班方式,著眼人才選拔,以劇目傳承為抓手,根據師資和生源情況,設立上海、吉林、天津、福建等幾個基地,分散播種,集中培養;以戲傳藝,以藝樹人。經過一年的實踐,取得了預期效果,并為以后更多流派傳承班的開辦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三屆“麒藝班”為推動麒派藝術、培養京劇接班人作了積極努力,也取得一定成績。然而我們發現,這種以麒派藝術普遍培養演員的方法,大多數學員并非專攻麒派的老生,多從麒派藝術中汲取豐厚營養,極大地提高了本行當的業務素養,的確可喜。但是,真正宗麒的老生數量仍然繼續銳減,麒派斷層的危機依然時時威脅我們事業的發展。
基于此,在上海文教結合辦與上海市文廣局的支持和組織下,從2010年起,正式啟動了“京劇麒派人才培訓五年計劃”。在全國范圍內吸收、挖掘優秀麒派人才,進行培養。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了相對長期的傳承計劃,循序漸進、由淺入深地對麒派尖子演員進行強化培訓,經過五年努力,姚中文、郭毅、魯肅、于輝等中青年人才浮出水面,才有第七屆“青京賽”中收獲一金二銀的佳績。
麒派藝術博大精深,對于寄予厚望的新生力量而言,五年的培訓只能是初窺門徑,想要成為合格的麒派藝術接班人,成為繼陳少云之后的麒門才俊,尚且任重道遠!
走出誤區直面困難
麒派要發展,必須有傳人,青年高端人才關乎麒派藝術的興衰。為此,還要厘清幾個問題。
首先,目前社會上對麒派藝術仍然存在認識上的誤區。
一是對麒派藝術認識膚淺。一些人將麒派藝術簡單理解成“不重演唱而專注表演”,因此“好嗓子不必學麒派”。這實在是對周信芳先生的大不敬!要知道,麒派神韻在蒼勁醇厚、樸質無華、雄渾剛健。雖曾有過倒倉經歷,而周信芳先生在唱、念中寬厚、蒼勁、老辣的風味,豈是尋常“好嗓”所企及?!所以,我認為還應該是靜下心來研究周先生的藝術特點。
另外,在戲校的教育中,存在流派學習的認知誤區。就戲曲基礎教育而言,確實應該以扎實的基本功學習為主。就連周信芳先生本人也主張“青年演員不要過早地學什么流派,學習路子越寬越好,不僅跟本行當老師學,也要跟其他行當老師學”。這里,“早”的度是什么?我以為在戲校的中專階段,前幾年一定得不分行當、不分流派地夯實基礎。但在高年級便可分流。一方面,經過前幾年的基礎學習,學生對京劇藝術及行當流派有一定的了解和認識。另一方面,從年齡段來看,這期間學生處于青春期,正是求知欲強、精力旺盛的時候,如在此時分行歸類,將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晚一二年,則可能錯失最佳學藝時機。
第二,麒派藝術傳承之難還在人才的標準高。麒派藝術對演員的要求極高,甚至苛刻。不僅要求有個頭扮相,還要有嗓子、有武功基礎,周信芳先生對青年人才的要求是“學文戲的要學幾出武戲。老生也好、小生也好,沒有腰腿功、沒有武功的底子,是不可能成為一個好演員”。此外,麒派藝術非常重視內心體驗和外形表現相結合,對表演的分寸有極高要求。周先生認為“麒派是唱出來的,是用心唱、用靈氣演”。怎樣用“心”、用“靈氣”?聽起來比較玄,其實內中包含除了京劇技藝、人生閱歷之外,更有文化修養、藝術鑒賞與感悟等多方面因素。已故京劇藝術家小王桂卿先生晚年曾感嘆:“學麒派太難!我學了幾十年麒派,到現在還只能算是業余。”雖是自謙之辭,從中亦可見麒派藝術的精深奧妙、難以掌握,往往使后人望而生畏,敬而遠之。
第三,培養缺位。
一是有關方面對麒派藝術重視度不夠。沒有切實將培養麒派藝術接班人放在重要位置。其實,人才稀缺匱乏已成為困擾麒派藝術傳承的難題,制約麒藝發展的瓶頸。人才梯隊的建設,優秀人才銜接有序和新秀輩出,是藝術綿延光大的根本保證。傳承與發展麒派藝術不是少數人或部門的事。必須依靠學校、劇院與社會三位一體共同努力,這是由麒派藝術的藝術價值與文化定位所決定的。
再者,師資長期缺失。隨著自然規律,一批老一輩藝術家、周先生的弟子們相繼去世,帶走了一些技能和劇目,使眼下京劇舞臺上“麒藝凋零”。給麒派藝術的繼承和發展帶來極大困難。新時期以來,上海戲校竟然沒有一位麒派專業教師為學生傳戲授藝。實在是不應該!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區還能怎樣?!
怎樣才能培養出德才兼備、符合時代要求的麒派高端藝術人才?我以為,藝術人才的缺失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也不能指望一蹴而就。目前,青年麒藝接班人從數量到質量都遠遠不能滿足舞臺的需要、觀眾的要求。有關部門必須高度重視麒派藝術人才斷層的問題,對麒派藝術進行高水平的搶救與傳承。麒派藝術的精華與活力主要在傳承人與教師身上,要珍惜僅存不多的寶貴資源,充分發揮他們的傳、幫、帶作用,有計劃、有步驟,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培養一批優秀的麒派傳人,培養標志性的領軍人物,是我們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從幾屆麒研班的師資情況來看,教師的年齡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少,這里,我要特別感謝為麒派藝術薪火相傳奉獻才智的諸位傳道者。張信忠、趙麟童兩位老師,雖八十高齡仍心系麒派,情牽弟子;王全熹、周公謹、逯興才三位老師年過七十壯心不已,全心投入; 陳少云、裴永杰兩位堪稱“壯年”,也都年屆花甲,在頻繁演出的同時,義不容辭地承擔起培養青年的重任。我們為他們的奉獻精神所感動;更為師資斷層的現實備感焦慮。因此,麒藝人才的培養,重在師資力量的延續。
我們希望宣傳主管部門更加關切、重視麒派藝術,保護麒派人才。在宣傳、評論麒藝人才的同時,幫助觀眾提高對麒派藝術的鑒賞能力。讓那些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麒藝學習者,經受社會與時代的檢驗,以此推動麒藝人才蓬勃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