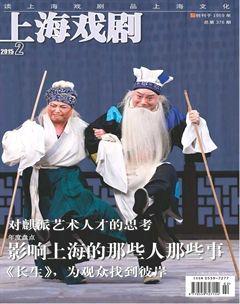話劇對我是一個意外
木葉
一個小男孩,手里拿著一張報紙,煞有介事地念著,一群小伙伴圍繞著他,非常認真地聽他講故事,時而唉聲嘆氣,時而鼓掌叫好……這便是吳念真最初的戲劇體驗。他說:“那樣子的成就感和快樂,在做電影的時候沒有感覺到,反而到做舞臺劇的時候卻充分感受到,看到觀眾在臺下大笑,或是互相分享面紙擦眼淚,那種時刻忽然就回到小時候念報紙的時光,得到一種最單純的快樂。”
選擇《臺北上午零時》作為在上海的首次亮相,是因為他在寫這個戲時“用情至深”,這戲里寫的是他自己的青春。那么,就讓我們走近這位臺灣知名作家、編劇、導演、演員、主持人,聊一聊他生命中關于戲劇的這些人、那些事。
(Q:上海戲劇雜志社;A:吳念真)
Q:劇名《臺北上午零時》有何深意?
A:“臺北上午零時”是這個故事講述的背景年代里面最流行的一首臺語歌,同時還是一個廣播節目的名稱,每天晚上十一點到凌晨一點,它安撫了當時很多從鄉下到臺北來工作的年輕人的心。這個節目到現在我都很懷念,一直想做一個三更半夜的廣播節目,陪大家聊天。所以“臺北上午零時”這幾個字,對于我來講是青春時候一種安定的力量,不曉得多少次是在那樣的音樂聲中安安靜靜地睡去。
Q:作為“臺灣最會講故事的人”,您是如何在戲中講故事的呢?
A:不論是戲劇、電影,任何形式的創作,都是生命經驗的交換。我一直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創作者,我好像就是聽到別人講給我的事和小細節,把它們累積起來做一個整理之后轉換,所以我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轉述者,把別人的故事用我的方式去告訴別人。蠻慶幸自己是個寫作的人,而且這個人看起來也蠻和藹可親的,所以常有人講故事給我聽,我很幸運,很多人愿意和我分享他們的生命經驗和故事,所以說,我不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我是一個善于轉述故事的人。
Q:您是怎么與創作、與戲劇結緣?
A:我人生很多事情都很意外。我是在礦村長大的孩子,初中畢業就到臺北工作,工作穩定了就去念夜間部高中,畢業后就去當兵,回來二十三歲了,幾乎沒有一技之長,于是決定考夜間部大學。那時候開始寫小說,關于礦工的小說,因為他們的生命沒有人去關懷,后來發現寫小說沒有用,因為幾乎沒有人在看,而你所寫的對象也不知道有人在寫他,也得不到被安慰的感覺,所以想著有機會一定要做影像。后來有朋友說我寫的小說很像劇本,于是有了機會去寫電影,他們覺得我這個人蠻用心和耐用,之后就跑去電影公司上班,就這樣一步步都是意外。戲劇也是意外,因為一群朋友做劇團,發現因為收入和支出的問題做得好辛苦,我就跟他們說你們為什么不把觀眾群拉大,做的戲可以更通俗一點,于是就進劇團幫忙,一直做到現在。
Q:您的戲被稱為“國民戲劇”,感覺如何?
A:我做的第一部戲《人間條件》很通俗,所以劇評人說我寫的是“國民戲劇”。我覺得“國民戲劇”很好啊,我不搞“菁英”戲劇,我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跟多數人溝通嘛。就像小時候被叫去念報紙給大家聽一樣,我感覺很開心。觀眾很鼓舞我,時常會在觀眾問卷上看到:導演謝謝你,我們被理解了,我們被安慰了。所以說,戲劇給我更直接的回應,于是有動力一直繼續做下去。
Q:不搞“菁英”戲劇,那么您想做怎樣的戲劇呢?
A:普羅大眾的。我看很多前衛的電影和音樂,然而我最佩服的導演是日本導演山田洋次,他幾乎沒得過世界性的獎項,但他是日本人最喜歡的導演,現在80歲還在拍電影,他拍的電影老少咸宜,講一個平凡的故事,一般人都能領受,所有看的人都懂。
Q:在您的戲中,希望演員呈現怎樣的狀態?
A:我是比較隨意的導演,我希望演員是比較寫實的調子。我沒受過舞臺訓練,所以我用自己的方法去想去做,于是臺灣的劇評就說我的舞臺劇呈現常常出現類似電影的感覺。對我來說,因為不懂,反而沒有拘束。但是旁邊很多懂的人會對你說不能這樣搞,比如舞臺劇很重視走位,但我在編導的時候就是不走位。我曾經有一出戲叫《清明時節》,里面一場戲三個演員幾乎都在講話,但他們就是不動。其他人都說不行,你這個應該走位,我卻不認為,我覺得如果講話內容是非常專注、情感很重,你一移動不是會把情緒搞淡嘛。后來證明,觀眾沒有任何不好的反應,全場安靜。所以,我認為自己的決定是對的,應當由內容去決定形式。所以不懂的人去做,或許又有他的好處。
Q:作為戲劇編導,您在舞臺上最想和觀眾分享的是什么?
A:一出戲里面,不可能把所有你想說的都塞給觀眾,觀眾自然會自取所需。創作者最好不要跑出來自己講我這出戲的意義是什么,戲劇如果有個部分能和在場觀眾產生一點共鳴,就夠了。
如果說小時候是見山是山,到做電影是見山不是山,那么現在這年紀做話劇是見山還是山,最簡單,最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