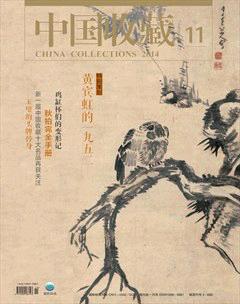一場友誼的見證
鮑艷囡



在清代“肖像國手”禹之鼎的繪畫里,有不少作品是描繪宮廷重大活動的。古代宮廷繪畫所具有的紀實作用便是忠實地記錄剛剛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情。在沒有影像拍攝技術的古代,形象化記錄古代宮廷生活、真實地保存好歷史的重任全部由眾多紀實性繪畫所承擔。除此之外,各朝天子通過宮廷繪畫表現他們的英明威武,弘揚他們統治的繁榮昌盛,把他們的豐功偉績載入史冊。
柴門倚杖
禹之鼎(1647年至1716年)康熙年間以畫供奉入直暢春園。擅山水、人物、花鳥、走獸,尤精肖像:“墨骨和色暈并重,既有淡墨渲染的堅實結構起伏,又有重色暈罩的明潤肌膚色澤。”“一時名人小像皆出其手”,飲譽于康熙朝。由于所繪肖像形神兼備,因此禹氏雖然職位不高(禹之鼎在康熙中入京任鴻臚寺序班),但也頗受器重。他曾經把皇帝賜予的書籍、硯臺精心畫下,并自題《賜書研圖》(藏于故宮博物院)。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琉球來使請封,禹之鼎也隨冊使到琉球。這是他一生中最顯赫的事跡,他的肖像畫譽滿京城,也與此次出使有密切關系。
山東博物館藏有宮廷畫家禹之鼎的一幅一級品,名為《柴門倚杖圖》卷,是畫給清初文壇領袖王漁洋的。全卷由三部分組成,縱35.8厘米,橫355.5厘米,為一幅詩書畫結合在一起的絹、紙手卷。第一部分為其門人書法家陳奕禧“寒山秋水”的題字,橫114厘米;第二部分是柴門倚杖圖,橫100厘米;第三部分為跋文,由漁洋山人的九位門生的書法作品構成,內容都是謳歌贊美禹之鼎高超的畫藝和王漁洋高遠清尚的情操。這一部分橫141.5厘米。畫心絹本設色,題跋為紙本。款識:新城王老大人命,廣陵禹之鼎寫于金臺。鈐印:禹之鼎印(白文),慎齋(朱文),押角印:逢佳(朱文)。禹之鼎本籍揚州府興化縣人,后寄籍江都。因揚州、江都古稱廣陵,故自署常稱“廣陵”人。
此畫像主王漁洋美髯瀟灑,戴斗笠,著長服,倚杖微笑而立,有若思狀,顯示出漁洋山人的優雅詩意。其衣紋用柳葉描,輕逸飄灑而又流利靈動。人物面部及手足等細部則施以工筆,面部采用明代肖像畫家曾鯨的墨骨畫法:用墨線勾出輪廓后,根據不同對象的膚色和不同部位的深淺,用淡墨和淡赭石按面部結構層層渲染,以顯現出結構上的明暗凹凸變化。這種以色暈為主的畫法,略帶西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肖像畫的質感和立體感,人物形象飽滿而神形兼備,呼之欲出。人物背后有柴門綠柳,柳樹下方一叢小草,是補景。旁邊是湖水,碧波蕩漾,溪流向遠處淡化,跳躍的浪花讓人仿佛聽到了潺潺的水聲,把動氣植入靜的畫面,更增添了山中的寂靜。近景蔥郁的叢林、橫臥的青山施以重彩,層層渲染;隔湖遠山無際,淡墨勾出,略施顏色。青綠山水,是禹氏常用筆法。白描和工筆穿插并用,整個作品畫面人體比例恰當、光線透視明顯、構思用色奇巧,令人贊嘆折服。古人作畫,極講陰陽平衡和照應,全畫的水和山為橫式,便用立的人、樹和柴門做豎式來補充照應,體現了作者謀篇布局的能力。
此幅肖像是按照王漁洋本人的意思,以唐代王維的詩句“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為主題而做,這首詩也被禹氏寫在畫面右上角。作者所描繪的是一位年事已高、飽經宦場風云、面有倦容、兩眼深邃很有洞察力的文人。布局、用筆、賦色都與詩句情趣相一致,人物與環境的安排都與主題相協調,稱得上是一幅構思嚴謹、筆墨周到之作。
作者用簡約朦朧的畫筆,對主人公遠離喧囂的人群,退隱山林的心態作寫意的勾勒,通過人與自然的交流傳達一種感悟和心有靈犀,使人與山水的對話產生詩情畫意的美感,而一切感受又都蘊含在景物描寫中,營造了“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的靜穆悠遠、自然沖談的意境。這種向往山林、向往幽靜的題材是禹氏為王漁洋所畫肖像畫中經常出現的。這種神韻如果不是深知王漁洋的為人本性,是不會繪得如此傳神的。禹氏在為王氏繪《放鷴圖》卷(現藏故宮博物院)中曾題詩:“五柳先生本在山,偶然為客落人間。秋來見月多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鷴。”也是把王氏和陶淵明相比。
詩畫相傳
禹之鼎和王漁洋,一個是供奉內廷的“肖像國手”,一個是位列九卿的“一代詩宗”,兩位同時代歷史人物的交往可謂順理成章。在禹氏與王漁洋交往的二十年間曾為他畫過許多肖像畫,有據可考的還有不少(如上圖)。
據張庚《國朝畫征錄》記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禹之鼎曾為文簡(王漁洋謚號)畫戎裝小照,王石谷補景,陳香泉題名《北征扈從圖》。后人繆荃孫在端方寓中見過此畫,并有著錄。”該件作品至今未見實物。據有關專家介紹分析,禹氏繪王漁洋的其他肖像畫在海內外流傳的還有一些。就以上這些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作品來說,兩人之間的友誼是十分深厚的。因為肖像畫不同于山水畫和花鳥畫,畫家可以率性發揮;好的肖像畫是像主和畫家良性互動的結果。王漁洋是當時的名流,對畫像的布局安排自然會有自己的要求,禹氏按照他的設想勾勒出作品的梗概,離席后再細細作畫,完成之前還要和像主共同商量,以期達到最佳效果。這個過程只有相處融洽才會合作得愉快。禹氏為王漁洋畫了近二十年肖像畫,足可以看出二人過從很密,關系非常和諧。這些畫生動傳神,面容與神態都酷肖王漁洋本人,如果作者對所畫對象沒有認真的觀察、了解,沒有精湛深厚的藝術功底,是難以達到如此逼真程度的。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畫面上的主人公形象隨著年齡增長,臉型、須發均有細微變化,足見禹氏畫藝之精湛。
從《柴門倚杖圖》卷和以上漁洋畫像可以看出:禹氏很少繪無背景的單身立、坐像,他的肖像畫往往把人物置于特定的情節和環境之中,展現主人公的具體活動和生活環境,力求真切反映他們的行為舉止和思緒心態,因此富有真實性和親切感。這種情景肖像圖的傳統手法,禹氏運用得嫻熟自如。他還根據被畫對象的詩意來構圖,此幅畫圖所繪場景和右上角王維的詩句結合得惟妙惟肖:柴門常常表現隱居生活和田園風味;倚杖則表現年事已高和意態安閑。柴門之外,倚杖臨風;聽晚樹鳴蟬、秋水叮咚;看渡頭落日、墟里孤煙,畫中人物那安逸的神態、瀟灑的閑情,和“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的陶淵明頗有幾分相似。《柴門倚杖圖》著力刻畫人物的表情,傳情寫照人物思想,較為突出地反映了禹之鼎作品的藝術特色:配景有致,構思巧妙,用筆精練。
禹之鼎肖像品格的形成,一方面是他悉心師法古人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與他身邊文人群體的影響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禹氏畫中人物曾為吳偉業、宋琬、朱彝尊、王翚、宋犖、王原祁、高士奇、納蘭性德等人畫過肖像,這些像主在文壇、書畫、鑒藏等領域內都是領袖人物,且在政壇上大多具有顯赫的地位。禹氏作畫常用“必逢佳士亦寫真”白文印,取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詩“偶逢佳士亦寫真”句化用之。可見他的刻畫對象都是儒雅高潔之士。《柴門倚杖圖》的壓角印“逢佳”應是“必逢佳士亦寫真”的縮寫。王漁洋、吳偉業、宋琬、汪懋麟、朱彝尊、宋犖等清初有重大影響的詩人和書法家的肖像能傳諸于世,皆賴于禹氏傳神妙筆。為這些顯赫當時、影響后世的重要作家繪像,無疑也提升了禹氏的知名度,正所謂“人以畫傳”。
《柴門倚杖圖》完成后,王漁洋門人爭相題詠,王氏的號召力和凝聚力可見一斑。這些題詠,把它們放在畫中是整幅藝術作品的一部分,分離出來,又是可以單獨閱讀的文學作品和書法作品。詩書畫結合在一起,珠聯璧合,相得益彰。既增強了畫的形象性,又觸發人們更多的藝術聯想,由此增添了審美情趣,深化了作品的主題,完整地體現了中國文人畫的藝術特色。這是世界各畫派中絕無僅有的一支,也是中國畫家追求的繪畫最高境界。
《柴門倚杖圖》卷,不僅體現了禹氏的繪畫成就,而且為研究清初的書法和王士禎創立的神韻詩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從這個意義上說,《柴門倚杖圖》卷無疑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寫作無聲詩。”黃庭堅這句詩是對文人畫的褒獎,也可以作為本幅手卷的評價。人與景,詩與墨,思與情,在一幅作品里渾然一體。江山可易,文脈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