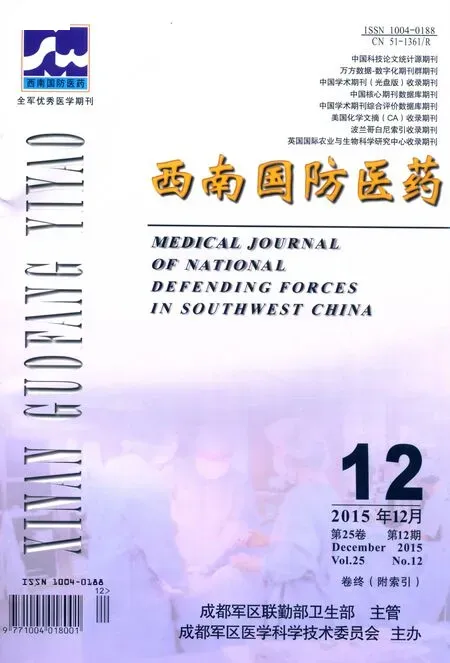Th1 細胞因子水平與鼻咽癌患者預后相關性及危險因素分析
姜鳳舉,彭裕萍,李 艷,申江江
鼻咽癌是臨床上常見的頭頸部腫瘤,鼻咽癌對放射治療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因此放射治療為臨床上的首選方案,并且隨著放療技術的發展進步,新型化療藥物的出現、 靶向治療的應用以及更多的綜合手段被用于鼻咽癌患者的治療, 使鼻咽癌患者的存活率也逐步升高[1]。 但是,大多數鼻咽癌患者為低分化,具有較高的惡性程度,放射治療后也常會發生遠處轉移或局部復發, 這也是導致鼻咽癌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2],大大降低了患者的預后及生活質量。 EB病毒是鼻咽癌發生發展的重要致病因素, 病毒感染常會引起機體的免疫應答,誘發炎癥反應,而Th1 細胞因子是評價機體免疫狀態的重要指標[3]。本研究對影響鼻咽癌患者的相關危險因素進行了分析,并對Th1 細胞因子與鼻咽癌患者的遠期預后的相關性進行了探討。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資料 選取我院2007 年1 月~2009 年12 月收治的124 例鼻咽癌患者, 均為首次治療,均符合鼻咽癌診斷標準,并由組織活檢確診,同時排除其他原發惡性腫瘤的患者。 其中男71 例,女53例,年齡28~72(47.6±7.1)歲;臨床分期:Ⅰ期11 例,Ⅱ期29 例,Ⅲ期45 例,Ⅳ期39 例。 所有患者均接受鼻咽癌及頸部的根治性治療,放療劑量為70~76 Gy,2 Gy/次,5 次/w。 所有患者至少接受了4 個周期的DF 化療方案(順鉑100 mg/㎡,靜脈滴注1 d;氟尿嘧啶750 mg/m2, 靜脈滴注1~5 d, 每3 w 重復)治療。 在治療結束后,根據Resist 標準評價治療效果,其中完全緩解(CR)65 例,部分緩解(PR)59 例。
1.2 檢測指標 在治療開始前, 抽取患者清晨空腹靜脈血, 離心分離血清, 采用ELISA 法檢測Th1細胞因子[白細胞介素-2(IL-2)、干擾素- γ(IFN-γ)及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表達水平。 儀器選用美國寶特Bio-Tek ELX800 全自動酶標儀,試劑選用北京方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產的人IL-2、TNF-α、IFN-γ 檢測試劑盒,檢測按照說明書操作,并嚴格控制檢測質量。
1.3 隨訪 通過門診復查、電話隨訪、上門隨訪以及問卷調查等方式,記錄患者入院后的一般病歷資料以及轉移、復發、生存情況等臨床特征資料;出院后每3 個月對患者進行1 次隨訪,隨訪日期截止于2014 年12 月。 其中如果死亡患者,則停止隨訪,而隨訪截止時生存的患者即為存活。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7.0 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分析,計數資料以例和百分率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 計量資料以±s 表示, 比較采用方差分析;雙向無序列聯表資料用Pearson χ2檢驗,單項有序列聯表資料用趨勢χ2檢驗,并對相關危險因素進行Logistic 多因素回歸分析, 假設檢驗水準為α=0.05。
2 結果
2.1 隨訪情況 截止到隨訪結束,124 例中,1 年生存率為85.5%(106/124),3 年生存率為70.2%(87/124),5 年生存率為59.7%(74/124), 其中包括了局部復發、遠期轉移。 治療后,近期有2 例出現骨髓抑制,4 例惡心、 嘔吐,2 例出現皮膚反應,3 例出現口腔黏膜反應,而遠期有3 例內涎腺損傷,2 例出現牙齒損傷,1 例出現皮下組織纖維化,不良反應的總發生率為13.7%。
2.2 不同預后患者的Th1 細胞因子水平分析 對患者的生存時間與其IL-2、IFN-γ、TNF-α 水平的關系分析發現, 隨著生存時間的增加,IL-2 水平升高,TNF-α 水平降低(P <0.05),而不同生存時間的患者其IFN-γ 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 >0.05),見表1。

表1 不同預后患者的Th1細胞因子水平分析(pg/ml)
2.3 單因素分析 根據治療后患者的3 年及5 年生存率的單因素分析可知,臨床分期、T 分期及N 分期對鼻咽癌患者的生存率存在顯著影響(P <0.05,表2),分期越高的患者預后越差。 因本組患者年齡跨度較大,因此,在本單因素分析中未納入。
2.4 多因素分析 通過多因素Logstic 回歸分析可知, 患者的年齡、T 分期、N 分期以及治療方式是影響鼻咽癌患者5 年生存率的獨立相關危險因素(P <0.05,表3)。

表2 患者治療后生存率的單因素分析(n=124)
3 討論
鼻咽癌多發于男性,并且主要以非角化型為主要病理分型, 而非角化型病變對放射治療敏感度高,因此多采取放療為主的治療,但極易導致局部復發或遠處轉移[4]。 有研究顯示,鼻咽癌的發生與EB 病毒感染有關[5]。 在機體內的免疫調節中,細胞因子具有重要的作用。 由Th1 細胞分泌的IL-2、IFN-γ 和TNF-α 參與調節細胞免疫, 其中IL-2 能夠在T 細胞增殖誘導促進B 細胞分泌釋放抗體中產生促進作用, 同時能夠提高T 細胞的殺傷作用, 并使NK 細胞的活性增強[6];IFN-γ 能夠產生較強的免疫調節及抗腫瘤作用,而TNF-α 能夠引起腫瘤出血、壞死并促進纖維細胞增生[7]。 癌癥患者的機體存在Th1及Th2 細胞因子間的免疫漂移,使得Th1 呈弱勢狀態,因此,導致機體的免疫抑制[8]。 有研究顯示,腫瘤患者體內IL-2 的水平較正常人顯著降低,并且可以通過IL-2 水平以觀察治療效果[9],同時也有許多研究表示,患者血清TNF-α 水平與腫瘤患者的預后具有相關性, 主要原因可能為TNF-α 能夠作用于腫瘤組織,但對正常組織不產生影響,同時能夠使腫瘤血管的內皮細胞凋亡,從而使腫瘤組織出血壞死[10]。 并且有研究表示,TNF-α 能夠改善血管的通透性,使得化療藥物能夠產生局部高濃度而降低耐藥性,盡管TNF-α 與IL-2 均屬于Th1 細胞因子,但其對患者的影響作用相反[11]。

表3 影響鼻咽癌患者預后的多因素回歸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鼻咽癌患者隨著生存時間的增加,IL-2 水平升高,TNF-α 水平降低, 表明IL-2 及TNF-α 水平均有可能作為鼻咽癌患者預后判斷的生物學指標。 同時,針對可能影響鼻咽癌患者預后的諸多因素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 年齡、T 分期、N 分期以及不同的治療方式均是影響鼻咽癌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P <0.05)。
綜上所述,鼻咽癌患者年齡越大、分期越高,其預后越差;Th1 細胞因子中的IL-2 及TNF-α 水平可作為鼻咽癌患者預后判斷的生物學指標,可以為臨床治療方案的選擇及預后的判斷提供參考。
[1] 冼獻清, 謝民強, 江剛. 鼻咽癌化療現狀及進展[J]. 臨床耳鼻咽喉頭頸外科雜志, 2013, 27(3): 164-168.
[2] 秦雷, 楊林. 鼻咽癌放射治療的進展[J]. 安徽醫科大學學報,2012, 47(6): 720-724.
[3] Chia WK, Teo M, Wang WW, et al. Adoptive T-cell transfer and chemotherapy in the first-line treatment of metastatic and/or locally recurrent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J]. Molecular Therapy,2014, 22(1): 132-139.
[4] 黃小顏, 許琳, 溫本, 等. 動態監測EB 病毒抗體對鼻咽癌的診治價值[J]. 中華實用診斷與治療雜志, 2014, 28(5): 498-499.
[5] 王朝陽, 李桂生, 黃海欣, 等. 鼻咽癌死亡原因和預后因素[J].廣東醫學, 2013, 34(5): 754-757.
[6] Cai MB, Wang XP, Zhang JX, et al. Expression of heat shock protein 70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s: different expression patterns correlate with distinct clinical prognosis[J]. J Transl Med,2012, 10(1): 96-107.
[7] 陳冬平, 齊斌, 余意, 等. 鼻咽癌遠期生存率及預后因素分析[J]. 實用醫學雜志, 2012, 28(12): 1999-2001.
[8] 項紅霞, 黎靜. 鼻咽癌淋巴結轉移診斷標準的研究進展[J]. 現代腫瘤醫學, 2013, 21(5): 1140-1142.
[9] Li J, Mo HY, Xiong G, et al. Tumor microenvironment macrophage inhibitory factor directs the accumulation of interleukin-17-producing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and predicts favorable survival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s[J].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012, 287(42): 35484-35495.
[10] 高云生, 胡超蘇. 局部晚期鼻咽癌綜合治療研究進展[J]. 中國腫瘤臨床, 2012, 29(24): 2044-2046.
[11] Ye S, Li ZL, Luo D, et al. Tumor-derived exosomes promote tumor progression and T-cell dysfunction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enriched exosomal microRNAs in huma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J]. Oncotarget, 2014, 5(14): 5439-5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