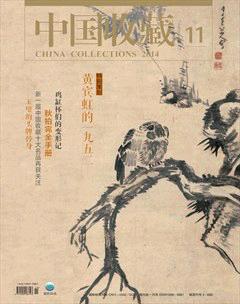靜心攻玉 用心制佛
賈理智



“掌握嫻熟的技藝之后,要以一顆虔誠的心,慈悲的心,無我的狀態,手隨心動,才能雕出感人的佛像。”—蘇然
深秋的一天,記者來到北京南城的一座院落。剛踏進門,就見一群人正圍著一位女士對幾塊和田籽料品頭論足。面對這些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玉料,這位女士雖話語不多,但她三言兩語的評判卻是一語破的。
這個絲毫沒有大師架子的女士就是中國玉石雕刻大師蘇然。蘇然的“靜”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不善言談的她總喜歡靜靜地站在一旁,靜靜地觀看一塊塊本無生命的原石,但轉瞬間在她眼中這些原石已經轉化成了一件件令人嘆服的藝術品。那一刻,再尋常不過的石頭也能被她雕出彩兒來。
記得蘇然制作過一件《玉舍利》。在創作這件作品時,大師沒有被傳統的經驗所束縛,而是以謙卑、純然、無私無欲之心體悟此玉料。她翻閱《涅經》讀到:“以勝金剛定,自碎金剛身,不舍于大悲,舍利猶分布。”突然有了靈感。大師在舍利之身不動一刀,只在天然形成的黃玉之表——材質厚重的頂部用梵文陽雕六字真言。看似簡單,卻造就了一件佛教藝術精品,讓人難以釋懷。
一提及佛教藝術作品,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菩薩造像、羅漢像等。但在蘇然的刀下,卻總能見到不同于他人的作品。《金山佛印》便是一例。其雖為現代形制的藝術品,但不乏深厚的內蘊與文化。璀璨的皮色,不僅高貴典雅,而且寓意深刻——象征著中華大地山河統一,禮儀之邦繁榮昌盛。印文中的“佛”字與依綹裂而雕的紋飾相得益彰。明明是枚印,卻禪味十足,這樣的佛教藝術品怎能不讓人心動?
善“讀”玉的蘇然,其刀下的一件件佛教題材作品也讓人“讀”出純粹、安寧、謙卑等涵義。這位玉雕界難得的女大師,是如何讓她的作品總是不乏圍觀者和收藏者呢?那就讓我們聽聽蘇大師是怎么說的。
《中國收藏》:很多玉雕師都會創作各種不同題材的作品,但是很難說他們專擅哪一類。然而提到您,人們自然而然地會想到您刀下的佛教作品。您為什么這么偏愛佛教題材?
蘇然:事實上,我對以佛教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情有獨鐘。作為“老北京”,從小就生活在這座歷史悠久、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城市里。雍和宮、白塔寺、潭柘寺、戒臺寺這些名勝古跡,也是我年輕時常去游玩的地方。每每面對佛像那慈祥的目光,我的心情就會變得很平靜,而我的思想也似乎得到了某種升華。
應該說,這種精神上的情愫是我選擇佛教內容作為主要雕刻題材的根本原因。眾所周知,佛教從漢代開始就與中華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濃厚中國特色的傳統宗教,并且上自宮廷、下自民間廣泛地以各種材質,特別是金、銀、玉等為佛陀造像,來表達人們對他的敬仰和熱愛。所以佛教題材自古就是玉雕工匠們的最愛。
佛像屬于玉雕中的人物類雕刻,我當年進入北京市玉雕廠就是在人物車間里師從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宋世義先生,學習人物雕刻。在玉器行里,宋先生是全國有名的大師,尤以帶徒嚴格著稱,為我打下了功底。另外,北京的人物玉雕有其地域文化優勢,傳承了明清宮廷風格,所以佛教題材作品中也鮮明地體現了這種大氣典雅的宮廷藝術特色。基于這些原因,讓我對佛教題材的創作才偏愛有加。
《中國收藏》:您雕刻的佛像為什么那么與眾不同?
蘇然:我認為一件玉雕做得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雕刻者的精神狀態。一般玉雕師在制作佛像時,是從一件商品的角度出發,是從市場和商品價值的角度去衡量。而我在創作佛像時,首先抱著一顆虔誠的心。佛是真、善、美的化身,這就要求你要把佛的莊嚴法相表現出來。而不是隨意地把佛雕成美女或是其他形象。
我為雕刻做了不少努力,主要在兩個方面:一個是雕刻技巧的磨練,一個是對佛教理論方面的學習以及對佛教造像的把握。雕刻技巧更多的是在最初的學習階段完成的,而對于佛教造像和理論的學習則幾乎貫穿了我整個玉雕生涯。這兩天我剛從青海考察回來,此行收獲甚多,完整地了解了藏傳佛教各分支之間的關系,以及熱貢唐卡藝術中眾佛的造型與體態。其實像這種專程的考察,我每年幾乎都會有幾次,敦煌、天水、拉薩、大同等地,都成了我考察學習佛教藝術的寶庫。
《中國收藏》:古人將玉比作君子,看重玉的溫和與典雅;而自古以來佛的形象也是大慈大悲、溫柔沉靜,您怎么理解玉與佛的這種微妙關系?
蘇然:這種關系其實不難理解。事實上,自古以來我們就對玉推崇備至。早在商周時期,玉就被看作是天地精氣的結晶,用做人神心靈溝通的中介,有著不同尋常的宗教意義。春秋戰國時,孔子曾對玉有專門的論述,后世更有“玉有五德”等說法,這些都說明了玉的珍貴性和神圣性。
佛陀在宗教中作為精神領袖,是神圣和純潔無瑕的,是智慧與真善美的化身。他教人慈悲、向善,引導人們在精神上達到一種新的境界。由于玉和佛的精神在某種程度上是相通的,因此歷代人們總會選擇珍貴的玉材來塑造佛像。明清時期隨著對玉料的進一步開發,人們發現和田白玉更適合創作佛像。從珍貴性來說,佛是至高無上的,因此必須要用最珍貴的材料;從純潔性來講,和田白玉是潔白無瑕的,也符合佛的精神。因此,在我的創作中,我會盡可能地將這二者合二為一,從而更好地表現佛的純凈與無私。
《中國收藏》:在當下,佛教題材的玉雕作品除了繼承傳統之外,在您看來還有沒有進一步創新的可能?
蘇然:在我看來,當代佛像玉雕所繼承的傳統,絕不僅是對我師父他們老一代玉雕大師的繼承,更是對中華民族歷代以來民間藝人在佛教造像以及雕塑藝術上的繼承。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在當今社會,有很多玉雕藝人對佛像造像并不了解,只是一味地模仿復制。外加上利益驅使,以至于很多玉雕師在不假思索的情況下雕刻佛像,所以才會千篇一律。但是歷史上卻有不少優秀佛教雕塑,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塑像的空間營造、神秘效果;唐代佛教造像的豐滿圓潤、和諧有序;宋代佛教造像的恬靜平和、市井氣息等等,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去研究學習和繼承的。
有了繼承的基礎才能去創新。我個人認為,越復古就是越創新。你能將古代石雕、泥塑搬到和田玉上來做,這本身就是一種創新;你能進一步熟悉和發掘和田玉的特性,用它來最大化地表現佛的精神,這還是創新;當然,如果你在方寸之間不僅僅塑造了佛陀,而且能塑造佛教人物和佛教故事、佛教建筑,那么你就更是創新了。
《中國收藏》:您的作品為什么總是那么富有生命力?
蘇然:玉雕的過程也是我修身與修心的過程,因為我塑造的是佛,佛對世人的要求就是去除思想中的貪、嗔、癡,保留內心的真、善、美。所以我在塑造佛時,要去理解佛、體悟佛,盡全力去還原佛的本意,而這個過程既是我對佛的塑造,也是佛對我的教化。就如同唐僧取經,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在達到目的取得真經的同時,也完成了自我的脫胎換骨。
《中國收藏》:每一位創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社會的認可,顯然您做到了。那您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帶給藏家以什么呢?
佛教是講因果、說輪回的。在佛的眼中,我們現在做的每一件事,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因,并且隨著事件的發展,最終又會成為果。其實我們創作玉雕藝術品何嘗不是如此?我想欣賞和收藏我作品的人,大多都是被我塑造的佛所感動。因為我將佛最慈悲、最智慧、最神圣的一面展現了出來。我用自己辛苦虔誠的“因”造就了被社會、藏家所認可的“果”,完成了一個美好的輪回。我想這些也是藏家所能體會到的。
另外,在佛的眼中,人體只是一具驅殼,只有精神是永恒的,物質不滅的。那么你活在人世間就必須要做出一些有意義的事,即“正能量”。而只有這樣,在你的肉體消失之后,你的精神依然存在,并且它會讓人感動,使人受益,這也是我想傳遞給廣大藏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