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吳天明
楊爭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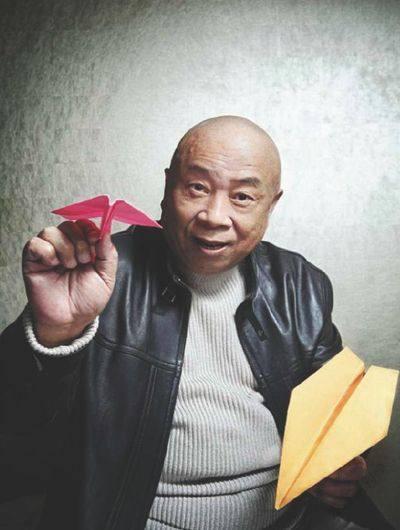
一
對逝者的追思與懷念,我更信任的是心,而不太相信口舌和文字。口舌之余可以攪拌謊言,默寫的文字容易裝飾作假。心則不會,也無須。心語是無聲的,只說給自己。就因為這樣的緣故,我幾乎沒有寫過追思、懷念一類的文字,給我逝去的親人和朋友。
我經歷過路遙的追思和懷念。對他的追思和懷念就多有說謊和裝飾作假的文字。路遙是我敬重的作家,也是對我有過兄長一樣關懷的朋友。對他以及和他有關的人與事,我是知道一些的。他為人行事的個性、所處的位置以及現實的情勢,是很容易招嫉遭恨的。事實上,在他活著的時候,對他的嫉與恨,多有事在,大有人在,甚至在睡夢里也要切齒的。嫉與恨,我并不輕薄,人性的弱點而已。要輕薄的是因嫉因恨而在背后口出惡言,在暗處施行傷害。
路遙逝后,那些在追思懷念中說謊作假的文字,正是這樣的他的朋友或同道們以筆墨寫出并公之于世的。對于這樣的文字我不但要給以輕薄,還要輕蔑的。我以為,嫉者恨者也可以寫追思和懷念的文字,如實寫出曾經的嫉與恨,寫出嫉與恨的緣由,甚至干脆連曾有的惡言和傷害也一并寫出。這樣的追思和懷念不僅真實,也可以明辨是非,既尊重死者也不失自尊。而說謊和作假,即使是滿篇頌詞,也是對逝者的又一次加害,對自己,則是又一次淪陷。
至于那些借逝者之名,趁追思之機,寫文章以抹靚自己的作為,則是可憐蟲的作為,很常見的。
就因為那些說謊和作假的文字給我的惡感,我只參加了路遙的追悼會,卻沒有參與到追思和懷念的行列,既不以口舌,也不以文字。倒是他逝世一年后,我在一篇題為《我不打算戒煙了》的短文中,表達了我對他的敬重與懷念。此時,對他的追思熱潮已經冷卻,很讓我有些逝者如斯活者如斯的感慨。
可見,對逝者的追思和懷念,其意義更多的不在逝者,而是活人的需要。這需要因人而異,有精神的,有情感的,有心理的,也有現實和功利的。也正是這因人而異的復雜的需要,對逝者的追思和懷念也是一個檢視,檢視也會逝去但還未逝去的活人,有沒有良知,有沒有感情,有沒有記憶,有沒有讓遺忘弄丟自己。籠統一點說,就是有沒有人味。
如此,對逝者的追思,懷念,寫文章又有了它的必要。而且,這必要還有其嚴正和莊重的一面。
二
我是在寫了兩部電影劇本之后調到西安電影制片廠的。那是1989年。兩部電影都已建組,后來的結果是,一個劇組解散,一個僥幸存活,終于投拍。拍攝出來的那一部,就是《雙旗鎮刀客》。
我進西影,廠長吳天明是否知情,是否主持了和我有關的兩部電影的決策,我不清楚。那時,他已出國。我進廠是11月,正趕上為《雙旗鎮刀客》采外景。轉過年,電影拍成了,吳天明被免職,漂泊海外。
《雙旗鎮刀客》導演何平,同時也是劇本創作的參與者,他和整個團隊沒有辜負吳天明擔任廠長時的西安電影制片廠的期待。我至今都認為,《雙旗鎮刀客》是吳天明時代的西安電影制片廠拍攝的最后一部真正具有中國西部電影品質的中國電影。調西影廠之前,我曾見過吳天明,卻沒有實質性的交往。
調入西影廠之后多年,干脆就沒見過他,只聽說他在美國以出租電影錄像帶謀生。就是說,吳天明在我的心目中,更多的是一個傳說。還有,我看過他的《人生》和《老井》。要說對他有所認知,是得之于傳說和他的作品,而不是交往和交情。
吳天明回國之后不久,曾找過我,是想有一次合作。我很高興他對我的信任和看重,且有些感動。很可惜,想有的這一次合作并沒有成為事實,原因在我。后來,又有幾次合作的機會,也是他找的我,依然沒有成為事實,原因依然在我。也就是因為這幾次沒有成為事實的合作,我對傳說中的吳天明和通過作品認知的吳天明有了生動而又實在的質感。
1997年,吳天明《非常愛情》獲“華表獎”。我是那一屆的評委,給他投票,我是懷有真誠的敬重的。他執導的《變臉》,還有后來的《百鳥朝鳳》,我都沒看過。聽到他獲電影終身成就獎的消息時,我很欣慰。中國電影界的良知還沒有泯滅。
然后,就是他的逝去。我沒有參加他的追悼會。我托西影廠的朋友代我送了一個花圈——給逝者送花圈,在我也是很不積極的。花圈也應該是真情的表達。僅出于禮貌,我寧可作罷。
這就是我和吳天明的交往和交情,很少,也說不上“深”,卻并不影響和減輕我對他的敬重。對一個人的敬重,并不完全由實際交往的多少和世俗意義的深淺決定。
三
我在西影廠整整十年,領略并享受過西安電影制片廠因吳天明而遺存的風骨、情懷和富有人性的電影創作傳統,是遲到的受益者。
我固執地認為,吳天明的《人生》《老井》是無法讓人忘懷的中國電影經典。它們不僅蘊含著吳天明的電影情懷,也實現了吳天明的電影美學和價值立場。
對于《人生》和《老井》,我還要說的是,這兩部電影,都是在他做廠長,一言九鼎的那一段時間里拍攝的,卻不是強塞的私貨。他不會因為自私而玷污自己的精神和人格,不會因強塞私貨而讓自己蒙羞。
一位古時的讀書人在陜西關中發出過這樣的聲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吳天明之于電影,就有著這樣的使命感,這樣的情懷、豪邁、精誠和膽識。正因為有著這樣的使命感,這樣的情懷、豪邁、精誠和膽識,也注定了他不僅屬于自己的電影,更屬于中國電影。同樣是在陜西關中,吳天明用電影把這樣的使命、情懷、豪邁、精誠和膽識變成了現實,引領了一個時代的電影風尚,把中國電影批量式地推出了國門,讓世界領略了中國電影和電影人的才華與風采,并起用和造就了一大批電影精英。把已經扎根和漂在北京的西影人整合起來,可以組建一打一流的中國電影創作團隊。
在中國想做成事情,尤其是拍電影,有情懷容易,有膽識難。有膽識是要付出代價的。吳天明因此而傷痕累累,身心俱疲,但他做到了。沒做到的,也盡力了。為了西影廠拍攝的電影,他無數次像一只憤怒的母雞,像護法的羅漢一樣,面對過嚴酷的電影審查。曾經的親歷者應該有記憶的。當西影廠的人稱吳天明“吳頭兒”的時候,是能聽出溫熱的眼淚的。就中國電影的整體來說,吳天明是一個時代的標志。也許還是唯一的。吳天明的電影時代已先吳天明而成為歷史。
現在,斯人也已逝矣。
對歷史的追索,對逝者的追思,能否喚醒記憶?
吳天明時代的電影觸碰的是人心,現在的電影觸碰的是眼球。如果這樣的判斷大致沒錯的話,對吳天明的追思,同時也就是對一個時代的電影的追思——我們可以思一思,在迎合時代與時俱進的同時,怎么能讓我們的電影從觀眾的眼球往下一點,重歸人心,是否也可以是一種開辟心路的探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