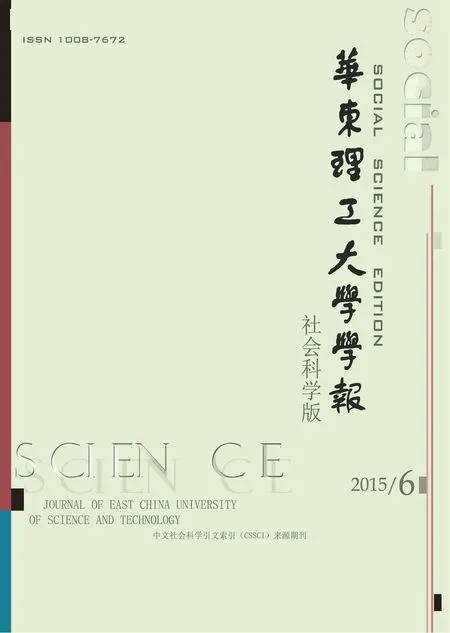民間環保集體行動產生邏輯及破局關鍵——基于太湖污染治理的考察
馬道明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江蘇南京210046)
民間環保集體行動產生邏輯及破局關鍵——基于太湖污染治理的考察
馬道明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江蘇南京210046)
[摘要]環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根據奧爾森的觀點環保集體行動產生的可能性很小,但事實上,在污染區域各種形式的民間環保集體行動時有發生,主要形式包括:有組織者的集體行動、無組織者的集體行動和環保精英們的行動。從風險社會理論分析,環境風險和環境沖突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產物,而環境污染屬于“被制造出來的風險”,這種風險存在分配的不公平性,弱勢群體“集體被剝奪感”的蔓延有力地催化了民間環保集體行動。環保NGO的成長會使作為環境受害者的弱勢群體受到常規性的力量支持和幫助,通過制度化參與的途徑實現環境正義,使環境沖突處于可調控的范圍內。環保NGO的成長才是民間環保集體行動破局的關鍵。
[關鍵詞]環境風險環保集體行動弱勢群體環保NGO
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或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r),是指某種帶有一定訴求、無明確組織、無明確計劃、臨時而起、利益雙方或多方面對面的具有一定規模的集群行為。集體行動的主要特征有:發生時是自發的、無正式組織的行動;是非制度化的行為,即違反常規的或不受制度和規范約束的行為;眾多人共同的行動即受到相互感染、影響、鼓舞的許多人的一致行動;臨時性、不能持久,行為周期較短暫。①朱力:《中國社會風險解析——群體性事件的社會沖突性質》,《學海》2009年第1期。集體行動的主體是準群體,它是一種準群體的行為方式。環保集體行動就是因經濟發展、經濟利益與民眾環境權益之間產生沖突,民眾帶有明確環境訴求目的、自發為主、無正式組織的較大規模的群體沖突行為。民間環保集體行為中的行為主體是環境權益受損的民眾。
美國學者奧爾森在1966年發表了著作《集體行動的邏輯》,根據該著作的觀點,集體行動的目標是公共物品,因為“公共物品是個人力量無法締造,必須依賴集體的力量才可以獲得的物品”。②董國禮:《作為經濟社會學議題的集體行動——從奧爾森到科爾曼》,《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并且公共物品的顯著特性是:“一旦存在,每個社會成員不管是否對這一物品的產生做過貢獻,都能享受這一物品所帶來的好處”。①趙鼎新:《集體行動、搭便車與形式社會學》,《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因此,當一群理性人聚在一起,想為獲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奮斗時,其中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想讓別人去為達到該目標而努力,自己卻坐享其成。用奧爾森的話來說,“盡管集團的所有成員對獲得這一集團利益有著共同的興趣,但他們對承擔為獲得這一集體利益而要付出的成本卻沒有共同的興趣。每個人都希望別人付出全部成本,而且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擔了成本,一般總能得到提供的利益”。②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陳郁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頁。根據這種推理,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即集體行動不可能產生,“除非一個集團中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個人按照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③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陳郁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頁。
根據奧爾森的理論,太湖污染地區環保集體行動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雖然太湖污染對每一個人都有影響,但是太湖水質的改善、環境的好轉,其受益者是每一個生活在太湖周邊的人,即一旦存在針對太湖污染集體行動,那么這種集體行動提供的公共物品就可以被所有人享受到,無論這些人參與了集體行動與否。盡管不可能每個人都能成為經濟學意義上的理性人,但是理性的算計是普遍存在的。在理性算計的影響下,集體行動產生似乎就不太可能了。但事實上,在筆者調查的太湖周邊地區,不同形式和規模的民間環保行動時有發生,這好像與奧爾森的理論分析似乎相悖,那么太湖地區民間環保集體行動產生的邏輯是什么?在中國當前的社會轉型期正確引導民間環保集體行動,以降低社會風險的破局關鍵又在哪里?這些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問題。
一、太湖周邊環保集體行動主要呈現形式
通過太湖實地調查,筆者發現,在太湖周邊地區存在不同形式的環保集體行為。如果從性質上考慮,這些環保集體行動更多的是針對污染企業的環境抗爭行為。實際上,不僅僅在太湖周邊地區,從全國范圍來看,近年來環境問題越來越受到普遍關注。據統計,目前環保問題排在當前全國群體性事件十大原因的第九位,因環境污染引起的群體性事件的增長速度排在第七位,其年增長率在29.8%。④數據來源:《中國環境群體事件增多,政府為企業埋單被指不公》,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news/local/2010-11/17 /content_21366872.htm。在筆者調查的地區,小企業普遍存在,且以化工企業為主。化工企業造成的污染是顯而易見的,由于小企業的小本運營,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負擔得起龐大的污染物處理費用。因此,將污水、廢氣等直接排入河渠、天空成為一個“不錯”的選擇。當地民眾與污染企業結怨已久矛盾尖銳,環保集體行動時有發生,主要呈現三種表現形式。
1.有組織者的集體行動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太湖污染也非“一日之功”。因此,當地居民和污染企業的針鋒相對已經有過一個漫長的恩怨期。居民曾經與這些污染企業進行過多次的談判和交涉,但成效甚微。面對眾多指責,污染企業表面上答應不再排放廢氣、廢水等,但是他們轉而采取在夜里偷偷直接排放,矛盾因此更加尖銳。在屢次交涉無果之后,當地的一位民營Z老板組織居民采取了果斷行動。經過反復思考,Z老板和兒子決定帶領附近居民去逼迫這家有污染的化工廠關閉。一位被訪者這樣向筆者講述了當時的情況:
“Z老板拿著喇叭對村民喊:‘鄉親們,他們(造成污染的企業和企業主)讓我們喝污染水,我們生產的菜都不能吃……我們要生存,我們必須采取行動……’在他的鼓勵下,我們(村民)占領了好幾個化工廠。后來鎮政府派人來,他們來了好幾輛警車要保護化工廠,還把Z老板抓了起來。我們非常生氣,他們不來幫我們解決問題,還要幫那些污染企業,我們就把警車給掀到了污水里,有幾個人也掉進了溝里。為了救出Z老板,我們也抓了一個政府的干部,和他們以人換人,這樣就把Z老板救了出來……后來,鎮上看事情很嚴重吧,就把當時被我們鬧過的幾個小化工廠都給關閉了。”
這是一次在當地民營Z老板的帶頭下開展的有組織、有目的的集體行動,他們試圖通過比較激烈的手段來占領工廠,以迫使工廠關閉。這樣的行動也引起了政府的干涉,政府的偏袒使得前來參與“解圍”的人成為村民斗爭的對象,警車也被掀到河里。現在看來,這些過激行為在關閉工廠中具有一定的效果。它促成了基層政府慎重考慮居民的要求,對污染企業采取了關閉措施。這樣的行動之所以能夠產生,關鍵有賴于一個堅強的領導——Z老板。在居民的眼中,Z老板是一個有責任心、有正義感的人。他通過發展企業富裕之后,出資修建道路,讓居民告別了鄉村泥巴路,走上了水泥路。在這次集體行動中,他積極倡導并組織,最終化工廠被迫關閉,這些令村民們對他更加敬佩。
2.無組織者的自發集體行動
在Q村的對面,隔河相望是一家化工廠。這家化工廠每天都排放大量的黑煙和有毒氣體到空氣中,還將大量的黑水排放到河里。與化工廠僅一河之隔的Z村村民受盡其苦。有被調查者告訴我們,近幾年,他們村先后有若干人死于食道癌,也有人得胃癌。該化工廠排放的有毒氣體氣味非常濃烈,村民反映人聞到這種味道會惡心、嘔吐,甚至昏厥。村民要求化工廠對廢氣進行處理然后再排放,沒有得到化工廠的響應。化工廠一再漠視村民的要求后,Q村村民開始了他們和化工廠的激烈抗爭。某年的一天夜里該化工廠又向河里排放了大量的“黑水”,導致很多村民半夜被臭味熏醒,難以入睡。第二天一大早,村民就三五成群地去了化工廠,對化工廠進行了圍堵,村民和廠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有的人還爬到工廠的廠房房頂,去揭廠房的瓦。村民和廠方對峙了近一個上午,廠方最終答應不再進行排放,但是村民已經不再相信廠方的承諾。村民最終警告廠方,如果再發生這樣的事情,將會再次來圍堵。次年冬天該化工廠被政府勒令關閉。
在這場村民和化工廠的對峙中,村民用激烈的手段對化工廠采取了行動,迫使化工廠作出了讓步。但是,與前面一個集體行動不同的是,在這次行動中,沒有出現明顯的組織者。村民大都是在親身感受到污染之后,自發前往化工廠,或者是看到其他人去了,自己也跟著去。
“去年的時候那家化工廠,它白天不排放,到夜里偷偷排,河水臭得不得了。我們村里就去了幾百人到工廠。這個根本不需要組織,一個人叫一聲,大家就都會去,不需要村長組織。也不需要通知,只要大家聞到了味道,人是吃不消的,我們就會自發地去。我們去了之后,有的爬屋,有的跟他們理論……”
實際上,在該村,與這個化工廠的對峙已經不是第一次,村民都已經比較熟悉了這樣的模式了:只要有一個人準備去化工廠抗議,其他人就會跟著去,并且會叫上自己的鄰居,不需要有人組織。這已經成為村民們相對熟悉的自發組織路徑,村民已經成為一個利益攸關的自發群體。
3.地方精英們的環保行動
在太湖周邊,除了村民的環保集體行動之外,還有一些地方“環保精英”在行動。在調查中,筆者訪談了五位曾經寫信舉報過太湖污染的人。這些人大都有較好的教育背景,他們的學歷都在高中以上,并且多擁有較好的工作,或者是已經退休。這五位被訪者分別是退休工人、退休教師、退休干部、農民和水電站管理員。他們主要通過寫信舉報等形式向相關部門反映太湖污染情況。這些環保行動的參與主體我們稱之為地方“環保精英”。迫使這些人成為環保精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養育他們的魚米之鄉的消逝”。
他們都是自幼生活在太湖周邊的人,目睹了太湖從魚米之鄉轉變為今天污染地帶的過程,他們對這種轉變深表擔憂,同時又有強烈的責任感和義務感。
“看到太湖水一步步變壞之后,我就很痛心。我認為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而我所喜歡的事情就是希望看到家鄉青山綠水,看到小河溝里再出現魚蝦,看到魚米之鄉的復現。于是,我就開始采取行動了。開始我是匿名舉報,向環保部門舉報有污染的企業、化工廠啊等等,但是效果不明顯。后來,我就改為實名舉報了。實名舉報的效果要好一些。但是,實名舉報也給自己惹了麻煩……”“我舉報的情況都是真實的,上面下來調查果然是這么回事,所以漸漸地開始在周圍有些名氣。在這之后呢,就有很多的人來找我反映他們的污染問題啊。”
因此,他們認為在太湖環境惡化的過程中,自己不應該袖手旁觀。當河渠的水由清澈變污濁時,當他們不得不放棄飲用河水改為飲用自來水時,當他們不得不呼吸有味道的空氣時,他們開始了行動——寫信舉報。他們曾經向鎮政府、縣級市政府、地級市政府的相關部門反映過情況,有的甚至曾經給國務院有關部門寫過舉報信。但是,這些舉報信往往石沉大海,鮮有得到重視。他們說:“只有寫到地級市政府以上的舉報信曾經得到過答復。”即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也沒有放棄過對政府的信任,他們深信政府是他們利益的維護者,他們仍然在堅定地走著自己的環保維權路。
這些環保精英們除寫信舉報之外,他們自己也是身體力行的“環保衛士”。他們自覺向當地居民宣傳保護太湖的知識,向居民宣傳自覺將垃圾放到垃圾回收處;他們每天去太湖邊撿垃圾,散步在各條河渠上,隨時制止往河渠里扔垃圾的行為;他們時刻關注著河水、湖水的變化,發現變化跡象即會向“河長”①為了更好地管理太湖流域,整個太湖流域的河流都實行“河長制”,每條河都有負責管理的河長,在每個河段都有標示牌,寫有河長的姓名、負責范圍、監督電話。反映。他們偶爾也會被政府相關部門邀請參加有關太湖問題的群眾會議或民主會議。調查中,一位被訪者曾經給筆者展示了去年他被邀請參加鎮里舉行的一次民主座談會的材料。
二、民間環保集體行動的產生邏輯
環保集體行動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沖突。科塞將社會沖突分為兩種類型:現實性社會沖突和非現實性社會沖突。“由于在關系中的某些要求得不到滿足以及由于對其他參與者所得所做的估價而發生的沖突,或目的在于追求沒有得到的目標的沖突可以叫做現實性沖突,因為這些沖突不過是獲得特定結果的手段”。②科塞:《社會沖突的功能》,孫立平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頁。從這一角度分析,民間的環保集體行動屬于現實性社會沖突。它是民眾表達自己的不滿,要求改變現狀的一種手段——盡管這種手段采取了激烈的方式。這是一種污染驅動型的環境抗爭,是民眾作為受害者,在遭遇環境污染的威脅下爭取健康不受損害、農作物不被污染的權利,因此是民眾爭取生存權的抗議運動。
中國農民是最不會惹是生非的一個群體,那么在太湖地區,如此忍耐的一個群體為什么會形成一些激烈的環保集體行動呢?我們可以從風險社會的視角來加以分析。
“風險社會”是由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提出來的。貝克認為,風險社會分為兩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社會被定義為工業社會。第二階段,社會被定義為“風險社會”。在第二階段,“風險意識已被普遍接受。各種后果都是現代化、技術化和經濟化進程的極端化不斷加劇所造成的后果,這些后果無可置疑地讓那種通過制度使副作用變得可以預測的做法受到挑戰,并使它成了問題”。③[德]烏爾里希·貝克、約翰內斯·威爾姆斯:《自由與資本主義——與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對話》,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頁。顯然,貝克所說的風險社會,應該就是他所說的第二個階段。在貝克看來,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生產效率的提高,傳統的財富分配和不平等問題得到了有效改善,但每個人卻要面臨未知的不可預測風險。而且“社會、政治、經濟和個人的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④[德]烏爾里希·貝克等:《自反性現代化:現代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傳統與美學》,趙文書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9頁。在風險社會中,工業化所產生的威脅開始占主導地位,并且這個威脅防不勝防,人們無法用常規的經驗來對付,而且這些新的風險是現代制度也無法解決的,風險已成為一種“制度化”風險。吉登斯則進一步區分了兩種類型的風險:外部風險(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來的風險(manufactured risk)。外部風險是“來自外部的、因為傳統或者自然的不變性和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⑤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紅云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頁。被制造出來的風險是“由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而產生的風險,是指我們沒有多少歷史經驗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風險”。科學技術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被制造出來的風險的產生。“在某個時刻,我們開始很少擔心自然能對我們怎么樣,而更多地擔心我們對自然所做的。這標志著外部風險所占的主導地位轉變成了被制造出來的風險占主要地位”。①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紅云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頁。
環境風險和環境沖突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產物,它是由環境問題而引起的社會風險和沖突。由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不可逆性以及系統性,因而環境風險和環境沖突也具有不確定性,而且這種不確定性的表現形式和存在方式具有特殊性,這就導致了環境風險和環境沖突也具有不同于傳統環境問題的社會風險。嚴燕等認為,我國環境污染及環境沖突的風險主要表現在現實風險和潛在風險兩方面,現實風險主要表現在健康風險、災害風險、經濟風險等,潛在風險主要表現在政治風險、法律風險和國家安全風險等。②嚴燕、劉祖云:《風險社會理論范式下中國“環境沖突”問題及其協同治理》,《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第3期。
引起當地民眾的環保集體行動的“風險”——環境污染,是科技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被制造出來的風險。同時,這種風險的分配又是不公平的,它是依附于階級模式的——“財富積累在社會上層,風險則聚積在社會底層,貧窮吸附了大量的風險,而財富則可以購買安全和規避開風險”。③朱力:《當代社會問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頁。顯然,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者不公平地承擔著大部分環境污染的風險,這樣的風險很現實地威脅到他們的生產、生活和健康。同時他們又沒有能力來應付由于環境污染帶來的災難和損害,他們缺少必要的物質基礎、基本設施和安全保障,而社會政治體系并沒有為他們提供有力或必要的支持。環境風險無疑加強了這種弱勢地位的感受,使他們產生更大的“相對剝奪感”。④趙闖、黃粹:《環境沖突與集群行為——環境群體性沖突的社會政治分析》,《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在中國農村地區,這種“相對剝奪感”就連當地的所謂的“精英們”(知識分子、一般企業主、普通地方官員等)也不例外,他們共同感受到了對他們不公正的環境剝奪,因為面對強勢地方企業和“財稅”地方政府的聯合,他們同樣無力改變現狀,同樣扮演著弱勢群體的角色。這種“集體被剝奪感”一旦形成,由此激發的不滿情緒會不斷地蔓延和相互感染,并可能在集體意識上達成某種默契,將有力地催化試圖改變這種“被剝奪”現狀的集體行動。環境集體行動者會對后果做出二元判定,即計算利弊得失,為了最大限度降低環境抗爭產生的風險,他們也會盡力增加人數。由此,集體行動蓄勢待發。⑤趙闖、黃粹:《環境沖突與集群行為——環境群體性沖突的社會政治分析》,《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
在太湖地區,上世紀80年代以來,工業化力量開始大規模地、有深度地向鄉村推進,這在極大地改變了鄉村經濟社會面貌的同時,也極大地改變了其環境面貌。城市工業化結構的調整,包含了將部分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向鄉村轉移。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受“發展(經濟)是硬道理”的影響,招商引資,在當地強力推進工業發展,而這種所謂的“發展”是以犧牲當地的環境為代價的。而污染的后果并不僅僅是“直接的經濟損失”,通常還意味著生產和生活秩序的紊亂,健康乃至生命本身的傷害,以及生活希望的破滅。這種災害所帶來的實際風險可能大大超過將無數的小農們折磨得死去活來的“農民負擔”。⑥張玉林、顧金土:《環境污染下的“三農問題”》,《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3期。當農民的土地、水源乃至呼吸的空氣都遭遇污染、生存環境遭到破壞,面臨生存風險時,在地方政府“污染保護主義”思想的驅使下,企業的排污和侵害行為得不到公共權力的有效制止,造成受害農民逐漸對當地政府不再抱有期望,而去選擇“自力型救濟”——太湖地區民間環境集體行動就此產生了。盡管由于環境的公共性,在面對環境問題時存在理性的算計,但當民眾共同面對風險以及集體被剝奪感時,不同形式和規模的集體行動的爆發也就不可阻擋了。
于建嶸曾經將農民的集體行動歸結為“壓迫性反應”,具體是指當“集團”并沒有明確的邊界即還沒有形成較明確組織形態時,社會群體中的部分成員為了改變某一社會政策或社會現實所進行集體行動,其真正原動力不是來自“集團”內部的“獎罰分明”,而更主要的來自“集團”外部的壓力。①于建嶸:《集體行動的原動力機制——基于H縣農民維權抗爭的考察》,《學海》2006年第2期。在太湖污染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找到這種外部壓力:一方面是來自于污染企業的污染,另一方面是來自基層政府的“不作為”。兩者的合力嚴重威脅了民眾的生存權,使當地民眾面臨超出承受范圍的生存風險。而生存倫理是根植于民眾社會的經濟實踐和社會交易之中的。當面臨呼吸不到新鮮的空氣、看不到藍天白云,周圍的親朋好友不斷被各種疾病折磨甚至被奪取生命之風險時,當地民眾捍衛生存權的集體行動就更加堅定了。
所以,在前文提到的幾個案例中,民眾和污染企業的抗爭都已經進行了多個回合。在調查過程中,許多村民表示,他們曾經多次向政府部門反映情況,但是都沒有得到回應。“即使在鎮長作出表態之后,污染企業仍然在繼續生產。”在當地農民看來,某些地方政府已經成為財稅政府,他們關心的是稅收的多少,而不是老百姓生活的疾苦。企業能夠給政府帶來稅收,正是這個利稅使得地方政府對其網開一面。盡管污染企業盈利頗多,但對農民的補償是不足的甚至是沒有的。在調查中筆者發現,絕大多數污染企業都沒有對農民進行補貼。少數企業雖然對農民進行了補貼,但是也少得可憐,如防腐廠——房屋遭到腐蝕的村民僅僅得到了一點水泥補貼,村里的老年人得每人300元的補貼。這是對農民的絕對剝奪,必然導致他們的強烈不滿。農民的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無論是相對剝奪感還是絕對剝奪感都比較強。面對這樣的具體情境下,無可奈何、忍無可忍,他們必然會選擇激烈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維護自己的生存權益,以降低自己不應該承擔的風險。如果沒有有效的“安全閥”機制緩沖這種不滿,隨著矛盾累積,對抗勢能增大,大規模民間集體行動的爆發只是時間問題。
三、NGO的成長是環保集體行動破局關鍵
孫立平曾經指出,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博弈時代。②孫立平:《博弈:斷裂社會的利益沖突與和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頁。但事實上,中國并沒有真正進入博弈時代。博弈要求博弈雙方的對等性。就太湖地區的民間環保行動而言,民眾相對于政府和企業雙方不是對等的對話主體。盡管民間的這些抗爭行動對正常的社會秩序造成了一定的沖擊,但是這絕不是一群“不明真相”的群眾被“別有用心”的人“煽動”而發起的抗爭行動。當地民眾的這些行動都有各自具體的、特殊的訴求目標,這些目標僅涉及經濟、民生利益,與政治不搭界,群眾也根本沒想到以體制外的行動方式來謀求體制內的權力再分配。③于建嶸、單光鼐、簡華新:《群體性事件應對與社會和諧》,中國社會學網,2009-1-7,http://www.sociology.cass.net. cn/shxw/shwt/ t20090107_19965.htm。這些環境行動背后實際上是底層群眾的利益受損和巨大的社會不公。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各種形式的民間環保集體行動。目前民間環保集體行動還存在一定的問題和不足。首先,目前的民間環保集體行動沒有規劃性,大都是針對突發的污染或者是積累起來的污染而做出的反應。也就是說,這些行動都是在環境問題產生之后才有的,是一種事后行為。而民間環保行動要有序開展,必須有事前的預防和事中的監督。但民眾由于認識能力的限制,往往只有等污染嚴重到一定程度時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被迫采取行動。其次,目前的民間環保行動分布還比較零散,僅僅是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主要是在環境污染比較嚴重的地區才出現,帶有“地方特色”。而在一些環境問題尚沒有嚴重到相當程度和僅存在潛在環境風險的地區,或政府“控制”得比較好的地區,還沒有形成預防性、組織性的全民環保聯合行動。
“風險社會”的到來意味著政府單方面的決策充滿風險,政府也因此意識到,只有實現決策結構的開放,才能使決策更具合法性,才能有效地規避風險。政府組織與非政府組織(NGO)的協同治理才是社會風險管理的發展趨勢。非政府組織是獨立于政府和市場的第三部門,其發展壯大將會更好地對政府活動形成輔助和監督作用,推動政府承擔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責任,減少弱勢群體的集體被剝奪感。環保NGO的成長會使作為環境受害者的弱勢群體受到常規性的力量支持和幫助,通過制度化參與的途徑實現環境正義,從而降低了受害者群體走向低組織化或無組織化的集體行動的可能性。①趙闖、黃粹:《環境沖突與集群行為——環境群體性沖突的社會政治分析》,《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可見,民間環保NGO參與環境利益沖突的解決,靠的不是控制和強制,而是通過群體間的共識、主動參與,互信互利,使沖突各方充分表達意愿,從而做出在最大程度上反映環境公平正義的決策,使環境沖突處于可調控的范圍內。因此環保NGO的成長是民間環保集體行動破局的關鍵。
晏陽初先生早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就預見到:“只有自動的組織才真能有力量。所以,要培養力量,還得從教育起始。有教育才能自動組織,有組織才能有自己的力量,才能有共同的力量,才能應付困難問題,創立新的生活方式,建樹新的社會結構。”②晏陽初:《十年來的中國鄉村建設》,載李培林、渠敬東、楊雅彬主編《中國社會學經典導讀(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頁。因此要實現環保NGO的良性發展,一方面政府要改變對環保NGO的管理機制,讓民眾可以自發組織起來。目前,我國政府對社會組織實行業務主管單位和登記管理機關雙重管理的制度。這種體制在強化社會組織準入條件并規避可能的政治風險的同時,也使其“降生門檻”過高。社會組織在跨越合法登記注冊的門檻之前,必須跨越業務主管部門的審批門檻,這種審批制度為所有的社會組織獲得合法身份設置了法律和行政制度障礙。據有關專家的調研估計,目前沒有合法登記注冊而開展活動的社會組織數量,大約十倍于合法登記的社會組織。在太湖調查中,筆者也聽到了當地環保精英希望成立民間環保NGO的愿望,但是由于政府的層層管制,最終未能被批準。“我的這些行為完全是個人的行動,不可能形成什么國外的NGO啊。我也曾經申請過成立環保NGO,但是沒有被允許,我也就沒有辦法了。地方政府還是不太喜歡總是挑刺的人。”所以,政府應改變對環保NGO不信任、不放心的態度。環保NGO的存在是為了讓民眾民主地、制度化地參與環境事務中來,更好地促進環境沖突的解決,而不是給政府制造麻煩。要從社會體制上讓民間環保NGO能自發組織、合法存在,并創造條件讓其能夠發展壯大。另一方面,環保NGO必須承擔起培養“環境公民”的職責。有教育才能自動組織,有組織才能有自己的力量。環保NGO通過環境講座、環境調查活動和環境拯救活動,激發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更重要的是通過環境教育和環保傳播,環保NGO吸引了大量志愿者長期獻身環境公益事業,為民間環保積蓄堅實的后備力量。吸引更多民眾自覺融入“環境公共領域”,實現參與者、行動主體從精英分子向普通民眾的擴展以及精英分子與普通民眾在“環境公民社會”中的深度融合,這需要環保NGO實施專業化、聯合化、互動化策略。③歐陽宏生、李朗:《傳媒、公民環境權、生態公民與環境NGO》,《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9期。總之,環保NGO在培養具有自覺批判精神、現代環境觀念和自組織能力的“環境公民”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優勢和不可推卸的責任。
(責任編輯:肖舟)
Folk Collective Action Logic and the Key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Based on Pollution Governance of Taihu Lake
MA Daoming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China)
Abstract:Environment is of public goods property,so the possibility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s very small according to Olson. But in fact,various sorts of folk environment collective action in pollution area happen from time to time. These mainly are: organized collective action,non -organized collective action and environment elites' action. Analyzed from risk society theory,environment risk and conflict are inevitabl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pollution is a kind of“made risk”. The spreading of“collective deprivation feeling”of vulnerable groups catalyzes effectively folk environment collective action. The growth of environment NGO can make the environment vulnerable groups supported and helped by conventional power,realiz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participation way,and making environment conflict in controllable range.
Key words:environment risk;environment collective action;vulnerable groups;environment NGO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672(2015)06-0106-08
[作者簡介]馬道明,男,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環境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