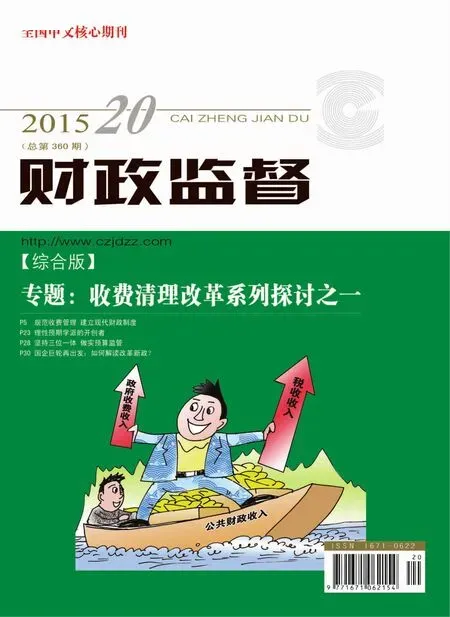中國歷史上工商雜稅的發(fā)展規(guī)律
●周春英
中國歷史上工商雜稅的發(fā)展規(guī)律
●周春英
作為新一屆政府推進簡政放權的一項重要任務,收費清理改革備受關注。自2013年以來,中央層面累計取消、停征和減免了420項行政事業(yè)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每年可減輕企業(yè)和個人負擔約920億元。2014年,各省區(qū)市累計取消收費已超過600項。為繼續(xù)減輕企業(yè)負擔,促進經濟健康發(fā)展,2015年4月,中央專門成立“國務院推進職能轉變協調小組”,在全國范圍內減審批、清理涉企收費(國辦發(fā)〔2015〕29號),顯示了官方清理規(guī)范對企業(yè)亂收費行為的決心,這不僅是出于當前減輕企業(yè)負擔、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需要,長遠來看還有利于營造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的市場經濟環(huán)境,推動更多人投身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本文擬從歷史視角,通過對歷史上中國工商雜稅發(fā)展、演變規(guī)律及成因的總結,探討當前我國推進清理收費改革面臨的境遇與下一步的發(fā)展方向。
一、工商雜稅的概念
歷朝歷代,賦稅收入構成了國家財政收入的主體。中國歷史上的賦稅種類頗多,如果按照課稅對象來劃分,大致可分為土地稅(或田稅、農業(yè)稅)、人頭稅(包括在歷史演變過程中與之相關的徭役、丁稅、戶稅)和工商稅收三大類。在中國近代以前以農業(yè)為主體經濟的社會里,田稅以及與之相關的丁稅、戶稅和徭役一直是國家的主體稅種和主要賦稅,在財政收入中起支柱性作用,故又被稱為“正稅”,即正額賦稅。
若從現代稅法角度看,“正稅”則指通過法定程序由最高權力機關公布稅法,或授權擬定條例以草案形式發(fā)布開征,具有獨立的計稅依據并正式列入國家預算收入的稅收。正稅與其他稅沒有連帶關系,有自己特定的征稅對象。
雜稅,亦稱“雜征”、“雜賦”,是對正稅以外的一切稅捐的總稱,是國家正稅的補充形式。據宋代高承《事物紀原·利源調度·雜稅》記載,雜稅產生于西周后期,“周衰之末,諸侯以強霸相尚,兵革不息,故費博而什一不足,此雜稅之法所由起也。”
在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歷史中,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者都程度不同地實施重農抑商政策,如統(tǒng)治者反復強調農業(yè)為本業(yè),商業(yè)為末業(yè),強化本末意識;強化戶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動;從政治(如限制商人、手工業(yè)者的政治權力,堵其仕途之路,不許后代做官;職業(yè)世代相襲,不得改業(yè)等)、經濟(如利用稅收制度以減少其利潤、對鹽鐵等重要行業(yè)及重要手工業(yè)采取官營,不許商人和民間工匠染指)、日常生活(如對其穿衣、建房、乘車的歧視性規(guī)定)等多方面對商人進行限制,以穩(wěn)固農業(yè)生產的基礎。重農抑商政策成為封建社會最基本的經濟政策,使社會上賤商之風盛行,商人的地位因而十分卑微,一直處在四民的末位。所謂士農工商的排列順序,似乎成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凝固不變的模式。這并不是說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工商業(yè)發(fā)展就停滯不前。事實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工商業(yè)作為社會經濟發(fā)展不可或缺的一個部門,也在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不斷向前發(fā)展。
工商業(yè)的發(fā)展、貨幣化程度的提高,為工商稅收的發(fā)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中國歷史上工商稅收的發(fā)展,一方面是商品經濟發(fā)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很多朝代的統(tǒng)治者,在工商稅稅種創(chuàng)新及征收手段的探索上費盡心機,推動了工商稅收的發(fā)展。但就總體而言,這種發(fā)展遠不足以使工商稅收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流形式,而且政府征稅目的在主觀上都是出于財政目的,是為了維持統(tǒng)治的需要而增加財政收入,并沒有從發(fā)展和管理經濟的角度考慮。因此,中國封建社會的工商稅收具有隨意性、不連續(xù)性和不規(guī)范性等特點,其收入也常被稱為 “工商雜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經過1950年統(tǒng)一稅制和1953年修訂稅制,實現了全國工商稅政和稅制的統(tǒng)一。然而,企業(yè)除了交納通過立法程序予以征收、列入中央預算和地方預算統(tǒng)一安排使用的工商稅之外,往往還要交多種由國家一些行政部門或者事業(yè)單位為面向社會提供服務而收取的包含重大項目建設、過路、過橋、綠化等方面的政府性基金、保證金、抵押金、行政審批前置服務項目收費等,還動輒被要求參加一些付費的培訓、展覽、會議,并要交多種“贊助”和“捐贈”等,這些收入,可以將之概括為“非稅收入”。
長期以來,針對工商稅收之外的各項收費收入,我國一直使用“預算外資金”的概念。在國家正式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并使用非稅收入這個概念,是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印發(fā)財政部國庫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方案的通知》(財庫〔2001〕24號)文件中。其后,在《關于200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zhí)行情況及2003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中,也提出要 “切實加強各種非稅收入的征收管理”。2003年5月,財政部、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監(jiān)察部、審計署聯合下發(fā)的《關于加強中央部門和單位行政事業(yè)性收費等收入“收支兩條線”管理的通知》(財綜〔2003〕29號)文件里,第一次對非稅收入的范圍作了較為明確的界定,即“中央部門和單位按照國家有關規(guī)定收取或取得的行政事業(yè)性收費、政府性基金、罰款和罰沒收入、彩票公益金和發(fā)行費、國有資產經營收益、以政府名義接受的捐贈收入、主管部門集中收入等屬于政府非稅收入”。這表明對非稅收入的認識開始從預算外資金轉向財政收入形式。在2004年7月財政部下發(fā)的《關于加強政府非稅收入管理的通知》(財綜〔2004〕53號)中,又進一步明確界定了政府非稅收入管理的范圍,包括行政事業(yè)性收費、政府性基金、國有資源和國有資產有償使用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益、彩票公益金、罰沒收入、以政府名義接受的捐贈收入、主管部門集中收入以及政府財政資金產生的利息收入等,并強調社會保障基金、住房公積金不納入政府非稅收入管理范圍。這說明,非稅收入作為一種財政收入形式正式登上我國的歷史舞臺。從概念上說,以上官方文件對非稅收入的界定都帶有過渡的性質,沒有揭示非稅收入的科學內涵,只是在承認現實收費的基礎上所劃定的一個收費范圍的政策界限而已。
世界銀行對非稅收入的概念作了一個界定,是指“政府為了公共利益而征收的所有非強制性、需償還的經常收入”(2000年世界發(fā)展報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非稅收入是政府在稅收之外取得的收入,它包括因公共目的而獲得的不需要歸還的補償性收入和非政府單位自愿和無償向政府支付的款項。兩大組織都對非稅收入的公共目的性、自愿性(非強制性)和有償性給予了明確的界定。
中國學者認為,非稅收入是政府為實現其職能,按照一定規(guī)則采取收費、基金等非稅方式,由中央和地方分別籌集用于特定專門用途的財政性資金。可見,政府非稅收入是按照收入形式來對政府財政收入進行分類的結果,是與稅收收入相對應,強調的是通過不同于稅收形式所取得的財政收入;而預算外資金則是相對于預算內資金而言的,是按照資金管理方式對政府收入進行分類的結果。因此,預算外資金一定包括在非稅收入范疇中,而非稅收入則不僅僅包括預算外資金,它跨越了預算內與預算外兩個范疇。長期以來,中國非稅收入的主體是預算外資金,但隨著部門預算和綜合預算的深入推進,預算外資金全部納入了預算管理。從“預算外資金”到“非稅收入”的轉變,標志著我國在建立公共財政體系、規(guī)范政府收入機制上認識的深化。
二、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工商雜稅
(一)先秦時期的工商雜稅
在夏、商和西周前期 “工商食官”,手工業(yè)和商業(yè)都屬官辦,所以沒有工商雜稅。到了西周后期,由于剩余的農產品和手工業(yè)產品的交換活動日益增多,在官營手工業(yè)和官營商業(yè)之外,出現了家庭副業(yè)形式的私營個體手工業(yè)和商業(yè),商人活動的范圍已不是幾十里、上百里的小范圍,而是來往于各諸侯國乃至海外。周統(tǒng)治者一方面出于保護農業(yè)勞動力的需要,對從商之人加以抑制;另一方面為了滿足日益增加的財政需求,開始對參加商品交換的物品征稅。西周專設“司關”和“廛人”兩征收機關,分別課征關稅和商稅。后又有針對山林、園池水澤、湖泊出產的各種物品所課征的稅,山林所砍伐之薪木,獵捕行獸之皮、角、齒、羽翮,河湖所捕之魚,池海所產之鹽等物均屬課征對象,繳實物,交由玉府,稱為“山澤稅”。
(二)秦漢時期的工商雜稅
秦漢時期作為國家支柱性財政收入的人頭稅和土地稅主要用于官吏俸祿、軍費等政府機構運轉開支,皇帝和宗室費用則來自于雜稅,主要為“關市之賦”和“山澤稅”。“關市之賦”,即“市井租稅”,是對通過國家所設關卡的行商征收的商品通過稅(時稱“關稅”)和市肆的坐賈按照市場上買賣成交額所征收的店鋪稅、商品交易稅(時稱“市租”)以及針對特產所征收的鹽稅、酒稅、礦產稅(如鐵稅)和漁稅等。隨著工商業(yè)的發(fā)展,收入不斷增加。如西漢初年,“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巨于長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另外,還有專門針對商人、高利貸者、手工作坊主征收的算緡錢、算商車(資產稅性質);按民戶財產價值征收的算貲(貲稅);對出貸貨幣或糧食收取利息所課的賒貸稅 (資本利息稅性質);對規(guī)定的家養(yǎng)牲畜所征的牲畜稅等。據《漢舊儀》載:“山澤魚鹽市稅,以給私用。”又《史記·平準書》曰:“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yǎng)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山澤魚鹽市稅”與“山川園池市井租稅”都是供皇室“私用”、“私奉養(yǎng)”的。其中,“山澤魚鹽”之稅應等同于“山川園池”之稅,即《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少府所掌“山海池澤之稅”。可見,從西漢時期工商雜稅就開始名目繁多,雜稅征收的目的主要在于增加財政收入,因此出現稅制混亂、無定制、課稅范圍廣、稅率高、稅額重、重復課稅嚴重等問題,嚴重危害和擾亂經濟發(fā)展。
(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工商雜稅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由于長期戰(zhàn)亂,政府從增加財政收入的角度使工商雜稅繁多,如兩晉時不斷在國內道路、河流、橋梁等重要交通要道上廣設關卡,征收商品通過稅,每卡“十分稅一”,南朝時稅率不斷加重(《隋書·食貨志》),成為逼商營私的工具。梁武帝時,不得不下令優(yōu)減,《南史·宋紀中·武帝》記載,“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市租,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亦征收,包括對行商所征收的入市稅和對坐賈所征收的店鋪稅。該稅具有營業(yè)稅性質,也許還有租用市肆店鋪租金性質。史載西晉末,廬江碩儒杜夷隱居不仕,刺史劉陶令廬江郡 “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說明在這之前市已成定制,地方牧守有權支配市租。
三國時,凡行商販賣貨物進入市區(qū)或坐商在市區(qū)內開設店鋪,皆征市稅。西晉建立之初,曾免除市稅一年。東晉、南朝視市稅、商稅為利藪,稅負加重,據《食貨志》記載,“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稅斂既重,時甚苦之”。東晉祖逖鎮(zhèn)豫州,與后趙互市,“收利十倍”,陶侃為武昌太守,也“立夷市于城東,大收其利”。祖逖、陶侃所得的厚利,一部分可能是官府直接參加做生意,但更大的可能是收商稅。劉宋初年(公元420年),曾“以市稅繁苦,優(yōu)量減降”(《宋書》,卷3,《武帝紀》)。另外,還有針對田宅、奴婢、牛馬等大額交易按成交價格征收的估稅 (后世契稅之起源),以及對不立文券的小額交易征收的散估稅,頗具有資本主義國家商品交易稅的雛形。估稅規(guī)定每交易1萬錢,官府征收400錢,稅率為4%,買賣雙方按1:3比例分攤。散估的稅率也是4%,稅額全部由賣方繳納(《隋書》,卷24,《食貨志》)。名目繁多的工商雜稅雖然增加了財政收入,卻抑制了工商業(yè)的發(fā)展。
(四)隋唐時期的工商雜稅
隋朝的文獻未見出現“市租”和“入市之稅”,隋初已廢止。唐朝開元(公元713年)以前也未見關市之稅。唐初統(tǒng)治者認為,“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舊唐書》,卷94,《崔融傳》),設關的目的,在于檢查貨物出入有無違禁,“凡關,譏而不征,司貨賄之出入,其犯禁者,舉其貨罰其人”(《唐六典·尚書刑部》)。但是,隋至唐前期的商人有賦役負擔,其負擔同于一般民戶,如隋朝的社倉稅與充官人祿力的要“計戶征稅”(《隋書》,卷24,《食貨志》),唐前期的戶稅、地稅,乃至租庸調,工商戶都要承擔,因為工商戶分得了土地 (《新唐書》,卷51,《食貨志》)。
到唐朝天寶年間 (公元 742-756),土地兼并加劇,農民流亡,國家控制的應稅土地和戶口越來越少,失去了賦役征收的依據,作為正稅的租庸調“所入無幾”(《舊唐書》,卷118,《楊炎傳》)。為了維持財政收入,各種繁雜商稅興起,“稅商”、“商稅”、“雜稅”都是唐代文獻用于代表今人所謂商稅的詞語。政府在課征內容、范圍、稅率等方面經常變化,很不穩(wěn)定,并交織著中央和藩鎮(zhèn)的抗爭。安史之亂以后,各節(jié)度使在所轄區(qū)內任意征稅。特別是兩稅法規(guī)定的“量出以制入”的財政原則,更為政府攤派各種雜征提供了借口。據《舊唐書·食貨志上》記載:“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兩稅焉,有鹽鐵焉,有漕運焉,有倉廩焉,有雜稅焉。”
當時主要的工商稅有入市稅,即市肆之稅,稱為“除陌錢”,是唐代對交易所得及公私支付錢物所征收的一種稅,有交易稅性質。玄宗天寶九年 (公元750年)除陌錢為每貫20文,即稅率為2%(《唐會要》,卷66,《太府寺》)。德宗于公元783年規(guī)定凡交易所得和公私支付錢物,每1000錢官抽50文錢,即將原稅率提高到5%(《舊唐書》,卷 49,《食貨志》)。若是物物交換,則要按物品價值計算征稅。當時交易稅有兩種,一種通過市牙(牙商),牙商持有官府發(fā)給的印紙,遇有買賣進行登記,負責核算交稅。第二種是由店鋪直接交易,則由店鋪自備私簿登記交易額,然后申報納稅。偷漏稅達百文的,杖60下,罰錢2000文;對告發(fā)者賞10千文,由犯者承擔 (《文獻通考》,卷19,《征榷考》六,《雜征斂》,“德宗時”條)。由于牙商得專其柄,而國家收入不能得其半,一般商人卻大受其苦,人民怨聲載道。對有市籍的商人還課市籍租,是唐代商人的主要賦稅負擔。還有針對行商按2%的稅率征收的商品通過稅;有針對竹、木、茶、漆等征收的特產稅;向田內有青苗的田主征收的青苗錢、地頭錢,甚至“田園荒盡尚征苗”。名目繁多的工商雜稅,使納稅人“旬輸月送無休息”,對百姓的危害很大,嚴重影響了社會生產。
進出口關稅征課形式有明確史籍記載的始于唐朝。唐朝經過百余年的治理后,生產發(fā)展,經濟繁榮,對外貿易有所發(fā)展。其陸路貿易在西北設互市,由市監(jiān)負責管理同邊境少數民族及外國的貿易諸事。在東南沿海許多地方設置商館招待外商,還在廣州設市舶司,由市舶司負責管理海外各國來中國貿易的商人使者,并對其貨物進行征稅,征課形式主要包括“陌腳”,又稱舶腳,或下碇稅,屬于國境關稅性質,可能相當于明清時的船料、噸稅一類的商船稅;也有少數學者認為舶腳與下碇稅屬于不同的稅種。另外,還抽分部分實物作為“進奉”,即上貢朝廷的珍異之物。此外,再無他稅,即所謂的“除腳舶、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全唐文》,卷75,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至于舶腳與進奉的稅率,無從查考。
(五)宋元明清時期的工商雜稅
宋代,商品經濟有了進一步發(fā)展,作為農業(yè)正稅補充的工商雜稅也被不斷累積推出,其收入成為財政收入中重要的一項,是晚清以前唯一的一個工商稅收入超過農業(yè)正稅的朝代。
關市之征在五代十國空前發(fā)展,成為嚴重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惡稅。這一時期商稅的興衰是與商品經濟發(fā)展的軌跡不相適應的,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主要原因在于財政需求,因為兩稅收入有限,而軍費需求孔急,卻不是出于管理工商業(yè)發(fā)展的需要。各國廣設關卡,對來往商人課征通行稅,幾乎是逢物必稅,即使過往渡口的空船也要征稅,對載貨的船只倍征之。關卡之多,以至商旅不通。商人為了逃避關稅,多取僻路行走。各國在山谷小路嚴加防守,緝拿過往商人。苛重的關稅嚴重影響了商品流通,既影響了人民生活,也阻礙了各地經濟的交流和工商業(yè)的發(fā)展。
宋初,曾對五代十國時期所留下的雜稅進行整頓,并將其以“雜變之賦”的名稱確定下來。宋初雜稅之所以被稱為“雜變之賦”,是為了保障財政收入,各項工商雜稅的征稅對象也都轉向田畝,變成了事實上的田稅附加稅。正如《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所言:“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為賦,所謂雜變之賦者也,亦謂之沿納。”《宋史·食貨志》中也進行了解釋:“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此處“變而輸之”,就是把其他征稅對象的雜稅都改為通過田畝征收,變成了隨田雜稅,或者說是田稅附加稅。但其本質上還沒有形成單一性質的雜稅,無論是稅種、稅額,還是稅率、稅物形態(tài)都各自獨立,整體上仍然處于多稅種聯合體狀態(tài),“名品煩細,其類不一”。陳靖在給宋真宗關于江南雜變之賦的上書中稱:“且江南偽命日,于夏稅正稅外,有元征錢物,曰鹽博紬絹、加耗絲綿、戶口鹽錢、耗腳斗面、鹽博斛斗、醞酒曲錢、率分紙筆錢、析生望戶錢、甲料絲、鹽博綿、公用錢米、鋪襯、蘆(竹席)、米面腳錢等凡一十四件,悉與諸路不同。”文中所列雜稅名目竟有十四種之多。張方平在《論免役札子》中也指出北方雜變之賦的繁雜名目:“自古田稅,谷帛而已。今二稅之外,諸色沿納,其目曰陪錢、地錢、食鹽錢、牛皮錢、蒿錢、鞋錢,如此雜料之類,大約出于五代之季急征橫斂,因而著籍,遂以為常。”
除了隨田征收的“雜變之賦”外,還有通常意義上的工商正稅——“科稅”。工商稅在宋朝時期空前發(fā)展,由全國1830多個商稅務、商稅場負責征收。所稅貨物種類,各個地區(qū)不一樣,法令把課稅物品種類、品名榜示在稅務機構的門口,以使官民共同遵守。有針對行商的“過稅”,相當于近代的商品流通稅,按物品價值的2%繳納,如果是官府所需物品,將被“抽稅”10%。應算物資如有隱藏,為官府所抓獲者,沒其1/3,販運不走官路者,抓獲者沒收1/10。對坐商則征收“住稅”,按3%的稅率對出售貨物就地征收(《宋史》,卷186,《食貨志》)。因為商稅是從價稅,為了避免官吏和客商之間發(fā)生爭執(zhí),以及估價的麻煩,官府還要在榜示上標明,某貨物量若干、收錢若干之類,實質上成了從量稅。
為搜刮到更多的財富,從公元992年起,政府干脆實行關稅、商稅預算定額制度,命令各州以公元988-992年間實際征收額最高年份的稅額為“比額”(祖額)。為完成預算或超額完成預算,官吏不斷增加稅欄(卡)、提高稅率、增加稅所。公元1077年(熙寧十年),全國各路(除四川外)稅務所由前幾年的1600余所增至1788所;四川各路稅務200余所,收稅167萬余貫(《宋會要輯稿·食貨》),商稅收入由真宗景德年間的450萬貫增加到仁宗嘉祐時的2220萬貫(《古今圖書集成》),致使商民負擔沉重,商旅不行。
元代商稅是一種交易稅,又稱住稅(坐賈),采用定額制征收。對于商稅,全國無統(tǒng)一的稅率,雖然公元1270年(至元七年),規(guī)定了三十分取一制,但又實行定額稅制,該年以銀4.5萬錠為額,“有溢額者別作增余”(《元史》,卷94,《食貨志》二,“商稅”),并規(guī)定“增羨者遷賞,虧兌者降黜”,鼓勵超額完成任務。公元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大增天下商稅定額,北方為20萬錠,江南為25萬錠,以后又陸續(xù)增稅。文宗天歷年間(公元1329年),總計商稅收入,比至元初的定額幾乎增加100倍 (《元史》,卷94,《食貨志》二,“商稅”)。元代商稅征管較嚴,規(guī)定即使是權勢之家,只要為商賈及以官銀買賣之人,務令輸稅,否則處罰同匿稅法,即物資一半沒官,笞50,將沒收來的物資的一半給予告發(fā)人。商稅收入主要來自全國三四十個大中城市,在元代錢鈔收入中占有僅次于鹽課的重要地位。
明清時期商品經濟進一步發(fā)展,在前代的基礎上,又相應產生和完善了一系列稅種,除了傳統(tǒng)的稱鹽課、茶課、商品通過稅、市稅外,還有塌房稅(相當于近代的堆棧收費,對商人儲存貨物及豬羊牲畜的堆棧,按三十稅一的原則課稅)、門攤稅(即市肆門攤稅,屬于營業(yè)稅性質)、牙稅(向牙行或牙商征收的一種營業(yè)稅)、當稅(當鋪營業(yè)稅)、契稅(對不動產的契約所征收的稅)、落地稅 (坐稅)、礦稅,等等。
由于宋、元兩代政府重視市舶,對外貿易比前代有所發(fā)展,交易的品種由北宋初期的50余種發(fā)展到南宋的300余種,市舶課收入大增,已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對進口商品的征課采取兩種方式,一曰抽解(分),二曰博買。宋太宗時 (公元976-996年),在都城設置榷易署,增價出賣進口商品,一年即得錢30萬緡,后又增至50萬緡 (《宋史》,卷268,《張遜傳》)。南宋初年,“市舶之利最厚”,收入“動以百萬計”,居然占全部歲入的1/5。公元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元朝市舶司歲輸珠400斤,金3400兩(《元史》),僅金就占歲入總額的1/6以上,要靠市舶收入以充“軍國之資”。
明代的市舶司,只負責商舶管理和監(jiān)視,通報敵情,不負責征稅。明代中葉,倭寇騷擾我國東南沿海,政府實行海禁政策,國內商船嚴禁出海。即使出海貿易,也只有經政府批準、官府派官率船出海,并規(guī)定范圍,按經商地區(qū)的遠近抽稅,當時海外貿易是以通好和懷柔等政治目的為主,經商為次。對海外來華貿易者,實行貢舶制度(朝貢,即為稱臣納貢,前提是承認自己的附庸國地位,是對中國皇帝表示敬誠之意,要定期覲見中國皇帝,并進貢一定數量的物品,其中有海外奇珍、香料等奢侈品),凡海外諸國來華貿易,必須由貢使向明王朝進貢方物后方準其貿易,否則不許貿易。對外商貨物采取“官給鈔買”的辦法,不抽商稅,只抽實物六分(抽六分,卻以優(yōu)價償其值,仍免其稅,這種抽分實際上是官府高價收買),其余允其貨賣互市。
清政府對海關稅征收實行定額制,根據《粵海關志》記載,在鴉片戰(zhàn)爭前的一百年間,粵海關年度收入約在白銀40萬兩到185萬兩之間,在財政收入中占1%-5%。
(六)晚清時期的工商雜稅
清政府于公元1853年開征的厘金,集以前各代市稅之大成,成為一個固定的商業(yè)稅。厘金從征收形式上看,有活厘(或行厘,對行商征收的通過稅性質)和板厘(或坐厘,對坐商征收交易稅或落地稅性質)兩種,值百抽一;征收范圍按其課稅品種劃分,有鹽厘、洋藥厘、土藥厘、百貨厘四種,其中以百貨厘課稅對象最廣。
厘金制度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見貨即征,不問巨細,收入規(guī)模不斷膨脹。厘金征課對象異常廣泛,“舉凡一切貧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無一不在被課之列”。據江蘇、浙江、四川、廣東等省厘金章程記載,其課稅貨物分別有25類1241項,29類1942項,12類682項,15類894項,小至手帕、荷包、扇袋,及米粉、醋、蒜,均要負擔厘金。總之,凡市上之物,達到無物無厘之程度。根據同治八年至光緒三十四年 (公元1869-1908年)全國各省厘金收入分類計算,百貨厘約占總收入的92%,茶稅約為1.8%,鹽厘約為0.8%,洋藥厘約為3.3%,土藥厘約為 2.1%(王文素,《財政百年》)。
厘金成為晚清政府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根據檔案材料計算,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14省厘金歲入最低數,在同治三年(1864年)以前每年在1360萬兩上下,最高達到1983萬兩左右。1911年,厘金預算收入4318.7余萬兩,占當年預算總收入的14.5%(清宮度支部,《度支部試辦宣統(tǒng)三年預算案總表》)。
二是稅制雜亂,地方各自為政。厘金的征收,清廷中央沒有制定統(tǒng)一的稅則,由各省自定稅則,任意征收。如厘金名義稅率為值百抽一,但實行以后,稅率不斷提高,且各省稅率都不一致。至光緒年間,多數省份稅率都已在5%以上,如江西、福建、浙江為10%,江蘇負擔更重,一般貨物均在10%以上。因為實行遇卡抽厘,如果稅率為5%,只要通過四卡,負擔率即為20%。所以,厘金的名稱已失去了原來的意義。由于厘金收入除以一定數額報效中央外,很大一部分由地方當局自由處置,地方上為增加收入,便不斷增設關卡,致卡局林立,一貨數征,稅負很重。如湖北初辦厘金時,設卡局至400余處,以后逐漸裁減,至光緒三十一年仍有局卡61處,分卡為數更多。以至 “所有行商坐賈,于發(fā)貨之地抽之,賣貨之地又抽之,以貨易錢之時,以錢換銀之時又抽之,資本微末之店鋪,戶挑步擔之生涯或行人攜帶盤川,女眷之隨身包裹,無不留難搜括”(《皇朝經世文續(xù)編》)。
三是稅吏營私舞弊,附加費嚴重。由于沒有制定統(tǒng)一的厘金稅收標準,上述5%或10%的稅率,也僅是法定的稅率,各省還規(guī)定了名目繁多的附加和手續(xù)費、規(guī)費等,于是除公開課稅、層層盤剝外,“更兼稅吏敲詐勒索”,勒索的名目多達十余種,有指捐、借捐、畝捐、房捐、鋪捐、船捐、鹽捐、米捐、餉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草捐、蘆蕩捐,等等。厘務最主要弊端就是負有管理責任的官員以及差役的營私舞弊,局卡稅吏侵蝕稅款,中飽私囊,如以多報少,以貴報賤,匿報罰款等,以至“每年千余萬之厘金,歸國家者十之三,飽私囊者十之七”(《裁卡增稅議》)。在征得的厘金中,“三分耗于隸仆,三分耗于官紳,其作四分除去正費、雜費外,國家所得無幾。”即使是最底層的小官,也是個肥缺,清末官場中有“署一年州縣缺,不及當一年厘局差”的俗語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
(七)民國時期的工商雜稅
民國時期的工商稅名目繁多,十分混亂。除了前述傳統(tǒng)的鹽稅、煙酒稅、礦稅、契稅、當稅、牙稅、船鈔稅、房稅等外,還有了仿效西方征收的現代稅,如印花稅、所得稅、遺產稅、牌照稅、屠宰稅、筵席及娛樂稅等。各種稅的附加名目繁多,如鹽稅,據統(tǒng)計,1924年,四川省鹽稅附加稅的名目多達26種,有的省多達上百種。而嚴重擾民的則是厘金,在1931年國民政府正式廢止厘金而征收統(tǒng)稅(貨物稅)前,有坐厘、行厘、貨厘、統(tǒng)捐、稅捐、鐵路捐、貨物捐、產銷捐、落地稅、統(tǒng)稅等,甚至對進城挑糞的農民征收糞捐,正如當時的成都詩人劉師亮在打油詩里所諷刺的:“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全國厘卡重重,1924年,全國有厘卡稅局784處,分局卡2500多處,幾乎所有主要水陸交通要道都設有厘卡(賈士毅,《民國續(xù)財政史》)。厘金征收各自為政,稅率各地不一,多數省份在2.5%-10%之間,也有少數省份高達20%以上。
即使在1931年裁撤厘金后,通過稅在各省仍然存在。以四川為例,從成都至重慶不到800里的途中關卡林立,有50多處,平均每十余里即有收稅關卡一所,100元雜貨須納捐稅在100元左右。各種對物征收的雜稅雜捐名目繁多,有護商捐、江防捐、鐵路貨捐、郵包捐、馬路捐、自來水捐、統(tǒng)捐、印花捐、印紅捐等,泛濫到十分嚴重的程度。1937年各省向財政部報送的材料顯示,擬廢除的雜稅雜捐多達7000種。苛繁的工商雜稅,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fā)展。
三、新中國成立前工商雜稅發(fā)展的規(guī)律
雜稅、雜課與無名攤派,是封建國家財政分配的重要特征,因此,歷朝歷代在所難免。但客觀地看,唐朝兩稅法實施前,這類情況并不十分突出。兩稅法“量出以制入”的財政原則,首開攤派定稅后,雜稅、雜課與無名攤派即如魚得水,日盛一日,雜稅作為國家正稅的補充形式,開始不可或缺。應該注意的是,由于雜稅缺乏定制,其數額記載闕略,使人們對雜稅在國家財政中所占的份額往往難以估計。尤其在戰(zhàn)爭、自然災害等非常時期、非常情況下,以及冗官、冗兵等弊政環(huán)境中,國家財政開支動輒成倍增長,雜稅在財政收入中可能會達到很高的比例,財政虧空的部分幾乎全都要靠雜稅來彌補。這里僅以兩稅法之后的兩宋為例,即可見一斑。
(一)兩宋的雜稅課名目
1、農器耕牛稅。宋初即有此稅,即對農器買賣、耕牛買賣進行征稅,而且牛死后,還以軍需物資為理由,要人民把牛皮筋角交給國家,其后改納物為納錢:牛皮一張、角一對、筋四兩,共納錢1500文,后成定制——“牛皮錢”。
2、縑稅、紗稅等特產稅。鄂州崇陽曾征收過縑稅 (絲織的細絹),杭州蕭山縣曾征收過紗稅,舒州宿松等地有芻稅、菰蒲稅,紹興市還有柴米稅、竹木稅,自北宋時一直存在。
3、度牒與官告。度牒是國家給僧、尼、道士、女冠出家的執(zhí)照,也可說是他們的身份證。由于出家人享有一定免役和免稅特權,又不從事農業(yè)生產,對國家財政有一定影響,所以須加以限制。政府便以高價出售度牒,兩宋時期一遇急需,輒發(fā)大量度牒,并稅僧尼。
4、免夫錢。宋與金合兵滅遼收復燕京時,軍費耗竭,于是收免夫錢,凡是應該出力役的人,都貢金出錢。僅此一項,共獲緡錢6200萬。
5、免行錢。凡是工商各行設肆賣東西的,都叫行鋪。五代時,軍人當政,他們到各個行商的店鋪買東西時,強不給錢或少給錢,商人受害很大。宋初循行未改,商人為免去這種負擔,情愿出錢來換得政府免除行鋪免費或減價供應財物的義務,這錢即為免行錢。
6、鈔旁定帖錢。又稱印契稅錢。公元969年 (宋太祖開寶二年)開征,對人民典賣田宅大宗貨物的買賣行為,依據典賣價格課征。凡百姓典賣土地、房產等,先自立契約,稱“白約”,在規(guī)定時間內到官府購買印契紙,將白契帖在鈔紙上,官府蓋印,視為合法契約,稱“紅契”。白契變紅契要納稅,官府依契約載明價格征收契稅,稅率最初為4%,后增為10%,而且稅目也增加了耕牛、舟車、嫁資、遺囑及民間葬地等內容(《文獻通考》,卷19)。嘉祐末(公元1062-1063年)按戶價每千錢輸40錢;宣和末(公元1124—1125年)又增為100錢。牙契之外,曾于每年收勘合錢十文,后又增三錢。大致每百千,交十千多的稅。戶絕后的產業(yè),包括部曲、奴婢、店宅、資財等,戶主死絕后,要近親轉易貨賣,所得的錢,除了營葬及功德等費而外,剩下的錢,如有出嫁女者,給她三之一,其余全數歸公。南宋以后,契稅進一步加重,以致成為按民戶物力科派的弊政,名為“預借契錢”,結果致民間逃避契稅的現象十分嚴重。
7、頭子錢。頭子錢是支付稅,凡是和官家往來而發(fā)生的銀錢出納事務要繳納。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規(guī)定:“役錢千,別納頭子五錢,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運類,皆許取以供費”(《宋史》)。這時頭子錢只是作為地方收入,充地方經費。南宋因財政困難,于公元1135年規(guī)定頭子錢增加到每貫收錢23文,南宋末為每貫56文。江西常平錢物,舊法每貫收頭子錢五文足,也依各色錢事例,增為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舊支用,余數輸給經制司。以頭子錢形式征課出納支付稅,這是中國稅制史上一個特例,是腐朽政權和腐朽行為的代表。
8、河渡錢。為國家出賣渡口行舟權利所取得的收入,宋采取包稅形式,即所謂買撲,凡是愿取得渡口行舟權利的,依法先要提供一定財產抵押作擔保,當承包期滿后如交不上承諾的稅金,即沒收其財產作抵。
9、鬻祠廟。對在祠廟所在地占據地皮經營商業(yè)的行為,除個別有重要意義的祠廟外,都要征收稅金,也采用包稅制辦法。
10、雜斂。以征商為主,宋代隨著工商業(yè)的發(fā)展,苛征雜斂也日益加重,歲有定額的叫常課,無定額叫額外課。額外課名目有32種之多,其中歷日(即歷書)課、契本課(即契本稅)、河泊課、山場課、窯冶課、房地租錢、蒲葦課7種,是全國性的額外征收,其余25種,均屬地方性苛雜。額外課以外,又有許多無名雜斂,如典當稅,典當之后再行賣出亦納稅;聘女的財禮也要納稅,等等。
(二)無名攤派
無名攤派一般指沒有法定的征收制度、沒有固定稅源的臨時征收。屬于這種性質的苛派,在南宋時期是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內容。
1、經總制錢。經制、總制原為宋地方官制名。為籌措軍政費用,宋創(chuàng)設經制錢,是多種苛捐雜稅的綜合體,匯集為一項上解款,方法是在賣酒、鬻漕、商稅、牙稅、契稅、頭子錢、樓店房錢七稅稅額基礎上,每貫增收20文,后來范圍不斷推廣,一歲得錢200萬緡。又添酒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錢,以充經制錢,季終輸送。總制錢為總制使翁彥國所創(chuàng),是以總制司為名。后又施行經制、總制合而為一,名經總制錢,各商稅每貫加征56文成為定制,包括賣酒鬻糟商稅、牙稅、頭子錢、樓店錢等20多項。經總制錢成為宋代的重要財政收入來源,到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經總制錢歲入由北宋末的200余萬緡增加到1440余萬緡,直至1700萬貫(《文獻通考》,卷19)。無怪乎葉適大呼“經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哀,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葉適集》),成為宋代獨創(chuàng)的苛稅,擾民虐民甚重,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指出,“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
2、月樁錢。紹興二年 (公元1132年),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令江東漕臣月樁發(fā)錢十萬緡以贍軍。當時漕司分攤于各州縣一例均科。結果,郡縣橫斂,銖積絲累,江東、江西受害最甚,這在當時本來是一時的應急調撥,后來卻成為專項用款,定期解繳的常賦了。
3、板帳錢。板帳錢亦屬苛派之列。“如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官,索盜贓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核實而入官,逃戶廢田不與消除而抑納,他如此類,不可遍舉。州縣之吏固知其非法,然其板賬錢額太重,雖欲不橫取于民,不可得己”(《宋史》)。 可見,上有所求,下有所法,苛派之生,是政治腐敗所致。
4、無額上供錢。又稱無名上供,這是五代的弊政,宋沿用未改。這種錢內容復雜,有錢、有銀、有羅。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無額上供錢達200萬緡。
5、缺額上供錢。宋代兵士常多逃亡,造成缺額。對缺額兵餉,中央巧立名目,以“缺額上供”名義收歸朝廷,這無疑是使“吃空額”合法化,兵制遭到破壞,有編制,有名額,無士卒,結果靖康之變,無兵抵抗。另還有上供助軍錢等。
除上述各項之外,宋代還有身丁鹽、錢,這是一種人頭稅,或收錢,或收絹,絹又折錢。其數額每州也是動以萬計。南宋時,對僧道征免丁錢,每名納二貫文至五貫文,職位高者,每名納八貫至十貫文,但歷年收入實數,遠遠低于僧道實有人數應繳之數。
(三)工商雜稅的發(fā)展規(guī)律
從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看,一個王朝建立之初,總是輕徭薄賦,王朝沒落之時總是苛捐雜稅,即工商雜稅作為財政收入的補充形式,在財政收入中的地位是“前輕后重”,甚至在兩宋時期和民國初期,雜稅比例超過正稅。由于正稅被法制化和規(guī)范化,因而其增稅的空間受到限制。相反,工商雜稅則比較靈活,具有隨意性、臨時性與非制度化等特征,可以實行多稅種和多稅率,所以若想在正稅之外增加稅額,工商雜稅便成為經常性的手段。但也正因為如此,工商雜稅經常游離于法律控制之外,若監(jiān)控不力,多無常制的雜稅便會成為滋生地方官吏巧取豪奪、腐敗行為的溫床,加重國家的財政危機,甚至能成為封建政權覆滅的重要誘因。非法雜稅的增多會導致百姓心目中政權的不合理性和非法性,這反過來促使歷代政府對雜稅進行整頓和規(guī)范。唐朝中期的兩稅法、北宋時期的方田均稅法和募役法、明代中期的一條鞭法和清代的攤丁入畝便是將農業(yè)正稅衍生出的雜稅合法化使之歸并到正稅的一個過程,國民政府時期進行的裁撤厘金、創(chuàng)辦統(tǒng)稅的改革,便是將名目繁多、重復征收的具有通過稅、貨物稅性質的厘金、雜捐等合并為統(tǒng)稅。通過改革,使以往諸類雜變之賦有了一個統(tǒng)一的稱謂,隱去那些繁雜的稅種名目,更重要的是還促使它們向單一稅種轉化。由雜稅的多稅種聯合體和單一稅種的區(qū)別在于征稅對象、征稅額度、征稅物品和稅率的差異,而通過改革將其歸并到正稅中,則簡化了稅目,使課稅范圍確定具體,不重復征稅,減少了征稅成本。
不過,當雜稅被規(guī)范進正稅而形成單一稅種后,它的增稅空間也受到了限制。當中央或地方財政困窘、需要在正稅之外增加稅額時,原來的雜稅由于已經單一化,顯然難以發(fā)揮作用,因而,從原有的制度土壤中再次萌生出新雜稅就成為必然。盡管出現的新雜稅使用了新名目,但其形成途徑與產生機理卻與原雜稅具有相似性,甚至有些雜稅仍沿用原來的名目,這一過程在雜稅發(fā)展史上具有一定的規(guī)律性。明末清初的三大啟蒙思想家之一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田制三》中曾經對這一規(guī)律進行過總結,認為“天下之賦日增,而后之為民者日困于前,使人民苦于暴稅之三害: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主張重定天下之賦,而定賦的標準應以下下為則。”當代學者秦暉教授以此為基礎總結出“黃宗羲定律”。秦暉主要強調的是“積累莫返之害”,認為唐代的 “兩稅法”、明朝的“一條鞭法”、康熙雍正年間的“攤丁入地”以及民國時期的“田賦三征”等,都是一種“并稅式改革”,其特點是把明暗正雜諸稅都納為正稅,此后又加雜派,導致農民的稅負不斷加重。此所謂“采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guī)”(《并稅式改革與“黃宗羲定律”》)。由此他提出一個公式:
bn=a+nx
式中bn為經過n次改制之后的新稅額,a為原始稅額,x為攤派,n為改制次數。
根據這個公式所表述的黃宗羲定律,農民的稅負呈間歇性單邊上揚的態(tài)勢。實際上,雜稅的歷史演進過程體現了國家對雜稅的法制化和規(guī)范化努力,其目的是促使雜稅稅種簡化、稅率固定,并最終實現雜稅的依法管理。然而,雜稅存在的前提是能夠通過法外增科形式來補充正稅稅額的不足。當已有雜稅被國家法律限定以后,其功能遂開始消失。于是,新的雜稅再次衍生。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社會雜稅去而復返、屢禁不絕的現象,不能單純地歸咎于王朝政治的腐敗,雜稅本身內在機制亦發(fā)揮著重要的支配作用。
此外,雜稅的演進及新雜稅的衍生也關涉到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央對雜變之賦整頓與合并的直接目的就是規(guī)范地方政府,使其對雜稅依法征收,即便南宋時期中央增加了新雜稅也是以財政調撥名義出現的。但地方政府往往借助雜稅以自肥,因而潛心尋找中央政府的制度漏洞。當南宋中央政府對地方賦稅的索取額大大超出實際封樁存留份額時,地方政府征收新雜稅便順理成章了 (吳樹國,《宋代雜稅演進考論》)。
由工商雜稅透視古代社會,能得出很多有益的啟示。從歷史上看,每一次雜稅在新朝代政府建立之初時進行的稅制改革后又生新的雜稅,居民稅負顯著提升。其原因可能來自四個方面:其一是土地兼并加劇所引起的稅源銳減,農業(yè)正稅不足,便想方設法通過工商雜稅以彌補;其二是戰(zhàn)亂不止,一方面使人口逃亡,稅源減少,另一方面鎮(zhèn)壓戰(zhàn)亂又增加了政府的財政需求,北宋、清末巨額的對外賠款也進一步加重了財政負擔,便設法開辟新的財源;其三是意在開展農村改革,又沒有相應的財政投入,如清末民初時期的鄉(xiāng)村自治;其四是官僚機構自身的膨脹、統(tǒng)治階級生活的奢靡和官吏的貪腐,如北宋時期,每隔30年,官吏人數和軍隊規(guī)模就增加約1倍。這一規(guī)律不僅在北宋起作用,而且在歷朝歷代一再發(fā)生作用。也就是說,雜派的出現與否與并稅改制并沒有必然聯系,只是與財政收支狀況有關,財政困難使加稅成為政府必然的選擇。
如果國家根據當時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及社會狀況,恰當地運用工商雜稅的征收去調節(jié)收入分配,調控經濟行為,調整階級關系,這對于緩和矛盾、穩(wěn)定社會也能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如秦漢時期利用工商雜稅的征收去抑制發(fā)展過熱的工商業(yè),協調農、工、商各業(yè)之間的關系;把原本供皇室“私用”的工商稅收中的一部分用于促進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實施社會救濟,等等。但在當時的社會機制下,封建國家通常不可能按與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相適應的價值規(guī)律辦事,往往只從增加財政收入考慮,以為政治權力可以隨意決定經濟生活的發(fā)展方向。雜稅的征收往往超過百姓的一般負擔能力,最終影響和制約了社會生產和發(fā)展,甚至要付出社會動蕩、改朝換代的代價。巨大的社會沖擊會使新朝代的統(tǒng)治者開始關注社會公平,減輕賦稅和徭役,收斂官僚大地主的特權,整肅官吏的貪腐,精簡政府開支,使農民負擔有相當的減輕,促進經濟恢復和發(fā)展,開始了新的循環(huán)。
要解決雜稅死灰復燃的問題,首先,要從機制上消除稅外加費的內在原因,即根除雜稅產生的 “病灶”——冗員冗費泛濫和統(tǒng)治階級的驕奢淫逸,這是雜派產生的根本動因,要精簡機構、吏治清明,否則,一旦財政拮據、“雜用”不足,便會重出加派,從而導致中長期簡化稅制、減輕稅負的效果與改革初衷相反。其次,應加強法制建設,限制政府的征稅權。在君權至上、家國一體的封建政治體制下,從制稅、征收到安排支出等財政決策都是直接在皇帝個人的強權控制下做出的安排,在缺乏法制限制政府征稅權的社會里,并稅除費后,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會發(fā)生因地、因事、因人“巧立名目”增加稅費的現象。■
(本研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è)務費專項資金”<31541010903>資助)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財政稅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