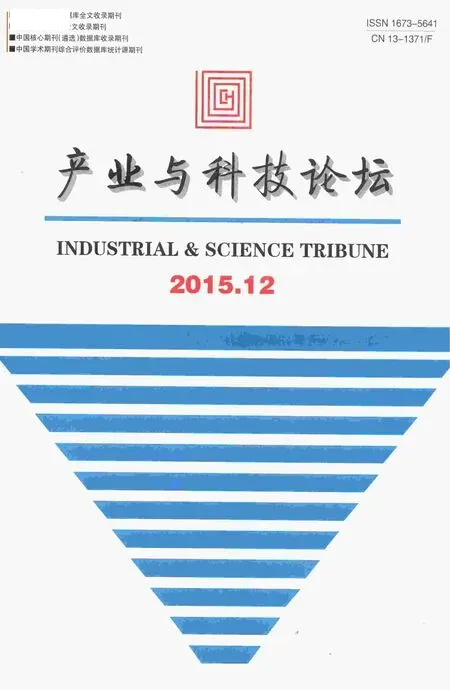網絡群體的非理性行為分析
□ 徐 漪
隨著傳統社會向網絡社會的不斷演進,網絡空間成為人們表達個人情感、觀點和訴求的公共平臺。在網絡空間,人們基于各自的興趣、關切、利益,對現實社會發生的某項公共事件發表不同或相同的觀點,當網絡空間的這種個體行為逐步演化為群體行為時,就可能影響社會公眾對該公共事件的理解和認識,甚至影響該公共事件未來發展的軌跡。
一、網絡群體行為的含義與特性
網絡群體行為的概念源自現實空間的群體行為,即傳統意義上的群體行為。傳統意義上的所謂群體行為是指,為了實現某個特定的目標,由兩個或更多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的個體組成的人群集合體的共同行為。組織、群體和個體是整個社會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體,群體介于組織和個人之間。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克(Parker)認為群體行為是“在公共和集體沖動的影響下發生的個人行為,換句話說,那是社會互動的結果”。斯梅爾瑟(SmelSer)認為群體行為是“在重新規定社會行為的信念的基礎上產生的社會動員”。波普諾(David Popenoe)更為詳細地指出,群體行為是“在相對自發不可預料無組織的以及不穩定的情況下對某一共同影響或刺激發生反應的行為”。
目前,關于網絡群體行為并無一個權威、公認的定義,學者們都是從各自不同的理論架構和學術邏輯對其進行不同的闡述。比如,國內有的學者將網絡環境下的群體行為定義為“數量較多的網民在非預期的某個特定階段,為達到某種共同訴求而以網絡的方式集中參與到社會事件中”,并認為網絡環境下的群體行為具有非預期性,因為所產生的集體行為是在特定感情支配下的,因此集體行為產生的結果也具有不確定性,這兩個特性使其與強組織性、計劃性的社會運動相區別;而有的學者則將網絡環境下的群體行為定義為“一定數量的、無組織的網絡群體,圍繞特定的現實主題,在一定誘發因素的刺激下產生的,以意見的強化與匯聚為特征的,具有現實影響力的網民聚集”。
一般認為,網絡群體行為可以被視作現實生活中群體行為的虛擬化,但是,這種虛擬化卻在相當大程度上真實地反映、還原或再現了現實生活的本質。在現實生活中,群體行為受到群體及其成員的社會地位、經濟利益、政治傾向、文化傳統等多因素的影響,而在網絡空間,群體行為除了這些"現實因素"以外,又依賴于網絡技術以及網絡治理本身的特性,呈現出與現實社會中的群體行為不同的特點。
(一)社會身份的隱匿化。在網絡空間,某一個個體都能夠虛構、改變或藏匿起現實社會中的真實身份,這給予其某種安全感,或者說是虛假的、并不存在的“法律豁免權”,使得網絡群體行為參與人可以毫無顧忌、不負責任地發表評論,甚至進行惡意的人身攻擊。社會身份的隱匿化特性放大了網絡空間交流平臺的負面作用,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廣大的網絡群體中,形成濃重的負面情緒,并可能溢出至現實社會,造成現實社會的劇烈動蕩。
(二)議題設置的偶然性。現實社會中的某個事件或話題,能否成為網絡群體行為的議題,這個網絡群體行為會演化成多大的規模,都事先難以預測。網絡群體行為的議題與現實社會的事件或話題具有一定的關聯度,但是,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必然姓,往往呈現出偶然性特點。一般而言,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的事件或話題,尤其是涉及當下現實社會的熱點問題時,更容易成為網絡群體行為的議題,而網絡群體行為的參與者的參與動機有時是明確的,有時則是模糊的。
(三)群體構成的快速化。在互聯網上,每個網絡群體行為的參與者都可以進入一個開放性公眾交流互動平臺,成為網絡群體行為的一員;或者就某一事項,創制一個開放性公眾交流互動平臺,成為網絡群體行為的發起人。基于現代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網絡群體行為的醞釀、生成、擴散、暴發、消退的整個“生命周期”中的每一個“生命階段”的過渡時間可以十分短暫,其群體數量的增長往往呈指數型特征,遠遠超出了傳統社會中一般公共事件的傳播速度。
(四)個體參與的隨意化。網絡群體行為,就其本質而言,是現實社會中群體行為在網絡空間的再現,反映的仍然是現實社會中不同的社會群體和個人的要求。由于網絡空間的開放性特征,每一個網絡群體行為的參與者都能夠參與現實社會中的某一公共事件的討論,隨意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形成了相對自由、寬松、獨立的輿論場,甚至由此影響到該公共事件的進展,從而獲得了在現實空間不易獲得的參與感、認同感和存在感,并強化了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的參與積極性。
(五)輿論表達的情緒化。網絡群體行為的參與者大多是社會中下層的弱勢群體,他們有的承受著就業的風險,抗爭著資本的貪婪,有的是面臨著話語權被剝奪和逐漸被邊緣化的趨勢,難以真正享受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因此,在網絡空間,網絡群體行為的參與者有的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切身利益,有的僅僅只是為了發泄個人的不滿,排解個人的不幸,而扮演一個“憤怒者”的角色,并且為了獲得他人的關注、同情或共鳴,而使用情緒化甚至是極端化的表達方式。
二、網絡群體的非理性行為及其產生原因
在本質上,網絡空間依然是現實社會原像的復制,現實社會中的矛盾與沖突無疑會在網絡空間中重現;正如現實社會中的群體行為不可能總是理性的一樣,網絡群體行為往往表現出非理性的特性。
對于網絡群體的非理性行為,目前國內外并無一個普遍認可的定義。有的學者也將網絡群體的非理性行為稱之為網絡“群體極化”或“群體失范”。1961年,傳媒學者詹姆斯·斯托納(JameSStoner)首先提出“群體極化”這一概念。所謂“群體極化”(grouppolarization)是指,群體中原已存在的傾向性通過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強,使一種觀點朝著更極端的方向轉移,即保守的會更保守,激進的會更冒險。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凱斯·桑斯坦(Cassunstein)在《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一書中指出,“群體極化的定義極其簡單:團隊成員一開始即有某種偏向,在商議之后,人們朝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桑斯坦得出的基本結論是:群體極化正發生在網絡上。所謂“群體失范”是指,網絡群體行為是在網絡空間與現實社會諸多負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現的與現實社會的行為規范、準則等的偏離。在網絡空間,人們原有的社會規則對于個人行為的制約作用被大幅削弱甚至徹底消解,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的個體行為成為了一種不受社會規則約束的虛擬行為。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使這種本來就缺乏約束的行為迅速擴散,由此產生網絡群體行為的失范。網絡群體的非理性行為的產生,從根本上來說,源自網絡群體行為的特性,并在現實社會各種負面因素的影響下顯現出來。具體而言,網絡群體的非理性行為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匿名制下的理性弱化。網絡空間普遍實行的匿名制,一方面給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帶來了參與的便捷和言論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也削弱了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的公民意識、法律觀念和社會責任,造成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自制能力的下降或者缺失,從而發泄并放大了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在現實社會中的負面感受,引起了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的共鳴,強化了網絡群體行為的非理性成分。二是趨同化導致的“疊加效應”。在網絡空間,一個特定的議題對于不同的群體具有不同的吸引力。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的職業屬性、文化程度、民族習慣、宗教信仰、思維特點等差異決定了其是否參與這一議題的討論以及參與的角色和程度。這種參與的選擇權完全在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手中。一般而言,具有相同的訴求、性格、意趣的個體,更容易成為某一項網絡群體行為的參與者,他們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從而產生了負面化的“疊加效應”,造成網絡群體行為的趨同化和極端化。三是“被關注”的心理需求。事實上,網絡群體行為并不一定具有明確的現實利益上的動機,他人往往難以理解或認可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的行為邏輯。研究表明,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在現實社會中往往是被忽視的群體,不但其切實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其意見訴求也得不到重視。因此,他們特別渴求在網絡空間這一虛擬社會獲得他人的關注和喝彩以得到心理補償和滿足。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常常使用夸張性語言,以獲得轟動效果,從而走向非理性化。四是“法制缺失”的主觀誤判。在網絡空間,現實社會中的各種法律、制度、權力、規范同樣有效。但是,這些法律、制度、權力、規范畢竟不如現實社會中這般真實。同時,網絡空間普遍實行的匿名制又使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獲得了一種“安全距離”,自以為可以脫離現實社會的法律規制。因此,對議題往往作出基于自身體驗、境遇基礎上的感情化判斷,甚至僅僅是逞一時之快,使一個現實社會中的守法、平和、穩重、理性的人,成為網絡空間中的違法、激進、沖動、非理性的人。
三、網絡群體非理性行為的應對
網絡空間與現實社會并不是兩個截然分割的空間,網絡群體行為是現實中的社會問題和社會關系的反映,因此,網絡群體的非理性行為的無限膨脹、蔓延,就必然會超越網絡空間的界限,溢出到現實社會之中,對現實社會的穩定造成沖擊。因此,對網絡群體的非理性行為進行合法、適度、有效的應對,是社會的理性要求,也是政府不可回避、不可推卸的職責。
但是,基于絕大多數的網絡群體非理性行為的真實動機并非是對現存的政治體制、社會秩序、道德規范的“惡意沖撞”,因此,對于網絡群體非理性行為——只要其沒有觸犯法律且局限在網絡空間的范疇內——就應當持寬容的態度,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當客觀、細心、冷靜地分析和思考發生網絡群體非理性行為的“現實因素”,從而采取合法、適度、有效的應對措施,對其予以及時疏解,避免網絡群體非理性行為惡化、失控,進而引發現實社會的動蕩。
當然,對網絡群體非理性行為持寬容的態度,并不意味著無所作為。一是從政府方面來看,應當及時轉變政府職能、強化服務意識、提高行政效率,積極應對公眾的合理訴求,切實解決公眾密切關注的熱點問題,以弱化乃至消除網絡群體非理性行為的“現實因素”。二是應當經常與公眾進行積極、主動、真誠的溝通,實現政府信息,尤其是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等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的公開,以最大限度地獲得公眾對政府決策的理解和支持,避免在公眾中形成政府“一意孤行”的感覺,激化公眾與政府的關系。三是從社會方面來看,社會各方包括網站、傳媒等機構、組織,對于網絡群體非理信行為決不可采取袖手旁觀的態度,應該自覺地承當起社會責任,對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進行正面引導,共同營造出積極、健康、有序的網絡輿論環境,倡導客觀、理性、克制的網絡言論規范,預防和阻止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受到不良信息,特別是虛假信息的影響,失去自己應有的正確判斷而趨于非理性化。四是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網站、傳媒等機構、組織決不能出于自身的商業利益,對網絡空間的非理性言論推波助瀾,以擴大自身的市場影響,謀取自身的經濟利益。從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自身來看,當務之急是加強自身的學習和修養,強化自身的社會責任感、法律意識和自律能力,培養自身客觀、理性、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習慣,避免偏聽偏信、輕信盲從。尤其是要牢固樹立法律意識和道德自律,避免將輿論自由與造謠、信謠、傳謠混為一談;避免將輿論監督與惡意中傷混為一談。更為重要的是,網絡群體行為參與者應當自覺地意識到,自己不應該僅僅只是現實社會的冷靜的批評者,而更應該成為理想社會的熱忱的建設者。
[1]戴海容,王麗萍.網絡環境下個體行為向群體行為演化路徑分析[J].商業時代,2013,34
[2]劉長龍.網絡群體行為與現實群體行為的比較分析[J].長白學刊,2012,6
[3]戴海容.社會沖突視野下網絡群體行為分析[J].學術探索,2013,10
[4]鄧希泉.網絡集群行為的主要特征及其發生機制研究[J].社會科學研究,2010,1
[5]王元卓等.網絡群體行為的演化博弈模型與分析方法[J].計算機學報,2014,37
[6]曾舟.對網絡群體失范行為的管理研究[J].神州,2014,15
[7]王筱孛.人肉搜索:網絡群體極化行為初探[J].青年記者,2008,12(下)
[8]薛國林.中國互聯網語境的現實邏輯——網絡群體行為與政府應對策略[J].學術前沿,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