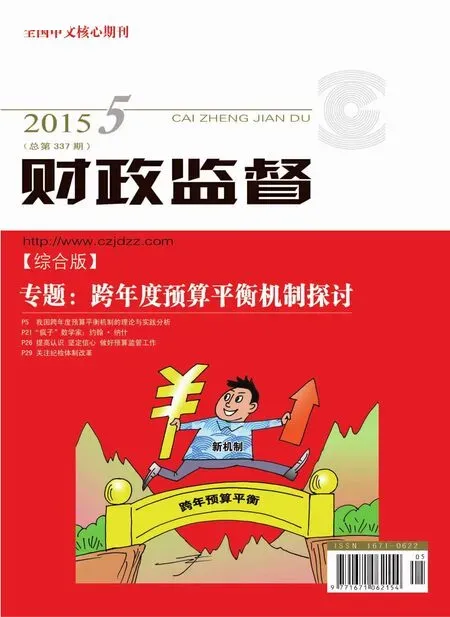芻議跨年度預(yù)算平衡
●王雍君
一、預(yù)算控制功能的弱化和救濟
現(xiàn)代預(yù)算制度的基石是人民對政府的法定控制。在民主治理背景下,政府得自人民的財政資源,必須按人民意愿使用,并致力產(chǎn)生人民期望的結(jié)果。預(yù)算制度在促進(jìn)和強化政府對人民的財政責(zé)任方面起著至關(guān)緊要的作用。
這種作用的首要方面,就是采納年度平衡機制對政府財政權(quán)力的約束和引導(dǎo):在每個財政年度,政府不得花比當(dāng)年收入更多的錢,只有出現(xiàn)諸如重大自然災(zāi)害和戰(zhàn)爭等不可抗拒情形才能例外。偶爾出現(xiàn)的小額赤字和債務(w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種情形只能是特例而非常規(guī)。在西方世界,這種謹(jǐn)慎理財觀長期以來支配了政府的財政行動,直到20世紀(jì)40年代開啟凱恩斯革命才被逐步終結(jié)。
凱恩斯革命的核心內(nèi)容就是周期財政平衡:預(yù)算必須作為宏觀經(jīng)濟穩(wěn)定的政策工具發(fā)揮作用,因此,沒有必要堅守嚴(yán)格的年度平衡;事實上,政府可以而且有必要在景氣循環(huán)的低谷多花錢、少征稅,通過預(yù)算赤字和舉借債務(wù)來促進(jìn)經(jīng)濟較快恢復(fù)到“充分就業(yè)水平”;而在經(jīng)濟向好的繁榮階段,政府有必要節(jié)制開支,形成財政盈余來彌補此前的赤字。
凱恩斯的周期財政平衡理論經(jīng)常被誤讀為“赤字財政”理論。實際上,這只是“半邊的”凱恩斯主義,因為關(guān)于財政盈余的思想被抽象掉了。
凱氏的周期財政平衡理論對政府的預(yù)算運作產(chǎn)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自然也遭遇了許多批評。直到今天,這種注重現(xiàn)實的經(jīng)濟思想和政策主張仍然有廣泛的市場,特別是在經(jīng)濟衰退(危機)時期。
最近20 多年來,中國也是凱恩斯財政理論的實踐者,盡管我們忌諱作如此表述。看看中國各級政府越來越大的實際赤字和債務(wù),再看看急劇增長的貨幣供應(yīng)量,完全可以說,就“只用不說”而言,中國對凱氏政策的偏好一點也不亞于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采納的是明顯的“半邊式”凱恩斯主義——偏好擴張而不是緊縮。財政支出和實際赤字顯著的“順周期”特征,就是最好的腳注。也就是說,經(jīng)濟增長越快,政府開支增長越快,而不是相反。
這就引發(fā)了一個問題:拿什么來控制政府開支公款和舉債的權(quán)力?
自古以來,財政權(quán)力就是國家權(quán)力的主要和核心部分。要想把權(quán)力關(guān)進(jìn)制度籠子,首先得把財政權(quán)力關(guān)進(jìn)制度籠子。要想把財政權(quán)力關(guān)進(jìn)制度籠子,首先就得把課稅權(quán)、其次便是把開支和舉債權(quán)關(guān)進(jìn)制度籠子。預(yù)算制度就是把開支公款和舉借債務(wù)關(guān)進(jìn)籠子的主要制度安排。
歷史和現(xiàn)實一再啟發(fā)人們:開支和舉債的失控會引發(fā)重大負(fù)面后果。有效的支出和債務(wù)控制——預(yù)算的法定控制功能——因而極為重要和不可或缺。
這種控制功能傳統(tǒng)上主要通過嚴(yán)格的預(yù)算平衡機制實施。跨年度預(yù)算平衡機制本質(zhì)上就是對年度平均規(guī)則的偏離。這種機制不要求每年必須平衡,而是要求在一個景氣循環(huán)(經(jīng)濟繁榮和衰退周期)內(nèi)實現(xiàn)平衡。原則上,后者也可以作為一種控制機制發(fā)揮作用,但相對于年度平衡規(guī)則而言,跨年度平衡的控制功能已經(jīng)大為弱化了。因此,轉(zhuǎn)向這種新的平衡機制(周期性赤字和周期性盈余交替)要求有額外的救濟機制,以防范借“穩(wěn)定”或“刺激”經(jīng)濟之名行權(quán)力濫用之實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在真實世界中非常高。
二、對預(yù)算審查的挑戰(zhàn)
除了附加嚴(yán)格的實施要求以平衡預(yù)算的控制功能和政策功能外,跨年度預(yù)算平衡也提出了預(yù)算審查的全新課題。首先,預(yù)算審查的視野需要覆蓋若干年度,由此引申出中期財政規(guī)劃(國際上稱為中期支出框架:MTEF)概念。國務(wù)院和財政部已經(jīng)決定從2015年開始推動這項改革。中期財政規(guī)劃可以為跨年度預(yù)算平衡機制提供一個理想的操作平臺,盡管這項改革的成功依賴于一系列苛刻的條件,包括高質(zhì)量的經(jīng)濟和財政預(yù)測、自上而下啟動的預(yù)算程序和基線籌劃(baseline projections),其中多數(shù)并不具備。
就宏觀經(jīng)濟穩(wěn)定而言,跨年度預(yù)算平衡帶來的最為深刻的影響,就是要求在預(yù)算政策制定的當(dāng)時——而不是事中或事后,就意識到預(yù)算政策對宏觀經(jīng)濟運行的影響,特別是量化對經(jīng)濟增長、就業(yè)、物價穩(wěn)定和國際收支等主要宏觀經(jīng)濟目標(biāo)的影響。最重要的概念是財政乘數(shù),包括稅收乘數(shù)、支出乘數(shù)和轉(zhuǎn)移支付乘數(shù)。乘數(shù)值反映財政變量(稅收、支出和轉(zhuǎn)移)影響產(chǎn)出(GDP)的程度。
因此,就人大審查預(yù)算而言,關(guān)注跨年度平衡機制并非看起來那么簡單。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機制要求審查預(yù)算的人大代表成為通曉預(yù)算的專家,特別是能夠理解和量化預(yù)算變量(稅收、支出和債務(wù)等)如何影響經(jīng)濟變量,以及后者反過來如何影響預(yù)算變量。預(yù)算政策與宏觀經(jīng)濟目標(biāo)是否相互協(xié)調(diào),成為審查預(yù)算的焦點之一。
傳統(tǒng)的審查只是關(guān)注預(yù)算草案是否滿足法定控制的要求,比如收入是否符合稅法、支出是否按照標(biāo)準(zhǔn)價格(比如年均標(biāo)準(zhǔn)工資支出)和標(biāo)準(zhǔn)數(shù)量(比如公務(wù)員編制)確定,以及是否遵循法律規(guī)定的其他管制,包括《教育法》、《科技法》等規(guī)定的“法定支出”。這種以合規(guī)性控制為焦點的審查模式有比較明確的標(biāo)準(zhǔn),需要的專業(yè)技能也沒有那么高。相比之下,對跨年度預(yù)算平衡機制的審查,需要關(guān)注擬定的預(yù)算對于宏觀經(jīng)濟目標(biāo)是否充分,這需要更高和更復(fù)雜的專業(yè)技能與知識。
三、技術(shù)性操作
許多文獻(xiàn)指出,官僚機構(gòu)的目標(biāo)即便未必是預(yù)算最大化,也會想方設(shè)法獲取更多的預(yù)算,而且逃避監(jiān)管的動機相當(dāng)強烈。官僚機構(gòu)也有巨大的空間和機會隱藏支出和預(yù)算,形成所謂的“黑箱預(yù)算”。預(yù)算過程中各種形式的“財政粉飾”(包括假平衡、真赤字)和機會主義行為,幾乎無處不在。
如果不對最基本的預(yù)算變量——預(yù)算赤字——作出嚴(yán)格的技術(shù)性定義,那么,在實踐中就很難對跨年度預(yù)算平衡機制建立起有效的技術(shù)性操作。舉例而言,如果允許把債務(wù)算作“收入”,那么,“平衡”就是一個很虛假的概念。所以,技術(shù)性定義和操作的一個基本要求是: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平衡”和“真正的赤字(或盈余)”?債務(wù)因素如何處理?
“預(yù)算收入”、“預(yù)算支出”也是如此。在計算赤字或盈余時,需要把上年的收入包括進(jìn)來嗎?變賣或銷售資產(chǎn)(“土地財政”)的收入是否應(yīng)該剔除?
同樣需要明確的是:應(yīng)按總額、不應(yīng)按凈額列示收入和支出。如果某年的交通罰款為500萬元,返還給執(zhí)罰部門300萬元,凈額就是500萬-300萬=200萬元。如果在計算預(yù)算赤字時,只是計入凈額300萬元,而不是同時記入收入500萬元、支出(返還)300萬元,那么結(jié)果將很不真實。
另一個更復(fù)雜的問題是預(yù)算收入、支出和赤字的范圍。國有企業(yè)和國有金融機構(gòu)是否應(yīng)包括在內(nèi)?“政府”的財政邊界應(yīng)劃在何處?
中國還有世界上規(guī)模最為龐大的“準(zhǔn)財政活動”。這些活動的收入和支出如何計量?
擔(dān)保、稅收優(yōu)惠和政府壟斷(電力、電訊、能源等行業(yè)尤其嚴(yán)重)都是準(zhǔn)財政活動的常見類型。利率管制和匯率管制也會形成準(zhǔn)財政活動,而且規(guī)模十分龐大。如果政府管制的價格高于市場價格,相當(dāng)于對當(dāng)事人的一筆隱蔽征稅;相反,則相當(dāng)于一筆補貼。
由此可見,跨年度平衡的技術(shù)性操作十分復(fù)雜。到目前為止,《預(yù)算法》對這些基本變量的技術(shù)性定義一直模糊不清,這就給實踐的機會主義行為留下了很多空間。
四、結(jié)語
跨年度預(yù)算平衡機制的復(fù)雜性遠(yuǎn)高于想象,特別是需要在預(yù)算制定和審查的當(dāng)時就考慮到其對宏觀經(jīng)濟影響。如果能夠做到真實(無粉飾)且合理(符合逆周期操作規(guī)則)的平衡,即使是周期性的平衡,也是可取的。但真正的問題在于,偏好赤字(多開支、多舉債、少征稅)的動機遠(yuǎn)比形成財政盈余的動機強烈。因此,跨年度平衡機制也可能給破壞財政紀(jì)律創(chuàng)設(shè)更多空間。另外,技術(shù)性定義也需要清晰明了,這是《預(yù)算法》實施細(xì)則需要承擔(dān)的任務(w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