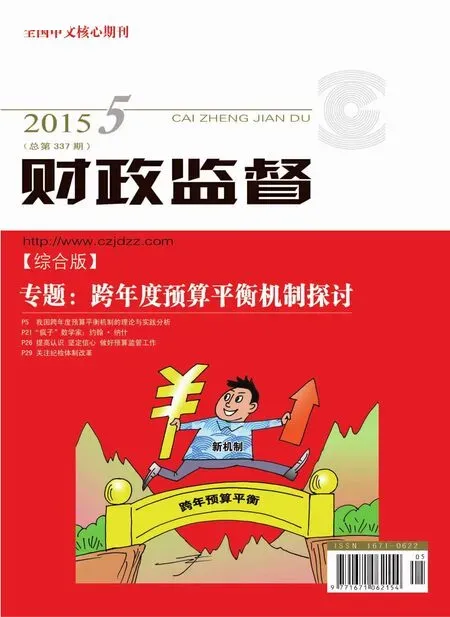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與中期預算框架是否是一回事?
●鄧淑蓮
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與中期預算框架是否是一回事?
●鄧淑蓮
我國新《預算法》規定,自2015年1月1日起,各級政府應當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對這樣一個新的預算名詞,無論學界,還是地方政府,都難以理解其中的含義,更不用說如何實行了。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與中期預算框架類似,甚至就是一回事。但仔細品味,發現二者是根本不同的兩種預算機制。
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中期預算框架是在年度預算背景下產生的預算思想,旨在消除年度預算對政策目標的切割影響,保證預期政策目標的實現。
確定性是人類對現實和未來的期許,因為現實和未來越具有確定性,人類越能夠規劃生活,在追求幸福的過程中交易成本越小。特別是在公共領域,未來越確定,人們制定的預算越準確,資源的配置與目標的聯系越緊密,目標實現的可能性就越大,交易成本越低。因而,從理想的角度看,人們希望制定的預算時期越長越好。但現實和未來總是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從而使長期預算不可靠。從確定性、成本以及對政府活動控制的有效性上考慮,人們確定了年度預算原則。即,每年編制政府預算,并由立法機構審查批準。年度預算對加強預算的立法控制是有效的、不可缺少的,因此,控制政府預算行為,使之符合公眾的利益是年度預算的目標。
但事物都有其兩面性。年度預算在有效控制政府行為的同時,也割裂了預算目標的完整、統一性,使公共活動趨于短期化,沒有長遠目標和規劃。制度安排和資源配置只關注短期目標。而有些目標從短期看符合公眾意愿,從長期看就有可能是損害公眾長遠利益的,由此將不可避免地造成資源浪費。
正是認識到了這樣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德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及部分發展中國家,都相繼采用中期預算框架。
中期預算框架是對3-5年人類的公共行為進行規劃和約束。之所以不能更長,不是人類不想,而是能力所限,或者說,超過3-5年的規劃的準確性將大打折扣,意義不大。
中期預算框架的核心內容如下:
首先,要有良好的預算計劃水平。計劃是現代預算具有的首要職能。預算的計劃職能要求必須制定出明確的,符合公眾意愿的跨年度發展目標以及預測實現目標所需要的資金總量。
跨年度目標的確定首先必須經由社會反復討論,形成共識,之后將目標細化和量化,分解成各年度目標。沒有明確的跨年度目標,預算資金的配置便沒有明確的方向和歸著點,其運行的有效性就無法保證。
其次,將年度目標與預算資金相聯系,制定年度預算。盡管跨年度預算重視的是多年度預算,瞄準的是多年度目標,但年度目標和年度預算是其重要環節,不可缺少。無論是3年目標,還是5年目標,最終都要落實到年度目標上,即要將多年度目標,按照目標本身的特點和進度要求,分解成多個年度目標,再根據年度目標編制年度預算,報經立法審批后執行。只有將多年度目標分解成各年度目標,才能配置預算資金。中期預算框架的邏輯是多年度目標與年度目標緊密關聯,而預算安排則與年度目標密切相聯。實行中期預算框架,并不是廢除年度預算,或削弱年度預算的作用,而是在享受年度預算嚴格控制政府預算行為這種好處的同時,消除其目標短期化的弊端。
最后,對跨年度預算執行結果進行“3E”績效評估。即經濟性評估(Economy)、效率性評估(Efficiency)和效果性評估(Effectiveness)。所謂經濟性評估是評估預算執行結果與預算之間的差距,差距越小,績效越好。效率性評估是指投入——產出之比。一定投入下,產出越大,績效越好。效果性評估是指預算資金的使用是否實現了確定的目標。
通過多年度目標確定——多年度預算總額控制——年度目標確定及年度預算安排——立法審批年度——預算執行——中期預算執行結束后的績效評估與考核這一完整的過程使預算目標與預算資金配置緊密聯結,形成嚴密的公共資金使用和控制體系,保證公共資金安全、有效運行。
與年度預算相比,中期預算將人類的規劃期拉長,從而將人類的規劃視野大大擴展,能夠從一個較長的時期審視人類與自然、人類自身的協調發展問題,這無疑是預算思想和實踐的一次有益突破。
與中期預算框架不同,我國采用的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強調的主要是跨年度預算平衡。這意味著放棄年度預算平衡原則。而年度平衡原則是重要的預算控制原則,放棄年度平衡原則,就意味著政府的收支不必保持年度平衡,也就是說,年度預算赤字將成為我國政府預算的常態。這其實是一種凱恩斯主義思想。在凱恩斯主義者看來,預算平衡與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預算支出的增加是否有利于社會總需求的擴大,進而刺激經濟的增長。凱恩斯主義實行的結果,必然導致預算對政府收支行為約束力的減弱,導致政府收支行為的失控。因而,在上世紀70年代,西方各國對大政府趨之若鶩。但凱恩斯主義并沒有帶來其所描繪的美好藍圖,反而造成西方國家上世紀70年代普遍出現的經濟滯漲,即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同時存在的局面,由此引發的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的危害最終導致凱恩斯主義退出主流經濟學地位,西方社會向自由市場經濟回歸。
不僅如此,所謂的跨年度預算平衡,到底跨多少年才平衡?還是一直不平衡?什么年份下才能平衡?收支預算不平衡的許可幅度是多少?有沒有年度預算赤字上限?有人還提出跨年度滾動預算平衡機制,這又是一個什么樣的機制?是赤字滾動預算,還是目標滾動預算?跨年度預算到底有沒有支出目標及支出上限?有無預算周期結束后的績效考核?這些問題官方至今都沒有明確說明。
此外,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基本支出預算的收支平衡是一條重要的預算原則,世界上主要國家都奉行這一原則。以美國為例,美國法律規定,地方政府運營預算(包括提供年度公共產品的人員經費和公務經費)必須收支平衡。資本預算(提供多年度公共產品)以地方政府公開發行的債務融資,而地方政府的債務融資能力受其財務狀況的嚴格約束。所以,無論是運營預算,還是資本預算,美國地方政府都受到嚴格的法律和財務限制,使其不能失控。
我國采用的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并沒有對地方政府的預算進行結構性區分對待,從而存在地方政府擴大基本支出,造成基本支出預算出現赤字的可能性。
可以這樣說,如果不對上述問題做出明確的、可操作性的規定,如果沒有如中期預算框架的目標、年度基本預算平衡要求以及績效考核這樣的約束機制,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的運作結果是令人擔憂的:進一步弱化人大或公眾對政府預算的監督,從而弱化對政府收支行為的約束作用;赤字規模和債務規模擴張,滯漲局面的出現或變相出現等。因此,建議采用真正的中期預算框架,充分發揮預算計劃、控制和管理三項職能。■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