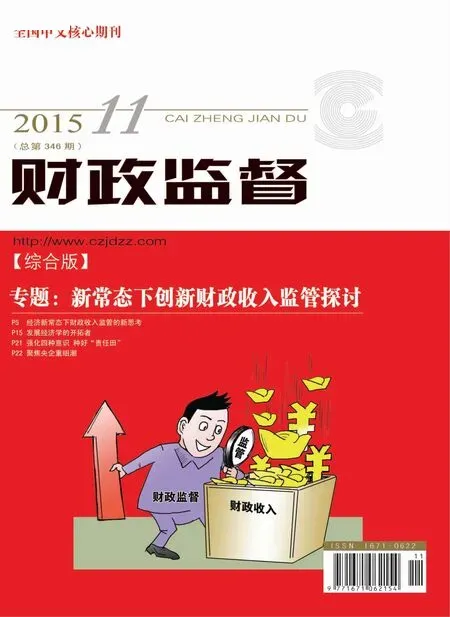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對中國的解釋力
●孫興全/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學系副教授
學者點評:
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對中國的解釋力
●孫興全/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學系副教授
中國過去乃至目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仍比較典型,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農村和農業領域落后的傳統產業聚集多,所占比重大,人均收入相當低,城鄉差距很大,較為符合劉易斯關于發展中國家存在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的預設。因此,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對中國經濟發展有較強的解釋力,特別是用于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城鄉一體化發展等方面面臨的問題和政策意義的揭示,至今仍對理論界和決策層有強大的吸引力。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在中國的應用價值不可否認,也要注意到這一理論不夠完善的方面,還要結合中國的現實國情,不能生搬硬套。目前,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在中國的應用需要引入更多的變量,也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主要揭示了農村勞動要素報酬率低下從而形成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市場機制。“二元”指的是發展中國家由以工業為主的現代部門和以農業為主的傳統部門構成,前者容納的人口眾多,生產技術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是一種邊際勞動生產率為0的剩余勞動力經濟體,呈現“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點;后者勞動生產率遠高于前者,能夠容納更多的勞動力。
這一理論說明,經濟發展過程是現代部門向傳統部門擴張的過程。農村包括勞動力在內的生產要素何以能向城市現代部門轉移,從而實現現代部門的擴張呢?劉易斯假定,傳統農業部門工資水平僅能維持基本生存,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高出農業部門生存工資一定幅度時(這取決于農村生存工資和影響農轉非增加的城市生活費用的高低),農村的生存工資水平和工業工資固定不變時,工業部門對農村勞動力就具有吸引力,使農業部門勞動力對工業部門的供給具有無限彈性。按劉易斯模型還可以推論出,如果工業部門以固定的工資率吸引到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得到更多的利潤,增加工業資本積累,加快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進一步強化工業部門相對農業部門的優勢,使勞動力流向工業部門的規模越來越大,這一過程持續進行直到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完全轉出為止。
在此基礎上,劉易斯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勞動無限供給階段和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階段。兩者的分界點被稱為“劉易斯拐點”。這一拐點的到來說明,發展中國家已經由資本稀缺、勞動力過剩階段轉向所有要素都稀缺,工資率不再是由生存工資而是由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決定的新階段。也標志著發展中國家人口紅利開始喪失,工資成本開始上升。
劉易斯理論的價值不言而喻,對于中國而言,中國正在由傳統農業國走向現代化,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這一進程與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解放并流入城市務工、創業有很強的關聯性,形成了中國數十年的低工資成本優勢或稱“人口紅利”。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滿足了工業化對勞動力的需求,低工資成本使“中國制造”在世界市場上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加快了現代部門發展速度,這與劉易斯的邏輯是一致的。有學者判斷,目前“劉易斯拐點”已開始出現,此時面對人口紅利開始喪失的“新常態”,需要分析勞動市場變化對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影響,采取相應的對策實現經濟平穩發展。要利用收入增長的契機,擴大內需,促進創業創新,形成經濟內生增長的力量。
同時,劉易斯理論還有更廣的適用領域。從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應用范圍來看,盡管這一模型主要揭示了勞動要素報酬低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市場機制,其實,城鄉收入差距大、農業比較利益低也是農村土地、資本、技術等各種要素報酬偏低的表現。因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下,市場的自發作用不僅促使農村勞動力要素的轉移,也會推進其他要素的轉移。特別是對土地等要素非農化的分析,完全可以采用這一理論。
我們也應看到劉易斯模型存在的一些缺陷。他的模型所采用的變量不全面。劉易斯只分析了勞動力非農化的市場力量,現代經濟學能夠說明制度的作用也非常巨大。由于缺乏制度變量的作用的分析,新中國前30年城鎮化發展滯后甚至出現大量城市人口“下鄉”的逆城市化就無法得到解釋,正因為人口遷移的管制因素才使中國在“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出現反市場的人口和勞動力流向,也就是說劉易斯的勞動市場完全競爭、勞動力流動自由選擇的假定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相悖。再如農村勞動力轉移還會受到工資水平之外的政策因素的牽制,包括國家對農業基礎地位的強化、糧食安全的保障而采取的農業支持政策會產生留住農村勞動力的拉力。除此而外,“所有權驕傲”及田園生活的吸引力也是制約農村勞動力流出的力量。農民擁有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完全或不完全的產權既有其經濟利益,也有其非經濟利益,包括安全感、歸屬感在內的“所有權的驕傲”;農村的田園生活也有一定的吸引力,農村特有的較為自由的生活節奏、緊密的宗族和鄉鄰關系、農民的故鄉情結、較好的生態環境,一定程度上使農民“故土難離”。
劉易斯的“靜態分析”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的解釋力也有所削弱。第一,農村生存工資率并非固定不變,城市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也往往具有剛性上升趨勢,農村生存工資率與城市工業部門工資率的差距是存在的,這不能否認,但是兩者的數量關系是動態變化的,因而農村勞動力對城市的無限供給是否存在,存在多久還需具體討論。第二,城市工業部門積累的資本能以固定比例來支付工資嗎?馬克思早就發現,隨著技術進步,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等量資本吸收的勞動力是下降的,這就是機器排擠工人的現象,這一現象說明,城市并不能無限度地容納農村剩余勞動力,還會產生城市內部的失業人口。第三,農村生產要素轉移中的市場力量很大程度上體現為要素報酬驅動,農村勞動力、土地等要素轉移可以因非農產業的要素報酬高而非農化,當然也可以因農業經營規模化、農業生產現代化、農業生產的技術要素增加、農業政策的調整提高了要素報酬而業內流轉。
總之,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對中國有很強的解釋力和適用性,同時我們也有必要進一步研究劉易斯忽略的一些因素,全面分析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各因素相互作用和影響的機理,深刻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解決發展中產生的問題。中國前30年,由于違背經濟發展規律,采用戶籍控制、用制度拉大城鄉待遇差距,還采取極端的逆城市化政策,沒有抓住“農村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契機,人為阻滯了工業化、城市化的步伐。后30多年,遵從經濟規律,放松勞動力流動的管制,使經濟得到高速發展,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大大加快。今天面臨新的形勢下,同樣要重視制度創新的力量,激發市場活力,進一步為包括農村人口在內的國民就業、創業、創新提供制度支持。■
(本欄目責任編輯:阮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