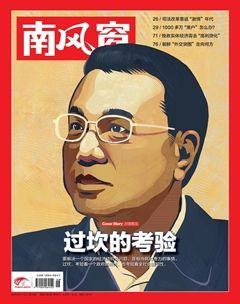一部非商業電影的另類突圍
甄靜慧

一開始,裴蓓不愿意大家把《青澀日記》看成一部教育片,“看電影是娛樂,沒人愿意進電影院受教育”,“這對本來就競爭不過商業片的我們更不利”。
然而這是個悖論:很多人喜歡這樣的片子,恰恰就是被它對青春期親子關系敲響的警鐘所震動。“反映社會問題、引發思考,跟說教不是同一回事。”她仍試圖分辯,可大眾管不了那么多,人們有自己慣常的思維方式。
到后來,她也默認了。
2015年1月,沒有明星,沒有充斥網絡的前期宣傳炒作,更沒有醒目的廣告位和打眼的巨幅海報,這部以青春期親子關系及朦朧之戀為主題的電影悄無聲息地出現在廣州市部分院線上,時段都是不起眼的,早晨或下午,唯一特別之處可能就是票價比較便宜。而僅一兩天后,還沒待留下印象的人騰出空來了解一下,它就如曇花一現般消失了。
“在強大的市場慣性面前,要做一部有社會意義的非商業片,太難了。”作為電影編劇兼出品人,以及原著小說作家,裴蓓說。
早上9:30,廣州市青宮電影城,小播映廳里稀稀落落地坐了七八個人:兩對夫婦,一對帶著孩子的父母。這里是廣州目前唯一還能看到《青澀日記》的影城,上午這個時段有點雞肋,但總有三三兩兩的人覓來。
作為年僅24歲的新銳導演謝悠的處女作,《青澀日記》在拍攝手法和藝術呈現上還遠稱不上盡善盡美。盡管裴蓓一再強調要拍一部觀賞性不遜色于商業片的精彩故事片,然而,畢竟只是500萬的小投資,新晉演員稚嫩的演技、文學化的敘事痕跡,部分鏡頭處理方式的不夠成熟等,都是繞不過的硬傷。
幸而,拋開細節的瑕疵,一個半小時的電影看下來,仍然能體會到導演和編劇的誠意。有別于很多同題材的青春校園影片,《青澀日記》延續了原著小說中的心理學視角,把一個早已在心理學界達成共識,卻偏偏為眾多父母視而不見的定律—每一個問題孩子的背后都有一個問題家庭—通過沉溺網癮并有自殘傾向的叛逆少年的故事,克制地呈現在觀眾面前。
裴蓓的名片上有兩個身份:作家、導演。但她在廣東最早的職業其實是調查記者,“那時候做了很多青少年心理問題調查,跟著心理學家采訪過不少孩子”。
直到成為專職作家后,這段經歷對她影響仍然重大。“記得那時鄰居中有個單親媽媽,帶著一個特別可愛的男孩,可是因為感情創傷,母親脾氣暴躁,對孩子嚴重缺乏耐性,孩子越來越脆弱敏感。”后來鄰居搬走,過了幾年再次相遇,她才知道孩子竟然已經癡呆了。
“我覺得自己有義務把這個故事及其折射的社會問題寫出來。”“所有孩子和家長間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問題,‘成才觀’的壓迫、愛的表達欠妥、教育方式不當、溝通斷層,我們不經意間就傷害了孩子。”

2008年,全國掀起網癮治療討論熱潮之際,中篇小說《媽媽不是我殺的》問世,講述在破碎家庭中長大、沉迷網游的少年曲曲因幻覺造成母親死亡的沉重故事—這就是《青澀日記》的藍本。
2013年,《媽媽不是我殺的》獲得第九屆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文學類),然而裴蓓并不滿足。“小說雖然獲了很多獎,我卻一直不是一個暢銷型作家。”她認為自己的寫作雖追求社會意義,影響卻不廣泛,“如果將它拍成電影,影響力會更大”。
這并不是她第一次試水電影。早在幾年前,她就曾將自己的獲獎小說《我們都是天上人》改編成電影《天上人》,并收獲第九屆廣東省魯迅文藝獎(藝術類),還入選第67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但同時,她也因這部處女作而首嘗了文人轉行電影人的糾結與辛酸。
“那次拍電影,是因為此前很多篇小說被購買了電影版權,可出來的作品對原著都進行了很多修改,我就想,能不能拍一部真正屬于自己的電影呢?”她找到了擅拍文藝片、曾屢獲國際獎項的知名導演寧瀛,雙方一拍即合。
然而,就跟很多小眾文藝片的普遍命運一樣,《天上人》也是叫好不叫座,眼看成為“票房毒藥”,投資就要打“水漂”,裴蓓一度急得流淚—電影沒有“金主”投資,是她砸鍋賣鐵、墊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底拍成的。幸好最后央視出資購買版權,才勉強收回成本。
之后,她寫了一篇小說《制片人》,講述女作家進入影視圈的故事,藝術理想與藝術商品化之間的強烈碰撞,那種心情,赫然就是自己的寫照。
有一次幾乎傾家蕩產的經歷,裴蓓并不是沒有考慮過《青澀日記》的市場前景。彼時她有兩個選擇:一是走商業片路線,請明星、名導演擔綱,炒作話題,讓電影爆紅賣座,然而她沒有那么多錢,“光是明星片酬就付不起”;二是走政府路線,與《天上人》不一樣,《青澀日記》涉及青少年心理問題,可以以教育片的旗號讓政府出資扶持,作為珠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的她完全有這個能耐—可她不愿意,“我不做主旋律編劇,主旋律片都要歌頌些什么,我只想闡述社會問題”。
最后她決定再冒一次險:出資500萬,找來年僅24歲的新銳導演謝悠,演員也全是海選回來的新面孔。
當然,此時她也不是當初那個完全的理想主義者了。謝悠看了故事,首先提出的就是修改意見:電影必須要有愛情,哪怕是很朦朧的愛情;小說的基調太壓抑,需要調整。

“他們年輕人會是這樣想問題的,我理解”—依照謝悠的意見,裴蓓對劇本進行了改頭換面:兩個男孩因游戲而產生的友誼,變成了問題少年和女學霸的朦朧戀情;母親香梅則由“二奶”變身正室;結局更讓被誤殺的母親“起死回生”。
但即便如此,《青澀日記》的發行仍然舉步維艱。
畢竟,對已經被好萊塢商業大片慣成重口味的主流觀眾來說,兩個初中生朦朦朧朧的早戀實在算不上噱頭。沒有明星和名導演、沒有特技、沒有話題與噱頭的電影,無異于白開水,連嘗試打動他們的機會都不會有。
家有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以及孩子本身倒是會有興趣:電影里流淌的情感非常真摯,催人淚下,當人的情感被打動,產生共鳴并由此而引發思考的話,作品的效果就達到了,其他瑕疵都屬于瑕不掩瑜。
問題是,他們并不是目前電影市場的主要消費群體。前期投資的500萬支付拍攝成本就已經捉襟見肘,根本沒有余錢支付昂貴的商業宣傳費用,如何讓這些平日不關注電影的人群知道這部電影并走進影院?無法破題。
“一部電影在發行前,需要先舉辦看片會,請各大影城老總來看,他們認可,就會排期。”楊思毅負責在廣州為《青澀日記》聯動影城,這是一份非常困難的工作,“首先看片會時很多人沒來”。老總們經驗豐富,一聽故事,再看班底,基本就能判斷一部電影有沒有賣座的可能,沒商機的,根本懶得去看。
觀眾到影院都是圖一樂,甚至是逃避現實的沉重和壓力,沒人愿意去深刻—這是商業院線的邏輯。
“有幾個月,我極度灰心。我認輸了,妥協了,積攢多年的挫折感爆發,不再想堅持。”裴蓓說。
然而,現實歸現實,影片總得發行下去。商業院線不接納,只能另外找路子。
裴蓓忐忑地拿著已完成的作品,回過頭去尋求政府部門的支持。結果峰回路轉,先是成功申請到廣東省文藝精品扶持的幾十萬宣傳資金。而杭州市廣電局也頗為豪邁,大筆一揮,就將《青澀日記》引為青少年電影伙伴計劃的一部分,一條院線6個影城,從寒假放到暑假。
而在廣州,青年文化宮影城劃出每天早上9:30~11:00的時段,支持《青澀日記》放映。據說有一位帶著女兒一起看電影的母親,散場后馬上向女兒道歉,女兒哭得淚流滿面;很多中學生則一直嘟囔著要讓自己的父母也來看看。
“如今商業影城確實存在這樣的問題,一切向噱頭,向商業利益看,很多真正對社會有警示和教育意義的片子卻無人問津。”廣州青年文化宮負責人李約堅感慨,在他看來,《青澀日記》只是其中一個例子,每年國內都有不少有社會價值的電影被市場拋棄,還有很多很好的國外青少年心理片無人愿意引進,這對文化發展非常不利。他建議將影片播映權以較低的價格給學校組織學生校內觀看,離青宮影城近的學校,則以低廉的價格包場,“向學校推廣的工作由我們青宮去做”。一開始裴蓓心里不是滋味,后來漸漸想通了:如果能讓更多人看到這部片子,別說低價,免費又何妨。
“這幾天我們正準備簽協議,青宮影城同意全年放映。”裴蓓說,“現在我不像之前那么擔心了,到目前為止,珠海和廣州的票房加起來將近200萬,3月啟動全國市場后,回本應該是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