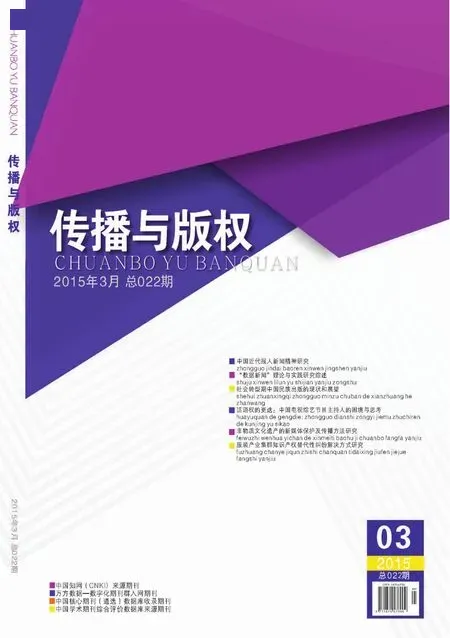夏衍與新中國電影
史興慶
夏衍與新中國電影
史興慶
[摘要]新中國成立后,夏衍為中國的電影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即便在動蕩的年代,夏衍也主張電影創作要將現實性和藝術性相結合,在他的主持推動下,涌現出一大批膾炙人口的電影新作,新中國電影迎來了第一個藝術高峰。
[關鍵詞]夏衍;電影;劇本
[作者]史興慶,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講師。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夏衍成為左翼電影的一面旗幟,新中國成立后,夏衍引領中國電影繼續前行,為新中國的電影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一、扶持上海民營電影
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夏衍從香港回到北京,短暫停留后南下上海,開始了六年的上海生涯。在上海,夏衍先后擔任了文教接管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等職務,主管上海乃至整個華東地區的文藝工作。在上海,“昆侖”和“文華”是兩個頗具規模的民營電影公司,長期和中共保持合作關系。上海解放后,接管委員會大力幫助這兩個公司恢復電影生產,尤其在解決“劇本荒”上夏衍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昆侖影業公司出品了《武訓傳》。這是一部以清朝末年真人真事改編的影片,講述了少年武訓的苦難以及從青年時代開始“行乞興學”,終獲“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譽的一生。影片于年底公映,社會反響很好,也得到了上海市及華東局領導的肯定。然而1951年風云突變,《武訓傳》被定性為反動影片,遭到全國性批判,作為上海電影負責人的夏衍為此寫了檢查。
受《武訓傳》事件的影響,加之解放之初百廢待興工作繁忙,夏衍在上海的六年只寫過一部《人民的巨掌》,講述了上海解放后,潛伏在工廠里的特務搞破壞,最終被公安干警識破并抓獲的故事。
二、改編文學名著
1955年夏衍回到北京,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分管外事和電影工作,開始了他十年的文化部生涯。
1956年,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調動了文藝創作的積極性,夏衍的電影創作激情空前高漲,他應北影廠的邀請將魯迅的《祝福》改編成了電影,這是新中國第一部彩色故事片。
夏衍改編名著的一個鮮明特征是運用現實主義手法豐富原著的時代內涵。比如,“砍門檻”這場戲就是原作中沒有的:在捐了門檻之后,祥林嫂依然受到魯家的歧視,被趕了出來,悲憤的她奔到普定廟,砍掉了用血汗錢捐的門檻——夏衍用這場砍門檻的戲,強化了祥林嫂的反抗意識,也符合新中國的意識形態。
1958年,夏衍又將茅盾的小說《林家鋪子》改編成了電影。《林家鋪子》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的江南小鎮,主人公林老板靠經營小雜貨鋪維持全家生計。在這部影片中,夏衍采用了散文化的手法,不僅描繪出動蕩時代下江南水鄉的風貌,也將林老板這個小人物被人欺壓也欺壓別人、“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生存狀態刻畫得入木三分,創造了新中國詩化電影、散文電影的一種風格。
三、為國慶十周年獻禮
1959年國慶是新中國的第一個十年大慶,作為獻禮片主要負責人的夏衍提出:必須創作出制作精良、代表中國最高藝術水準的影片向祖國獻禮。于是,他從劇本抓起,組織創作了一批優秀電影。
《五朵金花》便是其一。1959年4月長影導演王家乙和攝影師王春泉來到北京,夏衍請他們拍攝一部輕松的、政治色彩不濃的、甚至能在國外發行的影片,并提議以云南為背景。劇本初稿出來后夏衍不滿意,他對導演說不要搞說教,要用形象打動人,并親自主持改寫劇本。
1960年,夏衍和水華將陶成的自傳《我的一家》改編成了電影《革命家庭》。在這部影片中,夏衍將革命激情與家庭的親情雜糅在一起,塑造了一個真實感人的革命家庭形象。在新中國第一屆電影百花獎評選中,夏衍和水華憑借《革命家庭》獲得最佳編劇獎。
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前后,在夏衍的主持和推動下,電影界涌現出一批膾炙人口的佳作——《青春之歌》《林則徐》《萬水千山》《五朵金花》《我們村里的年輕人》《革命家庭》等,形成新中國電影藝術的第一座高峰。
四、“離經叛道”
將現實性和藝術性相結合,不僅是夏衍電影創作的
一貫主張,也是他領導電影事業的指導思想,即便身處動蕩的時代,夏衍對于兩者的堅持也從來沒有改變過。
1958年,因為受“大躍進”運動的影響,電影界粗制濫造、只求數量不講藝術性的創作風氣愈演愈烈。對這種情況,夏衍感到深深的憂慮。1959年7月21日,在全國故事片廠長會議上,夏衍針對當時電影創作圖解政治口號、題材內容越來越單一的現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將公式、概念化嚴重的革命題材影片和戰爭題材影片比喻為“革命經”和“戰爭道”,他說“我今天的發言就是要離經叛道”。
夏衍提倡電影創作一方面要突破“革命經”和“戰爭道”的限制;另一方面,要講求藝術性,提高專業水平。
1958年,夏衍應邀到北京電影學院,針對當時電影劇本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做了一系列講座,最后集成《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在這部著作中,夏衍集中談到了電影的目的性、結構與節奏、蒙太奇等基本問題。
五、主持電影界調整
1961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了全國文藝工作者座談會和電影故事片創作會,周恩來參加了會議,他強調文藝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藝術規律。
根據周恩來講話精神,夏衍發表了《把我國電影藝術提高到一個更新的水平》一文,批評了電影生產中存在的“直、露、粗、多”的傾向。直,就是直奔主題;露,就是不含蓄;多就是對話多、人物多;粗,就是粗制濫造。從此,中國的文藝界、電影界進入了一個短暫的調整期。
新僑會議后,夏衍、陳荒煤等人梳理了前幾年的電影作品,將《青春的腳步》《洞簫橫吹》等被禁的影片恢復上映。
電影《早春二月》的誕生是這次調整的結晶。《早春二月》是根據柔石的中篇小說《二月》改編的,講述了1926年前后青年教師蕭劍秋應邀來到鄉下小學任教,與陣亡的老同學的一家以及小學校長的妹妹之間發生的一段曲折的感情故事。《早春二月》于1962年開始創作劇本,夏衍給予了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導,他提出了兩條意見:要注意時代背景;要把人物的性格特殊起來,不做一般化處理。這個劇本共有470多個鏡頭,他改了100多處。
在夏衍的幫助下,《早春二月》不僅成功表現了大革命時代知識分子的苦悶與彷徨,并以其含蓄精煉的敘事和濃郁的民族風格,成為中國電影史上最為精致優美的影片之一。
六、在“烈火”中創作
1963年,北影廠打算將小說《紅巖》搬上銀幕,拍成電影《烈火中永生》,由于最初的劇本不能讓人滿意,于是北影廠向夏衍求援,夏衍對劇本進行了改編,突出了江姐的個性。夏衍將江姐和許云峰的活動作為貫穿全劇的線索,在情節上順勢而下自然發展,在刻畫英雄人物的同時強化了革命主題。
當時,《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等一大批電影被譽為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毒草”受到批判;夏衍分管電影,卻“放”出了這么多“毒草”也受到沖擊;1965年,當《烈火中永生》攝制完成時,夏衍的處境更為艱難,他已不能在編劇一欄署名“夏衍”,取而代之的是署上“周皓”這個陌生的名字。
不久,夏衍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長職務。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8月12日,夏衍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批斗,三個多月后的一天夏衍被投入秦城監獄,從此開始了長達八年零七個月的囚禁生活。
七、晚年的光輝
1975年7月,夏衍從秦城監獄出來,此時的他已年逾古稀、雙腿殘疾。面對家人的淚水,他以杜甫的詩句“亂世遭飄蕩,生還偶然隨”來寬慰他們。出獄最初兩年,夏衍賦閑在家,過的是再平常不過的百姓生活,他常坐在院子里讀書,和心愛的大黃貓一起曬太陽。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夏衍又開始活躍在電影戰線上,他參加了很多社會活動,1979年還出任中國電影家協會會長。
“文化大革命”后的夏衍不忘電影創作,修改過多個電影劇本,最后的一個是魯彥周的《廖仲愷》。1982年的7月,酷暑難當,為趕上廖仲愷和何香凝的紀念活動,正在養病的夏衍每天伏案在小茶幾上改劇本,在十萬字的長劇中,他僅有三頁沒有改動,增加的內容有460處之多。
1995年2月6日,夏衍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為表彰夏衍對中國電影的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1994年,國務院授予他“國家有杰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獲此殊榮的電影人,迄今為止只有夏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