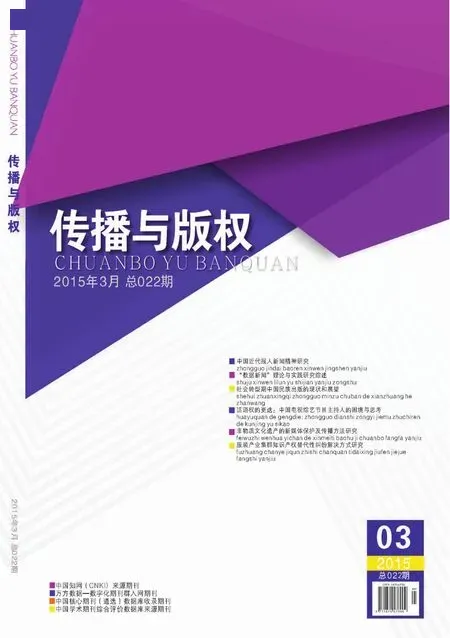視覺文化沖擊下莫言作品影視化改編之得失芻議
馮 嶺
視覺文化沖擊下莫言作品影視化改編之得失芻議
馮 嶺
[摘要]在視覺文化語境下,著名作家作品的影視化改編成為常說常新的話題。作為典型個案,莫言小說的改編,有成有敗,有得有失,所引起的正負效應相伴而生,并且十分鮮明、強烈,能為今后影視創作提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而且,在視覺文化時代,文學的影視化改編有著特別意義,文學與視覺文化共謀,會構建起具有超越意味的藝術世界,也給影視文化產業帶來新的活力。
[關鍵詞]視覺文化;改編;文學作品
[作者]馮嶺,副教授,江漢大學武漢語言文化研究中心。
當前,隨著現代媒體的迅猛發展,表達、傳播信息的媒介不再拘泥于文字符號,而大多代之以形象符號為主,如電影、電視、廣告、攝影、形象設計等。于是,以影視為代表的視覺文化大行其道,向生活的各個方面滲透和施加影響。所謂“視覺文化”,是指“以電子媒介為載體、以圖像或形象為信息傳遞方式、以信息為接受終端的影像文化”,“它的基本含義在于視覺因素,或者說形象或影像占據了我們文化的主導地位”。它的到來使“文字業已淪為圖像的‘奴仆’而退居次席”。所以,許多作家無法忍受文學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淘洗和沖擊下日漸邊緣化的境況,甚至棄筆從商。而作家莫言則默默堅守,并以其雄奇恣肆的想象、含蘊豐富的意義、深厚的民間文化內涵和絢爛多姿的語言以及多樣化的敘事策略,在喧囂浮躁的市場如魚得水,擁有了廣泛的讀者群,并于2012年以一尊諾貝爾文學獎獎杯,贏得了更為廣大讀者的矚目,包括國外的許多文學愛好者。而有趣的是,“其實他的走向世界是與張藝謀拍出經典影片《紅高粱》大有關系的。莫言就承認自己之所以被外國人重視,離不開張藝謀的電影在國際上頻頻得獎,使國外出版商關注起中國文學”。這個現象必然引起我們對其與影視深度接觸狀況的研究興趣。
莫言從未排斥過作品的影視化改編,從《紅高粱》和《高粱酒》改編成《紅高粱》(張藝謀導演)起,他的作品《白狗秋千架》《白棉花》《師傅越來越幽默》和《姑奶奶披紅綢》分別被改編拍成了《暖》(霍建起導演)《白棉花》(李幼禾導演)《幸福時光》(張藝謀導演)和《太陽有耳》(嚴浩導演)。改編有成有敗,有的影視作品榮獲國際電影節大獎,贏得了世界聲譽,如《紅高粱》《暖》和《太陽有耳》等;有的如《幸福時光》出品后屢遭非議,《白棉花》更被觀眾狠批一頓,被視為“最不值得看的影片”。原著同出莫言之手,但影視改編成效卻大相徑庭,其改編的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可為以后影視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不可多得的借鑒。
一、改編之得
《紅高粱》《暖》和《太陽有耳》等改編片通過傳遞本土文化的遺傳密碼,從一種全新的視角來審視當代文化話語的發展空間,以及在視覺媒介條件下建構文化話語的模式,贏得了好口碑,其經驗不得不引起人們研究和深思。
首先是人性的力量在莫言筆下得到了生動的再現,為改編打下了深厚的內涵基礎。在改編中,雖然導演試圖用自己的主觀感受和理性思考來表達自己對人性的理解,對原著的主題意蘊進行了修改,但不可否認,正是有莫言作品將生活還原為吃、喝、生育、性愛、暴力、死亡等與生命本身密不可分的形態,展現出了人性深層的本質特征,負載著更為深刻的歷史蘊涵和更為廣博的人文情懷,才使得導演改編的基礎沉郁厚重,能夠為觀眾提供如《紅高粱》般洋溢生命激情、張揚那種人之初狂野本性的精品。《紅高粱》原著中想象豐富,汪洋恣肆的鄉野傳奇、家族演義,在影片中則集中伸張為“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浪漫激情,針對在儒家文化桎梏下人的本真性的蒙蔽與失落,中國人原始生命力的退化與萎縮,而大力張揚其個性的解放、對生命的肯定以及對自由的追求,這些恰恰是對民族深層文化心理中郁積的冷漠和保守,現代人處于人性迷失而不能自拔的困境的反撥。
其次是莫言在消解權威話語的同時,選擇了一種“作為老百姓的寫作”的言說方式,力圖建構一套民間話語的言說系統。張藝謀、霍建起和嚴浩等導演在《紅高粱》《暖》和《太陽有耳》里則延續了這種話語特點。充分調動各種藝術形式,如色彩、影調、景別和聲音等,造成新鮮的場面、新的敘事信息,線索明晰,故事簡易明白。夢一般的美感賦予其作品以熱辣或幽深之美,使“我奶奶”“我爺爺”敢說敢干、叛逆反抗的個性精神和旺盛生命力盡情揮灑出來;使“暖”愛情故事的背后暗含著的城鄉文化的沖突凸顯出來;使油油對潘好愛恨交織、復雜幽微的感情傳遞出來,在那些人們似
曾相識但又有陌生感的人物和故事中,探尋一種新的話語實踐方式,使其審美張力與審美空間被放大。
最后,雖然莫言小說底蘊豐厚,對歷史理解、現實理解和文化理解都相當深入,影視改編中有所吸收,但畢竟兩種文本各自藝術規律不同,莫言小說的時空順序與情節邏輯被打破,隨著作者情緒的任意流動而自由的切割和講述,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和意識流特點。改編時自然不能亦步亦趨,按圖索驥。影片往往注重保持故事情節的連貫性和趣味性,就必須進行藝術改造和加工。比如,從《白狗秋千架》到《暖》,原作的主題、情節、人物、背景、語言等一系列的敘事因素都被改得“面目全非”,但是遵循了影視視聽語言的創作規律,將具有隱喻式的主觀意象實化為普通的客觀實體,由虛到實,把秋千架等物象作為載體加以形象化,使之敘述詩意盎然,含蓄蘊藉,也因此改編獲得了成功。
二、改編之失
雖說改編自莫言小說的影視作品成就不小,但也有改編不甚成功的作品,《白棉花》《幸福時光》等影片的藝術效果均評說不一,遭受非議的原因也值得我們去思考:
其一,改編后失敗之作的人物性格塑造缺乏個性,缺乏豐富的生活細節,遠離了人性的主題、缺少了心靈的震撼。比如,《白棉花》原著中22歲的方碧玉是一個“渾身上下裝著彈簧”的人,充滿生命活力,是個“周身都是迷人故事”的敢作敢為、敢愛敢恨的女人。她勇于追求自由的愛情,勇于沖破傳統的束縛,具有堅毅的品質和在苦難中生存的耐力。此形象也包含了對男性中心、夫權主義和失去人性的社會的批判。而影片中寧靜主演的這個人物,似乎沒有很多機會去體現她的女性美,也沒多少篇幅去展示人物個性魅力,缺少生氣,個性平庸甚至模糊。欲望化的敘述成為關注的焦點,成為影片建構敘事、塑造人物的主要支撐點。如此僅僅突出性愛欲望,視野顯得狹小局促。
其二,過于追求戲劇性效果,匠味太濃,掩蓋了作品應有的更為深刻的主題。比如,《師父越來越幽默》講的是下崗老工人在荒僻的林間開設了一座情人小屋,不得不以一種頗具諷刺性的方式謀生,其背后有著對城市文明積弊的思考。但改編成《幸福時光》后,加上了眾人一起幫助盲女的愛心故事,在張藝謀的電影世界中失去了現實本身豐富的色彩,而蛻化為清湯寡水的表述,生編硬造的戲劇色彩,無法將現實殘酷性的深度思考傳達出來,以輕飄的藝術感覺對待現實和感受現實,使現實的宏偉厚重在這個單薄牽強的故事中消失隱退,只剩下淺薄、柔情的氣息徘徊蔓延。
其三,試圖用溫婉傷感的唯美情調將“殘酷”略去,模糊和沖淡了作者的批判意識。比如,《暖》里人物對城市的向往一覽無余,去掉了原著中城鄉文化的矛盾與沖突,這恰恰反映出影片改編最大的疏漏,它將商業操作、受眾的懷舊心理和對溫情的渴望有機融合,創造了一個經典而唯美的消費神話,卻略去生活不堪承重的隱痛,過濾掉故事原本的殘酷色調,讓故事的精神內核與唯美的敘述情境之間產生了極不協調的敘述裂隙,使得在莫言作品里原本升騰起來的悲愴感受被消解掉,削弱了觀眾對崇高悲壯之美的深刻體會和感受。
三、給影視文化產業發展帶來的新啟示
將莫言小說的改編作為典型個案加以研究,總結其得與失,能為今后的文學改編提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也給影視文化產業發展提供新的啟示。如今,視覺文化早已為人們所關注和探究,顯而易見,它和當代傳媒的突進、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影視文化產業的趨向關系密切。文學作品借助具有傳播優勢與影響力的視覺媒介,將現代文化尤其是社會轉型時期富有時代內涵的文化,通過觀照心靈成長與文化生態的角度納入傳播視野,使得更多的讀者或觀眾對其加以逐步地認知和了解。正是在媒介傳播力量的帶動和擴散下,莫言作品能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傳播,讓更多國外讀者能欣賞到它。當然決定作家作品文化影響力的根本因素,是其自身屬性中蘊涵的歷史力量和現實價值,但這種文化歷史力量和現實價值的大眾認知,這種大眾認知的規模化,是借助媒介文化的影響功能實現的。因此,不可否認,從小說到影視劇的過程中,媒介的力量不容小覷。
隨著文化產業日益深化,影視走向市場,并參與國內國際文化資本的激烈競爭,就必須以“內容為王”,走品牌化建設之路,形成文化產業動向、文化資本流通、文化市場前景等信息服務的互通與共享。而要實現這一點,其中很重要的途徑就是借文學這股強勁的東風,加強影視藝術的含量,將豐富的文學資源提煉為影視藝術形象,并注入鮮活的元素進行包裝,通過影像化的技術手段使其成為極具影響力的作品,并發生傳播效應。故此,文學對影視文化產業的促動作用也不能忽視。
如此看來,視覺文化對于文學藝術具有無可爭議的傳播效能和改塑功能。同時,文學為影視提供了豐富的精神資源,其現代性思考的精神指歸和意義認同對影視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促進了影視文化產業的健康、長效發展。可見,在視覺文化時代,文學的影視化改編有著特別意義,文學與視覺文化共謀,會構建起具有超越意味的藝術世界,也給影視文化產業帶來新的活力。可以想見,莫言作品影視化改編在將來還會引發更多的思考。
【參考文獻】
[1]劉少華.大眾傳媒 視覺文化與當代體育[J].體育文化導刊,2003(3).
[2]周憲.視覺文化與消費社會[J].福建論壇,2001(2).
[3]蔣泥.“先鋒”莫言是如何“倒退”的[J].山西文學,2006(7).